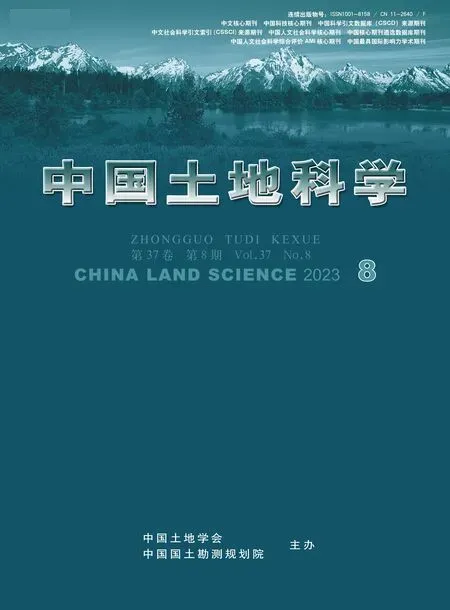耕地“非糧化”演化機制與治理策略
——基于刺激—反應模型的案例研究
杜國明,范曉雨,于鳳榮
(1.東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2.黑龍江省農墾科學院科技情報研究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8)
糧食事關國運民生,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2022 年12 月,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談到:“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始終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頭等大事,必須堅守18 億畝耕地紅線,將提升糧食產能作為首要任務。”然而現實情況卻是,近年來,耕地面積呈現減少趨勢[1],“非糧化”和 “非農化”趨勢明顯[2]。一方面,城鎮化與工業化的進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設用地,在存量土地有限的情況下,農用地轉變為建設用地則是必然之勢[3];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導致耕地“非糧化”頻頻發生。因此,中國的糧食安全壓力長期存在且必須予以重視。中央一號文件多次強調嚴格遏制耕地“非糧化”,全面加強耕地保護和土地用途管制,防止過度“非糧化”[4]。深入研究耕地“非糧化”的演化階段特征與驅動機制,對于進一步完善“非糧化”防控政策、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耕地“非糧化”作為一種農業經營的新形態,具有內在的生成機理。學術界對此開展了大量研究。武舜臣等認為,耕地“非糧化”是農戶主體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依據自身資源稟賦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結果[5]。作為耕地的直接利用者,農戶的年齡、性別、風險偏好等都會影響耕地的利用方式[6-8]。在探討農戶資源稟賦對“非糧化”的影響上,學者們的研究結論相對一致,即農戶資源稟賦越高,耕地“非糧化”的趨向越明顯,而勞動力稟賦較低的老年農戶與女性農戶在耕地利用過程中更傾向于種植糧食作物。與此同時,隨著農村社會高度分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快速成長和農戶兼業化趨勢不斷加快[9],種植模式也愈發多樣化。分化的農戶為“非糧化”提供了選擇空間。吳郁玲等提出耕地“非糧化”是“人—地”“人—人”交互作用的結果,受外部自然、社會、經濟、制度等多重環境的影響[10]。例如,各地區農業資源稟賦多元致使農業產業、產品類型多元[11],因而“非糧化”類型不同、程度不同。社會工商資本下鄉對“非糧化”的影響利弊皆有,農地的轉出不利于農戶維持糧食生產,生產性服務的提供增加了機械要素投入,有利于擴大糧食生產[12]。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種糧成本高、收益低導致農戶種糧積極性不高[13],農戶農地規模流轉可增加收入[14]。但是,隨著流轉面積的逐漸加大,耕地“非糧化”呈現明顯發展趨勢[15]。糧食補貼政策的不完善以及土地用途管制監管的不到位等都可能導致糧食播種面積不斷減少和“非糧化”規模不斷擴大[16]。可見,耕地“非糧化”具有復雜性與獨特性。
盡管現有研究成果對于耕地“非糧化”現象的驅動因素開展了大量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為耕地“非糧化”的治理提供了理論支撐。但是,存在過分注重微觀主體對于活動的反應與影響,忽視了整個耕地利用系統動態演化過程的問題。需要意識到耕地“非糧化”本就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動態變化的外部環境與微觀主體交互作用的過程。所以,考慮到微觀主體的行為對于宏觀組織整體的演化影響,本文選取內蒙古自治區中部農牧交錯區的一個村落,聚焦其耕地“非糧化”的演化歷程,采用單案例研究法,基于刺激—反應模型,通過梳理案例村耕地“非糧化”縱向時間序列的演變歷程,厘清耕地“非糧化”的階段特征和演化機制,為耕地“非糧化”的治理提供依據。
1 耕地利用系統分析框架
復雜適應系統理論(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由約翰·霍蘭教授于1994年提出。該理論認為一個動態演化的系統是由多個微觀主體相互聚集,不斷產生非線性相互作用關系并共同進化的網絡型組織[17]。該理論充分強調主體的主動性以及適應性在系統演化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主體通過改變自身行為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不斷推動系統實現由混沌到有序的秩序性躍升、由簡單到復雜的層次性躍升[18]。在微觀層面,主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通過刺激—反應模型來表現,該模型一般由三部分組成:探測器、執行系統和效應器[19]。探測器負責接收環境中的刺激,體現了主體提取環境信息的能力;效應器負責做出反應,表征了主體的行為結果;執行系統則是主體接收刺激做出反應的過程,體現了主體的信息處理能力。因此刺激—反應模型的核心思想有三點:一是強調主體的適應性;二是強調微觀個體與宏觀組織的結合性;三是強調主體與環境的互動性[20]。在耕地利用系統中,農戶主體不斷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能量與信息交流,從自身利益、偏好、價值觀等方面出發,形成對耕地利用的不同認知,最終促使主體推動耕地利用系統向著結構更加明晰、功能更加完善的層級演化。
基于此,本文結合以往對耕地“非糧化”的研究成果,考慮外部環境與農戶主體的互動,遵循刺激—反應模型,繪制耕地利用系統運轉機制的分析框架(圖1)。

圖1 基于刺激—反應模型的耕地利用系統框架Fig.1 A framework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systems based on stimulus-response model
耕地利用系統的外界刺激共分為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三類:自然環境是整個系統演化的重要基礎,提供物質載體和發展保障;經濟環境是系統演化的關鍵條件,對具有“理性人”屬性的農戶主體而言,種植行為的邏輯是經濟導向的,即實現個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社會環境是重要的調節器,相關政策制度作為行為決策的外部變量,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規范農業經營主體的行為[21]。
1.1 耕地立地條件的本底支撐力
耕地的立地條件如地形地貌、氣候條件、水資源豐缺程度等,直接決定了作物的適宜性,從而影響農戶主體的種植行為決策和農作物的空間格局[22]。各區域的優勢經濟作物存在差異,如北方地區常見種植棉花與蔬菜等,南方水熱條件較好,多見種植香蕉、火龍果等。
具體而言,就耕地質量來看,郝海廣等[23]通過小范圍調研發現,小麥、莜麥等糧食作物多耕作在地塊平整的耕地上,相反,經濟作物胡麻在坡耕地上耕種的面積偏多。還有研究顯示靠近河流和城市道路的耕地更容易發生耕地“非糧化”[24],而細碎化會強化農戶主體“非糧化”的種植意愿與擴大種植規模的行為[25]。就耕地地形來看,王善高等[26]認為在適宜機械耕作的平原地區,勞動力匱乏的家庭會相對提高機械化程度較高的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與之相反,難以使用大型農業機械的丘陵地區,需要投入更多勞動力的情況下,經濟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會提高。就氣候條件來看,以新疆地區為例,獨特的光熱條件與土地資源優勢是棉花增產的有力支撐。而急劇擴張的棉花種植面積也使其成為“糧棉爭地”最嚴重的省份之一[27]。就病蟲害防控來看,經濟作物與豆類作物或綠肥作物的合理輪換可以防治病蟲害,均衡土壤養分,調節土壤肥力[28]。
1.2 微觀農戶經營的利益驅動力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因素是整個農村社區中耕地“非糧化”最根本的誘導機制[29]。即使是由于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聚集在同一個社區內從事生產的農戶主體,也會因生計策略的不同,基于經濟效益和風險承擔的考量,根據外部環境與自身資源稟賦,調整農業種植結構保證自身利益最大化。
我國農民是經濟理性與生存理性的有機結合體,影響其種植行為的兩個重要因素就是農戶的生計盈利與家庭風險規避[1]。因而,農戶的種植決策是多目標的,不同類型農戶的目標權重有所差異,相同農戶的目標權重會隨時間有所調整[30]。就農戶的家計模式來看,在相同的耕地質量條件下,傳統農戶偏向于種植傳統糧食作物,家庭勞動力充裕且文化較高的農戶則偏向于種植經濟作物[31],“半耕半工”的兼業戶受家庭結構、生產成本、收入結構等要素的影響,偏好種植看護成本較低的糧食作物[32]。從普通農戶中分化出來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著更強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和風險感知力[5],大多傾向非糧生產甚至非農經營[33]。農戶是耕地利用的直接主體,也是耕地利用系統的神經中樞[34],在耕地利用中會根據自身“標識”不斷調整種植行為,產生“趨糧化”向“非糧化”,“單一化”向“多元化”的過渡形態。
1.3 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引導力
土地政策作為一項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保證農業生產活動有序開展,有效解決土地管理中的土地利用、土地市場問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一方面,要充分保證國內口糧自給,另一方面,要增強國家的農業競爭力,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35]。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糧食生產關系到社會公平和社會成員間的利益分配[36]。第一,對在耕地上種植糧食作物的農戶主體而言,他們承擔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責任的同時,也失去了農地發展權。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解決糧食生產的外部性問題,例如,通過對種植糧食的農戶發放糧食直補、良種以及農機具購置等農業補貼,有效提高了農戶種糧的積極性[37]。第二,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深化改革中,依托于承包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農業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和整合,進而促使農村土地流轉速度的加快和流轉規模的擴大[38]。與此同時,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促進了耕地“非糧化”:伴隨著農村土地流轉速度的加快,耕地“非糧化”率不斷提高[39-40]。第三,近年來,政府不斷強化和細化耕地保護與國土空間用途管制[41],從土地用途管制到耕地用途管制,再到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的種植用途管制,耕地保護層層加碼,逐步細化耕地的管控規則,從“必須種地”到“必須種什么地”的轉變,有利于遏制耕地“非糧化”現象的蔓延。
2 案例村選取與數據來源
2.1 案例選取
本文采用單案例研究法,以時間維度來分析案例變化,厘清促進耕地“非糧化”的關鍵驅動因素及演化歷程,整理和復盤整個過程中的關鍵事件節點,總結歸納其環境與主體間內在作用機制。
遵循典型性和理論抽樣的原則,選取Y 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作為案例對象。第一,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推進,Y 村人口流失嚴重,農戶主體發生分化,原先以糧食作物為主的農業種植結構受到沖擊,“非糧化”問題逐漸凸顯。這與大部分鄉村比較,具有相似性、代表性。第二,Y 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中,外部環境系統中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與社會環境均發生了較大變化,這與前文的構建的理論框架相吻合。第三,Y 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經歷了初期的萌芽、中期的激化、后期的減緩三階段,最終形成了科學合理的輪作模式,該歷程符合我國“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整體糧食安全戰略。
2.2 數據來源
案例調查時間為 2022年1—2月、2022年7—8月,采用半結構化訪談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調查對象包括Y村的村民委員會以及全體常住村民,訪談資料共計 88份,有效問卷76份,時間跨度為 2000—2022 年。
2.3 案例村概況
2.3.1 Y村農業經營狀況
Y 村位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淺山丘陵地區,全年無霜期115~120天,年均降水量350 mm左右,且主要集中在7—9月份。截至2022年,全村總戶數有525戶,常住戶數不足100 戶,耕地面積為9 970 畝,當地無霜期短、雨量較少。土地粗放經營導致肥力連年下降,為保證產量,當地一直實行傳統的壓青休閑耕作制。每年實際耕種面積約6 700 畝①村莊耕地總面積和實際種植面積是2019年航拍所得,由當地村委會提供。,主要為小麥和莜麥。2019 年,Y 村出現土地連片有償流轉,農業種植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值得注意的是,Y村正處于我國北方半濕潤農區與干旱、半干旱牧區接壤的過渡地帶,即連接種植業與畜牧業兩大食物生產系統界面的農牧交錯帶[42]。因此,當地產業發展除了種植業還有畜牧業,主要牲畜為綿羊,全村每年存欄量約2 400 只,養殖方式為放養與舍飼相結合。當地主要農作物的投入產出情況如表1。

表1 Y村主要農作物投入產出情況Tab.1 Main crop inputs and outputs in Village Y
2.3.2 村莊中的4類農戶
Y村農業經營狀況發生了改變,農戶主體也發生了分化。本文以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將Y 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主體劃分為以下4 類:維持生計類、規模收益類、種養結合類和半農半工類。
維持生計類農戶主要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較低的一類主體。一般來講,此類主體消費結構單一,主要是醫療衛生支出和生活用品支出。規模收益類農戶主要指經營耕地面積超過200畝②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中規模經營的農地規模標準是一年兩熟地區為 50 畝,一年一熟地區100畝。Y村雖然為一年一熟地區,但是考慮到耕地質量低下,所以本文將耕地經營規模達到200畝的農戶定義為規模收益類農戶。且獲得較好規模效益的主體。種養結合類農戶與半農半工類農戶收入渠道較為多樣,具有種植業收入的同時還有畜牧業收入或非農收入。種養結合類農戶留在村莊內從事種植業生產的同時也從事畜牧業生產。半農半工類農戶主要指外出務工,季節性返鄉務農的主體。此類農戶由于子女教育或者工作性質等大多居住在縣城中,除去返鄉務農時間,其余時間均留在縣城從事非農生產。2022年Y村4類農戶及其農地信息見表2。

表2 Y村4類農戶及其農地信息Tab.2 Information of four categories of farmers and their farmland in Village Y
3 案例分析:Y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
Y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中,外部環境刺激維持生計類、規模收益類、種養結合類、半農半工類農戶聚集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調整農業種植結構。這一過程中,Y 村種植結構更加多元化,耕地利用系統的“生態—生產”功能不斷完善,向著更加有序的方向演進。結合Y 村的案例資料,本文將Y 村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劃分為自組織萌芽階段、自適應發展階段與他組織優化階段。
3.1 自組織萌芽階段: 耕地隱性“非糧化”產生
3.1.1 外部環境刺激
該階段,外部環境變化主要是自然與經濟兩方面。其一,Y村生態環境不斷退化。對于以散養為主的Y村而言,公共草地是有限的,但人口不斷增加,農戶需要不斷開墾新的土地、擴大養殖規模來抵御“馬爾薩斯陷阱”。在氣候不穩定以及旱災頻繁的背景下,Y村進一步衍生出了北方農牧交錯帶所共有的土地沙漠化、氣候不穩定以及旱災頻繁等土地退化問題[43],耕地立地條件惡化導致以糧為主的種植結構受到了沖擊。其二,Y 村耕地資源質量低下,小麥連作很難保證產量,相比之下小麥的茬口更適合輪作莜麥。其三,種植業與畜牧業之間收益差距較大,例如種植30畝莜麥,在畝產100 kg的情況下,凈收入僅3 000 元左右。但是30 畝莜麥作為牧草可供50 只綿羊過冬,而50只綿羊一年收入1.5萬元左右。
3.1.2 主體反應
種養結合類農戶是Y 村耕地“非糧化”自組織萌芽階段演化的主導力量。在此階段,種養結合類農戶率先響應環境變化,在無外力直接影響種植行為的情況下,主動調整種植結構,降低小麥種植比例,擴大莜麥種植比例。面對生態環境退化以及種糧經濟效益低下的情況,其他兩類農戶也作出相應反應。其中,維持生計類農戶資源稟賦有限,家庭勞動力約束性強,主要選擇種植糧食作物小麥以供家庭食用。半農半工類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首要任務是節約勞動力,傾向于種植勞動率較低的小麥。此時,種養結合類農戶雖然種植作物為莜麥,但是主要用作飼料,屬于隱性“非糧化”。
3.1.3 環境與主體匹配規則
在自組織萌芽階段,耕地“非糧化”演化主要依賴主體對于外界環境變化的主動適應,且外部環境變化并未直接影響耕地利用系統的效應器部分。種養結合類農戶依據自身資源稟賦,通過在種植業與畜牧業之間合理配置土地與勞動力要素,實現了小范圍的資源要素整合,保證經濟效益的同時,達到了耕地資源效用的最大化。維持生計類農戶與半農半工類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傾向于延續傳統種植結構,規避自然災害、市場波動等風險,通過減少成本投入,實現自身經濟效益最大化。這一階段,耕地利用系統演化較為緩慢,系統開放程度有限,農戶主體與外部環境的交互行為在逐漸增強,但是適應性行為有限,并未發生大規模的耕地“非糧化”現象,屬于“非糧化”萌芽階段。
3.2 自適應發展階段:耕地顯性“非糧化”凸顯
3.2.1 外部環境刺激
該階段,外部環境變化主要是社會與經濟兩方面。政府為提高農業機械化、集約化水平,激活集體經濟,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鼓勵工商資本下鄉參與農業生產過程。在農民自愿的情況下,鼓勵耕地有序流轉。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土地流轉市場逐漸活躍,土地流轉率不斷提高。集中后的耕地資源打破了原來細碎化的格局,有利于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Y村逐漸開始出現耕地小規模流轉的現象。2020年春耕之際,由Y村村集體牽線,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當地農戶簽訂了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共承包1 500畝耕地。
3.2.2 主體反應
規模收益類農戶是Y 村耕地“非糧化”自適應發展階段的主導力量。在此階段,規模收益類農戶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連片后,迅速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在有償流入耕地后原有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結構全部調整為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向日葵。此類農戶主體憑借較強的資本稟賦配備的大型拖拉機、覆膜機、旋耕機等農業機械降低了勞動力投入,購買優質的向日葵種子增加了產量,實現了自身經濟效益最大化。種養結合類農戶、半農半工類農戶和維持生計類農戶不同于規模收益類農戶,這三類農戶主體大部分并未及時響應外部環境變化,而是維持原有以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結構,3 戶資本稟賦和勞動力稟賦較強的原有農戶主體嘗試擴大種植規模,調整種植結構,也出現了小范圍的“非糧化”現象。
3.2.3 環境與主體匹配規則
在自適應發展階段,耕地“非糧化”演化動力主要來自于主體與外部環境兩者的共同作用。工商資本下鄉促進了土地流轉,雖未直接影響種植結構,但影響了種植規模。規模收益類農戶主體和另外3戶資本與勞動力稟賦較強的農戶主體在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利用豐厚的資本在耕地資源上追加要素投入,整合自身資源,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實現耕地資源經濟效益最大化。其余三類農戶主體受制于自身的資源稟賦同樣未對環境變化做出響應,維持原有糧食為主的種植結構。這一階段,主體與外界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流變得頻繁且復雜,資源整合能力在增強。同時,Y村耕地“非糧化”面積急劇擴大,顯性“非糧化”面積共有1 900畝,約占有償流轉耕地面積的95.48%,實際種植面積的28.36%,屬于“非糧化”凸顯階段。
3.3 他組織優化階段:耕地“非糧化”趨勢減緩
3.3.1 外界環境刺激
該階段,外部環境的政策導向發生變化,輪作試點工作有序開展。為了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和提高耕地產能,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中央政府在北方農牧交錯區開展耕地輪作試點,探索建立科學的輪作制度。試點主要推廣“一主多輔”的輪作模式,以養帶種、以種促養,滿足草食畜牧業發展需要。其中“一主”主要指玉米與大豆輪作,“多輔”主要指實行玉米與馬鈴薯、小麥、油料、雜糧雜豆、苜蓿、飼用燕麥等作物輪作,鼓勵地方積極探索開展優勢特色作物與其他作物的輪作模式。試點的補助標準為:對輪作試點區經營耕地面積連片且達到400畝以上的農業經營主體,給予150 元/畝的補助。對規模收益類農戶主體而言,輪作補貼的發放大大提高了收入水平,為調整種植結構,種植糧食作物提供了經濟扶持。
3.3.2 主體反應
規模收益類農戶是此階段的主導力量。規模收益類農戶得到了縣政府輪作項目的重點扶持,依據輪作要求將種植結構調整為:莜麥500畝左右,黍子500畝左右,紅豆300畝左右,向日葵300畝左右,藜麥100 畝左右。其中,藜麥是由當地政府引進的農作物新品種,與當地傳統糧食作物小麥相比,藜麥不僅能適應當地干旱、寒冷的氣候條件,單產達到135 kg左右,而且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單價達到2.5元/kg左右。在輪作政策的刺激下,規模收益類農戶選擇使用可以改良土壤,提高作物品質的有機肥,調整種植結構開展輪作,兼顧耕地的生產效益與生態效益。
3.3.3 環境與主體匹配規則
在他組織優化階段,演化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環境中政策制度的刺激與調節。政府通過輪作補貼直接彌補了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之間的收益差距,調和了規模收益類農戶獲取經濟效益與種植糧食作物之間的矛盾。在政府的直接調控下,規模收益類農戶摒棄了原有完全為經濟作物的種植模式,變為更加多元科學的種植結構。這一階段,主體與外界環境的交互作用更加強烈,資源整合和學習能力更強,種植結構的調整與當前“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目標相協同,促使Y村耕地利用系統向更加科學有序的方向演化。顯性“非糧化”耕地面積共有700 畝①耕地輪作項目要求耕地連片經營規模達到400畝才可獲得項目補助。經營規模較小的農業經營主體種植結構未發生較大變化,“非糧化”狀況與上一年保持一致。,約占有償流轉耕地面積的35.18%,實際種植面積的10.45%,耕地“非糧化”程度減弱,“非糧化”趨勢減緩甚至逆轉。
通過對Y 村耕地“非糧化”現象演變階段特征的分析,根據“自組織萌芽—自適應發展—他組織優化”三個階段以及外部環境與主體之間所遵循的刺激—反應模型,建立Y村耕地利用系統演化歷程模型(圖2)。

圖2 Y村耕地利用系統演化歷程模型Fig.2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evolutionary course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system in village Y
4 結論與“非糧化”治理策略
4.1 結論
耕地利用系統是一個要素眾多、結構復雜、功能多樣、機制明確且動態變化的自然—社會—經濟過程,也是不同農戶主體對外界環境刺激的反應集合。為此,本文以Y村76戶農戶為調查樣本,基于刺激—反應模型,通過梳理Y村耕地“非糧化”的演化歷程,探究不同階段農戶主體在外部環境刺激下的響應特征及互作機制。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基于刺激—反應理論模型,構建了耕地利用系統的分析框架。該框架體現了“非糧化”演化歷程中多時序、多主體的特征,闡明了外部環境系統與內部主體系統之間的運行機理,證明了農戶主體在系統演化過程中所具有的主動性、適應性與目標性,與復雜適應系統特征非常契合。耕地“非糧化”演化歷程實質上是農戶主體對于外部環境變化做出的主動適應或被動反應,確保在自身有限的資源稟賦下獲得最大個人效益,推動耕地利用系統實現有序躍升。
(2)在宏觀實踐演繹中,耕地“非糧化”的演化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共經過自組織萌芽、自適應發展和他組織優化三個階段。在自組織萌芽階段,種養結合類農戶主體在自然環境與經濟環境刺激下,自發調整種植結構,系統內部實現小范圍資源整合;在自適應發展階段,社會環境變化、系統外資本的流入直接參與了農業生產過程,影響了種植規模,也導致規模收益類農戶主體主動適應調整種植結構;在他組織優化階段,政策環境刺激導致規模經營類農戶主體被動調整種植結構,在政府介入下有序開展輪作。耕地“非糧化”現象由產生到凸顯再到減緩過程中,系統內部要素逐漸增多,種植結構日趨多元,耕地的多功能性不斷增強。農戶主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信息交流逐漸變強,資源整合與協調能力逐漸提升。
(3)從微觀主體反應來看,正是不同主體的主動適應性投射出系統不同特征的演化階段。具體而言,在系統演化歷程中,不同主體的“非糧化”行為趨向存在差異。家庭勞動力約束與資本約束較弱的農戶主體對于外部環境反應更加明顯,反之,家庭勞動力約束與資本約束較強的農戶主體反應較弱。
4.2 “非糧化”治理策略
基于以上研究,耕地利用系統具有情景依賴特征,必須對其加強防控。根據實際情況,采用系統論思想,從系統自組織、系統他組織、系統要素協同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
第一,順應系統的自組織適應能力。要充分認識到耕地利用系統多時序、多層次、多主體的復雜性,重視系統內自下而上的自組織適應能力,立足于外部環境的差異性與農戶主體的主動性,有效開展“非糧化”治理行動。其一,基于當前大農業觀、大食物觀,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在耕地利用中,依據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理論,秉承“優質耕地優先種糧”的原則,切實穩定糧食主產區種糧格局的前提下,宜種則種、宜養則養、宜林則林,構建多元化食物供應體系,提升耕地產出效益。其二,依托當地自然資源特點與農業產業稟賦,充分發揮其優勢,本著“農民增收,產業增效”的思路,謀篇布局,堅持走特色化、差異化的農業產業發展道路,打造特色、優質農產品品牌。通過為農業賦能保障農戶主體收益,激發農戶主體自發的耕地保護動力。
第二,加強他組織的調控優化引導。系統演化過程中,政府強有力的介入具有強制性和誘致性的功能[18],大大改變了耕地利用系統演化方向,提升了演化水平。制定科學合理的約束型、激勵型、引導型政策制度是“非糧化”治理的核心手段。其一,細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嚴格管控耕地轉為其他用地,加強耕地種植用途管控機制的探索,實現永久基本農田、一般農田的分區精準化管控,形成糧食生產與耕地利用的長效保護機制。其二,優化農業補貼制度,協調區域之間的不公平發展。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顯化糧食生產與耕地保護的社會價值以及生態價值,對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進行經濟補償,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其三,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農戶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具有本能的逐利動機和規避風險的趨向,通過擴大農業保險品種及規模,提高農業保險補貼金額,切實穩定農戶主體種糧積極性。
第三,促進系統要素協同治理能力。其一,細碎化的土地利用特征和老齡化的人口特征不利于各類土地政策的推行,也不利于實現規模經濟效益,需深化耕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通過放活土地經營權,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土地流轉,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其二,現階段要素市場是非均衡的,農村土地、資金、勞動力要素不斷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且未能及時回流,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疲弱[44]。必須整合資本、技術、農機、人才等各類農業生產要素,圍繞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需求開展覆蓋生產整過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提供流程標準化、操作專業化和服務高效化的社會化服務內容,助力糧食種植大戶降本增效。其三,運用無人機航拍技術、農業遙感技術、實地調研等重點對流轉耕地地塊的作物類型、土壤理化性質開展動態監測工作,建立包含地塊屬性、地籍信息、流轉信息、作物類型的基礎信息數據庫,推進“非糧化”的全域精準治理與耕地保護的全方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