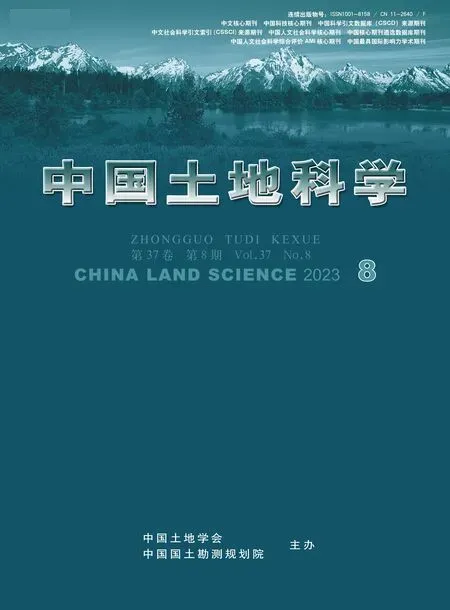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理論邏輯與實(shí)現(xiàn)路徑
宋 敏,張安錄
(1.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工商管理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3; 2.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0)
延續(xù)土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相關(guān)研究[1],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被定義為耕地利用的顯性形態(tài)和隱性形態(tài)在長(zhǎng)時(shí)間序列下的趨勢(shì)性轉(zhuǎn)折,是一個(gè)穩(wěn)定狀態(tài)向另一個(gè)穩(wěn)定狀態(tài)轉(zhuǎn)變的過(guò)程[2],常與區(qū)域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變化相聯(lián)系。其中耕地利用顯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主要涉及耕地?cái)?shù)量、結(jié)構(gòu)、空間分布等方面的變化,而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則體現(xiàn)為耕地質(zhì)量、經(jīng)營(yíng)方式、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功能釋放等方面的變化[3]。近年來(lái),為了揭示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復(fù)雜過(guò)程與機(jī)理,強(qiáng)化耕地利用調(diào)控進(jìn)而推動(dòng)耕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大量學(xué)者在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時(shí)空分異格局與驅(qū)動(dòng)機(jī)制[4-5]、影響因素[6]、綠色轉(zhuǎn)型[7]、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3]、路徑與調(diào)控[8]等多個(gè)領(lǐng)域持續(xù)展開(kāi)研究工作。當(dāng)前,我國(guó)正處在城鎮(zhèn)化快速推進(jìn)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重要?dú)v史階段,這使得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愈發(fā)成為重要的科學(xué)問(wèn)題和現(xiàn)實(shí)需要。
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外宏觀環(huán)境發(fā)生深刻變化。一方面,改革開(kāi)放后我國(guó)在確保糧食安全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以糧食生產(chǎn)“十九連豐”、口糧自給率100%、谷物自給率超過(guò)95%實(shí)現(xiàn)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duì)安全[9]。與此同時(shí),居民營(yíng)養(yǎng)全面提升,膳食結(jié)構(gòu)由“糧菜型”向“糧肉菜果奶”多元型、健康型食物需求轉(zhuǎn)變,進(jìn)入由“吃得飽”向“吃得好”嬗變的新階段。然而,油料、大豆、糖類(lèi)等非主糧類(lèi)農(nóng)產(chǎn)品自給率卻在2000—2020年呈下降趨勢(shì)且蛋白類(lèi)食物對(duì)外依存度不斷提升[10],難以適應(yīng)居民需求的不斷變化。另一方面,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地緣政治博弈、國(guó)際貿(mào)易環(huán)境惡化等因素導(dǎo)致的高度不確定的國(guó)際形勢(shì)決定了未來(lái)國(guó)際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的不穩(wěn)定性[11]。在此背景下,倡導(dǎo)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dòng)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的大食物觀逐漸形成,食物安全替代糧食安全成為保障國(guó)家安全的必然選擇[10]。盡管大食物觀提出要向整個(gè)國(guó)土資源要食物,但耕地資源仍是食物生產(chǎn)中最重要的生產(chǎn)資源,其合理利用是落實(shí)大食物觀的重要基礎(chǔ)。
圍繞耕地利用如何支撐大食物觀理念落地這一問(wèn)題,近年來(lái)學(xué)者們主要從優(yōu)化耕地利用管理制度或政策的角度開(kāi)展了一些討論。已有研究認(rèn)為,相比作物產(chǎn)量和人口的變化,居民膳食結(jié)構(gòu)變化對(duì)耕地利用的影響更為顯著[9]。應(yīng)當(dāng)以保護(hù)生產(chǎn)能力為導(dǎo)向制定耕地用途管制規(guī)則[12],通過(guò)耕地剛性管制與彈性調(diào)控協(xié)同等方式優(yōu)化耕地用途管制體系和管制規(guī)則促進(jìn)耕地利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13-14],以解決糧食與食物、增產(chǎn)與增收、管制約束與公平發(fā)展之間的多重矛盾,在保證糧食生產(chǎn)的同時(shí)兼顧其他食物生產(chǎn)的需求,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食物的多元供給[15-16]。此外,需要通過(guò)優(yōu)化耕地“占補(bǔ)”和“進(jìn)出”的雙平衡政策應(yīng)對(duì)食物生產(chǎn)收益與稀缺程度倒掛、農(nóng)民非糧化種植監(jiān)管困難等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17-18],并提議正視耕地“非糧化”中的合理需求,在不影響耕作層和糧食產(chǎn)能的前提下,以一定的優(yōu)先序引導(dǎo)耕地合理“食物化”利用,從而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給[19-20]。也有一些學(xué)者討論了促進(jìn)耕地利用方式轉(zhuǎn)變的政策支持問(wèn)題,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探索并鼓勵(lì)綠色、環(huán)保、低碳、可持續(xù)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實(shí)現(xiàn)耕地資源的可持續(xù)集約利用[21-22]。這些研究為推進(jìn)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的顯性和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
大食物觀在有效回應(yīng)居民食物需求變化和拓展糧食安全涵義的同時(shí),對(duì)耕地利用及其轉(zhuǎn)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鑒于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本質(zhì)是耕地利用系統(tǒng)的要素及結(jié)構(gòu)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國(guó)家發(fā)展戰(zhàn)略等外部條件階段性變化而出現(xiàn)的趨勢(shì)性轉(zhuǎn)折[15],而當(dāng)前尚不具備與大食物觀相適應(yīng)、相匹配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策略。因此,深刻認(rèn)識(shí)理解大食物觀的內(nèi)涵及其對(duì)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厘清大食物觀引領(lǐng)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邏輯框架并探尋其實(shí)現(xiàn)路徑,是新發(fā)展階段食物安全目標(biāo)下耕地變化研究的新命題,對(duì)于豐富土地變化領(lǐng)域的科學(xué)研究以及應(yīng)對(duì)我國(guó)食物安全與耕地利用的新形勢(shì)都具有重要意義。
1 大食物觀的內(nèi)涵及其與耕地資源的關(guān)系解析
1.1 大食物觀的內(nèi)涵闡釋
大食物觀的萌芽可追溯至1990年習(xí)近平在福建寧德地區(qū)工作時(shí)的論述——“現(xiàn)在講的糧食即食物,大糧食觀念替代了以糧為綱的舊觀念。”隨著2015年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huì)議首次提出“樹(shù)立大食物觀念”并于2016年寫(xiě)入中央一號(hào)文件,大食物觀被確立為國(guó)家層面的發(fā)展理念,并在此后多次出現(xiàn)在國(guó)家重要會(huì)議及文件中(圖1)。由此,以“滿(mǎn)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fèi)需求”為導(dǎo)向,以“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duì)安全”為前提,要求以“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為基礎(chǔ)“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dòng)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從而“保障肉類(lèi)、蔬菜、水果、水產(chǎn)品等各類(lèi)食物有效供給”的大食物觀逐漸清晰。總體而言,大食物觀就是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dòng)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的一種觀念[23]。

圖1 大食物觀理念演進(jìn)脈絡(luò)Fig.1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er Food” perspective
相對(duì)于傳統(tǒng)的糧食觀,大食物觀是基于國(guó)家尺度對(duì)食物安全的重新審視,強(qiáng)調(diào)重視多元食物的生產(chǎn)與供應(yīng),把維持一定的食物自給率作為保障國(guó)家食物安全和居民食物需求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基礎(chǔ),這對(duì)于我國(guó)這一受到資源環(huán)境硬約束的人口大國(guó)極為重要[18,24]。以大食物觀來(lái)統(tǒng)籌我國(guó)糧食及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供應(yīng)要求處理好食物生產(chǎn)與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一方面要以向整個(gè)國(guó)土資源要食物為導(dǎo)向,在生態(tài)適宜、資源可承受的前提下形成同市場(chǎng)需求相適應(yīng)的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和區(qū)域布局;另一方面也要求充分利用國(guó)際國(guó)內(nèi)兩個(gè)市場(chǎng)、兩種資源,利用比較優(yōu)勢(shì)滿(mǎn)足國(guó)內(nèi)對(duì)食物數(shù)量、結(jié)構(gòu)、品質(zhì)方面的要求,同時(shí)也可緩解我國(guó)水土資源不足等資源環(huán)境壓力[17]。因此,面向國(guó)家食物安全需求全方位、多向度地提高食物保障能力是大食物觀的尺度指向。
基于對(duì)大食物觀理念產(chǎn)生背景、發(fā)展脈絡(luò)、尺度指向以及相關(guān)研究[9,25-26]的解讀,本文認(rèn)為應(yīng)從5 個(gè)層面理解大食物觀(圖2):(1)需求層面:國(guó)內(nèi)外宏觀環(huán)境變化下的居民消費(fèi)結(jié)構(gòu)與水平升級(jí)是大食物觀提出的客觀依據(jù),要求以需求為導(dǎo)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2)對(duì)象層面:大食物觀關(guān)注的對(duì)象從“糧食”拓展到“食物”。即不僅包括四大口糧、也包括雜糧、豆類(lèi)等,同時(shí)蔬菜、瓜果、肉產(chǎn)品、水產(chǎn)品、菌菇等也非常重要。其中糧食安全是基礎(chǔ)和前提,食物安全是落腳點(diǎn)。(3)資源層面:一方面,生產(chǎn)資源由耕地拓展到整個(gè)國(guó)土資源,要求充分利用江河湖海林草挖掘動(dòng)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資源潛力、豐富食物品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減輕耕地的主糧生產(chǎn)壓力,緩解糧食安全“卡脖子”問(wèn)題;另一方面,大食物觀不僅關(guān)注各類(lèi)土地資源的食物供給水平,還強(qiáng)調(diào)要以可持續(xù)的方式合理地利用土地資源[12-13]。(4)供給層面:大食物觀要求構(gòu)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將單一的糧食生產(chǎn)拓展至動(dòng)物、植物、微生物等各類(lèi)食物的多元供給,以滿(mǎn)足居民不斷變化的需求。(5)目標(biāo)層面:大食物觀要求通過(guò)“有效供給”保障供給層面與需求層面的相對(duì)平衡。食物的充足性、多樣性、均衡性、穩(wěn)定性、可持續(xù)性和可負(fù)擔(dān)性構(gòu)成了有效供給的核心要義[9,15,18,27],它們表現(xiàn)為食物在數(shù)量、結(jié)構(gòu)和質(zhì)量三個(gè)維度的有效統(tǒng)一,從而確保實(shí)現(xiàn)食物的數(shù)量、質(zhì)量、營(yíng)養(yǎng)、生態(tài)多維安全,這為包括耕地資源在內(nèi)的各類(lèi)資源的開(kāi)發(fā)利用明確了目標(biāo),為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提供了方向性引領(lǐng)。

圖2 大食物觀涵義解析Fig.2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er Food” perspective
1.2 大食物觀與耕地資源
盡管大食物觀強(qiáng)調(diào)全方位多途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將食物生產(chǎn)用地由耕地資源拓展至整個(gè)國(guó)土資源,但耕地資源仍是確保大食物觀落地的核心和基礎(chǔ)性資源。首先,大食物觀堅(jiān)持以糧食生產(chǎn)為基礎(chǔ),以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duì)安全為前提,向耕地要主糧是長(zhǎng)期導(dǎo)向。這表明以糧食產(chǎn)能、數(shù)量提升為重點(diǎn)的耕地利用主要方向沒(méi)有改變[19]。其次,部分其他農(nóng)產(chǎn)品的供應(yīng)也需要耕地資源的支撐。在保障口糧安全的基礎(chǔ)上,大食物觀還強(qiáng)調(diào)肉蛋奶等動(dòng)物性食物和蔬菜、油、水果、堅(jiān)果等植物性食物的供給。隨著居民膳食結(jié)構(gòu)的變化,居民對(duì)動(dòng)物性食物的需求增長(zhǎng)將持續(xù)帶動(dòng)飼料糧的需求擴(kuò)大[24],部分蔬菜、油料作物等植物性食物消費(fèi)也仍有賴(lài)耕地資源的生產(chǎn)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從“糧食觀”到“大食物觀”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從強(qiáng)調(diào)主糧到注重多元食物均衡發(fā)展的策略調(diào)整為耕地利用轉(zhuǎn)型帶來(lái)了新的挑戰(zhàn)。2023 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特別提出要“構(gòu)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分領(lǐng)域制定實(shí)施方案”,其中耕地資源利用這一關(guān)鍵領(lǐng)域應(yīng)當(dāng)予以重視。由此可見(jiàn),針對(duì)耕地這一核心和基礎(chǔ)性資源的利用轉(zhuǎn)型問(wèn)題展開(kāi)研究,提出與大食物觀相適應(yīng)、相匹配的政策舉措和實(shí)施路徑是踐行大食物觀的必然選擇。
2 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
本文按照“內(nèi)涵演化—矛盾表現(xiàn)—轉(zhuǎn)型需求”的邏輯揭示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面臨的挑戰(zhàn)。當(dāng)前我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居民生活已進(jìn)入新發(fā)展階段,傳統(tǒng)的糧食安全觀發(fā)生深刻變化,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端與供給端的矛盾深化,傳統(tǒng)耕地利用方式和當(dāng)前耕地利用政策的缺陷在大食物觀的視閾下愈發(fā)明顯,亟需立足我國(guó)耕地利用的實(shí)際,站在系統(tǒng)和戰(zhàn)略高度予以統(tǒng)籌解決(圖3)。

圖3 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面臨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Fig.3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faced by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from the “Greater Food” perspective
2.1 糧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拓展
食物消費(fèi)是人類(lèi)營(yíng)養(yǎng)健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之間的重要聯(lián)系,糧食安全在各個(gè)國(guó)家的政策體系中均占據(jù)著優(yōu)先位置。中國(guó)的糧食安全問(wèn)題源自“誰(shuí)來(lái)養(yǎng)活中國(guó)”的布朗之問(wèn),意在基于國(guó)內(nèi)資源實(shí)現(xiàn)基本糧食自給自足。1996 年,《中國(guó)的糧食問(wèn)題》白皮書(shū)首次在中國(guó)語(yǔ)境下使用術(shù)語(yǔ)“糧食安全”,并提出“糧食自給率不低于95%,凈進(jìn)口量不超過(guò)國(guó)內(nèi)消費(fèi)量的5%”的具體目標(biāo)[28]。此后,糧食安全頻繁出現(xiàn)于官方表述中,且其內(nèi)涵與目標(biāo)不斷演化。近10年來(lái),聯(lián)合國(guó)糧農(nóng)組織倡導(dǎo)改變膳食結(jié)構(gòu)和食物系統(tǒng),以實(shí)現(xiàn)糧食安全、營(yíng)養(yǎng)改善和人人可負(fù)擔(dān)的健康飲食[29]。聚焦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促使居民的食物需求結(jié)構(gòu)不斷升級(jí),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和食物生產(chǎn)發(fā)展正在向滿(mǎn)足城鄉(xiāng)居民營(yíng)養(yǎng)健康需求轉(zhuǎn)變,邁入了由“吃飽”向“吃好”轉(zhuǎn)變的新階段,呈現(xiàn)主糧占比縮減化、食物種類(lèi)多元化的趨勢(shì),食物供給體系從注重食物數(shù)量向注重食物“數(shù)量—結(jié)構(gòu)—質(zhì)量”多維目標(biāo)延伸[9,22]。糧食安全的使命也由保障口糧供給向保障多元化食物供給轉(zhuǎn)變,因此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建議將傳統(tǒng)的“糧食安全”拓展為“食物安全”,將大食物觀下的食物安全視為糧食安全的進(jìn)一步延伸[16,19]。
在糧食安全向食物安全不斷拓展的背景下,亟需理解“食物需求—食物安全目標(biāo)—耕地利用目標(biāo)—耕地利用轉(zhuǎn)型”之間的關(guān)系,系統(tǒng)闡釋大食物觀引領(lǐng)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機(jī)理,這對(duì)于推動(dòng)目標(biāo)導(dǎo)向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具有基礎(chǔ)性作用。
2.2 耕地利用供給側(cè)與需求側(cè)矛盾加劇
近年來(lái),我國(guó)食物消費(fèi)端與供給端不平衡的矛盾不斷深化。從消費(fèi)端看,居民當(dāng)前在薯類(lèi)、蔬菜、瓜果、奶及奶制品方面的消費(fèi)水平仍與膳食指南推薦量的高值存在顯著差距(表1);對(duì)禽肉、牛肉、羊肉等的消費(fèi)呈增長(zhǎng)勢(shì)頭,預(yù)計(jì)未來(lái)5~10 年,對(duì)此類(lèi)食物的需求仍將繼續(xù)擴(kuò)大[11]。從供給端看,飼料糧安全問(wèn)題突出,大豆年進(jìn)口量高達(dá)1億t左右,在全球貿(mào)易總量中占比約60%,對(duì)外依存度達(dá)85.5%;且植物油、食糖2022 年的自給率分別僅為29%和64.8%。總體表現(xiàn)為水稻、小麥等口糧維持高水平自給,基本“實(shí)現(xiàn)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duì)安全”[11],但食物自給率持續(xù)下降,2022年僅為67.6%[23]。

表1 我國(guó)居民2021年各類(lèi)食物人均消費(fèi)量與平衡膳食寶塔對(duì)比Tab.1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foods and its quantity in Balanced Diet Pagoda in 2021 (g/d)
食物需求端與供給端的不平衡加劇著耕地利用供給側(cè)和需求側(cè)的矛盾。在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用途不僅要保證糧食生產(chǎn),也要合理兼顧其他食物生產(chǎn)需求。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快速城市化引發(fā)的人口變化、社會(huì)階層分化與膳食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等需求側(cè)變動(dòng)對(duì)食物供應(yīng)產(chǎn)生了極高的期望[9],但與之相對(duì)地,位于供給側(cè)的耕地?cái)?shù)量仍在持續(xù)減少、耕地利用方式尚未及時(shí)轉(zhuǎn)型,有礙新發(fā)展階段食物安全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如果把食物多元化作為衡量人們對(duì)更好生活需求的起點(diǎn),那么中國(guó)是否有足夠的耕地來(lái)養(yǎng)育其人口這一問(wèn)題已經(jīng)引起廣泛關(guān)注[15,30]。一些研究表明,當(dāng)前的耕地利用在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上均與大食物觀的要求存在巨大差距。從規(guī)模上看,未來(lái)進(jìn)一步擴(kuò)大糧食和飼料等生產(chǎn)用地的潛力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包括未利用地開(kāi)發(fā)的物理和經(jīng)濟(jì)限制以及生物燃料、城市擴(kuò)張、森林、緩解氣候變化和維持生物多樣性對(duì)土地利用的競(jìng)爭(zhēng)等[27]。從結(jié)構(gòu)上看,耕地利用的結(jié)構(gòu)性失衡問(wèn)題也很突出。當(dāng)前我國(guó)耕地的種植結(jié)構(gòu)導(dǎo)致了農(nóng)產(chǎn)品供應(yīng)短缺與供應(yīng)過(guò)剩并存的失衡現(xiàn)象:一方面,谷物處于生產(chǎn)增加、進(jìn)口增加和庫(kù)存增加(“三增”)的惡性循環(huán);另一方面,大豆和肉源作物的種植面積僅為肉、蛋和奶等動(dòng)物性食品所需飼料谷物的四分之一[30]。因此,我國(guó)迫切需要調(diào)整包括耕地在內(nèi)的土地利用戰(zhàn)略,以解決食物需求升級(jí)下的食物安全問(wèn)題。
當(dāng)前我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已進(jìn)入新發(fā)展階段,在大食物觀逐步確立、糧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拓展的背景下,已有研究難以為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和政策支持。大食物觀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呼喚學(xué)術(shù)界和管理者重新審視耕地資源利用過(guò)程中的具體問(wèn)題及其成因,通過(guò)推進(jìn)耕地利用的顯性和隱性轉(zhuǎn)型緩解耕地利用供給側(cè)與需求側(cè)的矛盾,推動(dòng)國(guó)家食物安全戰(zhàn)略驅(qū)動(dòng)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理論研究與實(shí)踐探索。
2.3 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需要面向大食物觀的系統(tǒng)性解決方案
近年來(lái),我國(guó)耕地利用面對(duì)的挑戰(zhàn)與日俱增,耕地?cái)?shù)量約束、質(zhì)量不高、肥力下降、耕作條件退化等問(wèn)題并存,耕地非農(nóng)化、非糧化、風(fēng)險(xiǎn)化、邊際化等趨勢(shì)明顯[13,30],加之自然災(zāi)害及極端天氣頻發(fā)導(dǎo)致耕地不斷減少,嚴(yán)重制約了耕地的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水平與供給能力。傳統(tǒng)以物質(zhì)投入為主、高度集約的耕地利用模式固化是當(dāng)前我國(guó)耕地利用的顯著特征之一[31],而且現(xiàn)行的耕地利用與管理政策仍將以口糧為主的糧食生產(chǎn)作為主要導(dǎo)向,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國(guó)家的糧食安全尤其是口糧安全,但也產(chǎn)生一系列突出問(wèn)題:(1)糧食生產(chǎn)重心持續(xù)北移具有潛在的可持續(xù)性風(fēng)險(xiǎn)和穩(wěn)定性風(fēng)險(xiǎn),這一方面表現(xiàn)為北方高強(qiáng)度耕地利用導(dǎo)致的水資源安全風(fēng)險(xiǎn)和生態(tài)代價(jià)高企,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產(chǎn)銷(xiāo)區(qū)域失衡、重心距離拉大帶來(lái)的運(yùn)輸難度提升、成本增加以及可能出現(xiàn)的局部區(qū)域供應(yīng)緊張,這在疫情防控等非傳統(tǒng)安全事件突發(fā)時(shí)已得到了體現(xiàn);(2)以行政命令為特征的規(guī)劃、分區(qū)等剛性管控體系存在耕地利用與質(zhì)量建設(shè)分割的現(xiàn)象,剛性有余彈性不足,耕地“非糧化”利用與耕地用途管制存在一定沖突,缺乏識(shí)別和支持合理性“非糧化”利用的分區(qū)分級(jí)利用策略,難以滿(mǎn)足大食物觀視閾下食物多樣性、均衡性及充足性的需求[29];(3)當(dāng)前耕地“非農(nóng)化”“非糧化”治理的主要手段仍以規(guī)劃管制等行政命令類(lèi)政策工具為主,對(duì)于由國(guó)土空間用途管制、種植用途管制等造成的區(qū)域間權(quán)責(zé)不對(duì)等和發(fā)展不平衡,缺乏經(jīng)濟(jì)激勵(lì)類(lèi)政策工具的支持[32],耕地利用主體合理利用耕地的內(nèi)生動(dòng)力缺失;(4)我國(guó)耕地利用效率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缺乏針對(duì)不同耕地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效率分類(lèi)提升機(jī)制[33];(5)持續(xù)高強(qiáng)度的耕地集約利用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導(dǎo)致高昂的資源環(huán)境代價(jià),耕地恢復(fù)力與韌性不足[13,20],農(nóng)產(chǎn)品供需處于緊平衡狀態(tài),難以滿(mǎn)足大食物觀視閾下對(duì)食物可持續(xù)性的需求。
大食物觀所涵蓋的多元食物需求、多重食物安全目標(biāo)決定了新形勢(shì)下耕地利用的多維目標(biāo),因此在大食物觀視閾下圍繞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方向、轉(zhuǎn)型路徑和政策選擇等關(guān)鍵問(wèn)題展開(kāi)研究,探索顯性與隱性協(xié)同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系統(tǒng)性解決方案迫在眉睫。
3 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理論邏輯
大食物觀引領(lǐng)了新時(shí)期的食物需求、食物安全目標(biāo)、耕地利用目標(biāo)并推動(dòng)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而由耕地利用的顯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和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復(fù)合的耕地利用系統(tǒng)性轉(zhuǎn)型則為踐行大食物觀提供重要支撐(圖4)。

圖4 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理論邏輯Fig.4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from the “Greater Food” perspective
3.1 食物需求與食物安全目標(biāo)
“大食物觀”發(fā)展理念下的食物需求變化表現(xiàn)為對(duì)食物數(shù)量、結(jié)構(gòu)、質(zhì)量的更高要求,以確保食物的充足性、多樣性、均衡性、穩(wěn)定性、可持續(xù)性和可負(fù)擔(dān)性[29]。因此,在確保糧食安全底線(xiàn)的基礎(chǔ)上,應(yīng)當(dāng)確立以數(shù)量安全、質(zhì)量安全、營(yíng)養(yǎng)安全、生態(tài)安全為表征的食物安全多維目標(biāo)。其中:(1)食物數(shù)量的充足性需要食物數(shù)量安全予以保障,高水平的總量上的食物數(shù)量安全是確保居民獲得足夠熱量的基礎(chǔ)。(2)居民對(duì)植物性食物(谷物、蔬菜、水果、油籽、糖)和動(dòng)物性食物(雞蛋、牛奶、肉類(lèi))在結(jié)構(gòu)上的多樣性需求同時(shí)涉及食物的數(shù)量安全和營(yíng)養(yǎng)安全。此時(shí)的食物數(shù)量安全更強(qiáng)調(diào)結(jié)構(gòu)性的數(shù)量安全,即在總量充足的基礎(chǔ)上各個(gè)類(lèi)型的食物數(shù)量也能滿(mǎn)足居民多樣性的食物需要。同時(shí),多樣性的食物也與營(yíng)養(yǎng)均衡有關(guān),事關(guān)食物營(yíng)養(yǎng)安全。《中國(guó)居民膳食指南(2022)》將“食物多樣,合理搭配”作為平衡膳食的首要準(zhǔn)則,強(qiáng)調(diào)了食物多樣性對(duì)居民膳食營(yíng)養(yǎng)的支撐性作用。(3)食物結(jié)構(gòu)與質(zhì)量的均衡性涉及食物的數(shù)量安全和營(yíng)養(yǎng)安全。《中國(guó)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議人們以1∶2.15∶0.54重量比例安排谷物薯類(lèi)及雜豆、蔬菜和水果、動(dòng)物性食物三個(gè)層次的食物進(jìn)食,以改善膳食營(yíng)養(yǎng)狀況。我國(guó)人均谷物、蔬菜的消費(fèi)量從1987年的198.4 kg、136.3 kg下降到2020年的126.3 kg、99.5 kg,而同期人均雞蛋、畜禽肉消費(fèi)量分別增加3.3倍、2.7倍,達(dá)到2020年的12.7 kg、61.1 kg,但仍低于當(dāng)前膳食指南中平均攝入量37.5 kg、62.5 kg的要求[30]。此外,當(dāng)前中國(guó)約有19.4%的可耕種土地受到鎘、鎳、砷等污染物的侵害[22],因此,在確保數(shù)量安全的基礎(chǔ)上,食物質(zhì)量達(dá)到安全標(biāo)準(zhǔn)是確保居民吃的健康、營(yíng)養(yǎng)、均衡的重要保障。(4)食物的穩(wěn)定性要求食物數(shù)量、質(zhì)量、營(yíng)養(yǎng)安全在面臨重大風(fēng)險(xiǎn)和威脅、突發(fā)沖擊和沖突時(shí)能夠得到保障[27]。(5)食物數(shù)量、結(jié)構(gòu)與質(zhì)量的可持續(xù)性要求食物數(shù)量、質(zhì)量、營(yíng)養(yǎng)、生態(tài)安全目標(biāo)長(zhǎng)期可實(shí)現(xiàn),即當(dāng)代的食物安全不損害子孫后代獲取足夠和有營(yíng)養(yǎng)食物的權(quán)利。(6)足夠數(shù)量的食物是確保食物供需平衡、價(jià)格可承受的基礎(chǔ),因此食物的可負(fù)擔(dān)性需要以食物數(shù)量安全為基礎(chǔ)。
3.2 食物安全目標(biāo)與耕地利用目標(biāo)
大食物觀所涵蓋的多元食物需求、多重食物安全目標(biāo)決定了新形勢(shì)下的耕地利用應(yīng)當(dāng)錨定“數(shù)量保障—質(zhì)量提升—生態(tài)改善”三維目標(biāo)。(1)大食物觀下耕地利用的數(shù)量保障目標(biāo)既要求維持耕地的“總量”也要求維持耕地的“結(jié)構(gòu)量”,以滿(mǎn)足食物的數(shù)量安全與營(yíng)養(yǎng)安全目標(biāo)。一方面,在耕地的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力條件下,需要保有足夠數(shù)量的耕地以滿(mǎn)足食物數(shù)量安全的需求,形成耕地“總量”的底線(xiàn)約束。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對(duì)于食物多樣性的需求日益強(qiáng)化,還應(yīng)當(dāng)在“總量”保障的基礎(chǔ)上形成科學(xué)的“高標(biāo)準(zhǔn)農(nóng)田—永久基本農(nóng)田—一般耕地”結(jié)構(gòu)性配置,合理進(jìn)行糧食種植和非糧化利用管控,提供多樣化的食物以滿(mǎn)足食物營(yíng)養(yǎng)安全的需要。(2)大食物觀下耕地利用的質(zhì)量提升目標(biāo)要求改善耕地質(zhì)量從而滿(mǎn)足食物安全的多維目標(biāo)。通過(guò)改良耕地的地表要素、氣候要素、工程要素、生態(tài)要素能夠深刻影響耕地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量、農(nóng)產(chǎn)品品質(zhì)和生態(tài)基底,提升耕地的產(chǎn)能與穩(wěn)定性,從而實(shí)現(xiàn)食物的數(shù)量、質(zhì)量、營(yíng)養(yǎng)、生態(tài)多維安全目標(biāo)。(3)大食物觀下耕地利用的生態(tài)改善目標(biāo)進(jìn)一步支持食物質(zhì)量、營(yíng)養(yǎng)、生態(tài)安全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受到高強(qiáng)度人工干預(yù)和調(diào)控的自然—人工復(fù)合生態(tài)系統(tǒng),良好而穩(wěn)定的生態(tài)狀況能夠?yàn)楦厣鷳B(tài)系統(tǒng)持續(xù)生產(chǎn)綠色、健康農(nóng)產(chǎn)品提供環(huán)境條件和基本保障,同時(shí)也有利于與其他資源要素一同確保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和可持續(xù)性。由此可見(jiàn),耕地的“數(shù)量保障”是基礎(chǔ)——是耕地“質(zhì)量提升”“生態(tài)改善”的基石;耕地的“質(zhì)量提升”是核心——通過(guò)與“生態(tài)改善”的互饋?zhàn)饔么_保耕地產(chǎn)能;耕地的“生態(tài)改善”是支撐——是耕地“數(shù)量保障”“質(zhì)量提升”的有力補(bǔ)充。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三維目標(biāo)服務(wù)于食物安全多維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3.3 耕地利用目標(biāo)與耕地利用轉(zhuǎn)型
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通常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具有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在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的“數(shù)量保障—質(zhì)量提升—生態(tài)改善”三維目標(biāo)對(duì)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是實(shí)現(xiàn)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目標(biāo)的必然選擇。在大食物觀引領(lǐng)下,以耕地規(guī)模增減、空間布局變化為表征的耕地顯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決定了耕地的總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性規(guī)模的變化趨勢(shì),關(guān)系到耕地利用數(shù)量保障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以耕地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耕作方式、經(jīng)營(yíng)效率、環(huán)境效應(yīng)變化等為表征的耕地利用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決定了耕地利用質(zhì)量提升目標(biāo)和生態(tài)改善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在大食物觀為食物安全賦予了新內(nèi)涵以及農(nóng)食系統(tǒng)持續(xù)向高質(zhì)高效、營(yíng)養(yǎng)健康、更有韌性、包容普惠轉(zhuǎn)型的趨勢(shì)下[9],耕地利用顯性形態(tài)與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對(duì)于耕地外在與潛在變化的影響需要重新得到審視,探尋兩者協(xié)同推進(jìn)的整體性轉(zhuǎn)型路徑。
4 面向大食物觀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實(shí)現(xiàn)路徑
路徑選擇決定著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方向和效果。大食物觀所涵蓋的多元食物需求、多重食物安全目標(biāo)決定了新形勢(shì)下耕地利用的多維目標(biāo),因此在大食物觀視閾下探索行之有效、系統(tǒng)性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解決方案是當(dāng)前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以推動(dòng)耕地利用向滿(mǎn)足大食物觀多維需求轉(zhuǎn)型為總體目標(biāo),形成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顯性形態(tài)和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路徑體系(圖5)。其中剛性管制與彈性調(diào)控復(fù)合分區(qū)機(jī)制和基于管制強(qiáng)度差異的耕地發(fā)展權(quán)交易機(jī)制共同形成“責(zé)任+激勵(lì)”路徑,通過(guò)控制耕地利用布局、規(guī)模以及優(yōu)化種植結(jié)構(gòu),協(xié)同推進(jìn)耕地利用的顯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基于耕作行為激勵(lì)的可持續(xù)集約利用機(jī)制、基于經(jīng)營(yíng)主體分類(lèi)引導(dǎo)的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機(jī)制致力于調(diào)整耕作方式和提升耕地的利用效率,從而推進(jìn)耕地利用的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通過(guò)上述路徑體系產(chǎn)生口糧安全、食物多樣、生態(tài)安全、生產(chǎn)發(fā)展、總量保障、質(zhì)量提升等多重效應(yīng),從而滿(mǎn)足居民食物需求,實(shí)現(xiàn)新時(shí)期國(guó)家的食物安全目標(biāo)及耕地利用目標(biāo)。
4.1 優(yōu)化區(qū)域生產(chǎn)布局:基于人口—資源—食物協(xié)調(diào)的布局機(jī)制
食物安全離不開(kāi)支撐性地理空間的合理布局。針對(duì)我國(guó)糧食產(chǎn)量持續(xù)北移的趨勢(shì)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水土資源空間錯(cuò)配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從全局出發(fā)審視食物生產(chǎn)的空間布局,尤其是糧食生產(chǎn)的空間布局。結(jié)合人口的總量、結(jié)構(gòu)、分布及其對(duì)食物的需求以及水土資源特征、資源環(huán)境的承載力與適宜性的區(qū)域差異科學(xué)劃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地域格局,合理確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功能區(qū)、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保護(hù)區(qū)等管控區(qū)域,實(shí)施糧食生產(chǎn)區(qū)與消費(fèi)區(qū)再平衡戰(zhàn)略,促進(jìn)人口—資源—食物三者形成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空間關(guān)聯(lián)。進(jìn)而以強(qiáng)化耕地用途管制為基礎(chǔ)因區(qū)施策,做到北方糧食產(chǎn)能穩(wěn)定、中部地區(qū)產(chǎn)能提升、西部地區(qū)產(chǎn)能拓展、南方地區(qū)產(chǎn)能恢復(fù),守好“南方地區(qū)的責(zé)任田”。由此穩(wěn)步提升我國(guó)包括糧食在內(nèi)的食物可持續(xù)供給能力和抵御風(fēng)險(xiǎn)能力,統(tǒng)籌食物供給可持續(xù)性與穩(wěn)定性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4.2 實(shí)施差別化管控:剛性管制與彈性調(diào)控復(fù)合分區(qū)機(jī)制
當(dāng)前的耕地利用存在農(nóng)民非糧化種植監(jiān)管困難、食物生產(chǎn)收益與稀缺程度倒掛等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17]。因此,正視耕地“非糧化”中的合理需求,在不影響耕作層產(chǎn)能和糧食供給的前提下,遵循因地制宜、地盡其利、地盡其用的原則,通過(guò)優(yōu)化耕地用途管制分區(qū)并形成相應(yīng)的管制規(guī)則,以一定的優(yōu)先序引導(dǎo)耕地合理“食物化”利用,是解決糧食與食物、增產(chǎn)與增收之間的多重矛盾,實(shí)現(xiàn)食物的多元供給的有效途徑[23]。應(yīng)綜合考慮糧食安全底線(xiàn)和膳食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需求,在分析及預(yù)測(cè)人口數(shù)量、居民膳食結(jié)構(gòu)以及單位面積耕地產(chǎn)出水平變化的基礎(chǔ)上確定滿(mǎn)足“大食物需求”的糧食作物用地規(guī)模和非糧食作物用地規(guī)模,結(jié)合區(qū)域耕地資源稟賦特征和質(zhì)量綜合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劃定耕地利用的剛性管制空間和彈性調(diào)控空間,并明確分區(qū)分級(jí)的利用規(guī)則。其中剛性管控區(qū)域是穩(wěn)固糧食安全底線(xiàn)的基石,應(yīng)實(shí)施最嚴(yán)格的剛性管制手段,保持其規(guī)模與空間布局的長(zhǎng)期穩(wěn)定,確保優(yōu)質(zhì)耕地做到“良田糧用”;彈性區(qū)域是滿(mǎn)足食物安全需要的支撐,應(yīng)在確保耕作層質(zhì)量穩(wěn)定和糧食生產(chǎn)能力能夠及時(shí)恢復(fù)的前提下制定作物種植的正、負(fù)面清單,允許合理的“非糧化”需求,通過(guò)科學(xué)引導(dǎo)蔬菜、瓜果、糖類(lèi)作物等農(nóng)作物的種植進(jìn)行耕地的“食物化”利用,從而滿(mǎn)足居民的食物需求并拓寬農(nóng)民收入來(lái)源,兼顧口糧安全與食物多樣。
4.3 匹配激勵(lì)性措施:基于管控強(qiáng)度差異的耕地發(fā)展權(quán)補(bǔ)償機(jī)制
耕地剛性與彈性利用分區(qū)必然導(dǎo)致管制的強(qiáng)約束性與發(fā)展的公平性之間的矛盾,需要匹配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jì)激勵(lì)性措施以確保分區(qū)管制能夠真正落地。對(duì)耕地進(jìn)行剛性與彈性利用的區(qū)域劃分意味著對(duì)耕地的種植用途進(jìn)行差異化的行政命令式管控,其實(shí)質(zhì)是運(yùn)用公權(quán)力對(duì)私權(quán)利進(jìn)行約束以滿(mǎn)足最大的公共利益,蘊(yùn)含著政府部分、耕地利用主體之間目標(biāo)的不一致,這使得分區(qū)的種植管控目標(biāo)與實(shí)際的執(zhí)行存在偏離風(fēng)險(xiǎn)。糧食穩(wěn)產(chǎn)增產(chǎn)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區(qū)域內(nèi)權(quán)利主體的發(fā)展機(jī)會(huì)和增收潛力為代價(jià)的。處于耕地剛性管控區(qū)域內(nèi)的權(quán)利主體將面對(duì)最為嚴(yán)格的糧食作物種植管控,其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決策中的自由選擇權(quán)受到了約束,這使得耕地權(quán)利主體尤其是直接經(jīng)營(yíng)者缺乏配合耕地種植用途管制的積極性,甚至產(chǎn)生不滿(mǎn)情緒和抵觸行為。因此,應(yīng)當(dāng)高度重視耕地權(quán)利主體的關(guān)切,建立基于管控強(qiáng)度差異的耕地發(fā)展權(quán)補(bǔ)償機(jī)制,尤其是對(duì)糧食種植主體加大發(fā)展權(quán)受限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力度,提升耕地利用的區(qū)域公平性,以經(jīng)濟(jì)手段推動(dòng)耕地剛性與彈性利用分區(qū)及其所確立的種植用途管制規(guī)則的落地。具體實(shí)施過(guò)程中,對(duì)處于不同分區(qū)的耕地權(quán)利主體,可通過(guò)耕地承包權(quán)登記或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流轉(zhuǎn)登記,嚴(yán)格制定耕地種植用途的限制性措施條款,并借助耕地種植監(jiān)測(cè)、衛(wèi)片執(zhí)法等手段進(jìn)行持續(xù)監(jiān)測(cè)和定期評(píng)估。對(duì)處于種植用途嚴(yán)格管制區(qū)域且嚴(yán)格遵守措施條款的耕作主體提供相應(yīng)的發(fā)展權(quán)受限補(bǔ)償,反之則進(jìn)行教育制止并責(zé)令整改。通過(guò)為剛性彈性的差別化管控分區(qū)匹配相應(yīng)的耕地發(fā)展權(quán)補(bǔ)償機(jī)制,實(shí)現(xiàn)耕地利用的“責(zé)任+激勵(lì)”協(xié)同轉(zhuǎn)型路徑,助力口糧安全與食物多樣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4.4 提升利用效率:基于經(jīng)營(yíng)主體分類(lèi)引導(dǎo)的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機(jī)制
提升耕地利用效率是耕地?cái)?shù)量約束下保障食物安全的必然選擇,耕地利用效率變化是耕地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的重要考量。當(dāng)前我國(guó)耕地的經(jīng)營(yíng)主體呈現(xiàn)以傳統(tǒng)家庭農(nóng)戶(hù)為主,家庭農(nóng)場(chǎng)、專(zhuān)業(yè)大戶(hù)、農(nóng)業(yè)合作社、龍頭企業(yè)等新型經(jīng)營(yíng)主體并存的多元化結(jié)構(gòu),各類(lèi)經(jīng)營(yíng)主體在自身特征、生產(chǎn)模式、資源稟賦及利用能力方面的差異導(dǎo)致其耕地利用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并不一致,因此需要針對(duì)性的對(duì)不同耕地經(jīng)營(yíng)主體進(jìn)行分類(lèi)引導(dǎo),進(jìn)而從總體上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推動(dòng)耕地利用的隱性轉(zhuǎn)型。對(duì)于傳統(tǒng)家庭農(nóng)戶(hù)而言,考慮到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背景下耕作主體老齡化、受教育程度偏低、耕種規(guī)模偏小等問(wèn)題,可通過(guò)普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社會(huì)化服務(wù)和推動(dòng)耕地流轉(zhuǎn)等方式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對(duì)于家庭農(nóng)場(chǎng)、專(zhuān)業(yè)大戶(hù)而言,重在破除規(guī)模效率的約束,可通過(guò)政策扶持幫助其解決耕地利用過(guò)程中的資金不足、信貸困難等問(wèn)題,進(jìn)而縮小實(shí)際種植規(guī)模與最優(yōu)種植規(guī)模的差距,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對(duì)于由受教育程度較高、更年輕的職業(yè)化農(nóng)民群體組成的農(nóng)業(yè)合作社而言,應(yīng)當(dāng)完善融資制度體系和健全政策性農(nóng)業(yè)保險(xiǎn)體系,以降低金融貸款門(mén)檻和農(nóng)業(yè)運(yùn)營(yíng)風(fēng)險(xiǎn),為耕地利用效率提升“保駕護(hù)航”;對(duì)于龍頭企業(yè)而言,提升種質(zhì)資源研發(fā)與應(yīng)用能力、加快農(nóng)業(yè)全產(chǎn)業(yè)鏈培育、提升耕地的智能化數(shù)字化管理水平等則是提升耕地利用效率的重點(diǎn)。
4.5 轉(zhuǎn)變耕作方式:基于耕作行為激勵(lì)的可持續(xù)集約利用機(jī)制
面對(duì)有限耕地資源的約束,我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lái)不得不依靠以大量物質(zhì)投入為表征的集約化經(jīng)營(yíng)應(yīng)對(duì)持續(xù)增加的糧食需求,但這在提高糧食產(chǎn)量的同時(shí)卻引發(fā)了日益突出的環(huán)境問(wèn)題和生態(tài)損害,這些負(fù)面環(huán)境影響反而會(huì)在長(zhǎng)期趨勢(shì)上導(dǎo)致糧食產(chǎn)量增長(zhǎng)放緩或停滯以及農(nóng)產(chǎn)品質(zhì)量下降等問(wèn)題[34]。在當(dāng)前居民對(duì)食物多樣化、供應(yīng)增加、質(zhì)量提升與營(yíng)養(yǎng)均衡的復(fù)雜需求下,以耕地的可持續(xù)集約利用(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SI)替代傳統(tǒng)的集約利用逐漸成為共識(shí),即倡導(dǎo)以綠色、環(huán)保、可持續(xù)的耕作方式維持農(nóng)業(yè)的穩(wěn)定高效產(chǎn)出[19],促使有限的耕地資源可持續(xù)地提供食物生產(chǎn)功能,這為促進(jìn)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隱性形態(tài)轉(zhuǎn)型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為了調(diào)動(dòng)耕地利用主體主動(dòng)轉(zhuǎn)變耕作方式以實(shí)現(xiàn)耕地可持續(xù)集約利用的積極性,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勵(lì)措施。鑒于輪作、少耕、綜合害蟲(chóng)管理等不同耕作行為在不犧牲生產(chǎn)力的情況下抵消環(huán)境危害的潛力是不同的,故應(yīng)當(dāng)按照“誰(shuí)耕種、誰(shuí)獲激勵(lì)”的原則,對(duì)自愿改變耕作方式實(shí)施耕地可持續(xù)集約利用的各類(lèi)耕地經(jīng)營(yíng)主體,視其可持續(xù)集約耕作行為的行為類(lèi)別和實(shí)施水平的不同明確相應(yīng)的獎(jiǎng)補(bǔ)金額,推進(jìn)“高質(zhì)多補(bǔ)”的獎(jiǎng)補(bǔ)策略。通過(guò)建立耕作行為轉(zhuǎn)變的差別化激勵(lì)機(jī)制,充分調(diào)動(dòng)耕地利用主體進(jìn)行耕地可持續(xù)集約利用的主動(dòng)性和積極性,在耕地利用過(guò)程中做到經(jīng)營(yíng)集約化、產(chǎn)出高效化、資源節(jié)約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不退化[35],兼顧生態(tài)安全、生產(chǎn)發(fā)展、總量保障和質(zhì)量提升的多維目標(biāo)。
5 結(jié)語(yǔ)
本文分析了大食物觀視閾下我國(guó)耕地利用轉(zhuǎn)型面臨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闡釋了食物需求、食物安全目標(biāo)、耕地利用目標(biāo)以及耕地利用轉(zhuǎn)型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在此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由基于人口—資源—食物協(xié)調(diào)的布局機(jī)制、剛性管制與彈性調(diào)控復(fù)合分區(qū)機(jī)制、基于管控強(qiáng)度差異的耕地發(fā)展權(quán)補(bǔ)償機(jī)制、基于經(jīng)營(yíng)主體分類(lèi)引導(dǎo)的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機(jī)制、基于耕作行為激勵(lì)的可持續(xù)集約利用機(jī)制構(gòu)成的兼顧顯性轉(zhuǎn)型和隱性轉(zhuǎn)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路徑體系。本文認(rèn)為,探索大食物觀引領(lǐng)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路徑,是新發(fā)展階段食物安全目標(biāo)下耕地變化研究的重要命題。大食物觀是新發(fā)展階段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重要引領(lǐng),而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是踐行大食物觀的關(guān)鍵支撐,探索和實(shí)施多路徑協(xié)同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策略能夠促進(jìn)耕地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和大食物觀理念的落地,進(jìn)而服務(wù)于國(guó)家食物安全重大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大食物觀作為一種新的理念仍處于發(fā)展階段,本文就大食物觀視閾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理論邏輯和實(shí)現(xiàn)路徑進(jìn)行了初步討論,搭建了推進(jìn)轉(zhuǎn)型的輪廓性路徑體系,仍有大量的具體問(wèn)題和細(xì)節(jié)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如何刻畫(huà)當(dāng)前耕地利用現(xiàn)狀與大食物觀視閾下食物需求、食物安全目標(biāo)、耕地利用目標(biāo)之間的時(shí)空背離,如何對(duì)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各條路徑展開(kāi)具體的分析與設(shè)計(jì)從而為路徑的落地提供科學(xué)依據(jù)和技術(shù)支持,如何進(jìn)一步搭建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政策支持體系,使之與耕地利用轉(zhuǎn)型路徑形成系統(tǒng)性耦合,從而為大食物觀視閾下的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提供系統(tǒng)性的解決方案。此外,大食物觀“全方位多途徑開(kāi)發(fā)食物資源”的理念要求探索包括耕地資源在內(nèi)的各類(lèi)國(guó)土資源的合理和優(yōu)化利用,需要重塑?chē)?guó)土空間開(kāi)發(fā)與保護(hù)的新格局,因此,耕地資源如何與草地、林地、海洋等其他國(guó)土資源協(xié)同利用以支持大食物觀落地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大食物觀理念的提出對(duì)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上述命題亟待展開(kāi)研究以推進(jìn)耕地利用轉(zhuǎn)型的實(shí)踐,為踐行大食物觀和保障國(guó)家食物安全提供支撐。
- 中國(guó)土地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市場(chǎng)一體化測(cè)度及實(shí)證分析
- 確權(quán)抑制農(nóng)戶(hù)宅基地退出意愿了嗎
——來(lái)自川豫皖三省的微觀調(diào)查 - 武漢城市圈耕地利用變化驅(qū)動(dòng)機(jī)制研究
- 環(huán)保考核、政府環(huán)境注意力與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
- 土地資源空間錯(cuò)配的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損失效應(yīng)與作用機(jī)制
- 農(nóng)地流轉(zhuǎn)履約環(huán)境對(duì)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發(fā)展的影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