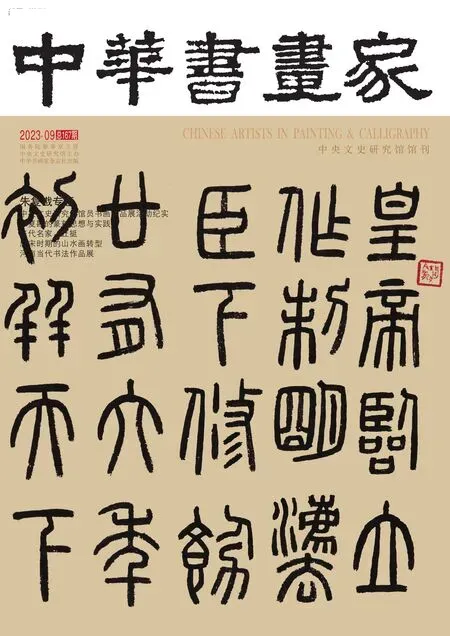潘天壽繪畫款識(shí)起源論研究
□ 陳 昭
款識(shí)藝術(shù)作為中國(guó)畫畫體結(jié)構(gòu)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化主題、豐富形式、拓展意境等功用。然而在一千多年的中國(guó)畫藝術(shù)的思想理論研究中,關(guān)于中國(guó)畫款識(shí)藝術(shù)起源的研究卻甚為稀缺,僅零星散見于畫史畫論中。潘天壽對(duì)中國(guó)畫款識(shí)藝術(shù)起源有著深刻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其《中國(guó)畫題款研究》《談?wù)勚袊?guó)傳統(tǒng)繪畫的風(fēng)格》《詩(shī)與畫的關(guān)系》《聽天閣畫談隨筆》《治印叢談》《關(guān)于“國(guó)畫與詩(shī)”的講稿》等文論、講稿以及與同道、學(xué)生、朋友的交談?wù)Z錄,皆包含著他對(duì)中國(guó)畫款識(shí)藝術(shù)起源研究和探索的思想結(jié)晶。文章通過(guò)梳理潘天壽相關(guān)畫理畫論,對(duì)潘天壽繪畫理論體系中關(guān)于繪畫款識(shí)起源的相關(guān)論斷進(jìn)行探研。
一、題榜—“屬其官爵姓名”
關(guān)于中國(guó)畫款識(shí)起源,潘天壽于《中國(guó)畫題款研究》一文中說(shuō):“中國(guó)畫的題款,究竟起于何代?無(wú)從詳考。從古籍稽查,大概起源于前漢時(shí)代。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曾在麒麟閣上畫《十一功臣像》。《漢書·蘇武傳》說(shuō):‘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①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就是依據(jù)十一人的形象描繪之后,再在每一幅畫像上都題寫上其姓名及官爵,從而表?yè)P(yáng)有功之臣之功績(jī)。可見款識(shí)發(fā)展之初,其功能性尤為重要。又如潘天壽所說(shuō):“故麒麟閣上圖寫的《十一功臣像》,在完成之后,必須題署每像的姓名及官爵,以補(bǔ)圖畫上功能之不足。這就是吾國(guó)繪畫上發(fā)展題款的最早事例與發(fā)展題款的主要原由。”②
這種題寫官爵姓名的形式就是漢代人物畫的題榜,題榜使得畫像身份一目了然,最終以起到表功頌德的功用。這也印證了唐張彥遠(yuǎn)于《歷代名畫記》中所說(shuō):“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cè)幽微,與六籍同功。……是時(shí)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chuàng)而猶略,無(wú)以傳其意,故有書,無(wú)以傳其形,故有畫。”③且張彥遠(yuǎn)又云:“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④可以說(shuō)正是因?yàn)閳D畫要達(dá)到“成教化,助人倫”,“存乎鑒戒”的目的,而由于圖畫本身的局限性則需要借助文字來(lái)完成圖像的表達(dá),漢畫題榜正隨之而產(chǎn)生了。亦可見繪畫作為政治、禮教的工具,題榜的意義十分重大。
《十一功臣像》這種書畫合璧的表現(xiàn)形式在當(dāng)時(shí)也絕非特例,由于漢代對(duì)賢者“表功頌德”的需求,地方政府也都紛紛效仿中央政府修建“麒麟閣”的做法,在《后漢書》的《胡光傳》《陳紀(jì)傳》《蔡邕傳》《方術(shù)傳》《南蠻傳》中都有相關(guān)記載。然而,由于時(shí)代久遠(yuǎn),漢壁畫能夠保存下來(lái)的極為稀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代壁畫如《河北望都漢墓壁畫》,就有隸書“門下小吏”的題榜。

山東孝堂山畫像祠之周公輔成王

后漢武氏祠石室畫像石之十一圖
二、畫題—“提綱挈領(lǐng)”
潘天壽把“屬其官爵姓名”的題榜又稱為畫題,言下之意,潘天壽認(rèn)為畫題亦起源于《十一功臣像》。其于《中國(guó)畫題款研究》一文又云:“又不論中西繪畫,作家在作畫之前,必然先有作畫的畫題及所配的畫材,然后下筆。用胸中先有的題材,畫成一幅繪畫以后,這幅畫的畫題,也就在這題材中了。故畫題往往在有繪畫之前,或與繪畫的題材,并時(shí)而生。例如‘十一功臣像’,目的在畫功臣,而每像的畫題,也就是這十一人的姓名了。十一功臣像,是總畫題,每像的畫題,是分畫題……使鑒賞畫的人,一知道總畫題及分畫題,就知道全畫的內(nèi)容了。畫的畫題可說(shuō)與文章的文題、戲劇的劇目、音樂(lè)的樂(lè)曲名稱,是完全相同的。”⑤
潘天壽還例舉了山東的孝堂山祠畫像石刻有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中立者為成王,形象幼小,左右分立周公、召公等十多人,成王像上方刻有“成王”兩字,潘天壽繼而表達(dá):“而在成王的立像上,刻有隸書‘成王’二字,以表明畫面上主題人物之所在,也就是表明畫題之所在。……中國(guó)繪畫,常常將提綱挈領(lǐng)的畫題簽寫到卷軸的包首上去,冊(cè)頁(yè)的面上,或畫幅的畫面上去,使畫題與畫面聯(lián)結(jié)在一起,作相關(guān)的啟發(fā)。題寫在畫面上的畫題,可以達(dá)到‘畫存題存’的目的,即流傳久遠(yuǎn),也少散失分割的流弊。”⑥
畫題移寫記錄十分方便,壽命遠(yuǎn)比繪畫悠久,至后世甚至畫作已經(jīng)損毀,畫題仍著錄于各古籍中,可供后人參考,可見古人之智慧。如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漢代張衡的《駭神圖》、魏晉時(shí)期曹髦所作的《新豐放雞犬圖》、衛(wèi)協(xié)的《楞嚴(yán)七佛圖》、梁元帝的《芙蓉蘸鼎圖》等皆為古籍所載,而這種記載均得益于畫題的存在,潘天壽認(rèn)為:“這全是我們祖先,對(duì)繪畫創(chuàng)作上作永久計(jì)劃的用心,絕不是毫無(wú)意義的將畫題題在畫面上,做隨便的涂寫。吾國(guó)繪畫,畫題的發(fā)展,由人像而到歷史故事,以及神圣、宗教風(fēng)俗等等,由人物而到山水、花鳥、蟲魚、走獸等等,可說(shuō)有一幅繪畫,就有一個(gè)畫題。”⑦
而畫題發(fā)展到唐代,由于詩(shī)歌與繪畫的結(jié)合,畫題亦逐漸寓有詩(shī)意。王維于《山水論》云:“凡畫山水,須按四時(shí)。或曰煙籠霧鎖,或曰楚岫云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冢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⑧據(jù)畫史記載第一個(gè)論述畫題的人是王維,唐以后花鳥畫的畫題與山水畫一致,亦有著詩(shī)意畫的傾向,潘天壽所言有題梅的“疏影橫斜”、題竹的“瀟湘煙雨”、題菊花的“東籬佳趣”、題鴨子桃花的“春江水暖”以及題荷花的“六郎風(fēng)韻”等,但元以前所論畫題多題于畫幅之外,正如其所云:“然吾國(guó)繪畫在元以前,各種畫題,雖也有寫到畫面上去,但大多數(shù)還是題寫在畫面以外的。到了宋代以后,始大通行題到畫幅上去。這也是吾國(guó)題款發(fā)展上的一種情況了。”⑨
依其所言,筆者通過(guò)搜索文獻(xiàn)及圖錄發(fā)現(xiàn)唐及五代題有畫題的作品雖多,但多為摹本或有爭(zhēng)議,亦多為他人或后人所題,且多不題于畫面之內(nèi),畫面內(nèi)題寫畫題且無(wú)爭(zhēng)議的作品至宋始有發(fā)現(xiàn)。宋代畫家自題畫題的作品最早可追溯到郭熙的《早春圖》《窠石平遠(yuǎn)圖》兩件作品,其分別題有“早春”及“窠石平遠(yuǎn)”的畫題。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為上品,無(wú)題便不成畫。”⑩可見,作畫立意為先的規(guī)律郭熙已有所論,命題即是立意,無(wú)意則無(wú)畫。作畫立意為先,前人于繪畫理論中對(duì)此亦多有重視,如清人笪重光于《畫筌》中云:“前人有題后畫,當(dāng)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wú)題,即強(qiáng)題而意索。”元代黃公望于《寫山水訣》亦有云:“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后著筆。若無(wú)題目,便不成畫。”以作品為例,宋代繪畫中,除了郭熙的《早春圖》《窠石平遠(yuǎn)圖》題有畫題之外,還有宋徽宗的《聽琴圖》《雪江歸棹圖》等亦于畫面之中題有畫題。可以看出,題寫畫題的款識(shí)形式始于漢畫,經(jīng)唐及五代的發(fā)展于北宋時(shí)期已較為普遍。
三、題畫贊—“長(zhǎng)款的遠(yuǎn)祖”
題榜、畫題之外,潘天壽認(rèn)為還有一種題畫贊的款識(shí)形式亦產(chǎn)生于漢代,其于《中國(guó)畫題款研究》中說(shuō):“又后漢武氏祠石室畫像石一之十一圖,刻有‘曾參殺人’故事,如圖二,在圖的左上角刻有曾參的贊語(yǔ)說(shuō):‘曾子質(zhì)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號(hào)來(lái)方,后世凱式,以正橅綱’,這就是吾國(guó)繪畫上題長(zhǎng)款的遠(yuǎn)祖了。”
潘天壽認(rèn)為贊語(yǔ)所贊為曾參,目的是說(shuō)明曾參絕不會(huì)殺人的事實(shí),曾母聰慧賢明,臨事不疑,但亦未能抵御讒言三至的威力,投杼而走,足可說(shuō)明讒言之厲害。又題以“讒言三至慈母投杼”的說(shuō)明,使得畫面的故事情節(jié)及主旨更為清楚。“此種情況,在漢畫像中所常見的事件。武氏祠石刻中一之十二的‘閔子騫’,一之十三的‘老萊子’,一之十四的‘丁蘭’,一之十六的‘專諸’各圖上,均刻有故事說(shuō)明的文字,與一之十一‘曾參殺人’的故事,完全相同。”可見,題畫贊在漢石刻畫中已極為流行,成為一種普遍的樣式。
縱觀漢代繪畫史,畫功臣烈士像已經(jīng)形成一種社會(huì)風(fēng)氣,王允的《論衡·須頌》中有云:“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漢代石刻畫在表彰功勛的實(shí)用性功能方面,由于題榜的局限性,某些時(shí)候顯得有些不夠充分,所以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的石刻畫在“屬其官爵姓名”的題榜形式以外,逐漸發(fā)展出了另一種不同于題榜的早期繪畫款識(shí)形式“題畫贊”。劉勰的《文心雕龍》有云:“贊者,明也,助也……容德厎頌,勛業(yè)垂贊”劉勰認(rèn)為贊與頌都是一種文體,“贊”的本意是說(shuō)明與輔助的意思,因功勛業(yè)績(jī)的流傳需要因而有了“贊”。王伯敏在《中國(guó)繪畫通史》中說(shuō):“這些壁畫,據(jù)蔡質(zhì)在漢宮典職中提到,在繪制形式上,似有一定的規(guī)格,如說(shuō)‘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贊’等。”“畫古烈士,重行書贊”有畫有書,書畫結(jié)合,從理論上講,漢畫中的“贊”必然跟款識(shí)有著血脈上的聯(lián)系。而且相較于題榜,題畫贊內(nèi)容更加豐富,不僅具有點(diǎn)明畫像人物身份,說(shuō)明畫像內(nèi)容的作用,更主要目的是對(duì)“屬其官爵姓名”的題榜以外的畫面內(nèi)容進(jìn)行補(bǔ)充和豐富,也正是潘天壽所認(rèn)為:“這就是吾國(guó)繪畫上題長(zhǎng)款的遠(yuǎn)祖。”
四、題畫記—“題與畫,互為注腳”
題畫記對(duì)于畫作多有記述功用,其內(nèi)容包括畫面內(nèi)容、畫家行蹤、作畫緣由以及情感的表達(dá)與抒發(fā)等,關(guān)于“題畫記”的起源問(wèn)題,潘天壽相關(guān)繪畫款識(shí)思想中亦有論及,其云:“明沈?yàn)懂媺m》說(shuō):‘題與畫,互為注腳’。吾國(guó)繪畫的題寫,銘贊詩(shī)文,為畫面上的注腳以外,尚有與畫面有關(guān)的記事題語(yǔ),以記明作畫的目的,當(dāng)時(shí)的情況,技法的心得,以及與畫幅有關(guān)的種種,例如五代黃筌的《珍禽圖》(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畫有珍禽及大小間雜的昆蟲,在左下角題有‘付子居寶’的一行字,這也是一個(gè)較早的例子。”
據(jù)《宣和畫譜》記載,著錄時(shí)黃筌的作品多達(dá)三百四十九件,但流傳至今且傳承有序的真跡的僅有《寫生珍禽圖》一件。其畫面繪有昆蟲、飛禽、烏龜?shù)葎?dòng)物二十余種,筆法工細(xì),設(shè)色柔和,寫生感強(qiáng),功力深厚。傳系黃筌為其次子居寶所作范本,以供其參考學(xué)習(xí)。但此圖并無(wú)名款,“付子居寶習(xí)”五字款乃是表明畫作用途及作畫目的題畫記款,后人對(duì)于此款雖有爭(zhēng)議,但亦無(wú)確鑿證據(jù)證明其為偽款。
“中國(guó)畫的題款,究竟起于何代?”潘天壽設(shè)問(wèn)自答,分別論述了題榜、畫題、題畫贊及題畫記等款識(shí)形式的歷史起源,最后總結(jié):“《畫塵》所說(shuō)的‘題與畫,互為注腳’,此意極是。這就是中國(guó)繪畫,由畫題及簽署官爵發(fā)展到銘贊、詩(shī)詞、長(zhǎng)記短跋的淵源,可說(shuō)非常的長(zhǎng)久了。”
五、潘天壽款識(shí)起源研究補(bǔ)遺
筆者發(fā)現(xiàn)先秦繪畫中的一件《楚帛書》似乎與中國(guó)畫及款識(shí)亦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楚帛書》出土于湖南長(zhǎng)沙楚墓。“帛書”亦稱作“繒書”,據(jù)考證,《楚帛書》為1942年于子彈庫(kù)楚墓被盜而出,現(xiàn)藏于美國(guó)紐約大都會(huì)藝術(shù)博物館。此帛書長(zhǎng)38.7厘米,寬47厘米,《楚帛書》中書寫約900字,互為顛倒方向排列。王伯敏對(duì)《楚帛書》曾有過(guò)描述:“繒書四方形,中間寫有墨書(斷片中也有朱書),筆畫勻整。四周畫有圖像,以細(xì)線描繪,上圖彩色。四角畫樹木,分青、赤、白、黑四種,以象征四方、四時(shí)。每邊還繪有12個(gè)詭怪形像,當(dāng)是代表春夏秋冬的季節(jié)神。……這種隨葬的繒書是一種巫術(shù)性的東西,但也與天象有關(guān),可能為死者‘鎮(zhèn)邪’之用。”
正如王伯敏所說(shuō),楚帛書上的圖像及諸多說(shuō)明文字記述了災(zāi)異與天象的聯(lián)系,涉及四時(shí)及晝夜的形成神話及伏羲、炎帝、祝融、共工等人物傳說(shuō)。《楚帛書》帛書除四角分別繪有青、赤、白、黑四色的樹枝狀植物外,帛書四周還繪有形狀怪異的十二月神像,每一月神像配一段文字記述,記載每月的宜忌。關(guān)于其文字書法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中指出其字體具有“體式簡(jiǎn)略,形態(tài)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隸書”的特點(diǎn)。
一方面,從時(shí)間上講,《楚帛書》是目前我國(guó)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書法與繪畫相結(jié)合藝術(shù)作品,并表現(xiàn)同一主題內(nèi)容,堪稱中國(guó)繪畫藝術(shù)中書畫結(jié)合的濫觴。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鐘鼎款識(shí)是款識(shí)藝術(shù)的最初萌芽的話,那么,《楚帛書》應(yīng)該就算是繪畫款識(shí)藝術(shù)可追溯到的最早狀態(tài)了。另一方面,從材料上講,《楚帛書》所繪動(dòng)植物及書寫文字,工具皆為堪稱文房四寶之首的毛筆,而且所用畫材“帛”亦是后人所說(shuō)的“絹帛”的一種,是繪畫最早使用的一種材料之一。《楚帛書》的出現(xiàn),使得文字與繪畫的結(jié)合在工具與材料上具有了統(tǒng)一性與一致性,其在考古界是史無(wú)前例的發(fā)現(xiàn),雖然不排除以后可能會(huì)有更多更早的發(fā)現(xiàn),但根據(jù)已發(fā)掘的《楚帛書》我們可以看到那個(gè)時(shí)代的楚國(guó),毛筆所書寫的文字與毛筆所繪制的圖像兩者之間的結(jié)合已經(jīng)存在。以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為依據(jù),周積寅、王鳳珠的《中國(guó)歷代畫目大典》所收錄的先秦帛書、帛畫僅有四件,其中《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并沒(méi)有文字出現(xiàn),《馬王堆1號(hào)墓帛畫》損毀嚴(yán)重且多有黏連,僅見有墨痕,畫面難以辨認(rèn),僅有《楚帛書》具有文字圖像相結(jié)合的形式。總之,在先秦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楚國(guó),書畫的結(jié)合形式已經(jīng)存在,《楚帛書》的出土對(duì)于研究中國(guó)繪畫款識(shí)的萌芽與起源有著十分重要的史料價(jià)值。

[五代]黃筌 寫生珍禽圖 絹本設(shè)色 故宮博物院藏
鑒于《楚帛書》的重要性,那為什么潘天壽在追溯款識(shí)起源時(shí)卻視而不見,且同樣有著書畫結(jié)合性質(zhì)的漢代《帛書云氣占圖》及《帛書導(dǎo)引圖》潘天壽為什么亦未提及呢?經(jīng)過(guò)筆者考證發(fā)現(xiàn),《楚帛書》最初為盜掘,時(shí)間雖早但為人所知的時(shí)間卻較晚,《楚帛書》被盜于1942年(子彈庫(kù)楚墓于1973年發(fā)掘),國(guó)人對(duì)于楚帛書的存在知之甚少,直到1982年才有中國(guó)研究員在美國(guó)紐約大都會(huì)博物館見到展出的《楚帛書》原件,并測(cè)量尺寸,而在1971年潘天壽就與世長(zhǎng)辭,離此時(shí)已有11年之久。比《楚帛書》稍晚,同樣有著書畫結(jié)合性質(zhì)的馬王堆三號(hào)漢墓出土的《帛書云氣占圖》和《帛書導(dǎo)引圖》考古發(fā)現(xiàn)的時(shí)間則為1974年,離潘天壽辭世亦有三年之久。且《中國(guó)畫題款研究》一文寫成于1957年,限于時(shí)代原因,潘天壽生前并未聽聞《楚帛書》及漢代帛書相關(guān)史料應(yīng)屬事實(shí)。
注釋:
①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3年,第119頁(yè)。
②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第120頁(yè)。
③俞劍華《中國(guó)古代畫論類編》(上),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8年,第27頁(yè)。
④俞劍華《中國(guó)古代畫論類編》(上),第28頁(yè)。
⑤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第120-121頁(yè)。
⑥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第121頁(yè)。
⑦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第121-122頁(yè)。
⑧俞劍華《中國(guó)古代畫論類編》(上),第597頁(yè)。
⑨潘天壽《潘天壽美術(shù)文集》,第123頁(yè)。
⑩俞劍華《中國(guó)古代畫論類編》(下),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8年,第776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