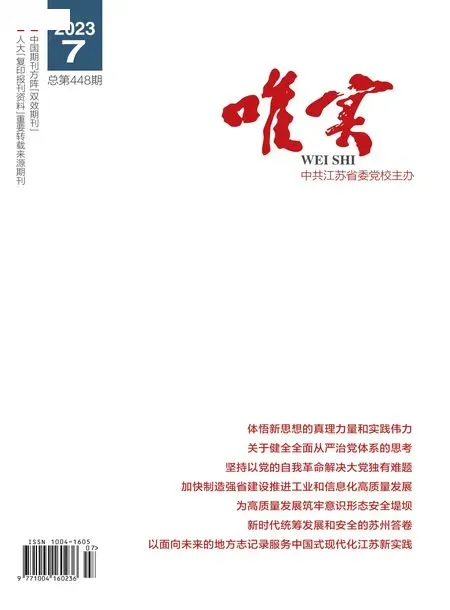明清時期的蘇州會館
劉維榮

唐宋以后經濟重心南移,蘇州“風物雄麗為東南冠”。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是維系國家經濟運轉的大動脈,而地處大運河要沖的蘇州依靠得天獨厚的水運優勢,雄踞全國商貿城市前列。此時的蘇州更被譽為“天下四端”之一,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云:“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足見蘇州被納入國內最繁華的城市之中,成為天下商業大都會。
一、明清之際蘇州會館的繁榮
(一)商業繁華的地緣條件
明中葉,蘇州才子唐伯虎寫過一首《閶門即事》:“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賣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詩中描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富商巨賈操著不同的方言通宵達旦地進行巨額交易的情景,更是形象地描繪了各地商人在蘇州從事貿易的繁忙情景。唐伯虎的父親在閶門皋橋開過酒店。因此,他的詩應是蘇州當時商業繁盛、貿易發達、經濟繁榮的真實寫照。
明、清時代的蘇州,不僅是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城市,也是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口岸。“其各省大賈,自為居停,亦曰會館,極壯麗之觀”,并最終在全國確立了四大中心之一的地位。明中葉至清同治、光緒年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行業競爭的加劇和不同區域經濟、文化交往的日趨頻繁,各大城市紛紛建立了一種地緣性的社會化群體組織——會館。值得一提的是,其繁衍之廣、影響之大,幾乎成為明清社會的時尚,客觀上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間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蘇州得益于極為優越的地理交通位置,加之繁華的商品經濟,亦成為人們心中向往之地。對此,《陜西會館碑記》作了高度概括:“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上自帝京,遠連交廣,以及海外諸洋,梯航畢至……此會館之建所宜亟也。”另有“姑蘇為東南一大都會,五方商賈,輻輳云集,百貨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貿易于斯者,莫不建立會館”。
(二)工商管理碑刻的見證
1959年,江蘇省博物館編纂的《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共收碑刻370件,其中蘇州一府就達322件。1981年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的《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共收碑刻258件。上述兩本資料集共收錄有關蘇州的碑刻資料400多件。根據碑刻集和有關地方文獻所載,蘇州及所屬城鎮一帶會館多達64所,不僅在江南為最多,而且在全國的同類地方城市之中也是最多的。蘇州的眾多會館分布在大運河以及它衍生出的水網之中,無論是仇英的《清明上河圖》還是徐揚的《盛世滋生圖》,都能看見沿岸“帆檣如云、游人如織”的熱鬧景象。那是來自天時的江南美景,是得于地利的姑蘇繁華,也是占盡人和的蘇州風雅。

蘇州碑刻博物館和蘇州所轄縣(市)的文博機構,現珍藏清代工商業碑刻約250塊,內容涉及絲綢刺繡業、棉布洋布業、造紙印刷業、土木建筑業、木器制造業、油漆業、銅錫鐵器業、金銀珠寶業、金融典當業、雜貨百貨業、糧食業、南北貨業、醬油菜櫥面餅業、柴炭煤燭業、漁業、煙草業、生活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18個大類,其數量之多、種類之全,居全國之首。這些工商業碑刻,大多數為全國各地商人和作坊主在蘇州建立會館時所立,少數為地方官府所立。
二、明清會館創設的文化心理
(一)個體對組織的社會化需求
會館作為同鄉人自發組織、捐資、置地而建起的社會性組織,在客觀上有利于同鄉經營者樹立行業優勢,減少經營風險,并且更容易結成利益整體,通過地域紐帶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康熙年間,楓橋的洞庭西山販米商日以百數,由于不堪牙行的盤剝而聯合起來建立了洞庭會館,取代了牙行的作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岡州會館坐落于蘇州著名的千年古街——七里山塘東首,康熙十七年(1678年)為義寧(今桂林)商人所創建。會館富有蘇州私家園林特色布局,典雅精致,內有小橋流水、亭臺樓閣,移步換景,寧靜舒適,堪稱山塘街明清會館建筑的典范。
蘭溪人戴曦則是這樣表述在蘇州創立金華會館的目的:“雖蘇之與婺,同處大江以南,而地分吳越,未免異鄉風土之思,故久羈者,每喜鄉人戾止,聿來者,唯望同里為歸,亦情所不能已也……為想春風秋月,同鄉偕來于斯館也,聯鄉語敘鄉情,暢然藹然,不獨逆旅之況賴以消釋,抑且相任相恤,脫近市之習,敦本里之淳,本來面目,他鄉無間,何樂如之。”陜西會館位于金家弄口的山塘街508號,又稱全秦會館、陜甘會館、雍秦會館和雍涼公墅。陜西會館為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建,歷時四年完工。史茂在蘇州《新修陜西會館記》中表達了完全同樣的意思:“余惟會館之設,所以聯鄉情,敦信義也。吾鄉幅員之廣,幾半天下,微論秦隴以西,判若兩省,即河渭之間,村墟鱗櫛,平時有不相浹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鄉音方語,一時靄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約而同于心。加以歲時伏臘,臨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鋪,歡呼把臂,異鄉骨肉,所極不忘耳。”
(二)地域性的商幫組織
會館主要是以地緣(籍貫)為紐帶,“會館之設,所以答神庥,睦鄉誼也”,“凡吾郡土商往來吳下,懋遷交易者,群萃而憩游燕息其中”,“各省郡邑貿易于斯者,莫不建立會館,恭祀明神,使同鄉之人聚集有地”。
最初,會館以同一地區旅蘇商人的集結為多,不分行業。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由同一地區同一行業的旅蘇商人組成工商行業的會館,大興會館為江蘇各府的木商幫,毗陵會館為常州的豬商幫。其最初作用重在“聯鄉語、敘鄉情”。后來隨著經貿活動的發展,又逐步成為商人們存放貨物、居住和議事的重要場所。“凡彈冠捧檄,貿遷有無而來者,類皆設會館,以為停驂地”。如光緒時的兩廣會館,是因為士商往來于蘇州,無處寄身,因此才興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鄉人至者,上棟下宇,得有所托”。
當然,還有一些已經突破地域界限,完全按照行業建立的會館,如藥行會館、靛行會館(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靛行會館碑記》稱:該館始建于嘉慶十五年,為山東、河北、山西等省藍靛商人和染坊共建)。
三、明清時期蘇州會館的功能價值
會館作為一種商業組織,廣置樓閣、多蓋屋舍的目的,很大程度是為同鄉、士紳、商旅駐足和貯存貨物提供方便。“查商賈捐資,建設會館,所以便往還而通貿易。或貨存于斯,或客棲于斯,誠為集商經營交易時不可缺之所”。使“士、商之游處四方者,道路無燥濕之虞,行李有聚處之樂”。作為外地前來的行商,迫切需要在他鄉穩定立足,從而滿足互助互濟之需,聯結同鄉之誼,增強團體自保自衛力量,撫恤同鄉或同業中的鰥寡孤獨、老死廢疾者。蘇州會館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層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鄉人互助的公益價值。蘇州會館設置后紛紛興起有利于同鄉的各種善舉。如對老弱失業者提供救濟,對傷殘病痛者給予醫療,對客死異鄉者供給殯舍,對無力歸葬者代為掩埋等等。有的更設立義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機會,或興建義渡、碼頭,方便經營者的運輸往來。陜西會館的普善堂、東越會館的公善堂、新安會館的積功堂、湖南會館的澤仁堂等都是為同鄉提供各種慈善服務的機構。不僅如此,一些會館本身就是先襄義舉,而后創建會館的。會館是辦理善舉與辦事會議之所,它的善舉對象是同鄉,從而為工商業者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障,強化了同鄉同行的凝聚力。
溝通信息的商業價值。會館作為行業的議事機構,推舉議董,訂立行規。如,錢江會館為杭州綢業商幫所建于蘇州,販運大批綢緞來蘇經營批發業務。東越會館是紹興蠟燭業商的燭業行幫會館,當時全蘇州的蠟燭行業全部由紹興人把持,目的就是保護紹興人的利益。位于蘇州舊城平江路張家巷的全晉會館(又稱山西會館)興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為旅蘇晉商們交流商情、相互借貸、調劑資金的洽談場所。據《清高宗實錄》記載:“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者,多系晉省人。”大量的山西商人來到蘇州,由于語言交流的困難以及蘇州地區越來越激烈的商業競爭,山西商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商業利益,于是便廣泛聯絡,共同協商,合力對外。如今,全晉會館早已演變成了昆曲博物館,占地面積約6000平方米,是蘇州現存會館中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富商巨賈,會館的大量涌現加強了蘇州地區與全國其他地區經濟與文化的聯系,對江南經濟社會的發展起了催化和推動作用。同時,這些會館的設立起到了鼓勵競爭,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有利于我國沿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