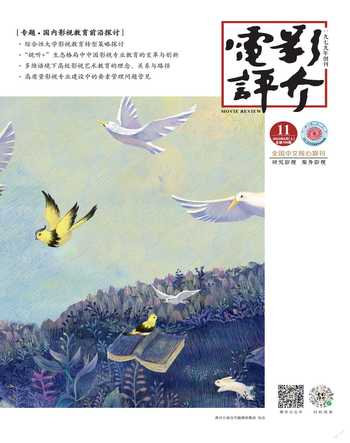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轉型策略探討
人類社會從文字時代、讀圖時代演進到視頻時代,影視傳媒越發廣泛和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技術的更迭促生著影視藝術的面貌持續更新。除了專業影視院校之外,中國很多綜合性大學也都開設了影視傳媒或影視藝術的相關專業,且數量占比遠超前者。
然而,中國綜合性大學的影視教育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是原有問題依舊明顯;二是現行的教育觀念和模式并不能滿足新形勢與智能時代的要求。關于第一點可以看到:在很多綜合性大學中,教育資源向其他重點學科和專業傾斜,影視學科相對被忽視,發展空間受限;影視學科現有教師中的一部分來自其他專業背景,難以深入、精準地講授專業課程,尤其在創作執行層面缺乏經驗和專業規范性;史論和鑒賞類專業課程實力較強,實踐課程的設置則未形成相對健全的系統,而且課程周期偏短,課時量較少,技術保障不足等等。關于第二點,涉及國家創新戰略在教育界的落地、影視傳媒方向專業碩士和專業博士的擴招等趨向,同時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對教育的轉型提出迫切要求。基于此,本文擬從以下五個方面對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轉型的策略展開探討。
一、重尋學科突破口
雖被稱為“象牙塔”,大學卻從未能夠離開國家和民族的大命運、國際國內的大環境而孤芳自賞、閉門造車,影視學科亦是如此。新舊困境和壓力之下,綜合性大學的影視教育整體上需要“有破有立”。對于處于時代風口的諸多教育單位而言,又常常是“先破先立”。當然,不是為了破而破,而是要從影視學科所涉及的諸多門類和分支領域中找準長遠發展的發力點。這關乎未來一段時間內學科方向的重新定位和路徑的重新開辟。在精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學科的調整不一定要面面俱到,求全求大,錯位發展、精準突破反而可能是一個優選項。在實事求是地分析過影視學科的家底兒和可整合利用的外部資源,并充分研判國家、社會和行業的需求趨勢的情況下,以全行業、全國乃至全球的視野來審視學科到底該干什么、不干什么,順應情勢,完善自身,增強規模實力,打造獨具特色優勢的專屬“品牌”。比如紀錄片重在人文素養和觀察社會問題的視角與反思,如果影視學科有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聯姻”機會,不妨考慮將紀錄片的研究和創作作為“拳頭產品”來建設;如果有條件將VR(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AR(Augmented Reality,增強現實)等新技術、新產品納入“產學研用”的鏈條,則不妨著重嘗試新媒體方向,等等。此外,也可以考慮拿出一部分資源開拓全新的領域,勇于試水,占領先機,在探路過程中逐步做大做強。
特別需要警惕“能力陷阱”問題——因為“我們很樂于去做那些我們擅長的事。做得越多,就越擅長,越擅長就越愿意去做……它還會讓我們產生誤區,讓我們相信我們擅長的事就是最有價值且最重要的事,所以值得我們花時間去做”。[1]影視學科需要膽識突破現有思維的限制,跳出受限視野和舒適圈,勇于觸碰未知,提高容錯率,并學會從波動中受益,在新的教育生態中找到或重塑自己的生態位。
二、加強創新人才培養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2]作為立國之本和強國之基,教育的自主、全面、系統創新已被提上日程。從“0”到“1”的創新遠比從“1”到“N”的標準化批量生產更為不易。柯政、梁燦兩位學者曾指出:“經過多年發展,我們在一般性人才培養上,積累了很多經驗,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但在培養杰出人才、拔尖創新人才上,我們無論是在思想、理念、制度、方法還是成效上,都相對缺乏。我國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國際優質教育資源。或者簡單說是,通過國際大循環完成的。”[3]在影視教育上,中國長年落后于歐美的一些國家,在原創性的技術發明和藝術實驗方面成果稀少,這與現行的教育體制和培養機制不無關系。健康有活力的影視教育理應鼓勵學生的好奇心、質疑態度和冒險精神,容忍更多的不確定性。唯有提升學生的競爭力,影視學科在行業的競爭力才有保證,中國的影視文化在國際上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才能得以有更大提升空間。
傳統的大學教育強調對學習時間和學習內容的高密度控制,比如設置大量的必修課(因為學分的要求和課程選擇范圍的限定,某些選修課其實也等同于必修課)。缺乏選擇性和跨學科性,掌握的知識千篇一律,在深度和廣度上拓展有限,造成的結果就是:讓擁有雷同能力的學生在同一個賽道上進行同質化的“內卷”,而不是讓他們能夠差異化共生于一個健康生態中。這種情況對有藝術天分和專業熱情的學生造成的傷害尤甚,而創新人才和拔尖人才往往有望誕生于這部分學生。
依靠封閉性的統一規則來維持受教育者的順從、就范不是教育的本意。每個學生都有自身的獨特之處,合格的教育者應當善于發現受教育者的個體差異,并因材施教,給予其適時適度的激發、引導和助推,讓不同的花朵結出不同的果實。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1983年出版的《智能的結構》(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書中,從心理學家的視角出發,首次提出并著重論述了多元智能理論(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基本結構。他認為每個人身上都相對獨立地存在著與特定的認知領域或知識范疇相聯系的多種主要智能包括語言智能①、音樂智能②、邏輯-數學智能③、空間智能④、身體-動覺智能⑤,以及人的認知智能⑥,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優勢組合。[4]在學生的影視創作實踐中能夠發現:語言智能突出的學生對劇作和策劃比較擅長,空間智能和“身體—動覺”智能較強的學生則更適合做攝影師,人際智能和“邏輯—數學”智能較強的學生更能夠勝任劇組的制片工作,等等。除了智能特質之外,每個學生的心性和興趣所在亦會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學生喜歡創作,而有的學生可能就是對理論研究更有熱情,等等。由此,可以通過設置進階性質的選修課、組織專題性質的工作坊等方式對學生進行分流或輔助,讓他們專注于做自己更喜歡、更擅長的事,包括磨練一些非標準化的技能和尋找一些非標準化的賽道,使他們盡量開發出自身獨特的潛能。
在大學畢業生與用人單位供需不平衡的時勢之下,社會將會越來越在乎受教育者的能力而非學歷。這里的能力既包含專業能力,也包含綜合能力。影視從業者的視聽思維和影視創作等專業能力需要在符號經驗和一手經驗的反復轉換和印證中加以培養。除了在相關課程中強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也不妨鏈接各種外部社會資源,比如設備生產/租賃商、影視技術研發/推廣機構、媒體公司、文旅部門、創作基地、電視臺、網絡平臺等,從器材保障、技術指導、營銷推廣到播出展映的上中下游都進行“開源”,讓更多的“支流”注入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的大江大河。此外,通過組織動員學生參展、參賽,或推薦實習、就業和參與影視項目,讓學生得以增進見識,培養自信,在各種“現場”的具身體驗中實現對專業知識技能全面、深入的理解與內化,習得“默會知識”⑦并能有效輸出應用,創造性地解決多種多樣的具體難題。
多學科的人文熏陶和積累是綜合性大學得天獨厚的優勢,對于學生開闊創意視野、樹立價值觀很有幫助。在當下的時代環境下,綜合性大學培養的影視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全媒體就業和自主創業,而不再局限于電影、電視這樣的傳統主流媒體,未來的他們無論是成為職業媒體人或是使用媒體的個人,他們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養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整個社會。因此,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環境條件,提升學生的審美、情操和表達能力,塑造學生向善、向美、向真的觀念,健全的人格,良好的適應能力和永續成長的意識,而非僅僅傳授一些固化的知識和技能,才是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守正創新的要義。如此,才能將學生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暢達地嵌入社會需求,為學生實現一生的幸福和價值奠定基礎。
三、主動對接新的智能時代
隨著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產品的推出,越來越多可被模仿、可被計算和重復操作的常規工作迅速被AI工具精簡和替代。人類社會的發展有望進入新的“奇點”①,以歸納總結、知識輸入為主的傳統教育模式面臨著被顛覆的可能。[5]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影視教育也必須直面厘革。目前,AI工具自動生成的數字影像幾已亂真,從前期到后期,從劇本創作到特效,影視制作繁瑣的工作流程越來越多地能夠被人工智能軟件高效完成。但務必清醒地認識到:AI替代的是工作而非是人。無論是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都不妨積極借助新的智能工具進階,做一個善于與AI合作的人,嘗試藝術與技術的新型融合。
在提出“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看來,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區分不同社會形態的標志。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社會生活和社會行為的新方式。而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響人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因此,對于社會來說,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媒體所傳播的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及帶來的社會變革。[6]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更善于“回答問題”和“解決問題”,而由誰來“問問題”就顯得尤其重要。一個優質的提問者才有可能問出對的問題和好的問題,何況提問者與人工智能的溝通、互動內容也將成為AI訓練的語料,從內部滋養其進化。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影視專業人才不僅需要有聰慧的頭腦,廣博的見識,完善的人格,開放、包容的心態,而且需要具備較強的感受力、審美力與原創意識——這是AI所不擅長的,掌握工具的人如果同樣缺失,在與人工智能的合作中就容易變成工具的附庸。基于此,綜合性大學影視專業教育宜有意強化學生的審美感知能力與田野調查能力,通過一些能夠針對性、系統性提升藝術感知力和增益原生體驗的實踐課程(比如訓練視聽乃至全感知覺的課程和實地勘景、搜集素材的游學活動),將人之所以為“人”的部分放大。在人把握主動權的前提下,人與工具各歸其位。
在這個復雜性呈指數級增長的年代,單一學科的邊界容易限制視野甚至人格,通識教育、素養教育和跨界學習的重要性日漸凸顯。而身處綜合性大學中的影視學科在這方面更具先天優勢——本專業之外的其他學科資源近在眼前,俯拾即是,而且多有經年的人文沉淀和學理氛圍,更利于學生從擅長單一能力變為復合型創作者。現在,有效借助AI工具的賦能,知識版圖的拓展和技能的增益從未如此簡單。在不遠的將來,一個具有跨界思維與綜合能力的影視專業學生可以聚焦于寫作、拍攝、制作等單項工種,還有可能兼顧全媒體采編、社群運營、文化項目策劃等,這樣的影視人才在未來更不容易被取代和淘汰。
四、更新媒介教育和媒介素養教育
媒介社會是經由媒介建構的擬態社會。在媒介社會里,每一個人都無法游離于媒介之外,在自我的形象建構和社會關系中盡是媒介的鏈接和投射。在媒介過度發達的當下,又遇新的人工智能崛起,前所未有的狀態正在顯現。
影視專業人才是塑造當下媒介文化的有生力量甚至是中堅力量。新的媒介文化反過來又會將裹挾其中的個體和群體進行沉浸式的塑造——從情感到價值觀,從日常生活模式、市場規則到意識形態。能夠清醒洞見媒介運作的底層邏輯和勘別真相的基本素養,仍然是今天和未來的媒介從業者所應具備的。媒介形態的更迭呼喚著新的媒介教育和媒介素養教育。
雖則AI披著聊天的“外衣”將自己擬人化,但其終究是假扮出的情智一體。眼下的AI所擅長的仍然是虛擬的網絡所及的疆域,其“成果”多是基于以往的理論、概念和既有模型、物料的仿制衍生品,是通過搜索和統計的結果及多點勾連的整合來提供應然的答案。這個自帶“算法黑箱”的新生力量能夠以遠超人類的效率將諸多事情化繁為簡、高質完成,在其幼年期給人類造成新的“文化休克”。如果人類任由其自由迭代和全面滲透,AI大面積接手媒介社會,進而主導人類思考的范疇、路徑、方向、方式只是早晚的事。而長期沉浸在媒介符號環境中學習的人,極有可能越來越像其賴以學習和掌握信息的工具而不自知,在與AI的雙向奔赴中,離“現場”越來越遠。當人們的一手經驗日漸缺失,發現和體驗真實之美的能力就會不斷弱化,甚至表達美的方式也是二手的,何以釋放個體獨特的創造潛能?當人機擬態交流大量替代了基于真實情境和親身經歷的人際交往與情感互動,再憑借算法推薦、“信息繭房”一步步固化個體的知識背景和思維模式,人就會被物化,被作為分工的“對象”而非秉持自主性的“主體”,換句話說,就是被自己的發明物架空和反噬。
智能工具是人類思想與能力的放大器,它可以將真、善、美的東西放大,也可以將假、丑、惡的東西放大。近年來,諸多媒介和AI產品背后隱藏的價值觀令人擔憂。無論是源于商業利益或是小我的驅動,媒介和AI產品及其內容所引發的上癮、焦慮、懈怠、虛榮、撕裂、消費主義、虛無主義……正侵擾著人們的精神文化空間。同時,在科學技術的理性張揚之際,藝術的力量正在坍縮,人類社會亟待建立新的平衡。
影視人才作為媒介社會文化產品的重要創造者、傳播者和把關人,尤其需要對新的媒介生態和運行規則具備通透的認識,以及從容應對的能力和素質。在綜合性大學的影視教育中,這是不應該也不能被忽視的。
人的注意力資源是有限的。當下,嚴重的信息過載導致社會人群越發普遍的心理健康問題,處于成長過渡期的大學生尤甚。他們中的一些習慣在媒體上獲取信息和娛樂,而現實中的人際交流則相對缺乏,難免陷入孤獨、麻木和冷漠;他們不斷被各種來源的新信息打斷,在頻繁的任務切換中效率下降,快速耗盡精力和專注力,又苦于不能以正常的傾訴和行動排解,精神內耗和渙散已成為常態。在碎片化的信息汪洋中樹立燈塔、規劃航線,引領航程,首先需要教育者對自身在當下的形象角色有正確的認知。教育是為了培養服務社會、推動社會進步的人才,而人才首先是“人”。教育不僅要讓人成“才”,更是要讓人成為“人”。世界本來是全息的,人本來是全感的,只有在身處現場的真實接觸和真誠互動中,人才能保持具身體驗的敏感與直覺反饋。很多真知和感動也只有在充滿未知的路上和生動鮮活的現場才能拾獲,尤其是那些個性化、原創性的實踐行為,并非當下的人工智能力所能及的。越是在人工智能興起的時代,越要強調人之為人在本能、感性、意義等精神層面的價值。
五、優化教師評價機制
優化資源配置和充分開發內部潛能的關鍵是建立科學、公正、規范,同時兼具生長性和靈活性的評價體系。作為一種導向機制。好的評價體系能不斷激發和推動人的進步,也能源源不斷地孕育出生力軍。
和專業影視院校相比,綜合性大學中的影視學科在制定評價體系時容易被所處大學的大環境所影響,對影視學科的特殊性則有所忽略。比如在教師的評價體系上,通常會將學術發表、課題、獎項等硬性科研指標居于首要位置。當這種評價體系占據上位,成為一種顯性的外部動機,相當一部分教師難免會重視紙面的“成果”而不重教育的“效果”,于是遵循“最小阻力原則”,為做學術而做學術,為獲獎而獲獎。而外在動機的強化又會弱化內在動機,造成教師在影視教學尤其是影視實踐教學上所占據的精力被削減,在科研上則追求達標和平穩。在“按圖索驥”完成個人職業規劃的過程中,這樣的教師或許會成為因循群體規則的典范,卻逐漸喪失了個性和創造力——這對于藝術教育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同時,注重結果而非過程的評價體系對看不見的“隱形付出”并不友好,明顯不適合那些創新型的人才——某些實踐領域的開創性探索往往需要抱持勇氣、親身試錯、不斷觸碰邊界和糾偏,這是長期的迷宮探路而非短跑沖刺。
在綜合性大學的影視院系中,能夠熟練講授和指導創作實踐課程的教師比例普遍不高。多數專業影視院校的學生在畢業后會選擇進入業內而非高校,而且擁有專業院校或影視專業學歷背景的科班生也未必能夠勝任教師崗位,因為還得具備相當的實踐功底和較深的專業認知,以及相匹配的教學科研能力。與理論課教師有別,實踐創作課的教師更多承擔著“輸出端”的任務,即指導學生出作品。不同專業方向的教師職責有別,評價體系也應有區別。例如,影視史論方向的教師多以常規的學術出版、發表、課題等作為主要成果,而對于主要承擔實踐課程的教師,可以將專業創作獲獎/入圍(尤其是指導學生獲獎/入圍)計入成果。在獲獎/入圍級別的設定上,也要綜合考慮其難度系數和中選比例,如果動輒以幾大國際電影節或國內最高級別的影視獎項作為標準,這些對于全職資深的影視創作者都難以企及——則有失公允。
綜合性大學影視教育需要抓住影視教育的核心,也需要清醒辨別當下的教育體制和機制中正阻礙著創新和進步的因素,并及時做出調整。
結語
在《全新思維》(A Whole New Mind)一書中,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平克(Daniel H. Pink)提出,“我們正邁向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右腦思維將決定誰處于領先地位。”[7]而我們需要六種必備的能力——設計感①、故事力②、交響力③、共情力④、娛樂感⑤、意義感⑥,以適應未來發展的趨勢。未來的影視行業是跨領域人才、故事型人才、創意型人才的天下。綜合性大學的影視教育正處于新的轉型期,無論教師、學生還是管理者,在持守教育本源的前提下,都應該通過超前學習,打破專業壁壘,打破課程設置和知識體系的條塊分割,拓展認知視野和跨界綜合能力,并在鮮活的實踐和現實的反饋中不斷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1][美]埃米尼亞·伊貝拉.能力陷阱[M].王臻,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45.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2-10-16)[2023-01-25].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3]柯政,梁燦.論應試教育與學生創造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04):72-82.
[4][美]霍華德·加德納.智能的結構[M].沈致隆,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1-275.
[5]騰訊研究院.什么是“奇點”?[EB/OL].(2021-10-22)[2023-01-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277290251936091&wfr=spider&for=pc.
[6][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3-50.
[7][美]丹尼爾·平克.全新思維:決勝未來的6大能力[M].高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9-30.
【作者簡介】? 侯海濤,男,河北邯鄲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視聽語言和攝影美學研究。
①②③④⑤⑥參見:[美]霍華德·加德納.智能的結構[M].沈致隆,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1,124,157,205,244,279.
⑦英籍猶太裔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在其著作《個人知識——朝向后批判哲學》(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中提出,人類的知識有兩種,通常被描述為知識的,即以書面文字、圖表和數學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種類型的知識,即可言傳知識(articulate knowledge)。而未被表述的知識,像我們在做某事的行動中所擁有的不可言傳知識(articulate knowledge),即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在本質上,默會知識密切關涉著個體的理解力、領悟力和判斷力,需要在反復操練后悄然內化,在長期積累一手經驗的過程中逐步獲得提升,比如審美趣味、鑒別力、技巧、創造力等。
①奇點(Singularity)是一個假設的時間點,該概念由英國物理學家霍金首次提出。在該時間點上,技術的增長變得不可控制和不可逆轉,從而導致人類文明發生無法預見的變化。
①②③④⑤⑥參見:[美]丹尼爾·平克.全新思維[M].高芳,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3:71;105;133,163,19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