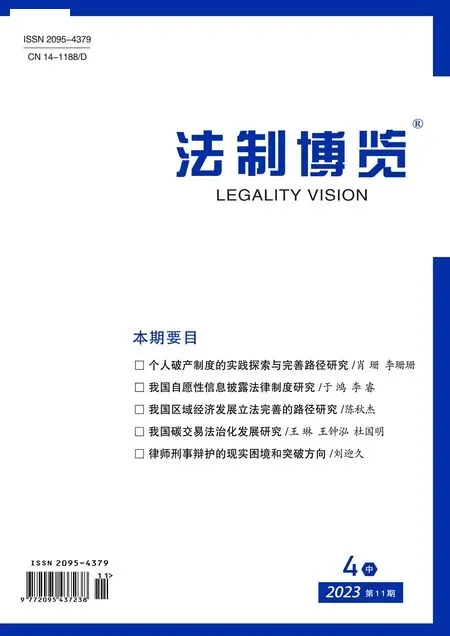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研究
相星宇 李杰賡
長春工業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一、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的關系
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是兩種不同的行為,應當對二者加以區別[1]。生態破壞通常是指人為原因造成的生態功能退化,影響生態的正常運行。而環境污染是由于人類向自然環境中過量添加某種物質,影響環境指標,導致環境惡化。二者的共同點是通過人為對生態環境進行影響,生態環境再反作用于人類,造成人的身體損害和財產損失。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是不能進行完全割裂的。嚴重的環境污染會造成生態系統功能變化,形成生態破壞。因此生態破壞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過度索取引起的生態破壞,例如因行為人的亂砍濫伐造成了水土流失,又或因偷盜珍稀野生動物造成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另一類是人類通過污染環境間接引起的生態破壞,例如排放含磷量高的污水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向空氣中排放二氧化硫含量超標的氣體引起的酸雨。
破壞生態與污染環境相比具有一定的特點。首先,具有隱蔽性強的特點。生態破壞一般由侵權人在正常的勞作的過程中,對生態不斷索取,直至破壞了生態環境。在實施破壞生態行為的初始,侵權人可能沒有破壞生態的意圖,但是它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的結果,從而導致了被侵害人的損害。相較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由于是過度索取,主觀上的故意不明顯;其次,具有周期長的特點。大部分造成生態破壞現象的周期較長,修復的周期也相對較長,甚至有些生態是一次性的難以得到修復。環境污染的過程雖然也是長期的,但相比之下其更易顯現。環境污染可以通過治理在預計的周期內得到恢復。
二、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侵權人因違反法律的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從而造成了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要求提出懲罰性賠償。很明顯,這是一項原則性規定。2022 年1 月隨即發布了配套的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侵權糾紛案件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共計一十四條,其中規定了生態破壞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原則,即要求審慎適用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因生態破壞而遭受到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可以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進而在訴訟中提起懲罰性賠償。將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限定在了生態環境私益訴訟當中。而在《司法解釋》第十二條中又規定了國家規定的機關和法律規定的組織可以作為被侵權人代表提出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對此,“被侵權人代表”的表述是否應當被理解為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可以同生態環境私益訴訟一樣提起懲罰性賠償,仍然存在疑問。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可以在何種訴訟類型中提起,一直是學術界與實務界探討的話題,其理由在于明確適用范圍是規范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的前提。
將主觀要件限定在“故意”層面存在疏漏。《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中明確將故意作為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但由于生態破壞的特殊性,侵權行為人一般表現為對生態的索取,而這種索取,往往不具有破壞生態的故意,而是在不斷索取的過程中逐漸造成了生態破壞的嚴重后果。以故意作為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往往難以被認定,且造成行為與責任的錯位。[2]
《司法解釋》第八條中規定了如何判斷造成了嚴重后果,但表示為造成他人死亡、健康嚴重損害、重大財產損失等,在司法解釋中并沒有明確列出嚴重后果的標準。根據《民法典》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在生態破壞案件中因生態破壞而受到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依據生態破壞對自身造成的嚴重后果在訴訟中提起懲罰性賠償。同時,法院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因此,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只能由受損害方自行提出。因此,有必要設立嚴重后果的標準,使被侵權人明確其是否可以依據標準提起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在沒有嚴重后果的標準下,被侵權人很難知道侵權人的生態破壞是否給自己造成了法律中要求達到的嚴重后果,以及被侵權人是否有權提起懲罰性損害賠償。
三、境外有關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雖然懲罰性賠償制度開始于英國,卻在美國法律制度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屬于私法手段,其目的在于激勵被侵權者主動維權,彌補法律執行的不足。[3]在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制度中,美國對侵權人要求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魯莽”,其中魯莽是介于故意與過失之間的,也可以表示為任意的不當的行為。在各州的司法判例中,只要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加重了一般侵權,則懲罰性賠償一般會被判決。
在加拿大,懲罰性賠償制度應用于民事侵權案件,其中也包括生態環境侵權案件。在這些案件當中,侵權人的故意和疏忽均可被判決承擔懲罰性賠償。也就是說,加拿大要求生態破壞案件的侵權人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者過失。在某種情況下,被告即使在刑事訴訟中受到了刑事處罰,依然可以被判決承擔懲罰性賠償。可見在加拿大,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制度更注重發揮懲罰性賠償的懲戒作用和預防作用。
在法國,一個人如果犯了明顯的故意過錯,特別是為了獲得利益而犯的過錯,除了補償性損害賠償外,還可被判以支付懲罰性損害賠償。其中“明顯故意”一詞的使用似乎表明,該條的一個中心組成部分是侵權人必須有意犯下過錯。但法國的學者認為,考慮到法國對糾正性司法和恢復道德平衡的承諾,將懲罰性賠償擴大到一方有惡意行為的情況似乎是該學說的一個邏輯延伸,即使侵權人的行為動機不是為了獲得利益。當侵權人犯有明顯的蓄意過失,無論是出于利益還是惡意,都符合法國侵權法的基本原則,因為它有助于恢復社會平衡,通過承認犯下了特別惡劣的侵權行為,并為受害者所遭受的不可估量的道德傷害提供一種形式的賠償,促進全面賠償。其將懲罰性損害賠償與過失,尤其是以獲利為目的的過失,明確聯系在一起。
韓國在《環境衛生法》中規定,因經營活動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產生的環境危害因素造成他人患環境疾病的,由經營人承擔舉證責任,以受害人損失的3 倍為賠償限額進行賠償。可以看出,在韓國的生態破壞懲罰性損害賠償體系中,對侵權行為人的主觀認定要求有意識的或重大過失。將重大過失囊括在內,其理由在于在生態環境侵權領域中重大過失具有高度主觀惡意,應當受到懲治。
綜上所述,境外國家對生態破壞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時要求侵權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需要主觀上具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對故意破壞生態的侵權人以及因重大過失造成生態嚴重破壞的侵權人加以懲罰,以期遏制破壞生態的行為以及預防其他潛在的生態破壞現象的發生。
四、我國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的完善
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適用于何種訴訟類型,是該法律制度規范適用的前提,應當予以明確。在這方面,筆者的觀點是應當在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謹慎適用懲罰性賠償,但基于我國生態環境訴訟制度是生態環境私益訴訟與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并行的結構,即使在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也應當加以限制,區分于生態環境私益訴訟。
根據文義解釋,首先,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以及《司法解釋》第二條中,明確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的主體應當是因生態破壞而遭受損害的被侵權人。在我國生態環保領域,既有生態環境私益訴訟,也有生態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并非因生態破壞而受到損害的被侵權人,其所代表的是不特定的主體;[4]其次,在《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應當以被侵權人受到的損害為基數。但在公益訴訟中并不存在具體的被侵權人,對于懲罰性賠償數額無法確定;最后,《司法解釋》第十二條規定,國家規定的機關或法律規定的組織作為被侵權人代表,請求判定侵權人承擔懲罰性賠償,人民法院可以參照前述規定進行處理。由此可見,《司法解釋》并沒有直接就生態損害懲罰性損害賠償和環境公益訴訟的適用作出規定。
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條規定,因違反法律規定造成生態破壞,可以進行生態修復的,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有權要求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承擔修復責任。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規定,違反法律規定造成生態破壞的,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有權要求侵權人賠償因生態環境損害、服務功能喪失、生態功能永久性損害、生態環境損害的調查、評估、污染的清理、生態環境的修復、損害的預防和擴大等導致的合理費用。可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條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均對生態環境公益訴訟的賠償問題加以規定,并不涉及懲罰性賠償。我國在民法領域特別是侵權領域一直遵循的是損害填補原則,期間功能損失本身就因無實際受益民事主體而超出填補性賠償的范圍。[5]如若在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提起懲罰性賠償恐有重復追責的現象。因此,在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缺乏直接適用該司法解釋的正當性,只可作為參考。懲罰性賠償的主要目的是對損害方的全面救濟,解決賠償金無法覆蓋被侵權人維權所需要的高額律師費用、鑒定費用,但這并不代表著任何一方可以從中獲利。若在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提起懲罰性賠償應當加以限制,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對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中勝訴獲得的資金的使用方式應當進行公開,并接受公眾監督。
綜上所述,筆者的觀點是生態破壞賠償懲罰性賠償應主要適用于生態環境私益訴訟。而對于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應當謹慎適用,必要時需要加以限制。
在主觀要素中加入“重大過失”。首先,基于生態破壞的特殊性,侵權者往往不具有明顯的主觀故意,更多的是在對生態資源不斷索取的過程中,對生態的破壞持一種放任結果發生的主觀狀態,最終造成了生態破壞的嚴重后果。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本質是懲罰具有主觀惡意的侵權人,因此,應當在生態破壞領域將重大過失加入主觀要件當中;其次,懲罰性賠償制度屬于舶來品,應當根據我國國情結合外國制度經驗,加以運用。上文介紹了境外的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制度,各國均將主觀要件限定在故意和重大過失或與重大過失具有相近意思表示的詞匯當中。其目的在于懲罰具有主觀惡性的侵權人,故意的范圍小于主觀惡意的范圍,重大過失介于故意與過失之間,在生態破壞領域具有主觀惡意,因此應當將重大過失納入到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當中;最后,侵權行為主體多數是具有法律知識儲備的工廠、企業,其應當具有生態環保的高度注意義務,而對主觀要件以故意限定,不能體現社會對其要求的高度注意義務,易使其尋找法律制度的漏洞,為自己本具有主觀惡意的侵權行為逃避懲罰。因此,筆者認為在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中有必要加入重大過失,以懲罰、預防破壞生態的行為。
嚴重后果應當有一定的標準。對于嚴重后果的認定依據雖然在《司法解釋》當中進行了規定,但由于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是由被侵權人提起。一般而言,被侵權人往往難以確定他或她所受的損害是否足以提起懲罰性賠償。法院雖可以依據司法解釋中的規定對嚴重后果進行判定,但因受制于“不告不理”原則,在被侵權人沒有主動提起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時,不得提起懲罰性賠償。此時,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會出現難以得到實際應用的困境。再者,在司法解釋的形成過程中,有些專家學者提出“南方的一棵樹可以等價于北方的一片林”,因此不應當為嚴重后果設立標準,尤其是造成生態嚴重損害的標準。雖然生態環境標準的設立是一個重大工程,但嚴重后果的標準不只有生態的嚴重損害,還有被侵權人死亡、人身損害、財產損失,只要滿足其中一項都應當認定為嚴重損害。并且在沒有標準的情況下會放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悖于適用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的審慎原則。因此,在生態環境標準難以確立之前,有必要確立被侵權人死亡、健康嚴重損害、重大財產損失的標準,以期在生態破壞領域謹慎適用懲罰性賠償。
五、結語
生態破壞因其具有特殊性,更有一部分生態是一次性的,遭到破壞后難以得到修復,因此,應當對生態加以嚴格的保護。生態破壞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的出現正是對生態加以嚴格保護的指引。面對嚴厲的生態保護法律制度,我們應當秉持謹慎、理性的態度,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保護生態,在保護生態的過程中發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