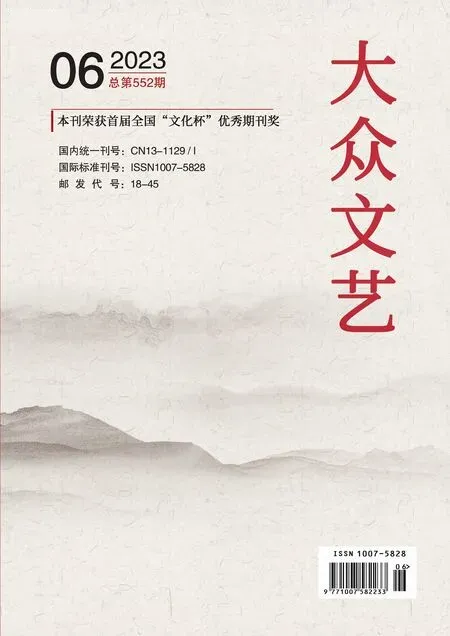淺析殯葬題材電影的藝術處理手法
——以《人生大事》為例
姚 北
(廣西藝術學院,廣西南寧 530000)
一、緒論
殯葬行業是國產電影較少觸及的題材之一,尤其還作為國人極忌諱的題材,《人生大事》的故事卻此以為切入點,描繪了一段平凡小人物們的生活和成長故事。與傳統的喜劇相比,“殯葬”題材的喜劇電影相對冷門,然而《人生大事》以其獨特的藝術處理方式挖掘到了這個冷門題材中獨特藝術價值,不僅展現了特殊行業的容貌,而且探討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展現真實的人性和社會風氣。這么一個特定題材的電影,能夠實現其商業價值,并非觀眾對主流題材影視作品的視覺疲勞,而是恰恰說明了《人生大事》的藝術處理手法和商業包裝模式契合觀眾和市場的需求。
讓冷門題材電影符合國人主流審美,是殯葬題材乃至所有冷門題材電影的必要舉措。首先,殯葬行業電影中的強邊界化是人為界定的,雖然大部分殯葬題材電影都有著極強的記錄性和專業性,但是在具體的藝術敘述過程中不應該局限于單一的主題和表現方式,否則就失去了表現特定主題所帶來的獨特藝術色彩。其次,對于表現殯葬題材所附加的一系列藝術手法不能完全脫離現實,附加的情感元素和敘事手法應該具有現實主義。在此基礎上再去理解殯葬題材電影,就能總結出殯葬題材電影創作的方法論。
二、藝術處理分析
冷門題材電影在影視藝術史和影視藝術的整體發展過程中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因為冷門題材電影的制作和順利上映乃至實現其商業變現,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了大眾審美的變化趨向。大眾對于殯葬題材電影這一特定類型電影接受度的提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與導演藝術處理的應用、電影視覺技術的成熟、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演員表現力度的呈現等多個因素息息相關。
1.邊界模糊
《人生大事》的藝術表現方式不同于以往的殯葬題材電影。與日本殯葬題材電影《入殮師》不同的是,《入殮師》記錄了殯葬行業入殮師的種種經歷,主角從一個演奏家到入殮師,從剛開始的反感和拒絕到后來的接受與認可,這種帶有記錄性和為我們非常直觀展現出殯葬行業從業者的方方面面,而《人生大事》則是融入了更多社會化的元素,將單一題材所限制的作品內核盡可能地拓寬,盡量去模糊殯葬題材電影的邊界,去挖掘影片所表達的更多可能性。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影視作品追求的是矛盾性、復雜性和多元化,采用非傳統的混搭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模糊感取代準確的清晰感,以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雜亂取代明確的邊界,形成多元化的藝術風格[1]。
與國內《哀樂女子天團》《吉祥如意》等優質影視作品不同的是,《人生大事》用極其戲劇化的敘事方式和藝術化的處理手法來減輕死亡帶來的殘酷,將殯葬題材盡可能地模糊化,拍出了人間煙火氣與社會溫情。
在人物設置方面,許多物品作為一種關聯性極強的意象也能夠代表出影片人物之間的關系。其中三妹與小文之間的關系可由緊箍手鐲所代表的孫悟空和紅纓槍、雙丫髻所代表的哪吒之間的強烈對抗表現出來。小文的手表象征著對外婆思念,她與外婆的人物關系也貫穿影片始終。莫三妹和父親反復爭執的房產證也象征了父子間的矛盾關系,而莫三妹和女友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組重要的情感對抗。這些重要的人物關系都將殯葬的主題弱化,更好地為導演所表達的思想服務。
2.角色安排
影片中每個角色安排都十分巧妙,他們各自承載了人生各個階段所代表的情感關系。各種人物的矛盾也復雜多樣,這種處理能夠最大限度地通過小人物鮮活的群像折射出人生百態。
影片安排了性格各異的市井小人物推動情節的發展,講述小人物的成長,進而傳遞治愈、溫暖的主題。其中的角色的進場、退場也有著深刻的含義,用這些人物的矛盾關系和戲劇化沖突映射出中國當代社會和家庭的現狀。通過女友的離開、小文的出現,以及身邊發生的一系列算得上“狗血”的事情,乃至最后父親的去世,莫三妹也逐漸獲得了擔當,也明白了人生除死無大事,表達出中國式溫情的核心旨意。
《人生大事》影片中值得一提的是小文這個角色,通過一個小孩來中和影片中“死亡”帶來的恐懼感,在劇情僵持的地方也通過小文的出現來推進故事的發展。觀者也能夠切切實實地看到武小文這個角色的成長和進步,以及她給周圍人帶來的影響,也會能夠在影片中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一份成長和感動。
莫三妹的父親老莫是導演安排壓陣的角色,一個存在喜劇元素的故事里,需要一個略帶嚴肅甚至刻板的角色,讓故事整體基調均衡,不會變得過分輕浮。而老莫作為殯葬資深從業者的身份也緊緊回扣了電影題材,不至于讓電影的核心過于偏散。同樣,他的退場也是完成劇情閉環的重要安排。
跟隨角色的演繹和劇情的深入,觀眾能夠看見每個的歸宿和結局,在角色的一言一行中也能夠看到觀者自己現實的影子,從而產生強烈的共振情緒,電影也隨之深入人心。
3.視聽語言
《人生大事》的視聽語言極富生活化并且存在諸多的細節化處理,影片的視聽語言帶有極強的真實性。拍攝時大量使用自然光讓影片更有質感,皮膚的紋理在燈光下顯得尤為真實。拍攝時采用手持攝影進行跟拍也能夠抓拍到人物瞬間的感情變化以及人物的內心,特寫鏡頭的使用進一步放大了人物的情緒,也讓觀眾的目光更加聚焦。這種質樸而生動的刻畫使得影片中的人物更加鮮活,也拉近了與觀者之間的距離。
影片的置景方面,導演對“上天堂”店鋪中的布置具有鮮明的生活特色和職業特征,凌亂而逼仄的小屋子和屋內物件的擺放有著很濃郁的殯葬職業氛圍,這些人物生活中的殯葬元素較好地呈現了人物的生活狀態和生存環境。
除此之外,電影的配樂與所對應部分的畫面十分契合,例如莫三妹抬棺喊號子時,肅穆的神情、莊嚴的號子、冷色調的全景鏡頭,那種充滿了肅敬的儀式感和嚴謹的職業精神,令觀者肅然起敬又不禁萬分感慨,這種處理能夠很好地將觀
4.情感寄托
電影《人生大事》中的帶有情感寄托的敘事意象豐富,這些意象組合構建出一個龐大而多姿多彩的隱喻世界,通過那些散發著本土文化和煙火氣息以及人文關懷的意象,表現出獨特的、有生命力的、富有情趣的藝術內涵和現實意義。影片整體敘述結構以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的雙線形式進行展開,具體呈現了莫三妹和武小文他們各自的生活際遇和情感世界,影片以莫三妹的情感經歷、家庭生活情況和職業發展軌跡為主線,以武小文的親身經歷為輔。電影中的諸多場景和物件都有著深刻的情感寄托和豐富的人文特質,這些構成影像世界并非具體的房舍但卻是充滿著寄托感和民族情感的,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難以割舍的精神棲息地,同時,影片中所呈現出的“家園感”也讓觀眾感受到滿足,在觀影體驗中得到歸屬感。
電休克治療是所有抗抑郁治療中,有效率和緩解率最高的治療,70%-90%的患者病情有改善。因此,難治型抑郁癥患者可考慮使用電休克療法。電休克療法對一些嚴重抑郁癥患者特別有效,可作為初始治療方案。ECT治療的副作用包括認知損害和遺忘等,一般在治療結束后恢復。因此,電休克療法整體上較為安全。
《人生大事》對現代化街道和摩登都市的車水馬龍式的描寫很少,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只能容一輛車通過的狹小弄堂,周圍則是老式居民樓,這也是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它寄托了當地市井百姓的熱鬧和喧囂,更是底層人民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承載了一代代人的獨特記憶。這些充滿寄托感的樓房屋舍很容易就喚起觀者最深處的情感記憶,進一步打動人心。影片中民居大多居住的是那些老舊的低層居民樓,表現的是延江市里老百姓破敗而繁重的生活狀態,同時映照出主人公莫三妹生活的無序,側面表現出小人物內心的孤獨感。莫三妹的房間存在著殯葬物品、西游記相關物品等諸多傳統元素,這些都是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特色印記和獨特標志,影片既體現出對死亡和生命的思考,也滲入了中華傳統文化,具有相對持久的文化內涵。
影片中殯葬元素眾多,所涵蓋的范圍廣泛,寄托了豐富的情感和寓意。例如寓意為逝者送財而在火盆里燒黃紙;作為逝者陪伴的紙人和紙物件;送別逝者時喊的哀悼號子;以及為表達對逝者的思念和哀悼而必須流淚、大聲哭喊的哭喪;守護逝者亡靈的守靈;手表電話寄托著對小文外婆的追思;煙花象征著轉瞬即逝的美好和恒久的希望、美好;布老虎代表著童心;房產證則象征著兒女對財產與住所的渴望;這些帶有豐富情感的多重元素,不僅成為情節銜接的橋梁,還成為塑造人物性格、組合電影時空、表達情緒轉化的關鍵樞紐。
影片中有幾個十分重要的帶有情感寄托的意象。有代表著束縛感與責任感的莫三妹的緊箍手鐲和小文的象征沖破桎梏精神的紅纓槍,這兩個帶有極強暗示色彩的物件比較直觀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莫三妹與小文之間的最初的關系也由孫悟空和哪吒的對抗表現出來,但與此同時,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雙向救贖。在影片開場,武小文的第一次登場,是在小文外婆去世的頗為混亂的現場:一副哪吒造型的武小文以“老子”自稱,并且狠狠地咬了莫三妹一口,給莫三妹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劇情推進過程中,他們之間的關系始終都不像是一對父女,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都是被拋出了傳統中心價值系統的叛逆者和邊緣人。在中國神話體系中,哪吒是女媧補天的六塊靈石的一部分碎片所化的靈珠子的轉世,孫悟空則是女媧補天用剩下的第七塊靈石所孕育的,他們二者存在極強的關聯性。在命運方面,二者也有相似之處,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天庭的邊緣人和反叛者,哪吒鬧海,是規矩的反抗者和破壁者,但是最后又融入整個神仙體系中。受到規訓與懲罰的叛逆者們,又成為《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和武小文。邊緣化的殯葬題材,面對逝者的生命感悟,武漢充滿地氣的市井小巷,只是改了頭換了面的西行路、梁山泊和大觀園而已[2]。
影片中存在著一個美好的比喻,莫三妹也將外婆的去世偽裝為美麗的童話,將逝去的人比作天上的星星,將殯葬行業從業者比作種星星的人。星星寄托著對逝去親人的無限思念和美好祝愿,也將殯葬這個行業賦予了一層更浪漫的含義,殯葬師所給予的是死者最后的體面,是對所有逝者最后的尊重和交代。導演想表達的就是職業不分大小、高低,每個職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都是社會運作中重要的一環。
5.風土人情的再現
《人生大事》這部電影發生的地點設定在虛構的延江市里,里面的對話也多采用湖北方言。除此之外,影片中還出現了大量的方言,有湖北話、四川話、廣東話、廣普等等。在電影的臺詞表述上使用方言,會讓人們覺得更加貼近現實從而讓觀眾產生更強烈的共鳴和共情,在觀賞電影的過程中也會更加投入。同時,使用大量的方言能進一步減弱因電影題材而給觀眾帶來的距離感和恐懼感,讓觀者更能深入地理解影片的內核和導演的思想。
在具體的表達方面,導演安排莫三妹通過“漢罵”來進一步傳達情感,所謂“漢罵”就是湖北武漢話中用來罵人的話。這種略帶粗糙和野蠻的言語表達使得觀者與劇中角色的情感更能貫通,也表明了電影的現實主義特征和生活化氣息。即使是影片中的普通話,也大多是帶有荊漢味道的普通話。這樣的語言表達狀態最大限度地演繹與再現武漢市民生活。影片中人物的刻畫和塑造也因為語言的應用,具有更為具象的形象。
這種高明的處理手段使得電影臺詞表達融入更多鄉土氣息和“煙火氣”,一定程度上再現了風土人情,更便于觀者和電影中人物同頻共振。
6.死亡教育
《人生大事》影片不僅有著藝術價值,也有著現實意義,它是一堂優秀的死亡教育課,不管是學校還是社會,我們在死亡教育這方面實在非常缺乏。這一點可能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中國文化是一種由儒家文化主導的世俗文化,缺乏終極關懷和彼岸求索[3]。
在武小文這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的視角中,她并不知曉生與死究竟是什么,對于人的逝去這個概念非常模糊,以至于小文始終認為外婆會回來,一直在追問外婆的去向。孩童的無知和天真與現實的殘酷形成鮮明的對比,主角莫三妹則用委婉的方式不斷教導小文,給娃娃取可愛的名字、告訴小文外婆變成了星星,這種溫柔呵護方式沖淡了死亡的陰影。
影片中總共出現了五場葬禮,分別是小文外婆的葬禮、與小文同齡小女孩的葬禮、要活出喪的劉爺爺的葬禮、三妹前女友的丈夫的葬禮、三妹父親老莫的葬禮。可以看出,影片并不忌諱死亡,而是直面它,導演大膽地將一場場葬禮安排為一次次的死亡教育課,影片中的人物和觀眾也在隨著一場場葬禮的舉行而逐漸成熟,慢慢領悟人生的真諦。
電影中無處不在的死亡和葬禮,看似在告訴人們死亡的恐怖以及它的無處不在,實際上卻在告誡人們要如何好好生活。在后疫情時代,死亡成了一個悲壯但并不算少見的話題,人們面對生死甚至已經開始逐漸麻木。正如電影所要傳達的,一味麻木永遠不是最佳的解決途徑,只有直面死亡,才能不懼死亡。
結語
綜上所述,《人生大事》影片的諸多藝術處理手法,能夠較好地為闡釋主題、表達導演思想、吸引觀眾眼球而服務。其中,富有特色的是模糊殯葬類型電影邊界的手法,使其融入更多社會元素以減少題材的限制,盡量消除大眾對于殯葬的忌諱和誤解,從而使得電影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富有鄉土情懷和煙火氣息的臺詞表達也是現實主義電影常用的藝術手法之一。《人生大事》作為一堂生動感人的死亡教育課,更是提升影片深度的所在,它所帶來的現實意義不僅僅流于表面,也能夠讓大眾不斷思索,在觀影體驗中獲得更加深刻的感受和悸動。《人生大事》正是因為這些獨到的處理方式,成了一部引人深思的優秀商業電影,通過分析和借鑒這些藝術處理,我們能夠看到殯葬題材電影更深層次的藝術價值,也能夠總結出一些更好地處理這類電影的方法論,為更好地破除冷門題材電影不賣座的難題做出貢獻,為中國電影藝術乃至世界電影藝術的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