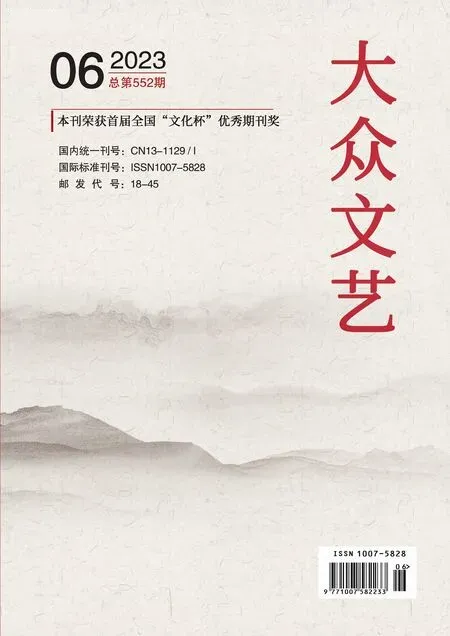創(chuàng)傷敘事、身體感知、空間修辭
——后3·11語境下電影《駕駛我的車》的美學(xué)分析
羅 欽
(重慶大學(xué),重慶市 400000)
引言:分裂的世界——?jiǎng)?chuàng)傷后哀悼者的“停滯”狀態(tài)
創(chuàng)傷理論從19世紀(jì)70年代發(fā)展至今,歷經(jīng)了由生理層面、心理層面、進(jìn)而到公共政治與社會(huì)話語層面的發(fā)展與突破,成為社會(huì)文化科學(xué)關(guān)注的對(duì)象。創(chuàng)傷敘事是以創(chuàng)傷理論為方法論,藝術(shù)再現(xiàn)創(chuàng)傷者的生活經(jīng)歷與心理狀態(tài),旨在關(guān)注創(chuàng)傷事件對(duì)個(gè)體與集體所產(chǎn)生的深遠(yuǎn)影響。[1]
正如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在《哀悼電影:電影中的失落和悲傷的批判性研究》中所表述的:“理解悲慟和電影的關(guān)鍵在于理解缺席,考察身體和心理流動(dòng)性在電影哀悼過程中的作用至關(guān)重要。”①面對(duì)至親的缺席,創(chuàng)傷的痛苦會(huì)以生理或心理上某種形式的緩滯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來。在電影中,“喪失”導(dǎo)致的精神創(chuàng)傷往往會(huì)造成情感綿延的效果,死亡作為“缺席”的符碼時(shí)刻提醒著哀悼的必要。
哀悼者既是災(zāi)難的幸存者又是被“拋下”的受害者,同時(shí)具有雙重身份屬性。當(dāng)社會(huì)環(huán)境缺乏為哀悼者提供一個(gè)合理且有效的釋放機(jī)制時(shí),哀悼者往往會(huì)產(chǎn)生“幸存者愧疚”這樣的負(fù)面情緒。在《哀悼與抑郁》中,弗洛伊德認(rèn)為:?jiǎn)适Т侔l(fā)抑郁,根源于抑郁個(gè)體與所喪失的客體的關(guān)系——一種“自戀性的客體選擇”②。哀悼者的喪失不僅是他者的喪失,而且伴隨著自我主體的一部分喪失。
以哀悼者作為主角的電影會(huì)暗示哀悼者的兩個(gè)世界——一個(gè)是生活在繼續(xù),就好像失去從未發(fā)生過一樣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另一個(gè)是“定義過去那個(gè)世界的人已經(jīng)不在了”的世界。哀悼電影中的主人公常常被困在這兩個(gè)世界之間,通過充滿記憶指示的空間強(qiáng)調(diào)缺席的存在,通過“平行的時(shí)間性”來描述死者。幸存者不能真正融入他現(xiàn)在所處的世界中,也無法進(jìn)入死者的世界去。哀悼者處于二者平行存在的雙重世界里。因此,哀悼電影的敘述不是歷時(shí)而是共時(shí)的。
下面筆者要論述的是濱口龍介如何在《駕駛我的車》中利用空間修辭和身體感知,展現(xiàn)哀悼者分裂的兩個(gè)世界,并試圖探討該電影在“后311”語境下特殊的文化指涉。進(jìn)而考察濱口電影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代人的精神困境以及濱口對(duì)此所提供的撫慰方式。
一、分裂的感受:身體的感知與語言的失效
(一)身體感知
電影中音在失去女兒后,停止了演員的工作。依靠在與家福做愛時(shí)創(chuàng)作故事,并由家福的轉(zhuǎn)述記錄下來,開啟了編劇的職業(yè)道路。面對(duì)女兒的缺席這一故事背景,濱口巧妙使用演員的身體,將過去與現(xiàn)在的兩個(gè)世界同時(shí)呈現(xiàn)。阿萊達(dá)阿斯曼在《回憶空間》里闡述:當(dāng)強(qiáng)烈的情感超過了有益的程度,轉(zhuǎn)而變成了一種過分,那它就不能再穩(wěn)定回憶,而是會(huì)打碎它,創(chuàng)傷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創(chuàng)傷的身體性令創(chuàng)傷經(jīng)驗(yàn)脫離語言秩序,創(chuàng)傷是言說的不可能性。[2]
創(chuàng)傷的不可闡釋性迫使音的主體性從象征界退卻到實(shí)在界與想象界,這解釋了在電影中音為何只能在失去社會(huì)監(jiān)禁和自我審判的潛意識(shí)狀態(tài)下進(jìn)行創(chuàng)作。音的意識(shí)寄居于過去時(shí)空而身體停留在現(xiàn)在時(shí)空中進(jìn)行敘述,二者同時(shí)分離,創(chuàng)造出平行的時(shí)間。雖然電影中沒有出現(xiàn)一個(gè)閃回鏡頭交代前情,但通過音同時(shí)承載了現(xiàn)在時(shí)空與過去時(shí)空的身體作為媒介,交代并強(qiáng)調(diào)了女兒的缺席,完整了觀眾對(duì)音的欲望的認(rèn)知和認(rèn)同。通過身體的媒介作用,觀眾能夠感知影片中人物的身體經(jīng)驗(yàn),進(jìn)而理解影片的意義。這樣的影像處理方式與梅洛龐蒂的“身體間性”不謀而合。
在知覺現(xiàn)象學(xué)理論中,梅洛龐蒂將身體從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中解救出來,將純粹意識(shí)主體改造成“肉身化的主體”。身體是知覺的主人,只有通過身體作為媒介,知覺才能建立起事物和心靈的關(guān)系。③
音在成為編劇后常常會(huì)與劇組的男演員保持身體上的關(guān)系說明了電影中家福與音通過虛構(gòu)故事克服喪女創(chuàng)傷,建立情感聯(lián)結(jié)的路徑是失效的。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陷入失語狀態(tài),構(gòu)成雅克·德里達(dá)所言的“溝通的不可能”。當(dāng)人類的情感表達(dá)從象征界的語言秩序中逃逸出去,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人們便開始朝向動(dòng)物性的轉(zhuǎn)變,即用身體替代語言來感受這個(gè)世界。[3]
家福在逃避妻子出軌的事實(shí)后眼部受損,被剝奪了開車的能力。能“看見”真相的器官被迫停滯在創(chuàng)傷到來的那一刻,身體功能的部分喪失隱喻著家福的世界已然分裂為處于真相的世界和選擇表演的兩個(gè)世界。直到音的死亡對(duì)家福造成二次創(chuàng)傷,家福置身于公路旅程真實(shí)發(fā)生的現(xiàn)實(shí)世界與以磁帶中聲音形式存在的音的世界中,二者并置建立了“平行的時(shí)間性”。通過時(shí)空運(yùn)動(dòng),將過去和現(xiàn)在同時(shí)投射到家福的語言與行為上,呈現(xiàn)出一種微妙的分裂狀態(tài)。
家福的分裂性首先體現(xiàn)在于他的表演觀與實(shí)踐之間產(chǎn)生的分歧。面對(duì)戲劇表演,家福堅(jiān)持以“去表演化”的手段抵達(dá)真實(shí),演員只需要作為“模特兒”念出臺(tái)詞即可。然而在家福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家福選擇以表演無知的方式面對(duì)妻子出軌的真相。家福呈現(xiàn)出“在藝術(shù)虛構(gòu)中尋找真實(shí),在真實(shí)生活中建立虛構(gòu)”的矛盾性。
梅洛龐蒂的身體現(xiàn)象學(xué)理論認(rèn)為個(gè)體在融入環(huán)境過程中會(huì)形成獨(dú)特的意向弧,而正是這種“環(huán)境意向弧”幫助我們參與這個(gè)世界。“意向弧在我們的周圍投射我們的過去與將來,更確切地說,它使我們置身于世間的所有關(guān)系中。”④
在電影中,家福的司機(jī)渡利表達(dá):開車這一行為不僅是自己過去與從事風(fēng)俗業(yè)的母親牽絆的方式,也是在母親遭受山洪去世后,她唯一謀生的手段。從創(chuàng)傷理論解讀,“駕駛”這一行為作為渡利的身體圖示,體現(xiàn)的是始終聯(lián)結(jié)那個(gè)“過去的,母親存在的世界”的意向。渡利的世界在母親去世后明確地分裂為“駕駛”的現(xiàn)實(shí)世界與陷入愧疚與悲傷的,停滯的精神世界。
綜上所述,無論是音尋找自我的身體敘述,還是家福自我保護(hù)的身體表演,抑或渡利偏好“駕駛”的身體圖式,身體都成為他們作為哀悼者在創(chuàng)傷作用的停滯狀態(tài)下自我意向的表達(dá)出口。身體作為一種隱喻的方式,將觀眾引導(dǎo)至自行選擇“意義”闡釋的分岔路口。人物不再僅僅是承載唯一具體意義的功能性符碼,而是回歸到日常生活狀態(tài)的“身體”本身,由于它是活的主體,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個(gè)體表達(dá),因而在虛構(gòu)中呼應(yīng)著生活更為普遍的“真實(shí)”。
(二)語言失效
“飯桌”在傳統(tǒng)日本家庭片中往往承載著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的文化含義,但在該片中,濱口將其賦予新的內(nèi)涵,即一種哀悼的儀式場(chǎng)所——哀悼語言的死亡。
人與人的溝通是否可能?當(dāng)人與人之間無法溝通時(shí),該怎樣彼此理解呢?
聾啞演員原本是舞蹈工作者,流產(chǎn)后失去了舞蹈的能力,在丈夫的鼓勵(lì)下嘗試表演。表演作為一種用身體與外界聯(lián)結(jié),表達(dá)自我的方式,成為聾啞演員從語言失效的停滯世界進(jìn)入意義流動(dòng)的新世界的一種路徑。
而年輕男演員高槻作為分裂的家福的反面,始終忠實(shí)于通過身體感知直接應(yīng)對(duì)這個(gè)不確定的世界。面對(duì)情人的丈夫,高槻并不避諱他對(duì)音的崇拜之情。面對(duì)偷拍者,高槻傾向于用身體做出直接的反擊。與發(fā)現(xiàn)妻子出軌第一時(shí)間選擇逃避和壓抑內(nèi)心的家福相反,高槻作為家福的鏡像,以“真實(shí)”的象征意味威脅性地存在于他的世界中。相比語言,高槻是用身體進(jìn)行學(xué)習(xí)和感知的人類。家福認(rèn)為“不能自控”是高槻作為演員的優(yōu)勢(shì),相對(duì)應(yīng)的“過于控制自己的情感”則是家福作為丈夫的失職。
從人物設(shè)置上看,面對(duì)語言溝通的失效,手語演員和男演員高槻給出的解答是:以身體回應(yīng)內(nèi)心,用身體表現(xiàn)內(nèi)心。從電影文本上看,濱口讓異國(guó)演員和聾啞演員一起排演戲劇,象征性地創(chuàng)造出一座語言的巴別塔,試圖探索人與人之間是否真的能夠互相溝通與理解。此外,契訶夫戲劇的臺(tái)詞與家福內(nèi)心情緒的契合,亡妻音口述的故事對(duì)自身及家福二人處境的影射,都共同為電影的劇作層次、人物形象深度注入了豐富的精神內(nèi)涵,呈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文本間性特征。在這其中,萬尼亞舅舅的戲劇世界與家福的精神世界重合對(duì)應(yīng),并與現(xiàn)實(shí)世界并置,創(chuàng)造出看似偶然實(shí)則精妙工整的平行發(fā)展的想象空間。戲劇與電影融合,演員與角色間離,現(xiàn)實(shí)與想象并行的文本策略成為《駕駛我的車》中行之有效的實(shí)驗(yàn)機(jī)制,為觀眾提供嘗試聽懂聽不懂的語言,看見看不見的東西的可能。
二、分裂的空間:建構(gòu)空間就是建構(gòu)內(nèi)心
(一)私人空間
濱口龍介擅長(zhǎng)利用空間修辭和時(shí)間變換促使人物命運(yùn)的戲劇性自然生發(fā),同時(shí)使用冷靜疏離、去戲劇化的鏡頭語言呈現(xiàn)偶然性事件,最大程度激發(fā)觀眾的想象空間,讓電影成為產(chǎn)生魔法般敘事效果的實(shí)驗(yàn)場(chǎng)所。在《駕駛我的車》中,心理創(chuàng)傷的空間化處理使得私人情感可視化,而實(shí)在空間的創(chuàng)傷化處理使得特定空間得以成為哀悼過程發(fā)生的舞臺(tái)。
莫里斯哈布瓦赫認(rèn)為:“每個(gè)家庭單獨(dú)保存的回憶和秘密,不僅再現(xiàn)過去還規(guī)定著它的本性、特征和弱點(diǎn)”⑤。因此,家庭空間往往是創(chuàng)傷敘事展開敘述的場(chǎng)域。家福與音的家雖然是濱口電影中常見的西方現(xiàn)代化空間造型,但二人的情感表達(dá)卻是十分東方化的隱匿。濱口用幽暗與明亮的對(duì)比色調(diào)表征家庭空間外在與內(nèi)核的反差。家福唯一一次瞥見這個(gè)“完美”空間的裂縫,是無意間撞見妻子出軌的場(chǎng)面,濱口利用鏡像將家福夾在分裂的兩個(gè)空間的縫隙中,外化著家福想象與現(xiàn)實(shí)的斷裂。無疑,家庭圖景成為呈現(xiàn)分裂狀態(tài)的社會(huì)的一個(gè)縮影與隱喻。[4]與實(shí)在的家庭空間相對(duì),音虛構(gòu)故事中男孩的家成為另一個(gè)具有表征意味的空間存在。在音口述的故事中,少女每次潛入男孩的家中都會(huì)留下一個(gè)物件作為自己存在的證據(jù),然而男孩卻選擇無視。虛構(gòu)故事中男孩的家是家福內(nèi)心的隱喻也是音心理創(chuàng)傷的空間化表征。音的身體處于現(xiàn)實(shí)的家宅空間中,意識(shí)寄居在虛構(gòu)的房子里。無論實(shí)在空間還是精神空間都同時(shí)詢喚起音的創(chuàng)傷記憶和情感想象。濱口對(duì)私人敘事的空間化處理決定了音獨(dú)自死在家中的偶然中存在著殘酷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與濱口影像相違和的強(qiáng)戲劇性元素,同時(shí)塑造出家福既是受到背叛的受害者,又是間接殺死妻子的加害者這一分裂的身份定位。
(二)公共空間
在電影中,家福作為藝術(shù)指導(dǎo)前往廣島排演一場(chǎng)戲劇。濱口將村上春樹原著里發(fā)生在釜山的故事搬往到了廣島。廣島作為對(duì)日本乃至世界都意味深長(zhǎng)的特殊地標(biāo),無疑是承載個(gè)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重要空間載體。作為日本人核災(zāi)難的記憶之場(chǎng)空間,電影幾乎是不可避免地提醒著日本觀眾共同的歷史創(chuàng)傷。濱口曾對(duì)記者說:“現(xiàn)在生活在廣島的百姓也負(fù)擔(dān)著這種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人的沉重感,把這種怪異的平衡感融入電影中也是很有趣的。”⑥不難看出濱口將故事搬到廣島暗含的地理政治化含義。
此外,電影中幾場(chǎng)重要的談話都是在酒館、海邊、和平紀(jì)念公園諸如此類的脫離社會(huì)監(jiān)禁的公共空間中進(jìn)行,這種游離中心權(quán)力以外的曖昧空間催生人物將注意力聚焦在私人問題上,使得平日所壓抑的情感得以浮出表面。而電影中極為關(guān)鍵的紅色轎車,作為彌合公共空間與私人領(lǐng)域,連接現(xiàn)代化都市表層與現(xiàn)代人孤獨(dú)內(nèi)里的能指符號(hào)存在。它既承擔(dān)著特定的敘事功能和表意功能,又成為人物身體感知的物質(zhì)化延伸。譬如在電影中,每當(dāng)家福在車內(nèi)與他人完成一場(chǎng)袒露內(nèi)心的交談后,車身便會(huì)穿過深長(zhǎng)的隧道,迎來光明。
在開往北海道漫長(zhǎng)的車程中,渡利談起自己尚未救出母親的事實(shí),家福也坦誠(chéng)傾訴了自己不敢回家從而間接殺死妻子的心結(jié)。二人作為幸存者,雙雙直面自己作為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雙重身份。由此,這段路程既是物理空間的流動(dòng)也是心理空間的前進(jìn),哀悼者通過回顧過去,將停滯的創(chuàng)傷時(shí)空與前進(jìn)的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平行化處理。一方面,觀眾所看到的是物理時(shí)間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另一方面,通過二人的講述,觀眾感知到那個(gè)過去的,由逝去之人賦予意義的世界。此時(shí)濱口的電影成為德雷茲所言的“時(shí)間-影像”,將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個(gè)時(shí)態(tài)置于同一畫面中,推動(dòng)觀眾對(duì)畫面以外所存在之物的想象與理解。
“創(chuàng)傷性地點(diǎn)的特征是它的故事是不能講述的。這個(gè)故事的講述被個(gè)人的心理壓力或者團(tuán)體的社會(huì)禁忌阻滯了。”⑦渡利和家福同時(shí)作為幸存者和加害者,對(duì)罪惡的懺悔是通過重回記憶之地直面創(chuàng)傷達(dá)成自我療愈。遭遇山洪的廢墟可以被個(gè)人記憶替換為任何一個(gè)創(chuàng)傷性地標(biāo)。此時(shí),多維的地標(biāo)凝結(jié)在同一個(gè)畫面中,這片被雪掩埋的廢墟作為可見的創(chuàng)傷實(shí)則隱喻著那些不可言說的創(chuàng)傷,召喚著觀眾身體中與意識(shí)切斷的創(chuàng)口,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幸存者和哀悼者的情感共振。
在過往的廢墟面前,家福與渡利相擁達(dá)成了對(duì)他人的理解和自我的和解,與死者的世界告別。像契訶夫筆下絕望的人物那樣,重建希望,繼續(xù)生活下去。作家霍桑認(rèn)為,罪責(zé)和創(chuàng)傷是社會(huì)疾病的癥狀,它們的根源是虛偽和對(duì)自我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濱口通過空間修辭締造的時(shí)間影像,將觀眾真實(shí)的自我從粉飾太平的虛幻謊言中拖拽出來。此時(shí)文本可以發(fā)生在任何人身上,萬尼亞舅舅可以是我們每一個(gè)人。
結(jié)語
哀悼作為一種儀式,所強(qiáng)調(diào)的并非忘記傷痛,而是如何帶著傷痛生活下去。濱口龍介通過捕捉后3·11時(shí)代下無處釋放的,以社會(huì)集體無意識(shí)存在的哀悼情緒,描寫具體人物在具體情境下的個(gè)性化感知。通過探索對(duì)外表演和對(duì)內(nèi)表演,書寫了對(duì)“絕望者如何生活下去”的現(xiàn)代性思考;3·11之后所有的樂觀都是絕望下的樂觀,希望就像等待戈多中的戈多,我們不知道他會(huì)不會(huì)來,什么時(shí)候來。但我們不能放棄。對(duì)于日本電影制作者來說,他們不能放棄表達(dá)。對(duì)于日本觀眾來說,他們不能放棄繼續(xù)生活。
“一切都會(huì)好起來的。”是家福在雪地里于己于人的鼓勵(lì),也是濱口送給日本意味深長(zhǎng)的禮物。
注釋:
①Yutaka Kubo.Still Grieving: mobility and absence in post-3/11 mourning films[J].Journal of Japanese and Korean Cinema,2019,11(1).
②吳艷茹.從電影《藍(lán)》看喪失、抑郁和哀悼[J].心理學(xué)通訊,2020,3(04):267-272.
③王寧寧.梅洛龐蒂身體現(xiàn)象學(xué)的語言觀[D].華東師范大學(xué),2017.
④[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181.
⑤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⑥乒乓臺(tái).電影的擴(kuò)容術(shù)——書影對(duì)照集之《駕駛我的車》[J].書城,2022(02):102-113.
⑦[德]阿萊達(dá)·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