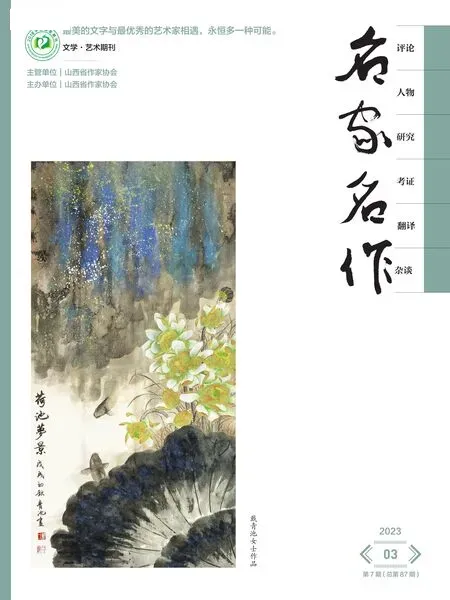從文字走向影像
——淺析小說《活著》的電影改編
李夢楠
一、引言
人們常說:小人物,大社會。長久以來,個人的生命歷程往往是所經歷的時代的反映,普通人的一生往往就是他所處時代的縮影。余華的《活著》正是通過徐福貴這一人物的命運及家庭變化展開論述的,而張藝謀導演改編的電影《活著》更是對徐福貴這一人物進行了細致的刻畫。從文字走向影像,無論《活著》如何改編,作者和導演都在講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難,講述人是為了活著本身活著。本文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淺析小說《活著》的電影改編,讓讀者能夠從不同的角度領悟活著的真正意義。
二、敘述角色的轉換
(一)小說中的敘述視角
在小說《活著》中,作者余華運用了兩個敘述者,這兩個敘述者分別是“我”和福貴。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的人,在收集民間歌謠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福貴,并聽他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我”是扮演對福貴一生經歷的重述者。這里的“我”并不是作者本身,而是作為一個敘述者陳述別人的故事,作為小說故事中的旁觀者,“我”與故事中的主要事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這種差距反而讓“我”對故事情節的敘述更加客觀。“我”雖然是小說中的第一人稱,但這個“我”同所講述的故事情節幾乎不發生任何關系,僅僅是個旁觀者而已,這樣的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更加接近。小說中另外一個重要的敘述者就是福貴,作為小說《活著》的主人公,福貴是在講述自己的故事。作者余華在日文版自序中寫道:“我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福貴的講述里不需要別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講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稱來敘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貴在讀者的眼中就會是一個苦難中的幸存者。”①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13,第11-12 頁。小說中“我”與福貴這兩種敘述視角相交織的手法更能讓讀者體會到福貴的生活經歷,體會到活著真正的意義。
(二)電影中的敘述視角
在張藝謀導演改編的電影《活著》中,電影的敘述視角并沒有小說中的“我”與福貴這兩種敘述視角相交織的手法復雜,電影《活著》把“我”這個第一人稱去掉了,把福貴這個人物放在熒幕前讓觀眾感受他的人生經歷,這種以旁觀者為主的視角去領悟“活著”真諦的做法,似乎與前一段所引述的作者余華在日文版自序中有關敘述視角的看法相違背,張藝謀導演是用一種溫情的視角詮釋作品,通過電影演繹感悟活著,領悟生活的真諦。此外,電影《活著》不同于小說的敘述順序,小說《活著》是采用倒敘的手法展開敘述的,是以福貴的回憶為主線敘述故事的,而電影《活著》是采用順序的手法展開敘述的,是從福貴的生活由富到窮一一展開的。另外,電影《活著》的敘述焦點更為集中,電影將焦點集中在福貴身上,由福貴自己講述自己的生活可以讓我們更加直觀地從福貴身上得到生命啟示。福貴這一人物貫穿電影的始終,電影中的故事情節是以福貴為中心展開敘述的。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的改編,《活著》中的福貴都讓我們體會到不管生活中經歷多大的苦難,只要我們自己能在苦難中感受到幸福,那我們就是生活的幸運者。
三、故事情節安排的變化
(一)背景的變化
小說《活著》中的福貴是一個在經歷家庭變故后生活在農村并以種地為生的農民,破舊的茅屋成了他與家人的避風港,五畝田地是他們一家人賴以生活的物質基礎,他們穿著破爛的衣服,看不起病甚至連一頓像樣的飯也吃不上。筆者認為,小說《活著》營造出了一種凄涼、同情的氛圍,而在電影《活著》中福貴雖然也經歷了由富到窮的生活過程,但是并沒有小說中那樣一貧如洗。電影中福貴一家是生活在城鎮上,這一點就與小說有所區別。此外,電影中福貴一家的生活也是貧苦的,但是并不像小說中那樣看不起病甚至是吃不上像樣的飯,他們一家過著如普通人一般平凡的生活。電影《活著》中福貴以表演皮影戲為生,他帶著皮影工具到處表演,這一點也與小說中福貴以種田為生有所區別。張藝謀導演在執導電影《活著》時并沒有一直沿襲小說《活著》悲涼、凄冷的基調,而是在電影中營造了一種溫情、溫暖的氛圍。小說與電影故事背景的不同并不能說明孰優孰劣,作者余華有他的創作意圖,當然張藝謀導演肯定也有他的改編之意,我們應該站在不同的故事背景下領悟“活著”真正的人生內涵。
(二)人物命運的變化
在小說《活著》中,與福貴有親戚關系的人都相繼離他而去,就連福貴的戰友春生及春生的老婆也都去世了,福貴成了無依無靠的孤獨老人,一頭牛是他唯一的生活伴侶和精神寄托。在小說中,福貴的父親從糞缸上摔下來摔死了,他的母親得病去世了,作為讀者本以為這已經是福貴經歷的最大苦難,但是苦難并沒有停止,幸運也似乎跟福貴毫無關系。他的兒子有慶在醫院被抽血抽死了,他的女兒鳳霞因為生孩子在醫院大出血死了,醫院成為福貴一家揮之不去的陰影。再后來他的妻子家珍因為得了軟骨病也去世了,他的女婿二喜被兩排水泥板夾死了,最后就連他唯一的親人外孫苦根也因為吃豆子撐死了。小說中親人一個個相繼離去,讓讀者感到悲痛不已。小說《活著》給予讀者的是一種悲情的氛圍,而在電影《活著》中悲的氛圍依然存在,但我們體會到更多的是溫情。在電影中,福貴的父親是因為福貴賭博輸光家產氣死的,這點與小說中福貴父親的死有所區別,他的母親與小說中寫的一樣因為生病去世了,他的兒子有慶被徐區長的車撞死了,這一點也與小說有所不同,他的女兒鳳霞也與小說中的人物命運一樣是因為生孩子大出血死了。雖然電影中福貴的爹娘和他的兒子有慶、女兒鳳霞的命運和小說中寫的一樣悲慘,但是電影并沒有像小說中寫的那樣,電影中福貴的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和外孫饅頭沒有和小說中一樣的悲慘命運,他們和福貴生活在一起,陪伴在福貴的身邊。電影中留給我們的最后一個鏡頭是福貴一家在飯桌前吃飯,這是多么溫暖的一個畫面,筆者認為張藝謀導演或許也是想向我們傳達這一份溫暖與溫情。電影《活著》對小說中各個人物的命運進行了移植和改動,而且電影就各個人物的結局來說更真實一點。無論小說與電影中人物的命運如何改變,唯一不變的是福貴這一人物,從福貴身上我們深切地體會到“活著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活著一切才都會有希望”。我們應該像福貴一樣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時堅韌地活下去。
(三)時間點的明確安排
作者余華曾在日文版自序中提到“時間”一詞,他說道:“我相信是時間創造了誕生和死亡,創造了幸福和痛苦,創造了平靜和動蕩,創造了記憶和感受,創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創造了故事和神奇。”①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13,第12 頁。小說《活著》就是作者在時間的神奇下得以完成的,時間是小說的發展線索,但是筆者認為在小說《活著》中時間這條線索是隱藏在故事之中的,我們需要在福貴的人生經歷中感受時間帶給他的遭遇和變化。小說《活著》這種時間點的隱藏在張藝謀導演改編的電影《活著》中被徹底顛覆了,電影在處理時間這一問題上不同于小說將時間表現得隱晦,而是明確表明各個階段的時間點,然后在這些時間點里講述福貴的人生起伏。比如,在20 世紀40 年代這個時間點里,福貴經歷了由富到窮的人生變化,因為賭博輸光了家產,父親也因為他輸光家產而被氣死了。福貴由地主變為窮人,一家人靠福貴到處表演皮影維持生活,此外在這一時間點里,電影也講述了福貴被抓去當壯丁的經歷。在20 世紀50 年代這一時間點里,中國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大躍進”運動,福貴在這一階段經歷的最大人生變故就是他的兒子有慶被車撞死了。20 世紀60 年代,中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一時間點里,對福貴一家既是物質滿足又是精神寄托的皮影被當作典型的“四舊”燒掉了。同時,福貴的女兒鳳霞經歷了結婚、生子,但是幸福對福貴一家來說是短暫的,鳳霞因為生孩子大出血去世了。在這一時間點里福貴一家經歷了不幸。電影還分割出“以后”這一時間點。20 世紀的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和“以后”這四個明確的時間點在電影中的安排不僅可以讓觀眾梳理出電影的故事脈絡,而且可以讓觀看者在不同的時間背景下真切地感受到福貴的人生起伏。
四、從“皮影”這一意象角度分析電影《活著》對小說《活著》的改編
皮影作為電影《活著》新添加的一種意象具有深遠的意義,它作為電影貫穿始終的意象,不僅僅是作為一條線索帶領觀眾體會福貴的人生變化,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著一種人生態度。皮影第一次出現是在福貴所在的賭場上,福貴在輸錢之后親自操演皮影戲,皮影與福貴的影子在布幕上相互交映,其實這也預示著福貴如皮影一樣被人操控,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在電影中皮影多次出現,如果說皮影的第一次出現是一種預示,那么電影中隨后皮影的多次出現可以說是一種印證,印證了福貴如被人操控的皮影一樣,命運悲苦。皮影第二次出現是在福貴輸光家產的一年多以后,他為了養家糊口,到龍四那里借來了皮影,開始了四處奔波的流浪藝人生活,但是他在外出謀生的時候卻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后又成了解放區的俘虜,最后又幸運地回到家中,一家人得以團聚,還為自己增加了一段干革命的經歷。福貴被人操控的皮影人生并沒有結束而是愈演愈烈。電影中有這樣一幕,當福貴的兒子有慶被徐區長的車撞死后抬回來時,福貴站在表演皮影的布幕前望著被抬回來的兒子的尸體,這一幕多少會讓觀眾有些心痛,我們會在同情福貴的同時也感嘆他如布幕上的皮影一樣被人擺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福貴家的皮影成了典型的“四舊”,福貴沒有保住皮影,在鎮長的監督下把皮影燒了。皮影在電影中再沒有出現,但是福貴的皮影人生并沒有結束,災難再一次降臨到福貴一家人身上,他的女兒鳳霞因為生孩子大出血去世。電影中皮影場景的安排無不在揭示福貴如皮影一般被人操控,但是電影中皮影的安排又有另外一番寓意。皮影是福貴悲慘命運的縮影,但皮影也是堅強的一種折射,福貴是被人擺弄的皮影,但他卻像皮影一樣歷經風雨仍堅強地活著。電影中福貴被人抓去當壯丁期間,有人讓他把皮影扔了,但是福貴說:“這是借人家的還得還,以后還指著它養家。”這說明在福貴心中或許皮影不僅是他養家的工具,從某種程度上還代表著他對回家的期盼與渴望。此外,在電影中當皮影被燒掉時,福貴對鎮長說:“家珍一看見這個,就想起有慶來了。”在這處場景中,我們會暫時忘記福貴被人操縱的皮影人生,我們更多想到的是皮影帶給福貴一家的念想和精神寄托,皮影作為電影中一個新的意象,也是最能表現福貴人生經歷的意象,它向我們揭示了福貴如皮影一樣被人操控的不幸命運,也從另一方面詮釋了活著的積極意義。皮影對福貴一家來說是不幸的縮影,但也是福貴一家的精神依靠。
五、結語
小說《活著》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境遇,展現了老百姓最普通的生活經歷,它讓我們知道什么是活著,“活著就是為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東西活著”。就《活著》來說,和現實相比,小說更具悲劇性,小說中的主人公福貴失去了所有的親人,最后只有一頭老牛和他相依為伴。當我們在讀小說時會沉浸在這種悲傷的氛圍中,感嘆福貴的悲慘命運。電影《活著》相比小說《活著》的悲劇性更顯溫情色彩,電影雖然也是在一種灰暗的色調下安排情節,但是電影中的主人公福貴則要比小說更幸運。在電影的最后福貴和他的老婆家珍、女婿二喜、外孫饅頭一起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同時,電影更貼近生活,更能讓觀眾透過電影中的福貴感同身受,從而拉近與觀眾的距離。無論是小說《活著》還是電影《活著》,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不管身處何種境地都應該明白唯有活著一切才會有希望,我們應該勇敢面對生活中的苦難,學會忍耐,只有忍耐住、經得住苦難的磨煉,我們才會更好地活著,從而體會到活著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