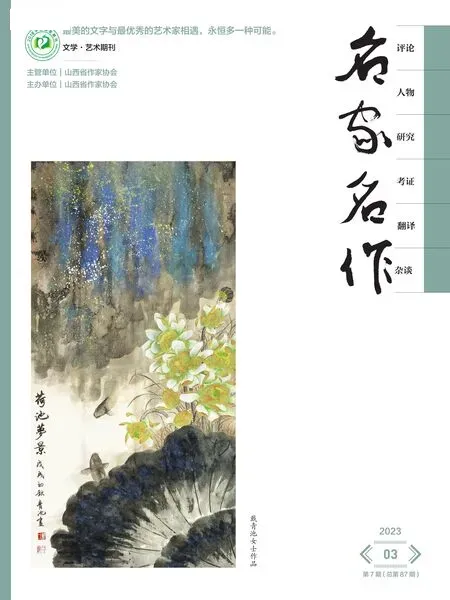電影中的表現美學、再現美學及二者的融合范例
趙小慶
一、表現美學
提及電影中的表現美學,最早應該追溯到著名電影大師、被譽為“戲劇電影之父”的喬治·梅里愛。與其說喬治·梅里愛是一位電影制作者,不如說他更像是一位電影魔術師。他把許多優秀戲劇進行改編,使其登上了電影銀幕。同時,他會把戲劇中所使用的技巧和方法運用到電影中去,演員們夸張的動作、手勢和奇異的裝扮,創造出許多戲劇化的場景和情節設定。在他眾多的電影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誕生于1902 年的《月球旅行記》,這部影片被譽為“歷史上最早的科幻電影”,講述了一群天文學家乘坐炮彈到月球探險的故事。梅里愛在影片中大膽嘗試了疊影、拼接鏡頭、淡入淡出等當時全新的手段,還融合了大量舞臺特效、蒙太奇手法,讓電影真正成為造夢的世界。
時代在不斷進步,電影產業和電影技術也跟隨著時代的洪流不斷向前推進,單一的情節和拍攝手法已經無法滿足電影造夢者們,他們試圖將更多的美學理論和藝術手法相結合,打造極具模式化和商業化的電影,為觀眾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視聽盛宴,好萊塢電影工業就此誕生。表現美學在經典好萊塢時期的影片中尤為凸顯。經典好萊塢時期為20 世紀20 年代至50 年代末,在這一時期,由于美國的經濟發展較快,好萊塢地區涌現了一批諸如米高梅、派拉蒙、哥倫比亞、華納兄弟等電影制片公司,逐步形成了制片人制度和明星制。與此同時,電影藝術的流程化制作逐漸產生了喜劇片、西部片、犯罪片、幻想片四大類型電影,進而產生經典好萊塢敘事系統。影片基本由攝影、場面調度和剪輯方面的常規慣例組成,其目的在于把虛構的事件、人物和時空自然地黏合在一起,將現實和虛構影片無限地接近,給予觀眾近乎真實之感。
從1903 年的《火車大劫案》的連續性剪輯到1915年的《一個國家的誕生》中的“最后一分鐘營救”,從機智勇敢的牛仔到兇狠的黑幫強盜,戲劇化的故事結構和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成為好萊塢影片必不可少的兩大元素,自然流暢的連續性剪輯和閉環式的大團圓結局也讓經典好萊塢的電影敘事系統逐漸完善。
二、再現美學
“再現”,顧名思義就是再次重現,電影的一大魅力就在于運用攝影機使得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可以再次重現在銀幕之上。被譽為“法國影迷的精神之父”“電影的亞里士多德”的世界電影大師安德烈·巴贊推崇紀實美學,發現并總結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的藝術特征和影片的重要價值。他在自己的兩本著作《電影影像本體》和《電影是什么》中深刻闡述了蒙太奇與景深鏡頭在電影語言中的重要性與辯證關系,并提出了長鏡頭理論。雖然巴贊沒有拍攝過電影,但他運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多種人文學科對電影進行研究,突破了傳統的電影格局,成為世界電影理論中不負盛名的電影理論家。巴贊之所以推崇景深鏡頭和長鏡頭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原因——真實性和思辨性:首先,他認為景深鏡頭能最大限度地拉近觀眾和畫面的距離,景深鏡頭更加貼近真實生活,不管影片內容是什么,在畫面上就能先讓觀眾感受到真實場景,從而引發觀眾的共鳴。其次,巴贊認為電影語言最大的特性是記錄時間和再現空間,如果采用大量的場面調度和蒙太奇,那么所傳達的事件和意義就顯得形式化和單一化,這就與真實生活產生悖論。生活是豐富且含義深刻的,是需要人們深入思考的,長鏡頭的節奏感更能引發觀眾思考其內涵,而不僅僅停留在畫面的美感和沖擊力上面。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無疑是安德烈·巴贊紀實美學的最好映射,也是再現美學的典例。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主張實景拍攝,強調自然光線的運用,不喜人為的加工、干預以及攝影棚拍攝。內容上主要聚焦人們真實的生活和底層小人物故事,多為“失業”“貧困”等戰后社會情況。在電影手法上,大量運用長鏡頭、景深鏡頭,用紀錄片的方式拍攝故事片,多選用非職業演員進行表演,以求真實的質感。在故事情節上做到刪繁就簡,通常情況下描繪的是一類人而不是單獨的個體,所以重要人物較少。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一定會提及《偷自行車的人》,這部作品根據真實新聞改編而成,在和生活的貼近性和真實感上毋庸置疑。《偷自行車的人》講述的是“二戰”過后,羅馬同許多城市一樣,充斥著失業和貧困,人們常常為一個工作機會爭得頭破血流,電影通過戰后意大利工人的悲涼遭遇,反映了當時意大利的真實社會狀況。新現實主義提倡“還我普通人”“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去”等口號,在這部影片中大量使用了長鏡頭跟拍,極少使用特寫鏡頭,光線上力求使用自然光,也沒有使用任何布景,整個事件發生的地點都在羅馬的街頭。電影中的主角安東的扮演者本身就是一名失業工人, 故事情節也非常簡單,甚至可以用一句話簡單概括:失業工人和他的孩子,為了尋找他們丟失的自行車,在羅馬街頭奔波24 小時,結果一無所獲。但是越簡單,越深邃,正因為這簡單情節的敘述,影片卻傳達出直抵人心的無奈與悲愴。最后的鏡頭,孩子拉著父親的手,兩人繼續向前走,如此細膩的鏡頭展現出感人至深的父子情。
用最直接的方式拍攝真實生活,表現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才是再現美學給觀眾帶來的思考。
三、表現美學與再現美學的融合范例
時代在進步,電影思維也在與時俱進。如果固化在某種方式上去做一件事,可能結果并不會理想,拍攝電影亦是如此。過于在乎畫面和戲劇化劇情的呈現,可能會陷入浮夸風思維,長時間的工業化產出想必觀眾也會審美疲勞;反之,一味追求場景和故事的真實,執著于單一鏡頭的拍攝手法而忽視了電影娛樂性和可看性的特征,可能會讓影片缺少活力。優秀的電影人努力在探索和嘗試,不斷將表現美學和再現美學相磨合,我們不難發現二者并不是對立關系,在保持各自獨特性的同時使兩者相結合,會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而這樣的嘗試從未停止,從而誕生出許多在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
(一)《摩登時代》
在經典好萊塢時期,涌現出許多影視巨星,查理·卓別林就是其中之一。肥褲子、破禮帽、小胡子、大頭鞋,再加上一根從來都不舍得離手的拐杖,這些帶有記憶點和符號性的物品都讓卓別林成為影史中的經典。在卓別林的電影中,他一直關注對社會底層人物的描寫,不管是《城市之光》中的賣花女、流浪漢還是《摩登時代》中被壓榨的工人,他的創作都取材于真實生活中的小人物。要想創作出好的電影和人物,離不開觀察生活,從生活中汲取人物原型和故事靈感,所以他所塑造出的流浪漢角色和失業工人角色都家喻戶曉。
1928—1934 年,是美國電影轉變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工業生產面臨危機,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這時卓別林自編自導自演了《摩登時代》。卓別林在拍攝《摩登時代》的時候,好萊塢已經進入了有聲時代,但是他堅持以默片的手段拍攝,沒有對白的加持,只靠滑稽的動作和表情,或許更能從喜劇中體味出悲劇意味,領悟到生活的真實。影片絕大部分鏡頭使用全景,卓別林曾經說過:用特寫鏡頭看生活,生活是一個悲劇;但用長鏡頭看生活,生活則是個喜劇。所以在影片中我們能看出卓別林的整體思維——喜劇用全景,悲劇用特寫,這是對他電影及表演的最好詮釋。在《摩登時代》中,卓別林并不按照經典好萊塢的敘事模式故意營造沖突,也不常使用剪輯來切換影片的空間和節奏,而是著眼于他大段的長鏡頭個人表演段落。卓別林對小人物的塑造和長鏡頭使用的創作思維反映出他對再現美學所倡導的真實性的理解和詮釋。
但與此同時,卓別林并沒有完全摒棄戲劇化敘事手法,最值得提及的就是他在影片中采用了蒙太奇手法致敬電影《罷工》,影片一開頭就通過羊群和工人的對比蒙太奇,諷刺了在機械時代中的工人就和被飼養的羊群沒有任何差別,任人宰割。工人就像羊,是資本家的奴隸。而失業之后由于種種陰差陽錯,被警察誤抓后在監獄里意外成為英雄等許多滑稽的情節,在好萊塢敘事模式基礎之上,引發了人們更深層次的思索。
卓別林用黑色幽默的方式開創式地詮釋了現實與幻想,生動地展現了普通工人在社會大背景下的無奈和心酸。安德烈·巴贊曾評價《摩登時代》這部影片:“ 稱得上是唯一充分再現了20 世紀人類面對社會和技術機械時的彷徨感的電影寓言。”
(二)《1917》
同為好萊塢影片,與經典好萊塢時期的特征不同的是,當代好萊塢影片多為科幻、魔幻、特工和超級英雄等題材,多為表現美學特征極強的大制作,紀實性電影出現在大銀幕的頻率在減少。但在2020 年斬獲奧斯卡最佳攝影、最佳視聽效果和最佳音響效果三項大獎的《1917》,是近年來表現美學與再現美學結合的佳作。《1917》講述的是“一戰”時期,因為敵人切斷了所有的電話線,兩名年輕的英國士兵斯科菲爾德和布萊克被長官派去前線第二營,告知他們在黎明時停止作戰。為了拯救成百上千的生命,兩人冒險穿越敵境傳遞重要情報。
從劇本結構來看,影片呈現出表現美學的特征,延續了好萊塢經典敘事手法和閉環結構——設立典型人物和“謎團”,圍繞人物展開“解謎”過程,最后解決問題達到大團圓結局。尤其是在斯科菲爾德獨自一人遭受槍林彈雨的攻擊之后,卻在防空洞里遇見了避難的女子與嬰兒,刻畫出典型的好萊塢鐵漢柔情形象。影片開頭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原野,兩個士兵在大樹下悠閑地小憩;影片結尾斯科菲爾德獨自一人坐在大樹下撫摸家人的照片,前方仍然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原野,呼應了開頭,形成閉合結構,讓觀眾產生更多的思考。
但是影片最為震撼的一大核心要素是鏡頭語言,極致展現了再現美學的拍攝手法。攝影師應用了巴贊紀實美學“長鏡頭理論”,全片采用“偽”一鏡到底的方式,從士兵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敘述,最大限度地還原真實的“一戰”場景,把慘烈的戰爭現場和兩個士兵送信途中的種種磨難刻畫得十分細膩。影片中最為震撼的三個長鏡頭表達了主角不同階段的心境和處境:在影片最開始時,兩個士兵從大樹下走到戰壕里,接受命令后再次在戰壕中行進,整個節奏用長鏡頭語言一氣呵成,把士兵從最開始的欣喜到知曉任務后的焦慮這一過程都在兩人行走的途中展現出來;同時,這一長鏡頭把戰壕里的士兵群像也刻畫得十分真實,展現了備戰的焦灼狀態。第二個值得回味的長鏡頭是半夜斯科菲爾德在被狙擊手襲擊后醒來,在火光的映射下、在槍林彈雨中絕處逢生。他的影子倒映在破敗的墻面,光影交錯形成極致美感。他內心的信念感支撐著他一直向前奔跑,在絕望中奔跑。第三個鏡頭為影片的高潮部分,斯科菲爾德到達目的地戰壕后,在戰火中不顧一切地奔跑,驚心動魄的爆破場景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張弛有度的長鏡頭和細膩的場面調度讓動和靜、虛與實都融洽地在這部影片中共存。
四、總結
在電影藝術中,表現美學和再現美學絕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互相成就的關系。表現美學用肆意張揚的技巧捕捉每一個動人的故事,像是熱血的青年在田野上肆意奔跑;而再現美學使用原始的不加修飾的鏡頭語言,更像是返璞歸真的長者,冷靜地觀察世界。如果導演只在一種風格上追求極致無疑值得觀眾細細品鑒,但容易讓影片本身缺少彈性和包容性。基于二者獨特性之上的融合發展,會使得影片的敘述手段更加多元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