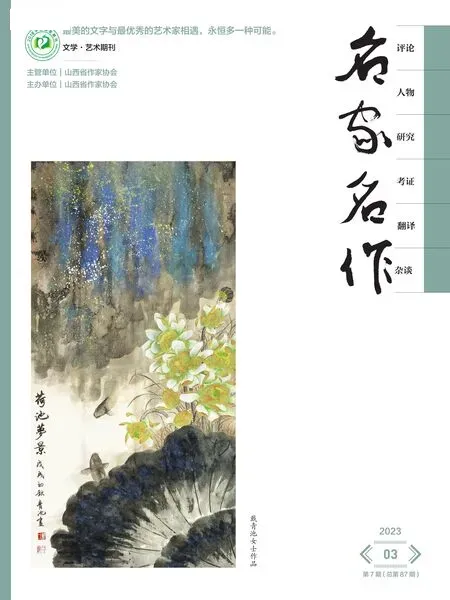舊體詩詞的當代命運
——以《詩刊》為例
祝 歡
一、引言
近年來,舊體詩詞研究逐漸成為熱點,研究成果碩果累累。眾多研究成果之中,個案研究與舊體詩詞入史問題研究較多,回到歷史現場,在報刊上從傳播視角研究舊體詩詞文體命運的成果還比較少。受語言工具所限,舊體詩詞自現代文學開端就被打上“舊”的標簽驅逐出新文學的行列,舊體詩的“非法”性甚至延續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然而隨著《詩刊》創辦與領導人舊體詩詞的發表,區分新舊文學的標準由只看形式擴大到兼顧內容,舊體詩詞在此背景下才獲得呼吸,取得了本該有的“合法性”地位。本文試圖從《詩刊》(1956—1964)創刊情況談起,分析這一權威性刊物是如何為舊體詩詞爭取“合法性”地位,《詩刊》對舊體詩詞在當代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并說明語言問題是限制傳統詩詞在當代發展的關鍵因素。
二、《詩刊》的雙重屬性
《詩刊》的創刊經過,目前有兩個比較可信的說法,一是臧克家的爭取。“大家都說,詩歌需要一個陣地,應該搞個刊物才好……我把這些事情向黨組負責人劉白羽同志談了……不久,劉白羽同志到我筆管胡同的宿舍來了,說:領導已經同意詩刊出版。”[1]二是說《詩刊》的創立是徐遲的積極倡導,在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二次理事會議快要閉幕的時候,“他舉手從坐席臺上站起來發言:中國是個泱泱詩國,建議創辦一個專門發表詩歌創作和評論的刊物,就叫《詩刊》好了。”[2]不論《詩刊》具體的創刊情況是哪一個,我們都可以從當事人的回憶中發現,從一開始《詩刊》就帶有官方與民間雙重性質。
不論具體的創刊情況怎么樣,“黨的關懷”是回憶錄中著重強調的一點。強調這點說明的不僅僅是《詩刊》的合法性地位,更強調的是《詩刊》是全國性的權威詩歌刊物。
第一,在詩人群體選擇上,應“雙[1]百”方針的倡導,《詩刊》編輯部團結老中青三代作家并積極挖掘新人,繁榮詩歌創作,廣泛邀請各派詩人參與。艾青在《詩刊》上發表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代表了早期詩風的回歸,抽象、新穎、獨特,給詩壇帶來了從只注重思想到也注重藝術性的新變化。甚至《詩刊》還請已經在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陳夢家在刊物上談談其人其詩在很長時間都是禁區的徐志摩的詩。不僅如此,《詩刊》同時還邀請公劉發表了《遲開的薔薇》,敢在刊物上發表愛情詩,在當時來說是大膽的。第二,《詩刊》個性的是主編與副主編的政治身份。在強調階級成分的年代,臧克家是地主階級出身,從政治面貌來說,臧克家是民盟成員。《詩刊》副主編的徐遲也非黨員身份,但最能體現《詩刊》獨創性與個性的大膽舉措是公開刊登舊體詩詞。
這個時期人們普遍認識到新詩的發展仍然存在不足,蘇聯文學的前車之鑒使大家認識到,民族化發展才是新詩發展的出路,新詩發展應該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這個時期關于如何繼承古代文學遺產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李煜詞、陶淵明詩、山水詩、李清照詞、李白杜甫的詩都曾是20 世紀50 年代文藝界討論的熱點問題。討論并不在于就舊體詩論、舊體詩,討論的出發點與立足點是在如何借鑒古代的優秀遺產蓬勃當下的創作。這些討論最后形成的共識是,新詩應向古典詩歌和民歌學習。大眾一系列的關于如何借鑒與繼承古代遺產以及關于新舊詩歌的討論,正是立足于如何蓬勃新詩發展,一系列關于古典文學遺產的討論,使得詩歌與舊體詩又重新活躍了起來。正是在此背景下,《詩刊》發表舊體詩詞不僅僅是合乎風氣的做法,同時也有敢為人先、引領示范的勇氣。正是《詩刊》既具有官方的權威專業性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空間的雙重性,才可能會有發表并開創舊體詩欄目的自主性。
三、舊體詩“合法性”地位的獲得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文言為語言工具的傳統詩詞被冠以“舊”的標簽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白話文為語言工具的現代文學。以追求現代性為旨歸的現代文學拋棄了在他們看來束縛現代人思想的古代漢語,進而給一切文言作品貼上落后的標簽,自此傳統詩詞在文學史上一直被壓抑,其“非法性”地位甚至延續到了當代文學時期。但《詩刊》從創刊開始就為“非法”的舊體詩保留了位置,在《詩刊》的引領下舊體詩詞“合法性”地位最終得到確認。
1957 年創刊之前,毛澤東詩詞廣泛流傳但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版本,《詩刊》編輯部提議請毛主席在《詩刊》上發表一個定本。于是編輯部去信希望得到毛主席的回復與肯定,很快毛主席回信包括十八首舊體詩詞和關于詩的一封信。《詩刊》將《毛澤東詩詞十八首》和《關于詩的一封信》發表在《詩刊》創刊號頭條,引起了詩界巨大的反響。在1957—1964 年這八年中《詩刊》又陸續發表了毛主席共十九首舊體詩詞作。除此之外,《詩刊》還發表朱德、陳毅、董必武、李濟深等人的舊體詩詞共約四十首。領導人舊體詩詞的廣泛刊登,對于提高舊體詩的“合法”地位來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自從毛主席詩詞發表后,舊詩漸漸多起來了,并且也神氣起來了。”[3]許多作家和寫新詩的詩人開始寫作舊體詩詞,既寫新詩也寫舊詩的“兩棲”文人逐漸增多,例如茅盾、老舍、沈從文等新文學家都是在1957 年前后又開始寫作舊體詩詞的。
舊體詩能在當代取得“合法”性地位,領導人公開刊登舊體詩詞是根本原因,但《詩刊》煞費苦心創辦并保留舊體詩欄目也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然而“舊體詩頁”開辟出來后,要鞏固這個欄目絕非易事。雖然毛主席同意刊發其舊體詩鼓勵了舊體詩創作,但同時刊登的《關于詩的一封信》中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4]編輯部成員為鞏固舊體詩欄目,開始向社會各界詩人約稿。據《詩刊》原常務副主編楊金亭回憶,臧克家及《詩刊》社的同志們為了鞏固和堅守舊體詩這個欄目,動了不少腦筋“發表黨和國家領導人和文壇名家之作的不定期欄目,向詩人詞家乃至一般詩詞作家的每期兩頁的固定欄目過渡。”[5]從而擺脫了“舊體詩頁”只能借用領導人和名家名作維持的局面,使得“舊體詩頁”成為廣大詩人都能平等發表的欄目。由此,舊體詩才最終由“非法”性走上了“合法”的地位。
四、舊體詩復興的艱難
自《詩刊》刊登舊體詩詞后,最顯而易見的影響是公開發表舊體詩詞的刊物增多。各個雜志放開了手腳競相發表舊體詩,“而1957年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匯報》《人民文學》《詩刊》等中央和省市報刊上紛紛發表舊體詩詞作品,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文學景觀。其中,《光明日報》自1958 年1 月1 日起創辦了《東風》副刊,發表名家舊體詩詞是其特色之一。”[6]《詩刊》的成功示范后眾多刊物紛紛效仿,擴大了舊體詩的傳播途徑與生存空間。
其次是刺激了舊體詞創作。“各地報刊上發表了很多舊詩,甚至有些新詩人也寫起舊詩來,青年人也競相效仿。”[7]舊體詩詞合法性地位的取得,加之舊體詩詞作為中國古典遺產其自身魅力自不待言等因素,共同刺激了舊體詩詞的創作。既寫新詩又作舊詩的“兩棲”文人越來越多,許多新文學家“勒馬回韁作舊詩”,如沈從文、茅盾等人,甚至五四時期竭力批判排斥舊體詩、提倡新詩的先驅者們,都開始寫作舊體詩,如葉圣陶等。舊體詩的創作隊伍不斷擴大,創作數量不斷增多,這是舊體詩生命在當代得以延續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影響是改變了人們對舊體詩的看法,相比于僅僅是從形式上區分新舊,在《詩刊》發表舊體詩后,區分新舊文學的標準有所擴大,不僅僅是從形式上區分舊體詩,注意內容才是區分新舊文學的重點。1962 年郭沫若在《詩刊》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主席的詩詞不能說是舊的。應該從內容、思想、情感、詞匯上來判斷新舊。”[3]陳夢家在《詩刊》上說:“從形式上來看詩,是不妥當的。”[8]陳毅在詩刊社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也說:“我主張新詩可以做,舊詩也可以做。”[3]在《詩刊》發表舊體詩以后,改變了人們傳統對立的新舊詩歌觀念,新詩與舊詩的界限被重新定義。如上面所分析過的,由于新詩發展不足使大家意識到傳統的舊體詩詞可以作為新詩發展所需的養料。新舊體詩歌之間的界限被重新定義,新舊對立的思維才被打破,舊體詩詞的“合法”性地位才最終得以確立。
雖然《詩刊》發表舊體詩、保留舊體詩欄目使得舊體詩的地位上升,為舊體詩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但是舊體詩詞仍然沒有與新詩或者說舊文學仍然沒有與新文學取得同等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語言。語言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在創造語言的過程中人有很大的能動性,但一旦語言被確定下來,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它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根深蒂固性,如果沒有外部的巨大壓力和內在自我變革的強烈需求,轉型是非常困難的,更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從現代語言哲學看來,以語言的新舊來區分新舊文學是合理的。因為語言不僅僅是工具符號還是思維思想本體。高玉認為,雖然提倡“五四”白話文運動的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沒充分意識到語言不僅是工具同時也是思想思維本身,但由于提倡改革的他們本來留學歐美,受西方現代文化浸染,無意卻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將文學帶到了現代,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變革。語言不僅僅是工具也是思維本身,運用不同的語言寫作,背后體現的是不同的思維方式。自白話文運動以后,白話文成為文學創作使用的語言,文言被貶低被邊緣化,白話成為文學正宗,是不可逆的潮流。即使是領導人以及名家的示范與倡導,即使是官方權威刊物刊登舊體詩詞,從語言角度說來,以文言為工具的舊體詩在當代已經不可能與新詩平分秋色。
從創作者與讀者接受角度來說,舊體詩創作相對新詩來說更需要門檻。傳統詩詞是文言的產物,能寫會讀舊體詩至少需要有文言的功底,但自從白話成為文學正宗以及教育部規定在教學中使用白話以來,文言已經與普通讀者漸行漸遠,創作與欣賞舊體詩詞必須具備的文學或者說文化修養如今普遍不足,也導致了舊體詩詞在當代復興的艱難。
五、結語
《詩刊》雖為新詩的代表刊物,但實際上對當代舊體詩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以《詩刊》為例,運用現代傳播視角在《詩刊》中考察舊體詩詞當代的文體命運。探究舊體詩是如何重新由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如何由“非法”地位走向合法地位。但這種“合法”在某種程度上是無力的,在現代漢語背景下,舊體詩詞創作雖然一直延續,但舊體詩詞入現當代文學史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五四”后被打上“非法”標簽的舊體詩詞,雖然在《詩刊》的引領示范下,在當代獲得了“合法”地位,但“落后”的語言形式,一直是阻礙舊體詩詞合法進入在“現代性”焦慮影響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