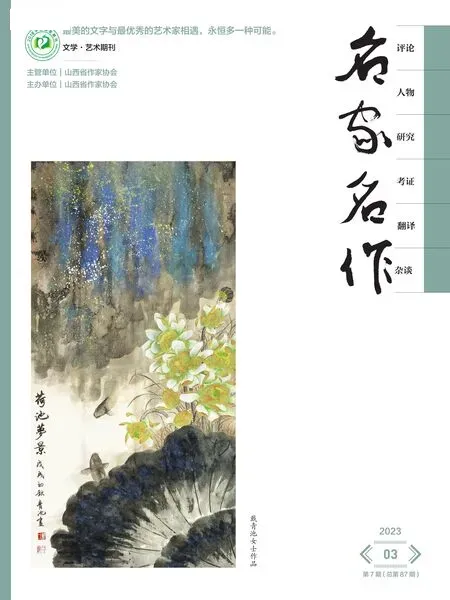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花束般的戀愛》:愛情電影中的敘事策略與細節表達
岳書婷
《花束般的戀愛》于2021 年初在日本公映,由執導經驗豐富的土井裕泰、編劇經驗豐富的坂元裕二聯手創作。上映期間,其曾一度拿下了日本2021 年上半年真人電影票房第二名,在我國豆瓣網電影平臺的評分更是高達8.6 分,是豆瓣網2021 年度評分最高的愛情電影,可謂是近年來成績最亮眼的愛情電影之一。
一、開始,是結束的開始:鏡像世界拉近心理距離
《花束般的戀愛》講述的是一對男女從相識相愛到熱戀、到愛情逐漸歸于平淡、再到成為陌路人的故事,正如影片名稱所提示的,這是一個有“花期”的愛情故事。花束從剪下的瞬間就開始枯萎,因為它沒有根、遠離土壤,所以無論其曾經多么光鮮亮麗,最終都終將歸于凋零、化為塵埃。影片正是通過這個概念揭示了愛情具有時效性的問題。
朱光潛在其對“心理距離說”的闡述中提到,審美體驗作為一種精神活動,必然會因創作者和接受者個人的因素而產生不同的體驗。作品創作越是與接受者接近,越是能引起其相應的共鳴,從而產生美感。[1]影片的敘事結構并不復雜,一定程度上屬于傳統的線性敘事,影片在開場前插入了男女主人公分手后的情節作為“楔子”,營造懸念感。而這個“楔子”在影片結尾又有接續的體現,形成了一種首尾呼應。《花束般的戀愛》敘事的高明之處在于,它的主線敘事雖然采用了平鋪直敘的方式,但這種平淡的方式本身就很貼近觀眾的日常生活。其建構了一個影像化的鏡像世界,更加拉近了觀眾與影片的心理距離。可以說,影片的敘事方式在多個層面都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輝,對現實世界的鏡像反映滲透著一層現實底色。
(一)有始有終——敘事結構上的首尾呼應
《花束般的戀愛》是一部首尾呼應、運用線性敘事的影片。其中,首尾呼應不僅僅體現在前文提到的影片開場前的“楔子”與影片結尾兩人背對揮手作別的情節,更體現在許多小的細節之中。這些小細節不僅推動了影片的敘事,更是將情感氛圍推向了高潮。
其中,影片男女主人公在戀愛前與分手前心里的想法十分相似——“末班車來之前就表白”“婚宴結束后就分手”。而兩人在分手前去的 KTV 正是兩人戀愛前去過的 KTV,分手前去的餐廳正是他們互相表白時所在的餐廳,甚至兩人在餐廳里遇到了“年輕版的自己”。從紅綠燈下的第一次接吻到分手告別時紅綠燈下的擁抱,從給同居的愛巢裝上窗簾到分手后將其取下,這部影片沒有一處不在告知觀眾: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些情節和細節更加增添了影片的現實色彩。
(二)鏡像建構——敘事細節拉近心理距離
一般而言,從鏡像理論出發,對電影進行深度解讀與分析主要有以下兩大維度:其一是影像世界中的情境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似、相通之處;其二是影片中的人物主體在主我與客我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最終形成帶有社會性質與個體特殊性質的主體。[2]
影片通過設計一些小的細節和情節,通過將現實界(Real)、想象界(Immaginary) 、象征界(Symbolic)三層界域有機統一[3],成功建構起一個鏡像世界,即一個現實世界的縮影。可以說,《花束般的戀愛》并不是僅聚焦于主人公的感情故事本身,而是在講好故事的基礎上穿插描繪了現實的日本社會,豐富立體地表現了當代日本年輕人的社會困境:固化的階級、嚴苛的上下級觀念、壓得人喘不過氣的高壓工作制度等。
現實界中,男女主的生活條件并不優渥。二人所生活的日本第一大城市東京無疑是日本年輕人生活壓力最大的地方。二人在工作上的不順心,無疑是影片對受日本沉重壓抑的社會氛圍壓迫的日本年輕人的困境進行的精確、立體的鏡像化描繪。
想象界中,二人受到了來自他者的固化認知的壓制。二人的父母對其職業選擇、個人意志都表達了不支持、不鼓勵的態度:八谷娟的父母是東京本地的廣告商,雖然不愁吃喝,但處世圓滑,是影片中標準的成年人形象;山音麥的父親則是一家煙花廠的老板,希望山音麥不要再漂泊在東京,應該回家繼承家業。而山音麥在公司里被代表社會的固化認知的上司所規訓。
象征界中,二人在戀愛的五年成長過程中,都有著其作為主體本身的感知,感受著外界對其自身的凝視。比如,影片后期山音麥在公司加班時,借由一段指代別人的談話,感知到了同事的凝視,產生了憤怒的情緒。八谷娟在辭去工作入職密室逃脫的工作室時,也感知到了山音麥的凝視,而山音麥同樣感知到了八谷娟的反饋凝視,二人的對話段落看似平靜,實則波濤洶涌。
影片中對社會及主體鏡像的建構塑造了一個現實社會的縮影,透過這些狀似現實的藝術真實創作,使觀眾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縮影,產生了共鳴,從而達到了拉近其心理距離的效果。
(三)審美主體——敘事細節烘托情感
貫穿《花束般的戀愛》這部影片的是數不盡的細節。其中八谷娟作為一個文藝青年,喜歡的事物都比較小眾。影片中提到,在男女主熱戀時,八谷娟喜歡的一位情感博主“戀愛生存率”自殺,海邊的這場戲居于影片整體時長的三分之一處,從這一場戲之后,劇情開始從男女主人公戀愛的甜蜜轉向兩人感情歸于平淡。這個情節不僅暗示了后續的劇情發展,更體現了八谷娟作為審美主體的情感依托的消逝。而八谷娟作為影片外的審美客體,其遭遇與經歷更是引發了有相似經歷觀眾的深深共鳴。
影片中,“戀愛生存率”博客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使用了《開始,是結束的開始》作為標題,而后八谷娟對“戀愛生存率”博客進行了如下描述:“‘相遇總是伴隨著離別……我們的派對,現在正在高潮部分。”
由此得知,女主人公對自身戀愛的生存率雖然持肯定態度,但字里行間充斥著對這段感情的不信任,為后續二人感情歸于平淡、相忘于俗世間埋下了伏筆。作品的審美主體形象框架需要承載審美主體的情感依托,需要建立起第三視角下的情感聯系。八谷娟作為“戀愛生存率”的一個關注者,這無疑是她作為審美主體的情感寄托;而影片外的觀眾作為影片的接受者,其作為審美主體,無疑會將八谷娟的情感遭遇作為自己的情感寄托。與此同時,“戀愛生存率”博主自殺只是一個很小的情節,但這個情節之中的細節,如山音麥去買沙丁魚蓋飯途中突然消失,八谷娟說“你不要突然消失”,不僅是暗示,更推動了劇情向后發展,助力了八谷娟的情感態度轉變。
二、成長與反成長敘事:反襯式人物塑造
在塑造女主人公八谷娟與男主人公山音麥時,創作者使用了成長敘事與反成長敘事相結合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襯的作用。
(一)獨白塑造人物形象
《花束般的戀愛》中大量使用了男女主人公的畫外音內心獨白,這種獨白不僅起到了交代情節的作用,更為人物塑造做出了貢獻。影片開頭男女主人公各自進行了大段的內心獨白,從而簡明扼要地讓觀眾了解了男女主人公的人物設定,從而對兩人有了如同朋友一般的了解,開啟了“上帝視角”,拉近了觀眾與兩位主人公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更加期待男女主人公兩人的相遇,期待兩人碰撞出火花。
(二)成長與反成長敘事
在這部影片之中,創作者運用一定的反襯手法,同時使用了成長敘事與反成長敘事。成長敘事的基本范式可以簡要概括為:由“少年”過渡為“成人”階段的年輕人,反復遭遇種種挫折,繼而努力習得了種種規則、博弈與妥協的策略,最終融入社會,成為游刃有余的成年人。[4]而反成長敘事,顧名思義,是與成長敘事相反的敘事手段。
影片中,山音麥的人物形象變化無疑是常規的成長敘事,即從開始到結尾,他一直在按照線性的時間“成長”,其人物形象被按照傳統的成長敘事情節塑造著。從影片開始的青澀大學生形象到影片后期成長為社會中摸爬滾打的成年人,其內心在潛移默化之中被社會所同化,深刻體現了八谷娟母親所說的“進社會就像泡澡”。影片開始時他為成為職業插畫家而努力,而后遭遇挫折后選擇找工作,認為自己可以在工作之余畫插畫。但他在忙碌的工作中被磨平了棱角——他成為滿口工作的成年人,說出了八谷娟父親曾經說過的話:“生活就是責任。 ”八谷娟的父母作為影片中少數出現的成年人,代表的其實就是這個社會的規則,其每一句臺詞都在之后有所體現。
而八谷娟的人物形象則恰恰相反,雖然她也在生活的重壓之下進入了社會,但她為自己的內心留存了一片凈土,是一種成長中的反成長敘事模式——八谷娟的成長體現在內心,她變得更堅強,更有勇氣和能力去守護自己熱愛的事物,并沒有被社會所同化。她考了會計資格證,工作一段時間后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找了一個被認為是不務正業的工作,她變得更堅韌,做到了在成長的過程中“反成長”。
八谷娟與山音麥隨著時間變化的對比更加反襯出山音麥的“成長”。譬如,八谷娟一直沒有放棄在工作之余給自己喘息的空間,保留了每天在閑暇時間看書、玩游戲的習慣,而山音麥則每天都坐在書桌前加班工作,追過的漫畫最后甚至忘記了情節。在八谷娟辭去工作時,山音麥稱其不務正業,本質上是在玩樂。影片重復出現的一段對話情節非常有趣:在八谷娟找工作失敗時,山音麥問面試官是誰,八谷娟說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山音麥說:“他如果看了今村夏子的《野餐》,肯定毫無感覺 。”而在影片后期,當山音麥遭遇挫折時,八谷娟用同樣的話安慰他,他卻回應道:“我可能也沒感覺了。”
三、球鞋、耳機與面包店:細節表達悲劇意象
在《花束般的戀愛》中,細節的設計不僅助力了前文所述的敘事結構建構、人物塑造,更為情感的傳達和氣氛的營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影片中許多細節的表現,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美好,對于接受者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審美主體的情感寄托。而這些細節卻被通過反襯的手段毀滅給人看,更加烘托了影片作為一部愛情電影若有似無的悲劇氣氛。
在影片的開場,男女主人公作為獨特的個體,擁有許多相似的愛好,這些愛好在一般人看來可謂小眾,但從他們的言談透露的細節之中,二人驚奇地發現了彼此的契合:他們都因為一些無聊的瑣事錯過了天竺鼠展覽,笑稱天竺鼠展覽的門票是“兩人相遇的門票”;兩人都喜歡用電影票根做書簽;兩人穿著相同的白色球鞋;兩人的耳機線都會打結;兩人喜歡的作家高度重合,如石井慎二、今村夏子等。
然而,這些美好的細節在影片后期卻逐個被消解:山音麥不再愿意跟八谷娟去看展覽和話劇,覺得這并非“正事”,放棄了自己曾經的興趣愛好;兩人從穿著相同的白色球鞋到變成了不同的黑色皮鞋;八谷娟發現山音麥在看有趣的電影時會流露出無聊的神情;而電影票根做書簽本身就象征了他們之間的愛情終將如電影票根上的字一樣消亡;兩人逛書店時,山音麥不再看小說,而是看起了“成功學”書籍《人生的勝算》……
而耳機作為貫穿影片的細節元素,在這一點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兩人的耳機線都經常打結;而后是在兩人確定關系的夜晚,為烘托氣氛,兩人共戴一副耳機聽一首情歌,結果被一位職業錄音師教育耳機分有左右聲道;兩人戀愛后不約而同地送了對方無線耳機,而使用無線耳機之后,兩人的感情逐漸歸于平淡,甚至各自聽各自的音樂,誰都不理誰;影片最后兩人決定分手時,坐在曾約會的餐廳里,看到一對酷似曾經自己的男女共戴一副耳機。在影片中,耳機不再僅僅是一個細節元素,而是一種意象,所指代的正是男女主之間的情感距離,從嘗試靠近,到共通,到疏遠,最后成為陌路人。
面包店則體現了兩人破裂最終的“和解”。兩人剛同居時發現樓下的面包非常好吃;而山音麥“成長”之后,對于面包店關門的態度卻變成了“車站前買面包”;時間來到兩人分手很久之后,某天山音麥突然發現在街景地圖上和八谷娟一起買面包回家的場景。盡管在戀愛后期兩人的感情從分裂走向平淡,最后相逢不相識,但在山音麥“人生第二次奇跡”發生的時刻,兩人的關系在無形中走向了和解。
從白色球鞋到耳機,再到面包店,這些貫穿全片的細節無一不昭示著兩人感情的變化過程,體現了再美好的愛情也會有花期,從感情開始的一瞬間就開始了枯萎,這無疑是對美好事物的解構,是一種悲劇的體現。
四、結語
愛情電影一直以來都是商業電影所青睞的類型之一,而《花束般的戀愛》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更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上做到了很好的結合,從其極具現實底色的敘事方式、成長敘事和反成長敘事的有機結合、反襯手法的有效運用和貫穿始終的細節與意象呈現可以看出創作者之匠心獨具。與之相比,我國的愛情電影更多喜歡通過情節中激烈的戲劇沖突來體現轟轟烈烈的愛情,這兩種模式并無優劣之分,但這種較為平淡、貼近現實的敘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為我國影視工作者提供新角度、新方法,在兩種方式之間取得一種微妙的平衡,從而給國內對固定模式已審美疲勞的觀眾帶來全新體驗。不過,這種方式仍需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進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