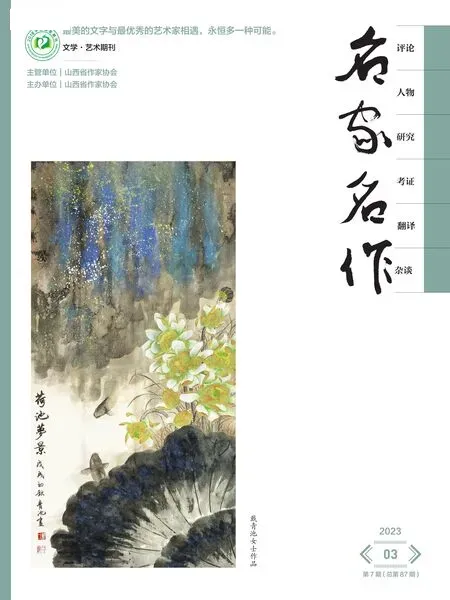城與鄉的擺渡人
——王安憶的創作梳理及其城鄉構建比較
周琪兒
從空間上來講,王安憶將創作分為城市與鄉村。城市并不是先進文化的代名詞,而鄉村也并不是腐朽落后的。王安憶在作品創作中加入了自己的審美與考量,并將城鄉的差異落實到了具體的人物塑造與細節描寫之中。王安憶在安徽插隊有過一段不長的知青生活,正是這一插隊記憶為她日后的創作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我們不得不關注作為“上海作家”的王安憶的另一種身份——知青作家。這一身份讓王安憶具有了獨特的鄉土觀察的出發點和寫作視角。縱觀王安憶近30 多年的創作,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生活”與“上海生活”經常交叉、交融地出現在她的作品中。于是,我們不僅要考察如《小鮑莊》《大劉莊》《姊妹們》《隱居的年代》等以鄉土為主體的作品,而且要考察王安憶在不同的時代際遇中如何處理城鄉關系,其中包括在大的時代節點上王安憶對城鄉社會的體驗和感悟。
一、歸去來兮——創作脈絡梳理
當我們梳理王安憶的小說時,發現其創作大致路線為:農村—城市—反觀農村。
20 世紀80 年代“上山下鄉”,體驗農村生活,在當時一眾尋根熱潮中批判農村不變的、落后的文化。
20 世紀90 年代回到上海,思索城市精神及文化底蘊,也就是《長恨歌》的創作階段。
20 世紀9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思想成熟,反觀農村,退居于“我們的村莊與我們的城市之間”。
王安憶在創作中心上實現了“歸去來”。在20 世紀80 年代“上山下鄉”時,她的創作主要是基于農村插隊生活的經驗,而20 世紀9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期的鄉土作品是從城市寫作中回歸而來的,此時她對城市與農村有了深刻的領會和把控,在談農村時則呈現出了另一種全新的視域——“我們的村莊與我們的城市之間”。王安憶前期的鄉土作品是基于現實的虛構,后期的鄉土作品則是從大量的虛構中回到了現實之中,由絢爛歸于平淡,從最普通的生活中尋找情景和形式以探究它們的審美本質,帶有重新發現與重新審視的意味。這種“歸去來”的寫作脈絡與時代浪潮緊緊相連,20 世紀80 年代的文學亟須轉型,而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下放的知青發現了鄉間無路可走,便又返回了城市,而后農村中的新生一代也不斷地尋求走出農村,因而形成了從城市到農村再到城市的人口遷徙大趨勢,這一趨勢也反映在了作家們的文學創作之中。王安憶便是其中的一位。
(一)20 世紀80 年代的群像敘事與城鄉墻基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王安憶的鄉土文學作品有《小鮑莊》《大劉莊》《流水三十章》等,此時,王安憶被劃入了當時的尋根派作家群。其實,王安憶就其創作本身而言并不完全聚焦于“尋根”“農村”這類,她涉獵的范圍比尋根派更廣。如果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的話,其實是上山下鄉與改革開放在文學上的反映。“上山下鄉”是近代中國規模空前的文化移置和改造運動,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同時“山”“鄉”也被知識分子融入小說的建構之中。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學從20 世紀70 年代末的呼喚改革轉向了20 世紀80年代的面向世界,呈現出多向度探尋特征,繼而引發了“尋根文學”這一文學思潮,帶有特定的時代文化背景與主題話語模式,帶著特有的地方性經驗。王安憶在尋根主題上并沒有將目光聚焦于特定的女性形象,而是塑造了一個農村群像。
《小鮑莊》中有這么勸喪孫的鮑五爺的:“現在是社會主義,新社會了。就算倒退一百年來說,咱莊上,你老見過哪個老的,沒人養餓死凍死的!”這句話其實就是一個揭露點。“社會主義新社會”和“倒退一百年”之間用了“就算”一詞連接,也就是說,一百年前與現在也并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在沒有實現共產主義、推崇無私奉獻精神的情況下,村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價值觀念已經代代維系了下來,農村有其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一套價值、宗法體系。再如《隱居的時代》中作者寫道:“這樣的以家族為組織單位的鄉村就是一座堅實的堡壘。”亦是談的這種制度堅不可摧。《小鮑莊》寫的是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時間線是與當下時間所吻合的。它強調了“仁義”,同時農村人也不斷地對城市進行主觀想象,比如“城里瘋人院”;當談及童養媳時寫道:“小鮑莊的童養媳是最好做的了,方圓幾百里都知曉,這莊的人最仁義 ,可惜太窮了。”有一種正話反說的意思。在第十節作者則提到了北京和上海兩座城市的斗爭狀況,將處于虛構時空的農村與歷史時間聯通了起來,同時也通過對比表現了農村的閉塞滯后與城鄉墻基的牢不可破。在這種以村莊為規模的敘事中,王安憶的視角是廣闊而深沉的,她借助新現實主義的文學觀與地域文化掩體顯示出獨立的文化覺醒。
(二)20 世紀90 年代的知青文學與鄉土女性
20 世紀90 年代初,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城鄉之變與社會轉型,文學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收獲期,同時也受到了市場浪潮的沖擊。在這樣的浪潮之中,王安憶在知青文學的延長線上更傾向于女性成長小說,同時在尋根文學的延長線上向20 世紀90 年代展開。
構成王安憶20 世紀90 年代小說創作主流的是《姊妹們》《蚌埠》《喜宴》《開會》《青年突擊隊》《花園的小紅》《王漢芳》等一批鄉村小說,多為短篇,風格寫實,創作靈感來自王安憶“感性的經驗”,即知青插隊的生活體驗。王安憶認為:“我寫農村,并不是出于懷舊,也不是為了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王安憶通過小說所表現出來的并不是純粹的農村生活在她筆下的反照,而是通過作者有意的審美加工,使作品擁有了另一番世俗的人間情懷。王安憶為了維護農村生活未經雕琢的、質樸本真的特性,特意壓低了敘述聲調,拉開了敘述距離,而在冷靜客觀的敘述中又蘊含著敘述者的溫情與懷想。《喜宴》中的知識青年、《開會》中的孫俠子、《青年突擊隊》中的小勉子也接續了20 世紀80 年代《大劉莊》《小鮑莊》和《姊妹們》的時空架構,作者仿佛寫成了不同形態的連載短篇小說,相互銜接呼應。
知青作家的心理結構具有半制度化半知識分子化的特點,他們一面立足于對農村的崇敬,另一面卻站在城市知識分子的美學立場上。王安憶的插隊生活讓她擁有了地方性經驗,她同時又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對這一經驗進行了文學建構,將具體的情節安置在知青時代,主題也與知青文學的戀愛、勞動、思想相關,而實際的敘述卻更致力于獲得一種失去時空特征的恒定感,因而使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創作具有了自身以及20 世紀90 年代的審美特征。
(三)21 世紀初的移民文學與城鄉流動
21 世紀初,王安憶出版了《富萍》《剃度》《上種紅菱下種藕》《遍地梟雄》等鄉土小說,其主人公通常流動于農村與城市之間。在這一階段,作者不再強調城市與鄉村的地域性和時代性,而是重點落在了城市與農村兩者之間的關系上,這種特征在《遍地梟雄》這一作品中表現得極為突出。在經歷了市民社會中年代以來樸素的勞動與審美觀念的失落以后,王安憶在移民文學中重新發現并解構了城市中的“勞動與美”的歷史。
《富萍》是城市里的農村,而《上種紅菱下種藕》則是正在城市化的農村。因此,《上種紅菱下種藕》的主人公秧寶寶是成長著的,而農村也是成長著的。秧寶寶年僅9 歲,女孩成長歲月中的瑣瑣碎碎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身處江南古鎮轉型期細膩敏感的少女形象。小說的結尾,她即將走入紹興、走入城市。從農村到鄉鎮,再到小城紹興,還有隱含的更大城市,都指明隨著經濟的發展,父親夏介民的生意做得越大,秧寶寶也會走得更遠,與農村的距離也越來越大。她不自覺地被父母的愿望拖著走,而她本人也在父母的愿望中成長,正如正在城市化的農村一樣,也會與原本的模樣產生天翻地覆的改變。而《富萍》則更像是秧寶寶的接續,她依舊從農村走向城市。《富萍》寫的是一個名叫富萍的揚州鄉下女孩,因在鄉下與男青年李天華的婚約關系而到上海看望李天華在上海幫傭的奶奶。盡管歷經艱辛,在上海的生活使富萍漸漸了解了上海,最重要的是在這座城市里她感受到了雖然作為女性,但只要辛勤勞動,“在哪里活不下去?”最終富萍選擇留在了上海,嫁給一個自尊、樂觀 、肯干的殘疾青年。通過對21 世紀初王安憶鄉土女性文學作品的解讀,我們可以發現該階段女性主義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更加成熟,女性形象也更為復雜,不再是單一的農村婦女或者女知青,而是城里的異鄉人和鄉里的異城人,在接續了20 世紀90 年代女性成長小說的基礎上,開始關注女性的自我認知、自我發展和如何成長的問題。
其實,王安憶的城鄉小說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她不僅會在城鎮敘事中摻雜鄉土元素,也會在鄉土作品中插入城市。我們可以這樣看,農村的對面是城市,城市的對面是農村,兩者是相呼應的,王安憶在寫城市的時候也是對農村的投射,而在寫農村的時候也一樣會對照城市,所以在她的筆下,城市與農村絕非二元對立體,而是在思考兩種文化交織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以用一種共通的視角來觀之,城與鄉在其創作中有著同樣重要的地位,王安憶期待在城市中發現鄉村,期待在文本中創造出“勞動與美”的理想形態。
二、常與變——女性主義敘寫
從人物塑造來看,王安憶的都市小說基本上都由女性來充當主角,因為她要通過城市與女性之間的密切關系來展現城市的精神與生活圖式,而這一關系是相對于男性城市更加穩定且綿遠的,類似于“點滴到天明”的細膩溫暾的感觸。王安憶的小說始終貫穿著一個永恒的主題,即對女性的人生經驗與個人的獨立意識的書寫,而在這個主題的下面又出現了一些階段性的轉變。
從鄉土女性的人物形象出發,自20 世紀80 年代的《小鮑莊》到20 世紀90 年代的《王漢芳》以及后來的《富萍》,她對女性的心靈世界的理解,不僅是對物質的拷問,更是對心靈的反省,使我們看到了一部埋藏在歷史塵埃中的女性的心靈史與奮斗史。王安憶在借鑒西方女性主義意識的不自覺中,表現出了一種動態的發展歷程。其創作主題在不同時期呈現出循序漸進的特點,即女性的自我覺醒、自我發展、自我重構。這三個階段與鄉土創作的階段呈現出一種動態映照的關系。鄉土女性的自我覺醒較為突出的是《小鮑莊》中的小翠子這一童養媳形象,她以“我才十六歲” 進行著宣告與反抗,并不愿意犧牲自己的愛情。創作重心落在女性的自我發展上的應該是《王漢芳》一類的知青文學,王安憶關注的重點并不是知青女性尋求發展,而是農村婦女尋求發展。她從日常生活出發,把女性放置在持久的農村日常生活中,其筆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審美能力與實踐能力,同時女性自身的魅力又美化了日常生活。到了20 世紀末,隨著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的衰落與女性主義研究的轉向,書寫鄉土世界成為女作家重新打開廣闊的外在世界并尋求女性主體解放與新生的重要途徑,此時王安憶以富萍的形象以及其內在的勞動美實現了重構,走向了生命的舒展以及兩性和諧。
在王安憶筆下,城市的變化就象征著女性的變化,女性的命運也暗示著城市的改變,對于女性的敘述與描寫在王安憶的城市小說中呈現出一種縱向聚合的能指世界,女性也成為紛繁的城市意象中的一種。而王安憶的整體鄉土小說并沒有完全地凝聚于女性,她不同時期的創作重心都有所偏移。她雖然寫的鄉村在地理范疇上并不大,但是所塑造的農村人際關系卻是復雜宏大的。在鄉土小說中,王安憶也更多地觸及了城鄉關系之間的問題,例如《姊妹們》中關于走出去的言論:“事實上,她們大多只能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但這種宿命并不能消除她們對外面世界的憧憬,她們特別熱心她們也許永遠不能企及的地方。”當然,這種宏觀又局限的視角到了21 世紀初跟隨著王安憶創作經驗的積累也發生了流變,比如《上種紅菱下種藕》和《富萍》的敘事重新聚焦在了女主人公的形象上,而聚焦的問題也跟隨時代產生了新的變化,她開始探討女性如何從農村走向城市,又為何從城市走回農村等一系列問題,較之于前期龐大的宗法村落敘事體系,王安憶將筆觸落在了女性身上,筆下的農村也發生了新變,它不再像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凝固,而是受到城市、工業文明的影響開始發生轉型,揭露的是傳統與現代的根本關系,并且農村的轉型與蛻變表現出一種蒼涼之感。
當討論王安憶的鄉土文學作品時,我們不僅要進行城鄉的對照、階段的對照,還可以從中挖掘女性主義的發展與成熟,以及在不同階段的鄉土文學作品中女性與農村之間的緊密聯系。在王安憶的創作中,“女性筆下的鄉土”與“鄉土中的女性”在互動的目光之中構成了對于改革開放后鄉土世界的女性言說,并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性別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