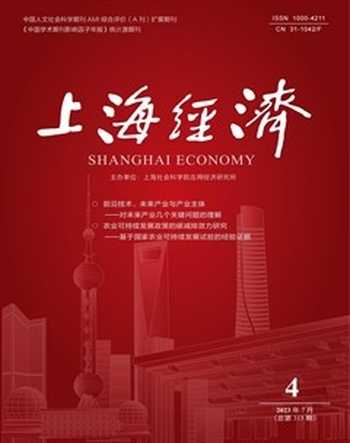美國產業政策的歷史脈絡、演進規律與政策啟示
[摘要]2020年以來,拜登政府致力于提出一套體系化的產業政策理論,通過規則和補貼的制定,并綜合各項干預措施將私人資本引向重點發展領域,引發了廣泛的政策討論。循此,本文從產業政策的主流思想、主要任務、政策領域和政策工具等角度詳細梳理了美國在產業萌芽期、發展期、調整升級期和新發展時期的主要產業政策,總結了美國產業政策實踐中的演進規律,并針對我國目前產業政策中的主要困境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第一,堅持自主發展的基本原則上保持戰略定力;第二,著重功能性產業政策的運用,推進產業界自立的政策導向;第三,在政策表述、政策延續以及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政策協調等方面借鑒美國經驗;第四,注重公私部門的合作,增強官民協同;第五,注重產業政策的體系性與協調性。
[關鍵詞] 美國;產業政策;演進規律;政策啟示
[中圖分類號] 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11(2023)04-0010-14
[收稿日期] 2023-01-11
[作者簡介]任宛竹,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文化經濟學。
一、引言
新冠疫情前后,美國的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發生重要轉變,拜登政府重塑美國產業政策,將亨利克萊的“美國制度”思想體系重新拉回歷史舞臺。拜登政府簽署《美國救援計劃》,相繼推出《通脹削減法案》、《芯片和科學法案》以及《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以法律形式強調了產業政策對美國的經濟引導與干預作用,在優勢領域進一步鞏固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在新興領域確保美國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產業主導者,在關鍵領域構筑貿易壁壘、維護美國的產業鏈安全。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報告《重構美國國家產業政策》文末論述:“中國并非產業政策的發明者,美國產業政策將確保美國未來經濟保持強勁,技術領先地位得到鞏固”。長期以來,美國為鞏固自身全球政治經濟領域主導者的地位,不僅聲稱未曾實施過產業政策,還主張他國消除貿易壁壘等經濟干預手段,并以裁判者身份對他國產業政策加以干預和指責。因此,拜登政府重申產業政策的意義,推翻了美國先前對于實施產業政策的掩飾態度,激發了政界、學界與業界各方關于產業政策的廣泛討論。
本文對美國自建國以來實行的產業政策加以梳理,將美國產業政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產業政策的萌芽期、發展期、產業調整升級期和新發展期四個階段,概括了美國各個經濟運行時期的主流經濟思想、產業政策的任務、主要領域以及政策工具等特征,并總結了美國產業政策的演進規律。在產業萌芽期和發展初期,美國往往以直接干預手段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的發展,并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在技術研發與應用領域投入巨額資金。隨著美國工業體系的成熟和世界領先地位的確立,美國政府逐漸轉向功能性和服務性產業政策,以更為隱蔽的手段支持美國產業發展。近年來,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經濟威脅,其產業政策逐漸顯現更多選擇性產業政策的特征,以“挑選贏家”的方式促進本國優勢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無論政府主張和主流經濟思想為何,美國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均運用了直接或間接的產業政策支持本國產業,并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進行適時調整。
中國在以往產業政策實踐中大量借鑒了歐美日韓等國的產業政策經驗,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是中國與這些國家往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程度、地緣政治環境等背景差異較大,僅僅對經濟政策進行同時期的橫向比較往往有失公允。因此,本文對美國產業政策的梳理與總結,也可以將中美產業政策的比較嵌入更為宏大的歷史格局之中,而不拘泥于同期對比,具有更強的可對照性,從而為中國產業政策的實踐提供啟示。
二、美國的產業政策實踐
美國聯邦層面的產業政策由美國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共同實施,產業政策通過聯邦政府機構的各種計劃之間進行銜接協調,形成較強政策合力(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2018)。美國產業政策的發布形式主要包括政府部門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實施方案、評估報告、政策指引。產業政策類型主要包括產業技術政策、區域政策以及其他以改善經濟環境、促進就業為目的的產業政策。
產業技術政策由國防部、國立衛生研究院、能源部、國家航空航天局、國家科學基金、農業部、商務部等機構實施;產業組織政策由聯邦貿易委員會、司法部、各級司法機構實施;其他產業政策由聯邦小企業管理局、經濟發展局、農業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負責實施(周建軍,2017)。同時,各個州可以制定符合本地發展需求的產業政策,包括現金補助、企業所得稅減免、銷售稅減免或退稅、財產稅減免、低成本貸款或貸款擔保、工人培訓等免費服務等。
(一)萌芽期
美國產業政策的萌芽期是1776年至1944年二戰結束前夕。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前后,英國一方面對美國采取了抬高關稅壁壘、取消貿易優惠等貿易保護手段,另一方面向美國大規模傾銷廉價工業制造品,使剛剛起步的美國經濟陷入破產、失業加劇和資金匱乏的困境中。面對內憂外患,美國在產業發展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獨立和完善的本國工業體系。
漢密爾頓的公私部門資源整合思想與克萊的美國制度等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主張是萌芽期產業政策的指導思想。美國學派的主要觀點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推崇技術進步,追求生產效率提升。第二,放棄自由貿易,實施幼稚產業保護。第三,實施內部改革,以內需升級驅動工業化進程。美國學派的政治經濟學主張是未來“生產效率-內部改善-關稅保護”工業化戰略思想的雛形(沈梓鑫和江飛濤,2019),是美國未來完成工業化體系建設和實現經濟趕超的重要指導思想,對美國產業政策的制定影響深遠,并為美國應對20世紀上半葉經濟危機提供了行動指南。如兩次世界大戰中成立的戰時工業、生產委員會積極尋求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在生產與服務中的戰略合作,協調商品定價與分配,使美國在戰時得以保障社會需求,并為戰后經濟重建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礎。在促進本國工業發展的同時,美國并未忽視對農業發展的推動,1933年開始美國通過立法保護、巨額補貼等政策工具扶植本國私有農業的發展。
至產業萌芽末期,基于國防需求,聯邦政府意識到科技創新的重要性,產業政策逐漸呈現出整合資源、推進科技邊界的創新政策屬性,以舉國體制塑造科技前沿。如1940年成立的國防研究委員會投入巨額資金并召集科研人才,與大學和工業實驗室合作開發新型武器開發。這一模式充分發揮了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力,迅速重建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優勢,避免在建立國家實驗室等方面浪費資源。
美國依靠創新的融資和企業組織方式、合理的人才戰略與產業技術政策,充分挖掘了本國市場潛力與企業家才能,使美國在19世紀末即躋身于世界工業大國和創新創業的中心區域前列。
(二)發展期
美國產業政策發展期為1945年至2007年。二戰結束后美蘇冷戰拉開序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同時展開,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議題,此時的美國已從經濟趕超者躍升為全球政治經濟領域的主導者。根據美國面臨的國際形勢與產業發展任務的差異,本階段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應對蘇聯的軍事威脅,美國在這一階段加快了國防科技體系的建設,建立起了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的產業政策支持體系。第二個時期始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不僅需要應對蘇聯的威脅,也要面對日本德國等國的崛起、本國科技成果轉化薄弱等問題,開始加強應用技術的成果轉化,大力推行產業技術政策。第三個時期始于21世紀初,美國在恐怖主義、能源危機、經濟衰退等議題的沖擊下進一步轉變增長方式,通過扶持重點產業和實施人才戰略穩固全球領先地位。
這一時期占據美國主流經濟思想地位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這使得美國政府不僅主張消除貿易壁壘等經濟干預手段,還以裁判者的身份對實行產業政策的國家加以指責。如里根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堅持的小政府和更有限的政府,Backer(1985)認為最好的產業政策就是沒有產業政策。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美國的產業政策并未得到外界的過多關注,美國政府甚至聲稱根本沒有實施過產業政策。實際上,在這段長歷史中,美國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實施了大量以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為主要著力點的功能性、服務性產業政策,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優良的營商環境,以舉國體制構建了完善的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支撐機制,美國取得的經濟成果已經遠遠超出了國防安全的范疇(沈梓鑫和江飛濤,2019)。同時,美國也會以直接干預的方式參與經濟發展,憑借自身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開展貿易保護,遏制競爭者的相關產業發展。美國在這一階段實施的產業政策領域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基礎研究領域。美國在戰后初期的產業發展戰略為“先軍后民、以軍帶民”,在萬內瓦爾·布什的推動下,美國產業政策強調對國防相關的基礎研究的支持,財政支持重點領域為基礎科學研究、基礎技術和通用技術,以確保美國是“戰略技術意外事件的發起者而非受害者”。美國政府成立了高度結構化和散點化的研究支撐機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等,這些機構成立多所國家實驗室,并在計算機科學、航空航天、生物技術等領域設立高校研究的資助計劃,聯邦政府的研發投資始終是美國科技創新的重要來源,根據NSF數據,聯邦政府研發投資占比在這一時期波動較大但始終保持在50%以上。同時,政府采購在這一時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半導體領域,發展初期美國政府對半導體設備采購占比在40%以上,最高時達到50%(馬偉,2020)。
第二,知識產權制度改革。美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始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臺了《拜杜法案》、《斯蒂文森—魏德勒技術創新法案》等一系列專利法案,以法律形式保障研究主體的知識產權財產分配,促進了科技成果在產業內的轉移、擴散與商業化轉化。
第三,創新政策。美國在這一階段實施的創新政策營造了共同協作和公平競爭的創新要素市場環境,有力地促進了創新主體的積極性與研發效率。如美國鼓勵私營部門的研發創新,啟動了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1982年)和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1992年),為從事基礎技術和競爭前技術研發的小企業提供早期支持,通過加強小企業與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之間的創新合作,提高基礎研究的商業化轉化效率(沈梓鑫和賈根良,2018)。1988年開始實施的制造業擴展伙伴計劃和先進技術計劃,向中小公司提供一系列培訓,并通過建立區域性制造業技術服務與轉移中心,將聯邦實驗室、高校和企業中產生的新技術與方法以技術服務的方式直接轉移到中小型制造企業中,加強中小企業的合作與聯合研發(汪琦和鐘昌標,2018)。
第四,培育創新人才。美國通過立法和戰略規劃等形式構建了支持基礎科學和應用研究的多層次人才培養制度,如2006年《美國競爭力計劃》、2007年《美國競爭法》,均強調了創新人才培養在國家戰略中的核心地位。美國政府通過加大高等教育投資、在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設科技創新教育項目、引進海外創新人才和設置獎勵計劃等方式吸引和培養了大量創新人才。
第五,貿易保護。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阻礙外部產業競爭者是美國這一階段的一項重要產業政策,美國施行特殊關稅制度(反傾銷稅和特別保障稅),設置進口配額限制特定商品進口數量,簽訂貿易協議保護本國產業,向本國產業提供補貼和稅收減免,利用反傾銷措施限制外國公司在本國市場的競爭。
(三)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期
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階段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至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前夕。在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開始意識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開始推行制造業復興計劃,應對危機后的經濟復蘇與重建。2009年奧巴馬上任后以振興制造業為基礎,出臺了一系列扭轉脫實向虛局面的再工業化戰略,同時配套技術創新與貿易保護政策用以支持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從而鞏固美國的國際領先地位。隨后特朗普蕭規曹隨,延續了奧巴馬的先進制造業戰略,美國逐漸形成了以先進制造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政策框架。在這一時期,美國實行的產業政策更為靈活多變,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基礎上發揮功能性和服務性作用,有效地規避了國際貿易法規的限制和審查,使其以更為隱蔽的形式支持美國的產業發展。這一階段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稅收減免、知識產權立法和政府投資。
1.復蘇計劃與創新戰略
為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美國在2009年后出臺了一系列計劃法案提振本國經濟,如ARRA法案(美國復蘇與在投資法案)向特定產業注資7870億美元加速經濟復蘇,《美國創新戰略》系列構建并完善了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架構和未來向度,復蘇計劃與創新戰略的行動重點在于對基礎研究,尤其是創新鏈前端的基礎研究給予更高的資助,促進基礎科學研究、基礎技術和通用技術的發展,根據沈梓鑫和江飛濤(2018)的計算,聯邦政府對創新鏈前端基礎研究的貢獻度高達44.3%,對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的貢獻度分別為35.5%和15.7%。這一資助結構可以在降低產業政策扭曲技術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有效提升基礎研發的動能,同時,聯邦政府對高校與研究機構的資助遠高于對私人部門的補貼,這也使美國的創新支持政策更具有隱蔽性。除直接出資外,聯邦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政策(包括研發和試驗抵稅)、金融政策(向開放性資本市場配置資源)和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鼓勵基于市場機制的創新研究,促進技術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與擴散。創新政策支持的重點技術領域包括生物技術、納米技術、清潔能源、現金車輛技術、精準醫療技術等。
2.以先進制造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政策框架
美國政府在這一階段的核心任務在于發展先進制造業,確保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優勢。奧巴馬的再工業化戰略與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歸口號一脈相承,具有較強的政策延續性。奧巴馬政府的產業政策重點是構建制造業合作伙伴關系,拓展公共部門與私人領域的協同合作,注重技術領域的基礎創新與長遠發展,據此制定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等創新政策和行動計劃。特朗普政府則更傾向于促進短期的制造業回流,通過減稅、基礎設施投資和寬松的金融政策創造制造業就業崗位,通過支持人才體系建設匹配先進制造業勞動力需求,推廣新的制造技術激活美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
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先進制造業計劃的目標是為了脫虛向實,改變美國對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過度依賴,培育本土制造業,增強制造業的創新能力與投資活力,縮小美國貿易逆差。第二,美國制造業的復興過程,是重新融合美國的技術優勢與產業優勢的過程。隨著制造業活動大規模向海外轉移,美國的制造業規模和貢獻快速下降,同時也影響到了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穩定和創新研發能力,因此,制造業的復興不僅意味著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更重要的是要促進制造業回流,吸納本國勞動力,重新提振美國的工業創新能力。第三,先進制造業計劃的方向,是爭奪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黃陽華,2018)。
在基本的政策思路上,美國不是簡單地通過財政、金融等措施直接幫扶特定企業,而是構建可持續的政策框架和服務體系,為制造業企業營造有利的內外部商業環境,促進以先進制造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投資。其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建立高效的公共治理體系,以匹配和服務本國制造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二,綜合多種政策工具,一方面為本國產業提供稅收和投資優惠,另一方面高筑貿易壁壘,通過高關稅和管制措施限制對手國家相關產業的發展。第三,在國際貿易中以堅持自由貿易的口號攫取資源,爭奪規則的制定權,穩固本國的領先地位。第四,完善發展先進制造的產業和技術基礎設施。第五,大幅提升對先進制造技術的R&D支持。第六,堅持人才戰略,大量培育和吸引滿足本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所需的技能工人和專業人才。從上述分析看,后危機時代美國的產業政策與美國長期奉行的美國學派產業政策核心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3.貿易保護與產業安全政策
這一時期美國的貿易政策在特朗普政府階段的表現較為鮮明。在傳統貿易領域,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撇清美國作為全球經濟和貿易主導者的責任,認為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貿易優惠有損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進一步強化貿易保護措施,重新定義美國在全球貿易與生產體系中的權利與義務。第一,為了改善對外貿易逆差,2017年開始,美國退出或更新多邊貿易協定,如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推進美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更新完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二,推行嚴格的技術移民政策,反對低技術移民;第三,在商品和服務貿易領域,與中國、歐盟、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不斷發生貿易摩擦,在技術領域重視產業技術安全,強化對中國等國家的技術產品出口管制,保護本國關鍵技術的安全(閆德利和高曉雨,2018)。
與傳統貿易領域不同,特朗普政府在數字貿易這一新興領域則主張自由貿易,致力于消除數字貿易壁壘,維護美國的數字商業利益,塑造美國在數字領域的主導地位。如2016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成立數字貿易工作組,同年商務部啟動數字專員項目,2018年在《電子商務倡議聯合聲明》中提出用數字貿易取代電子商務概念,其概念范圍和定義均由美國決定(陳昭峰和張紅倩,2022)。這些政策均為確保美國企業能夠順利打開全球數字經濟市場,成為數字貿易領域的領先者和規則制定者。
(四)新發展期
新發展時期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延續至今,這一階段美國產業政策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全球經濟的領先地位和應對中國的挑戰。金融危機后,隨著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中美差距不斷縮小。近年來中國實施了一系列深刻影響區域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格局的國家產業策略,如“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制造2025”等,使美國視中國為政治經濟威脅。在2020年前后,美國的經濟意識形態發生變化,摒棄了其建國以來始終堅持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在新的立法中不斷注入產業政策概念,認為政府應該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拜登上任后,更是推動多項產業政策提案轉變為法律。拜登實施的美國新產業政策著眼于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鞏固美國在全球工業和科技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提升美國競爭力,增強美國經濟韌性,并與中國競爭。
現階段實施的產業政策包括貿易、基建、創新、能源、國防和軍事幾個方面。第一,貿易政策,美國政府推行“美國優先”政策,促進本土生產和制造,保護美國產業免受外部環境的沖擊,通過補貼、稅收優惠和貸款計劃加強政府購買和投資相關技術產品的力度。第二,基礎設施領域,美國政府出臺《美國防止性能退化法案》《能源和水基礎設施法案》等相關政策,投入數萬億美元改善道路、橋梁、公共交通、清潔能源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等公共基礎設施。第三,技術和創新政策,美國政府加強對技術和創新領域的投資支持,保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5G等關鍵領域的領先地位。2021年參議院通過《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投入250億美元規模的補貼用于半導體制造,2000億美元用于科學和創新研究開發。第四,能源政策,包括推動本土能源生產和使用,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增加清潔能源的使用,從而提高國內能源自給率,實現能源安全和綠色發展。第五,國防和軍事產業,增加國防投資,加強軍備,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發展,提高美國軍隊的戰斗力。美國在原有功能性產業政策的基礎上越來越多地注入選擇性產業政策的特征,針對多個前沿科技產業出臺對應的發展綱要,明確發展目標,并對相關產業注入巨額資金,以“挑選贏家”的方式促進優勢產業的發展。
三、美國產業政策實踐的效果與演進規律
(一)美國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的研究進展
美國主流學術界在美國甚至世界的產業政策實踐過程中長期持否定態度,因此,在美國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經濟學家的參與程度較低。美國近年來頒布的CHIPS和IRA等重要法案,經濟學家往往被認為充當旁觀者的角色。(Juhász et al.,2023)但是,縱觀美國產業政策的研究歷史,仍然可以梳理出清晰的產業政策理論發展脈絡。
1.美國產業萌芽期和發展期產業政策理論
產業發展萌芽期的主流思想為幼稚產業理論,漢密爾頓構建出一個落后國家保護本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制造業,利用保護性政策,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揭示了古典經濟理論提倡的完全市場機制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在發展落后國家經濟時的不足(姜達洋,2011),使扶持新興產業的思想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
在產業發展期的代表性理論包括新增長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理論。新增長理論以保羅·羅默與羅伯特·盧卡斯為推動者,認為研發、創新與知識獨占性的強弱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新增長理論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對于后進國家來說,只有加大對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的投入,提高國民總體人力資本水平,加大對專業化人才的培養,引進先進技術,并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才能發揮后發優勢,在經濟上趕超先行國家(周紹森和胡德龍,2019);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發揮“有為政府”的角色,建立起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維護產權市場的正常運轉,才能保證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順利進行。發展型國家的概念源自《通商產業省與日本奇跡》,約翰遜將日本的發展模式稱為“計劃-理性”模式:第一,政府擁有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具有足夠的政治空間進行有效運作;第二,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順應市場規律;第三,需要存在一個像日本通產省一樣的政府機構,積極引導經濟發展并落實各項產業政策。
2.美國產業調整升級和新發展時期產業政策理論
美國產業調整升級和新發展時期的代表性理論包括技術動態創新理論、隱形發展型政府和企業家型政府理論。技術創新理論(techno-innovation dynamics)基于演化經濟學,以結構動態演化為視角,分析一般性的產業系統動態,而非專注于單一的企業或部門,其出發點是提高經濟系統的演化能力,解決創新過程中的系統或網絡失靈問題。系統失靈來自演化經濟學的資源創造理論, 對系統失靈的糾正旨在促進經濟行為者的知識創造、知識獲取和創新活動等資源創造的行為。在演化經濟學框架下,功能性產業政策居于經濟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主體具有短視性,可能處于低水平的局部均衡;第二,經濟個體具有異質性,市場可能會忽視一些無法達成一致的重要社會目標(如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等),因此需要構建功能性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系統擺脫低水平均衡,并實現其他重要社會目標。(Smith K,2000)
在對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討論中,美國學者布洛克和瑪祖卡托(2017)根據美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歷史和事實的研究判斷,分別將美國政府稱為“隱形發展型政府”和“企業家型政府”,否認了哈耶克“守夜人政府”理論,認為美國政府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企業培育等方面扮演了市場“塑造者”的角色(周建軍,2017)。例如,美國的“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和“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直接為創新型小企業提供贈款和貸款,微軟、戴爾、康柏和英特爾等企業在早期發展中都得到過這兩個“計劃”的資助。隱形發展型政府理論和企業家型政府理論擴展了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前沿,進一步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地位,揭示了政府在塑造和創造市場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賈詩玥和李曉峰,2018)。
3.近年來美國產業政策研究動態
隨著世界范圍內產業政策的研究與應用,產業政策的學術含義也隨之從貿易壁壘等傳統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延伸至服務性、功能性產業政策,美國經濟學者對產業政策理論的爭辯從產業政策的存廢,轉為對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經驗研究,對產業政策的應用持更為積極和開放的態度。政策支持者認為通過產業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就業率、提升國家競爭力,尤其應重視在綠色轉型、供應鏈的韌性、促進就業和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等方面的政策運用(Rodrick,1995;Lin,2012)。也有一些學者對產業政策持懷疑態度,認為政府的干預可能導致資源分配的扭曲,增加了效率和公平的難題(Ito和Krueger,1995;Lall,1996)。近年來,出現了大量文獻提供了關于產業政策的運作方式、評估產業政策在特定情境下引發的經濟預期反應等方面的證據,為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啟示。
在論述產業政策的效果與影響方面,美國學術界的研究包含了宏觀經濟數據分析(Szirmai et al.,2013;Rodrik,2012)、政策文本分析(Juhász et al,2022)、企業調查與案例研究(Lin和Monga,2011)等不同研究層次,評估內容包括貿易自由化、大規模研發支持等產業政策對行業與企業生產力和創新的影響,評估州和地方商業激勵措施的效果(Slatery C和 Zidar O,2020)等方面。
在產業政策的歷史經驗梳理方面,近年的研究文獻對東亞奇跡及產業政策的運用較為關注,包括東亞國家的政策規模(DiPippo, L., Li, N., and Lu, Y.,2022)、投資補貼等政策工具的運用(Barwick, P., Li, F., and Lu, Y.,2019)、政治環境與企業制度(Wade, R.,1990;Malesky, E., and London, J.,2014)等方面,并認為東亞經濟政策的經驗與教訓具備一定的普適性。
在研究范式方面,早期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注產業政策與行業績效之間的相關性,如生產率和與產業政策使用的相關性與外部性。而近年來的研究文獻則更加注重產業政策的測量和因果推斷,提供了更為準確和可靠的評估產業政策效果的方法,包括自然實驗(Aghion et al.,2015;Garin和Rothbaum,2022)、隨機實驗(Bruhn and Gallego,2012;Atkin et al.,2017)、斷點回歸(Diewert et al.,1990)等因果推斷技術。
(二)美國產業政策實踐的效果評價
美國的產業政策在歷史中起到了推動產業發展、提升國家基礎創新能力、增強國防安全等重要作用,但是同時也給經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美國產業政策的開展,學界和業界對產業政策的評估隨之持續。如1976年,蘭德公司發布的《聯邦資助的示范項目分析》,評估了聯邦機構在20世紀60~70年代發起的24個技術示范項目,其中有10個項目成功,9個失敗,5個未知,失敗的原因包括倚重大型項目、給予項目時間不足、技術尚未成熟即進行公示等。1982年,理查德·R·納爾遜在《政府與技術進步》中研究美國的公共政策和七個行業的技術進步,認為美國政府支持基礎研發的創新政策是最為成功的產業政策。2021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布了《美國50年產業政策評估(1970-2020)》,回顧了美國在貿易、補貼、創新支持等領域的產業政策,評估了其中的部分重點項目,并重點關注了東亞,尤其是與中國的經濟博弈。根據以往產業政策評估研究的梳理,美國歷史上實施的重點產業政策包括公共研發、貿易措施、促進就業三大領域。
第一,大規模的公共研發項目。威爾遜(1982)認為美國政府刺激工業創新的最佳方式是研發支持政策,尤其是政府資助非專利研究、知識產權分配政策以及政府購買。這類產業政策有助于向前推進技術邊界,使美國本土制造業與服務業更具創造力和競爭力。根據以往評估,當美國的創新政策更具選擇性特征時,這一類政策往往以失敗告終,原因在于技術創新的周期長,預期回報不確定性較高,使用挑選贏家的政策在商業競爭激烈的應用技術開發行業很難獲得成功。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1)對美國政府歷史上以技術創新為目的的補貼措施進行評估后發現,面對前沿技術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若將公共資金集中于一兩家規模較大的項目,正如將雞蛋投放于一個籃子中,往往以失敗告終;若以散點式的方式對多個企業同時進行補貼,則更容易成功。
第二,以保護幼稚產業為主的貿易措施。美國政府在鋼材、紡織品和服裝、汽車裝配和零件、半導體、太陽能電池板等眾多產業均實行過貿易保護政策。貿易措施之所以廣泛施行,是因為貿易措施相較其他的產業政策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受到聯邦預算的約束。美國的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國產業,并吸引大量海外生產商在美國落戶,但是,貿易措施的施行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一方面,貿易措施雖然具有非預算性,但是將成本轉移到了家庭和企業用戶上,使其承擔更高的支出成本;另一方面,過于依賴貿易保護和產業保護,限制境外企業的投資和進口行為,有違國際貿易的自由公平規則,引發貿易摩擦,使國際關系更為緊張。值得指出的是,貿易保護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產業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應該注意避免其過度使用和不當實施,以免造成負面影響。美國產業政策在制定時需要更加綜合考慮其他政策領域,以確保國內產業的發展與國際貿易規則相協調,并推動構建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國際經濟體系。同時,注重提升本國產業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將有助于提高產業的自主可控性,從而更好地應對全球經濟挑戰。
第三,就業支持政策。2021年拜登在國會首次演講中宣稱,就業是他的基礎設施建議和“購買美國貨”任務的核心內容。有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在摩擦就業領域進行工作重組,可以有效支持失業工人再就業。但主流的經濟學思想認為支持就業不應是產業政策的職能。以支持就業為目的政策評估結果更為模糊,如各州為吸引投資紛紛推出補貼優惠政策,區域引資競爭使得就業補貼政策從國家層面衡量時正負效益相抵,成為零和博弈。促進就業的產業政策也可能會引致額外的社會成本。例如,一些企業可能出于政策需要而雇傭失業工人,而這種舉措可能導致下游企業面臨更高的投入成本。因此,中央政府應采取服務性和功能性產業政策,這些政策可以通過提供STEM課程、職業教育和勞動培訓計劃等方式來促進就業。這些政策的目標是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技能水平和競爭力,使失業工人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并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這樣的產業政策更加注重長期效益和可持續性,有助于提高整體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
(三)美國產業政策的演進規律
1.產業政策需要不斷調整升級
從美國的產業政策實踐中可以看到,產業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跟隨本國和全球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而不斷做出調整。產業政策的最初存在的價值在于應對市場失靈,在市場調控無法觸及的領域對公共資源和市場要素加以引導和分配,從而促進經濟的健康運行。但是經濟運行的現實更為復雜多變,為了更好地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產業政策的體系、重點和實施方式必須適時進行調整(黃群慧等,2019)。
一方面,新技術的出現改變了經濟增長的固有模式,衍生出了新的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點,尤其是當代正在經歷的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變革,對產業政策的靈活性與適應性提出了挑戰。數字經濟改變了企業依賴價格機制和供求關系確定產量和價格的方式,轉而采用“數據驅動法”獲得供求均衡數據(吳軍,2016)。
另一方面,生產網絡和產業集聚模式的轉變,影響了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行為范式、經濟組織結構以及生產模式等產業組織要素的變化(杜傳忠和寧朝山,2016),需要政府在產業政策中支持和鼓勵跨界合作,通過提供跨產業的合作項目資金,建立合作平臺促進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交流與協同。
2.產業政策由縱向體系轉變為橫向體系
在全球產業演進的歷史中,產業政策的特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第一,產業政策隨著世界經濟聯系的逐漸密切和本國經濟體系的成熟,從保護主義轉為開放政策,早期的產業政策通常具有保護主義傾向,避免本國幼稚產業受到國外競爭的沖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貿易自由化的增加,許多國家轉向更為開放的政策,鼓勵國際貿易與跨境投資。
第二,產業政策從選擇性產業政策過渡到功能性產業政策。早期產業政策往往給予特定產業或部門優惠支持,隨著產業的演進和經濟結構的復雜化,以及新興經濟發展的巨大不確定性,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功能性產業政策,注重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但是近年來由于世界經濟局勢的緊張和逆全球化的趨勢,產業政策更加強調本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政策體系又逐漸強化了選擇性產業政策工具的運用。
第三,產業政策由重視資本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過去的產業政策通常注重資本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以促進工業化和制造業的發展。在數字經濟時代,資本投入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概念,基礎和應用技術研發與創新成了產業政策的重中之重。
第四,產業政策的實施從單一產業到關注多元化產業集群。歷史上產業政策的實施往往著眼于發展單一產業或特定產業集群,隨著經濟的復雜性和全球供應鏈的形成,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多元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現代產業政策更加關注多個產業的發展,以降低經濟的風險和依賴程度。
第五,產業政策向橫向產業政策的轉變,與本國政治體制變遷、政府決策效率相伴相生,產業政策的功效有賴于政策的延續性。一方面,產業的發展與本國的公共治理效率相互促進,公共治理效率和經濟現代化的統一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缺乏長期規劃,過于依賴于短期刺激措施,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容易導致政策效果的短暫性和不穩定性。在美國產業政策實踐中,政治斗爭干擾對產業政策的實施產生較強的負面影響,甚至決定產業政策的成敗。政府之間的政治斗爭和利益分配可能會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也容易導致政策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
3.大國的產業治理模式特征存在獨特性
第一,大國在實行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具有經濟規模優勢。相比與小國經濟,大國經濟體、超大規模經濟體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具有諸多不同,其調整的理論與機制也存在較大的差異。超大規模經濟體具有規模優勢、研發成本的分攤優勢、產業體系完整性與多樣性優勢等,這些為產業機構的調整提供了更大的騰挪空間,形成經濟發展的雁陣模式。雁陣模式的產業升級是推進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的大國效應可以通過產業集聚與擴散的動態循環推進雁陣模式產業升級進程,地區間分工經濟的實現提高了雁陣模式產業升級的經濟效率與質量。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依據不同的決策區間,科學選擇扶持與調控模式,合理定位其不同角色,從而推動產業升級(紀玉俊和張莉健,2018)。
第二,大國經濟體具有多層級的央地關系。多層級的央地關系有利于制定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對多樣化區域發展戰略具有較強的包容性。中國和美國等大國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的潛在優勢,本身存在多層級的央地關系,地方競爭也在中國經濟與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能夠容納多種戰略的存在,這是大國產業升級過程中并行不悖的路徑,包括自主創新戰略、基于內需的全球化戰略、自主可控產業體系的構建戰略等。然而,多層級政府關系也使得決策執行機構過于復雜,容易造成區域之間的無效率競爭。
四、美國產業政策實踐給我國的政策啟示
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與美國存在較大差異,政策、制度、文化等方面不盡相同。但通過對美國產業政策的回顧,以及產業政策效應的分析,仍能為中國提供寶貴的經驗:
第一,我國必須在堅持自主發展的基本原則上保持戰略定力,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做好事前評估。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下,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既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支撐,也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的關鍵。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要加強對其可能產生國際影響的事前評估。中國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堅決維持自主發展的基本原則,但在政策表述、政策解讀和對外宣傳中應盡可能地考慮國內外的輿論反應,并提前設計應對預案,爭取政策的解釋權與正向的輿論引導,創造有利于我國產業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
第二,著重功能性產業政策的運用,推進產業界自立的政策導向。美國和中國的產業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產業政策多是直接針對產業界內部實施資金補助和供需匹配的政策,扶持產業發展,政府直接作用和介入產業發展。而美國的產業政策以更大程度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為前提,多數圍繞強化環境政策、提出城市規劃和產業指導、對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進行鼓勵和保護等間接引導政策。我國的產業政策也應該轉變思路,從環境和外圍條件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提供競爭機制,推行產業界自立的政策,這樣政府調控產業可以進退自如,不被束縛。
第三,借鑒美國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豐富經驗。在政策表述、政策延續以及和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政策協調方面,美國政府積累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如2018《先進制造業領先者戰略》提到了擴大國內制造業供應鏈能力,而《中國制造2025》表述語境是努力提高本土產品市場份額,這就往往成為中國政府干預市場的把柄。美國產業政策的政策延續性較強,我國要從國家層面加強統籌規劃,滾動制定發展戰略,使各種發展要素相互配套。
第四,注重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增強官民協同。美國在產業政策實施初期,就具備功能型產業政策的特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依靠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合作持續推動關鍵領域的創新和競爭力的提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為市場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和創新的動力,同時市場的靈活性和競爭性使得創新得以迅速應用和商業化。這種合作模式在美國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美國政府與私營部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合作開展太空探索,帶動了航天技術、衛星通信和航天工業的迅速發展。
第五,針對大國治理特點,加強產業政策的體系性與協調性。我國產業政策具有點多、面廣、量少的特點,中央與地方、地方產業政策之間的協同性較弱,需要借鑒美國政府機構協作和政策協調的經驗。可成立各種協調機構和委員會,如國家經濟委員會、工業政策委員會等,負責協調不同產業政策之間的沖突和重疊。在政策制定中注重政策整合和交叉支持,鼓勵各利益相關者參與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制定橫向產業政策,涵蓋多個產業領域,以確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協調性。美國政府還會對現有的法規和政策進行評估和調整,以適應產業發展的變化和需求。
參考文獻:
[1]Aghion, P., Dewartripont, M., Du, L.,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015(07).
[2]Cimoli, M., Dosi, G., Stiglitz, J. E, The Rationale for Industrial and Innovation Policy[J]. Intereconomics, 2015(03).
[3]E. Kilcrease, E. Jin, Rebuild: Toolkit for a New Amerian Industrial Policy[R]. CNAS Reports, 2022.
[4]Hufbauer G C, Jung E, Scoring 50 years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1970-2020[R]. 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Special Reports, 2021.
[5]Lin J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2).
[6]M. Rasser, M. Lamberth, H. Kelley, R. Johnson, Reboot: Framework For a New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R]. CNAS Reports, 2022.
[7]Réka Juhász, Nathan J. Lane, Dani Rodrik,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8, https://www.nber.org/papers/w31538.
[8]Rodrik D., Geting Interventions Right: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J]. Economic Policy.1995(10).
[9]Rodrik D., Why We Learn Nothing from Regressing Economic Growth on Policies[J]. Seoul J. Econ. 2012(2).
[10]Slatery C, Zidar O., Evaluating State and Local Business Incentives[J]. Economic Perspect, 2020(2).
[11]Smith K, Innovation as a Systemic Phenomenon: Rethinking the Role of Policy[J].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udies, 2000(01).
[12]Soete, L., From Industrial to Innovation Policy[J].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2007(07).
[13]杜傳忠, 寧朝山, 網絡經濟條件下產業組織變革探析[J]. 河北學刊, 2016. 36(04): 135-139.
[14]干春暉, 王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回顧與展望[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8. 39(08): 3-14.
[15]黃群慧, 余泳澤, 張松林, 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 中國工業經濟, 2019(08):5-23.
[16]紀玉俊, 張莉健, 全球價值鏈、行政壟斷與產業升級[J]. 產經評論, 2018. 9(06): 21-33.
[17]賈詩玥, 李曉峰, 超越市場失靈:產業政策理論前沿與中國啟示[J]. 南方經濟, 2018(05):22-31.
[18]姜達洋, 戰略性新興產業扶持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溯源[J]. 山東財政學院學報, 2011(03):63-67.
[19]沈梓鑫, 賈根良, 美國小企業創新風險投資系列計劃及其產業政策——兼論軍民融合對我國的啟示[J]. 學習與探索, 2018(01): 120-129.
[20]沈梓鑫, 江飛濤, 美國產業政策的真相: 歷史透視、理論探討與現實追蹤[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9(06): 92-103.
[21]盛斌, 陳帥, 全球價值鏈如何改變了貿易政策: 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和啟示[J]. 國際經濟評論, 2015(01): 85-97+6.
[22]汪琦, 鐘昌標, 美國中小制造業創新政策體系構建、運作機制及其啟示[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8(01): 160-169.
[23]吳軍, 智能時代大數據與智能革命重新定義未來[J]. 張江科技評論, 2019(01): 80.
[24]楊繼東, 劉誠, 產業政策經驗研究的新進展——一個文獻綜述[J]. 產業經濟評論, 2021(06): 31-45.
[25]周建軍, 美國產業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從產業技術政策到產業組織政策[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7(01): 80-94.
[26]周紹森, 胡德龍, 保羅·羅默的新增長理論及其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因素中的應用[J].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04):71-81.
Historical Context,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U.S. Industrial Policies
Ren Wanzhu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Since 2020, the Biden government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posing a systematic industrial policy theory that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private capital towards key development area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subsidies,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which is sparking extensive policy discussio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United States' main industrial policies during the stages of forming, 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and new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instream ideas, primary objectives, policy domain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Firstly, it suggests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strategic consistency. Secondly, it emphasizes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a self-reliant policy orientation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irdly, it advocate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in policy articulation, continuity, and coord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Fourth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government-business synergy. Lastly,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ystemic and coordin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America;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Im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