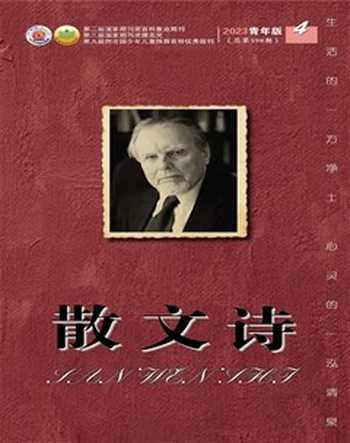神往的園地
曹爾
斷想
來到博物館,人聲寥寥——
我看到草原上升起一輪深紅的太陽,它的光芒鋪灑在沙河之中。戰靴、刀戟,不完整的頭骨和器皿,一一搬了出來,搬出來的還有棺槨。一副骨架到底留有多少過人的膽識、超凡的才能、顯赫的功名?我說不上來。但為了一段塵封的歷史,為了一處神往的園地,我仍縱馬馳騁。古道傳來悠遠的嘶鳴。
天下攘攘,人心離亂,我似乎看到一個英雄正策馬而來。他一意角逐群雄,抗衡命運,天下黎民莫不盡人彀中;他一意構筑更宏大的藍圖,成就偉業。捻一把隔代的風塵,還原連天的碧草和混沌的長河,是無數個來到草原上的人所需要做的事情。
真正來到草原,我的心,平靜得像清晨第一絲風兒吹開的花蕾。那是風和日麗的一天,是興之所起而千里以赴的一天,是不遑多言的一天。我的工作無非是將煤礦研磨成粉,送去化驗,日復一日。這與我所向往的草原出入頗大。我帶著一懷熱忱而來,落得一身自在而去,如同生長在草原低處的青草,牧羊人揮出的鞭影。
市井
微冷的春風,明媚的春光。
在人群里,我接住來自陌生人的目光,有時,覺得它像麥芒一樣,上上下下撲棱到我的身上。有時,又覺出它所析出的璞玉似的澄澈。常常在街市、火車站、農貿市場這些地方打轉,做一些不稱手的活計,遇到一些不稱心的人,這是我走出校園以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喜憂參半的每一天,無不充滿未知的可能性,雖說某些個日子意義非凡,而我覺得其中也沒有什么可值得特別地供奉。
生活,有時出其不意,有時略作抵償。
農貿市場,一個關涉到利益所指就格外不能容情的地方。一次,一輛小汽車與我的三輪車相撞,讓人不解的是,某些冷眼的看客勿論黑白便都一口咬定地說錯在我。這件事讓人倒吸一口涼氣,讓我知道人心是偏斜的,往往總偏向殷實的一方,而排斥貧弱的一方。唯有心存善念,心懷寬廣,方能篤定前行。
不管在任何場所,我最是看重一個人有著怎樣的襟懷,有著怎樣的韌勁,我堅信每個人都有一顆傾盡全力的心。我堅信,與眾多胼手胝足的人聲息相通,活得才更具真實性。
出游
久別了綿遠的公路,久別了凌風的跨河大橋。
記不得多久沒有外出旅行了,只記得那里滿是風浮動不止的油菜花田,緩坡上隨意標識著幾棵樹。站在長路的凸起處,可望見一圍湖泊之全貌,呈扁葫蘆形。既得其形,就姑且想當然地賦其以貌,以為它很美便是了,至于它需抵御著什么樣的風浪,四時陪護著什么樣的山神和馬匹,全不在本人的考慮之列。
我喜歡走馬觀花的旅行方式,喜歡輕描淡寫的寫作。
我寫下,模糊的更加模糊,明晰的明晰起來。
2017年6月,我和朋友前往貴德,相約去看遠處的山。那里的峰巒被起伏的山嵐吐納,那里的崖壁映射著褐色的光,那里的山脊線棱角分明,有章可循。若把山拋到一邊,那里便顏面頓失。如果把山上諸多微小的植株和縱橫交錯的丘壑一并拋進我的心里,那便自是另一番景況。
回來的路上,我若有所悟:得失順逆,接過世道人心的獻禮,一嘗其中甘苦交雜的滋味,我所尋求的目標,不外乎像這些湖、這些山一樣地活著。
果園
水渠北側睡著一座果園,已遭園丁擱棄了。
我曾一度想把它重建起來。低矮的夯土圍墻,不成體統,其上點染著塊狀的苔痕,如礦山上的積灰。一條小路把園子分作兩半,一頭是灰溜溜的園門,一頭是土坯房;路兩旁分置柵欄,外加幾種攀緣植物。地勢略高的一半種蘋果,低的一半種梨樹,皆以碧桃為埂。
春天來時,花木繁復。冬天來時,圍爐小坐。
來到土坯房,一應家什尚能對付,故可越俎代庖。待到冰消瓦解,便全身活絡起來,及至一葉知秋,略有所得。房前種豆點瓜,弄草蒔花。我想試一試,盡管我并不擅長飼養鴿兔。
這是梭羅給出的一個無妄的設想,后來與霜打的薩迪攜手同行,他那直橛橛的胡茬,傳布到了我的嘴邊。昔日的果園,化作一長串音符,從我和他之間的歌聲中飛散。我已久不入果園,已打消了再見它的念頭。實質上,當我隱微地想起,我的雙腳便觸及到了它。
到底是我想重建它,抑或是它要重塑我,我已無心討究。
- 散文詩(青年版)的其它文章
- 故鄉的儀式
- 青春書
- 人生如秀
- 十月(外三首)
- 我像往常一樣和你對話
- 那些詞語在懸崖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