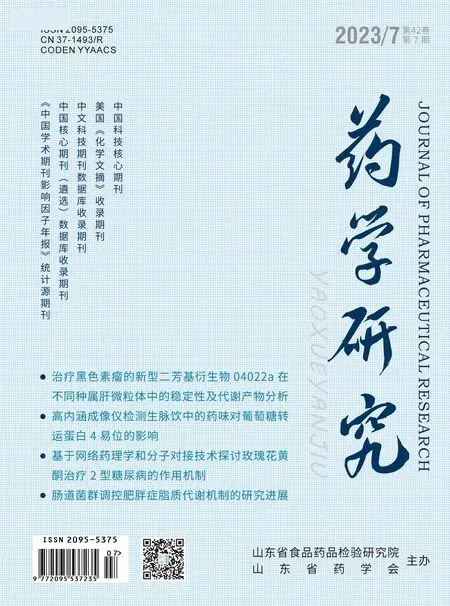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直接和間接調控作用研究進展
劉琪彧,穆泓宇,高源*,王伽伯*
(1.首都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北京 100069;2.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北京 100069)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是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急性突發性傳染病,截至2022年12月17日全球已有超過6.5億確診病例,死亡人數超過660萬。近1個月我國新冠上呼吸道感染確診人數超過98萬,死亡病例達515例[1]。
千百年來,中醫在與疫病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建了以三焦辨證和衛氣營血辨證等為代表的系統辨證方法,并形成了傷寒學說和溫病學說等完備的疫病理論體系。自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充分發揮中醫藥防治疫病方面的獨特優勢,始終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聯用的治療策略,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傳播與擴散。2022年4月,WHO發文建議各成員國使用中西醫聯合防治新冠的治療策略,肯定了中藥減輕臨床癥狀,降低病死率,減少向重癥轉化等作用[2]。然而,相較于Paxlovid(輝瑞)、瑞德西韋等具有明確的藥物作用靶點和藥理機制的西藥,中藥因其有效成分繁多、作用靶點復雜、藥理機制眾說紛紜等特點,往往難以綜合闡明其防治新冠的具體作用機制。事實上,中醫藥學基于系統論,將患者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來看,根據患者的全身狀況,統籌考慮器官(臟腑)之間、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遠程調控。因此,中醫藥的優勢不僅僅體現在其直接的抗病毒作用,更體現在對機體整體的間接調控作用,即通過抗炎、抑制細胞因子風暴以及調節腸道菌群等間接途徑發揮防治作用。
因此,本研究基于系統論,分別從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的新視角,綜合探討了中醫藥防治新冠/新冠上呼吸道感染的作用機制,以期從中西醫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全面闡釋中醫藥治療新冠/新冠上呼吸道感染的作用機理,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
1 新冠感染的中西醫認識
SARS-CoV-2屬于β冠狀病毒屬,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目前,Omicron變異株是繼Alpha、Beta、Gamma、Delta后新出現的第5種“關切變異株(VOC)”,其刺突蛋白受體保護區(RBD)的氨基酸易發生突變,使得Omicron變異株具有高感染性、高傳播性和高免疫逃逸性的特點[3]。我國現階段流行毒株以Omicron 亞分支BA.5及其變種(BA5.2、BF5.7)為主,其致病力明顯下降,感染潛伏期明顯縮短,疫苗接種的保護效果也下降[4]。絕大多數Omicron感染者表現為無癥狀和輕癥,有臨床癥狀者主要表現為中低度發熱、咽干、咽痛、鼻塞以及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癥狀[5]。癥狀出現后的5~6 d內,SARS-CoV-2病毒載量達到峰值。隨著SARS-CoV-2在體內的復制擴散,引起局部和全身的炎癥反應、過氧化損傷、組織細胞缺氧等,輕者可無明顯臨床癥狀,重者在癥狀發作后平均約 8~9 d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進而導致呼吸衰竭,這是70%的新冠患者死亡病例的原因[6]。
從中醫角度來看,新冠感染屬于“疫病”的范疇,主要病因是疫戾之氣挾“四時不正之氣”。從臨床表現上看,Omicron變異株感染初期病情輕緩,主要以風溫襲表為主,隨后逐漸出現熱毒犯肺證和濕蘊脾胃證,病至后期則多表現為余邪未盡,氣陰兩虛之證[7]。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其毒株的毒力大幅下降,但在證候表現上看極易化熱、化燥,因而咽干、咽痛、咳嗽、鼻干等上呼吸道癥狀比較明顯。且隨著毒株特點、流行地域、季節氣候等因素的變化,COVID-19的中醫病機也在不斷演變,故臨床辨證分析仍需三因制宜。
2 中藥的直接調控作用
SARS-CoV-2的生命周期包括吸附、穿入、脫殼、生物合成、組裝與釋放。SARS-CoV-2 通過S蛋白介導病毒與細胞表面血管緊張素2(ACE2)結合,使病毒以脫殼或膜融合方式侵入細胞[8]。ACE2廣泛分布于人體各組織,尤其在肺泡上皮、小腸上皮和血管內皮細胞[9]。因此,SARS-CoV-2感染后可引起以肺臟損傷為主的全身多器官損傷,包括心、腎、肝和腦等[10]。病毒進入宿主細胞后解體,將核衣殼和病毒RNA釋放入宿主細胞質中。病毒基因組RNA首先作為mRNA進行多蛋白pp1a和pp1ab的翻譯,并被主蛋白酶(Mpro)和木瓜樣蛋白酶(PLpro)切割為非結構蛋白(Nsps),同時作為模板在RdRp介導下合成新的全長基因組RNA和各種結構蛋白的mRNA,翻譯出結構蛋白和輔助蛋白,最終組裝成成熟病毒顆粒,繼續新的病毒復制周期[11]。研究證實[10],不少中藥(尤其是清熱解毒藥,如金銀花、黃芩等)可以通過阻止病毒與受體結合(靶向S蛋白或ACE2)、抑制病毒RNA復制(靶向RdRp)以及抑制蛋白裂解(靶向Mpro、PLpro)等方式直接作用于SARS-CoV-2,發揮直接抗病毒作用。
根據第九版新冠防治用藥指南,連花清瘟膠囊主要用于新冠輕型、普通型的常規治療中,也可用于流行性感冒屬熱毒襲肺證等,主要基于中醫絡病理論由銀翹散與麻杏石甘湯化裁而成的復方制劑,包含連翹、金銀花、麻黃(炙)、苦杏仁(炒)、石膏、板藍根、綿馬貫眾、魚腥草、廣藿香、大黃、紅景天、薄荷腦、甘草等13味藥,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熱之效。臨床研究[12]顯示,其與新冠常規療法聯合使用時,總體有效率可達92.73%,伴發熱、咳嗽、乏力以及胸悶等主要癥狀明顯減輕。在體外實驗中,連花清瘟膠囊顯著抑制SARS-CoV-2的復制,抗病毒活性IC50為411.2 μg·mL-1[13]。其活性成分大黃酸、連翹酯苷A、新綠原酸等可通過影響病毒S蛋白和宿主ACE2的結合來對SARS-CoV-2起抑制作用;槲皮素、山柰酚、黃芩素等可通過抑制Mpro從而阻斷SARS-CoV-2的生命周期[14];甘草酸可能通過阻斷Nsp1與RNA的相互結合從而抑制 SARS-CoV-2的復制、轉錄和翻譯過程[15]。此外,疏風解毒顆粒、藿香正氣顆粒等[16]都被證實其活性成分(如槲皮素、黃芩素等)具有靶向主蛋白酶的直接抗病毒作用。
綜上所述,中藥多組分的特點使其在抗病毒過程中可以直接靶向病毒生命周期的多個關鍵過程,大大提高了整體的直接抗病毒活性。而中藥多靶點的特征使其可以降低病毒產生耐藥的可能性,且部分靶標具有保守性,使中藥具有了成為廣譜抗病毒藥物的潛力。
3 中藥的間接調控作用
從患者臨床表現及檢測指標不難發現,中醫藥除了針對SARS-CoV-2發揮直接作用,改善呼吸系統癥狀之外,對于全身性的癥狀,如發熱、寒戰、乏力、全身肌肉酸痛,都起到了很好的治療或緩解作用。因此基于中醫系統論,作者思考除了直接作用外,中醫藥方面還可以通過跨器官(臟腑)、跨系統、遠程調控的間接調控機制來防治新冠/新冠上呼吸道感染。這些理論上不具有直接抗病毒效應的中藥可能通過細胞因子、抗體、腸道菌群等中間媒介物質(intermediate substances,IMS)作用于免疫細胞,發揮間接調控作用,以綜合全面調控機體的抗病毒能力,從而達到防治新冠/新冠上呼吸道感染的作用。
3.1 調節免疫《素問》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是人體抵御外邪的重要基礎,相當于現代醫學所說的“免疫反應”。SARS-CoV-2感染后,正常細胞免疫反應對機體具有保護作用。病毒與宿主細胞表面受體ACE2結合后,病毒的復制和釋放會導致宿主細胞焦亡并釋放相關分子模式,啟動固有免疫機制。同時,肺泡上皮細胞、內皮細胞和巨噬細胞釋放細胞因子,募集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和NK細胞等固有免疫細胞,并加工提呈抗原激活CD4+T細胞和CD8+B細胞,啟動適應性免疫過程[6]。若病毒誘導機體免疫力缺失,機體表現出臨床癥狀,則需要借助藥物增加適應性免疫力對抗感染;但若免疫應答被過度激活也可誘發細胞因子風暴,加重組織損傷,此時則可通過間接調控作用來抑制細胞因子風暴。而多項研究表明[17-18],在防治新冠/新冠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中藥可通過激活免疫細胞、促進抗體分泌和調節細胞因子的分泌等方式起到較強的調節機體免疫平衡的作用。
3.1.1 增強機體免疫力王永炎院士認為,新冠感染的主要病位在肺,其次涉及衛表與脾胃,重要證候特點是正氣不足、虛實并見,辨證治療時要格外注意顧護正氣,隨證加入補虛扶正之品[19]。臨床研究[20]亦證實,新冠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細胞(CD4+T細胞、CD8+T細胞、CD19+B細胞)顯著減少,出現抗體依賴性增強(ADE效應)的特征,提示患者適應性免疫應答受損。事實上,在防治新冠感染的組方過程中,除清熱解毒藥外,常用的中藥還包括黃芪、麻黃、黨參等扶正益氣類中藥,從而調控適應性免疫,在整體上增強機體抵抗力。例如,黨參多糖可以增加巨噬細胞釋放TNF-α、IL-6,以抑制病毒蛋白合成,刺激 T細胞、B細胞增殖及抗體分泌[21]。茯苓多糖可提高NK細胞和巨噬細胞活性及血清TNF-α的含量,起到增強免疫的作用[22]。就中藥復方而言,麻杏石甘湯(主要成分為麻黃、杏仁、石膏、甘草等)可通過阻礙Th2/Th17分化,促進CD4+FoxP3+Treg細胞生成并抑制mTOR和NF-κB活性來增強機體免疫功能,以減弱哮喘小鼠的氣道高反應性,改善肺部炎癥與損傷[23]。
除此之外,新冠的另一個特征是脾臟和淋巴結中的生發中心萎縮,在重癥患者的未萎縮生發中心發現了大量的 TNF,這可能會限制B細胞親和力成熟、同種型轉換和成熟抗體的產生,導致患者預后不良[24]。研究發現[25],大青葉可以促進小鼠脾淋巴細胞的增殖,并可以增強小鼠腹腔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從而提高體內細胞免疫功能來抗病毒感染。上述研究表明,中醫藥在防治新冠方面并沒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是從機體整體狀態出發,充分考量“正氣”的調控作用,通過增強機體免疫力,達到治療作用。
3.1.2 抑制細胞因子風暴細胞因子風暴(cytokine storm)是機體在外界強烈刺激下產生的以細胞因子(IL-1、IL-2、IL-6、NF-κB、COX-2、MCP-1、TNF-α等)大量釋放為特征的過激性免疫反應,其原因復雜、進展迅速、預后較差,常引起發熱、DIC、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多器官衰竭等嚴重并發癥,甚至造成患者死亡。目前,主要采用激素療法和抗細胞因子療法來調控過度活化的細胞因子,但存在延長病程和增加繼發感染的可能[24,26]。而許多中藥活性成分因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更低的毒副作用在抑制細胞因子風暴方面受到了廣泛關注。連翹的活性成分連翹酯苷A可通過抑制NF-κB活化和上調Nrf2/HO-1信號通路活化,抑制TNF-α、IL-1β、NO和PGE2的釋放從而發揮抗炎作用[27]。甘草作為新冠處方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中藥[28],具有良好的清熱解毒、化痰止咳、調和諸藥的功效,其活性成分甘草酸可通過調節HMGB1、NF-κB、ILS、COX-2和TNF等因子的表達,減少細胞因氧化應激而出現的損傷和凋亡,從而抑制細胞因子風暴,防治新冠感染[15]。
此外,中藥復方也被證實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抑制細胞因子風暴,調節機體免疫。清肺排毒湯可以通過調節NF-κB和MAPK通路等多種細胞因子風暴相關信號通路和抑制TNF-α、IL-1β、IL-8等細胞因子釋放來治療新冠感染[29-30]。連花清瘟膠囊可以在mRNA水平減少宿主細胞釋放TNF-α、IL-6、MCP-1、IP-10等細胞因子,減緩炎癥滲出物對機體的損傷,有效緩解病情[31]。宣肺敗毒湯可以下調THP-1誘導的M1巨噬細胞中IL-6、TNF-α、MCP-1和CXCL10等細胞因子水平[32],通過抑制PD-1/IL17A途徑和IL-6/STAT3通路減少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的浸潤,并抑制成纖維細胞膠原沉積、下調α-SMA水平,從而改善肺纖維化、緩解急性肺損傷[33-34]。綜上所述,中藥可有效抑制細胞因子風暴,通過調節機體免疫活性,間接地調控肺功能從而發揮治療作用。
3.2 調控腸道菌群腸道菌群是腸道微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復雜的動態網絡調控機制與宿主相互作用,參與調節宿主的代謝與免疫[35]。《黃帝內經》中 “大腸為肺之腑而主大便,邪痹于大腸,故上則為氣喘爭……故大腸之病亦能上逆而反遺于肺”,明確指出了呼吸和消化系統在病理上的聯系。而研究發現[36],新冠患者腸道有益菌減少而條件致病菌增加,且菌群失調的程度與疾病的危重程度成正相關。因此,可以通過中藥來改善腸道菌群失調,促進益生菌及代謝產物的增加,抑制致病菌的繁殖,從而激活機體免疫系統,減輕炎癥反應,以達到防治新冠感染的目的(見圖1)。

圖1 中醫藥防治新冠感染的作用機制
宣肺敗毒方是由麻杏石甘湯和麻杏薏甘湯等經典方化裁而成的新冠“三方”之一。將宣肺敗毒湯應用于DSS誘導的腸道紊亂小鼠,并對其結腸內容物進行基因測序,結果顯示,Akkermansia、Muribaculaceae和Lachnospiraceae等有益菌的豐度增加, Shigellae等致病菌的豐度減小,菌群失調程度緩解,說明宣肺敗毒湯可以通過重塑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群落,恢復腸道微環境的穩態,改善病毒引起的嘔吐、腹瀉等腸道紊亂癥狀[37]。此外,代謝組學和腸道微生物組學證實清肺排毒湯顯著調節了大鼠腸道菌群的結構,明顯上調羅姆布茨菌Romboutsia、Turicibacter、Clostridium sensu stricto1的相對豐度,下調Norankf、Lachnospiraceae的相對豐度,提示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冠的臨床療效可能與其對腸道菌群的調節有關[38]。
同時,不少早期研究也發現,一些常用的清熱解毒中藥可以通過調控腸道菌群發揮抗炎、抗感染效應,對治療新冠感染表現出巨大潛力。例如,魚腥草作為治療肺癰的要藥,其所含的魚腥草多糖可以恢復腸道微生物群,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腸道穩態,緩解HINI病毒造成的炎癥損傷[39];黃芩素可以使乳酸桿菌取代H9N2 AIV誘導出現的大腸埃希菌,從而改善腸道菌群紊亂,并有效防止SPF雞H9N2 AIV感染后腸道細菌易位,從而抑制繼發性細菌感染[40]。
4 結論和展望
4.1 中西醫結合共同防治新冠肺炎的理論探討西醫認為新冠感染是由SARS-CoV-2引起的傳染性疾病,故多聚焦于靶向病毒本身的藥物研發,這種直接的抗病毒機制確實在理論上最為基本。但隨著新冠不同變異株的出現,以及“長新冠”對新冠并發癥和后遺癥的關注,西醫這種藥物研發思路往往有所局限。而中醫“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辨證論治理念很好地彌補了西醫在整體上的局限性。中西醫聯合治療新冠已被證實確實可以縮短病毒清除時間、臨床癥狀緩解時間和住院時間,改善輕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預后。中醫藥在防治疫病過程始終堅持辨證論治的個體化治療,而面對大流行階段有限的醫療資源無法實現精準的個體化“辨證論治”時,中醫藥同樣可以通過“通治方”來實現“辨病論治”。“辨病論治”是在病因、病機、病變部位等很明確的基礎上,針對“病”的共性規律采用“通治方”治療,與個體化的“辨證論治”相互補充。基于這種“通治方”所提出的“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顆粒和膠囊、血必凈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4.2 綜合闡釋中藥防治新冠肺炎的直接/間接作用從系統論的角度看,中醫認為人體具有元整體性,任何部分性的病變都是整體生命活動失常的結果,所謂治病求“本”就是對人整體的平衡與協調。中醫治療新冠并非一味地采用對抗醫學的思想攻伐病邪,而是從多途徑、多靶點、多角度整體調控人體機能。因此,中藥除通過阻止病毒與受體結合、抑制病毒RNA復制以及抑制蛋白裂解等方式直接作用于SARS-CoV-2,發揮直接抗病毒作用,改善呼吸系統癥狀外,還可以通過多種中間媒介物質間接調控人體系統中各個層次的功能,對全身性的癥狀都起到了很好的治療或緩解作用。作者認為中醫藥在新冠防治中的獨特優勢正是體現在這種兼具直接和間接機制的綜合全面調控機體的能力,不僅關注病毒本身,更關注患者整體,從而充分認識疾病發生的原因,病機,病變部位轉歸等,從整體、全局的觀念看待疾病。這種“審病求因,治病求本”的理念不僅在防治新冠中優勢明顯,對其他流行的呼吸道病毒及新冠感染的可能復燃同樣能夠發揮“異病同治”的優勢。
4.3 總結中醫藥防治傳染病歷史悠久,在此次新冠感染防治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中藥在新冠防治的全過程發揮作用,既可改善普通型患者癥狀,縮短療程,促進痊愈;又可減輕重癥、危重癥患者肺部滲出,控制炎癥過度反應,防止病情惡化。第二,由于中藥多組分、多靶點、多通路的特點,且常多組分發揮協同作用,其抗病毒機制往往復雜,大大降低了病毒發生突變產生耐藥性的可能。最后,中醫藥的系統論和整合醫學的方法論,將機體看作一個整體,避免了“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將其和西醫聯合使用,相互補充,取長補短。在新冠感染的全過程中,中醫藥不僅可以針對病毒生命周期的多個節點,阻斷病毒的侵入和復制,發揮直接治療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基于系統論,從機體整體出發,通過增強機體免疫、防止細胞因子風暴、調節腸道菌群等方式,調節機體穩態,綜合發揮重要的治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