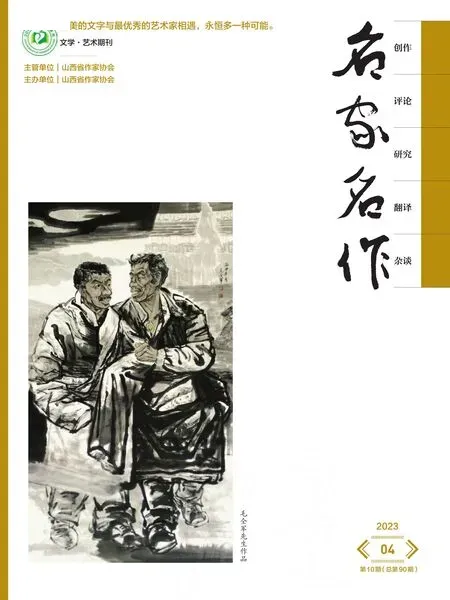淺析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詩學與詩文創作中的理性因素
蘇源宸
興起于18世紀晚期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對僵化的理性主義做出了激烈的反叛,在該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熱情及全新的、異質化的思想,為浪漫主義的產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此,我們與其說浪漫主義是哲學家的事情,倒不如說它是詩人、藝術家和“天才”人物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義者雖對理性持批判態度,但理性精神仍作為一種恒久存在的神話,存在于浪漫主義美學與作品之中,并深刻影響著它們的思想內涵。
一、美學思想中的理性精神
當我們追溯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文論時,便會驚奇地發現理性精神在其中仍舊占據著重要地位。縱然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對人的本質(理性還是感性)、國家的構建(契約還是文化)、歷史的進程(普遍還是各異)的看法大相徑庭。但是我們不能僅以此便將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比作一根繩子的兩端,將二者徹底分離,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早期浪漫主義尚不能脫離理性而立足。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浪漫主義者在詩學與美學層面仍舊認可理性對人的啟蒙作用,充分繼承了自古希臘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即將詩歌作為連接塵世生活與彼岸的精神橋梁,積極地運用藝術審美的方法去關照人類,賦予藝術關注人類命運的母題,承擔起塵世啟蒙者的角色。毋庸置疑,這是貫徹了啟蒙主義對文學的主題要求,即對人類命運的普適性關注,并啟迪民眾掃蕩思想中的封建殘余。作為浪漫主義者,雖然他們將這種責任感隱埋在諸如上帝、自然等宏大的、超越的理念里,但我們仍可從這些縹緲的意象之中窺見他們對世俗的關照。從這個角度來看,德國浪漫主義更是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審美人文主義的基石。
這種與理性的曖昧還體現了對絕對主體——“自我”的承認,只不過在啟蒙思想家那里“自我”被理性一以貫之,他們雖然自覺地認識到人自身作為一種主體的存在地位,但他們把“我思”前置于“自我”這一自然主體之前,運用二元論對問題進行考量,將人類理性化的思考視作更重要的存在。而浪漫派在此基礎上還強調人作為一種感性動物,他們充分繼承了費希特的自然哲學,費希特追溯了“我思”之前的“我”,用“自我”這一實存的、主客統一的絕對主體代替了“我思”,使浪漫主義者的思考出發點從傳統二元論的“我思”轉向以“我是”為優先思考的最高原理,如蔣孔陽在《德國古典美學》指出:“費希特‘解放’了浪漫主義者主觀世界,強調‘自我’的獨立性與自由。”[1]由此,在浪漫主義者的哲學之中,“自我”便是蘊含著各種感情與內心的不確定性,而心靈永遠是包含著激情與個性的統一整體,并不能劃分為各種機能,強調每個個體的多元性和無規律性。而這是邏輯與理性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由此他們提出要了解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意趣,更傾向于關注真實的“自我”。
此外,浪漫派也分享了啟蒙運動的線性時間觀,他們對民族歷史和過去的沉湎正是預設了“現時”,只不過他們與理性主義者對“現時”的樂觀不同,浪漫主義者更多表現出的是對現代的不信任;浪漫主義者也沒有拋棄歷史的進步觀,相比于理性主義者對現代化的自信,他們更注重歷史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辯證眼光,他們雖懷念中世紀的精神,但卻為了在歷史中探尋理想世界,“在回家的路上,尋找父親的宅子。”呼吁人們關注過往孕育現代性的東西,讓民族的傳統照亮墮落的現代,從而實現精神世界的“返鄉”。
由上可知,也許我們可以將早期浪漫派確立的信念稱之為“新理性”,他們承認理性的存在和價值,堅持啟蒙思想中對人類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理想,但同時又認為理性不能完全主導人類的認識和文化,而應與感性一道,共同促進人類進步。實質上,浪漫主義者是繼續了康德等人對理性批判和界定的工作,高揚獨立思考,體現人的自主性,敢于去除神話與迷信的啟蒙運動宗旨。與此同時,他們將感性的地位拔高,試圖將理性和感性統一起來,他們認為只有當理性和感性達到一種和諧的統一時,人類才能獲得完整的認識和真正的自由。而正是由于他們的觀點,使唯美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震蕩代替了理性的一統天下,在啟蒙運動后用理性為人類在經驗世界中祛魅,但他們又將理性神話了,傲慢的理性主義便從這時逐漸開始失去人們的信仰,大眾逐步對由理性的盲目崇拜造成的冰冷的歷史和工具的人性進行不自覺的抵制。而在藝術創作領域,浪漫主義者認為,人類內心的情感和感性體驗的重要性是相當的,甚至理性的方法可能更為重要,例如要在詩歌創作的過程中恰當地運用理性的形式,以此讓詩更富張力。由此可見,浪漫主義還沒有將理性主義的太陽徹底拉下地平線,他們讓太陽還保留著余光,讓理性神話得以延續。這正是在理性與感性、光明與黑暗交替的時節,也正是這一光明與黑暗參半的情形又為理性塑造了強大的張力,促進了富含理性的浪漫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二、浪漫主義詩歌中的理性烏托邦
在尚未與理性完全分道揚鑣的浪漫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浪漫主義者創作出的文學作品具有理性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義者們所強調的浪漫精神與感性精神其本質上就是“詩”的精神,對事物的浪漫化就是對事物的詩化,并非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經驗世界更深層次的思考,而這種感性的理解是與理性的認知相輔相成的。因此,我們若要具體找尋理性在浪漫主義中的余韻,就必須要深入詩中尋覓答案。
浪漫主義者認為詩是高于哲學存在的,其擁有救世之功用;在這個層面上,詩歌與啟蒙運動后所宣揚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在浪漫主義者眼中,詩又可以被分為有形之詩與無形之詩。有形之詩即是我們通常認識的詩歌,其作為文學作品,是由詩人心中的靈性感受“無形之詩”創造出來的,擁有詩所應具備的內容與形式。而無形之詩則是一種詩化哲學,即“宇宙之詩”,其連接著有限與無限,將個體與整體完全統一,是自然與宇宙創造力的顯現。當然,作為詩人,浪漫主義者自然是通過有形之詩來反應無形之詩,展現“天才”的思想與情緒;而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新理性主義,其詩文便不由自主地蘊藏著理性的光輝,其中以諾瓦利斯的詩文最為典型。
諾瓦利斯作為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夜頌》組詩充分反映出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詩的特點。詩歌中通過對自我的剖析,對萬物自由的想象代替了對客觀世界的摹仿,而自然作為詩歌表達的主要依托,寄托了詩人無限的幻想,又通過自然這一神秘的景象將詩人的主體情感轉移到客體的心靈。其內容通過超驗的手法充分表達了浪漫主義式的追求。而在這些顯然的美學特征背后,諾瓦利斯在詩歌主題的塑造過程中亦繼承了德意志民族重思辨、重內涵的傳統,并由此展現出理性的光輝,即對世界的期待與憐憫之情與對烏托邦式理想世界的追尋。正如其寫道:
你是那個少年,
他長久以來
就站在我們的墓地上思考;
黑暗中出現一個令人寬慰的信號——
更高尚的人類已經欣然起步。
讓我們陷入悲傷的,
現在讓我們生出甜蜜的渴望。
死亡中預示著永生,
你的就義換得我們的健康。[2]
在此,他將一位少年作為重點敘事的對象,如后世新批評學家艾略特提出的情感表達應有“客觀對應物”的觀點,少年就是整段詩歌的“客觀對應物”。在艾略特看來,“在藝術作品中,藝術家要表達某種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尋找一種客觀對應物。一組事物、一連串的事件等都可以成為這樣一種客觀對應物。藝術家借助作品結構使情感客觀化,批評家也就能夠根據這種客觀化的對象形態作出自己的解釋和評價。”[3]在此,詩人借少年的意象展現出一種年輕而富有生命力的情感,這位少年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做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一個欣喜的結論:“更高尚的人類已經欣然起步。”而通過這一思考所要表明的思想內容與新古典主義詩歌中出現的主旨是一致的,即對人類發展的自信與期待。在啟蒙運動后,理性主義者對人類理性抱有極大的信心,其認為人類的判斷力是優秀的,即便犯錯,也可以在后天通過學習訓練進行改善,由此來達成認識世界的目的,并成為更加完善的人,也就是諾瓦利斯在詩中所言的更高尚的人類。
通過少年的救世之舉不僅能反映出諾瓦利斯本人的浪漫主義情懷,即通過死亡回歸夜晚,獲得某種意義上通向彼岸世界的永恒。而且這種以自身之死換取的人類健康的要求,以近乎“詩”的形式來拯救客觀世界,構成了一種全體人類都能達到幸福的理想烏托邦式的場景。通過這種建構更能體現出他對于物質世界的憐憫與關注,反映出啟蒙主義者式的對世界充滿理性的關照之情。
同樣是在《夜頌》之中,諾瓦利斯通過將私人化的宗教經驗進行詩性的處理,以此來寄托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設想:
你,夜之靈感,天國的瞌睡降臨到我的頭上。
四周的地面慢慢地高起——在地面上漂著我的解放了的新生的靈氣。
丘冢化為云煙,透過云煙,
我看到我的戀人的凈化的容貌——她的眼睛里棲息著永恒。
——我握住她的手,眼淚流成割不斷的閃光的飄帶。
千年的韶光墜入遠方,像暴風雨一樣,
——我吊住她的脖子,流下對新生感到喜悅的眼淚。
這是在你、黑夜中的最初之夢。
夢過去了,可是留下它的光輝,
對夜空和它的太陽、戀人的永遠不可動搖的信仰。[2]
部分浪漫主義詩歌中濃厚的基督教式的對神明的崇敬在諾瓦利斯的詩句中被消解了。宗教不再是世俗所理解的一個現世的基督,而變成了一個寄托人類心靈情感的棲息之所,一個承載著泛神論幻象的極度美好的環境。這與在理性思維指導下的烏托邦文學有極大的相似之處。18世紀的烏托邦小說大多運用想象構建出一個遠比現實社會美好、幸福、自由、和平、富足的未來社會,即正面烏托邦,通過構建一個以理性王國所主導的完美社會來批判現實生活中尚不完備的資本主義社會。其作為一種以啟蒙思想為基礎的價值取向,達到了一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這與諾瓦利斯詩中提及的以基督教為根本環境,但卻蘊含著人性光輝的環境類似,二者雖在指導思想上有著差異,但其在存在性與指向性上是相似的,二者于現實世界都是一種恒久的“缺席”,亦為人類未來的幸福指明了道路。總而言之,當人類在現實世界陷入困境、遁入想象之中時,便描繪出理想世界的文學創作方向作為一種共性,并兼容于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之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學現象。
三、浪漫主義詩文中的反思理性
諾瓦利斯在《夜頌》組詩中構建出與理性烏托邦近似的浪漫世界,與此同時,在他的其他作品創作中,如短詩與長篇散文之中,亦能充分體現出蘊含其中的理性精神,在這些作品中,他對浪漫主義思想本身進行了反思與再創造。如他的一首小詩《致一只蚊子》寫道:
你這小蟲,不要飛得過分靠近這明亮的燭光
它使你眼花,你飛進去,它會燒掉你的小翅膀……許多聰明人也常像這樣,
當他被迷誤的假象所欺,盲目地奔了過去,
就會意料不到地跌倒在那里。
許多青年人也是如此,
碰到亮光,情欲的溫暖,
就受到迷惑,高高興興地投入那燒焦他的火焰。[4]
在這首小短詩中,詩人先從蚊子撲火這一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引入話題,而聰明人、青年人等在浪漫主義者眼中象征著天才與美好的形象在某些方面卻與蚊子無異,當他們面對假象或誘惑時,也會如昆蟲般不顧一切地沖上前去,即便被灼燒也不自知,他們正是被“本我”沖昏了頭腦,導致悲劇的發生。這與浪漫主義者所提倡的對自由、感性不顧一切的酒神狂歡式的想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對于過度浪漫的反思與批判在浪漫主義詩歌中是不常見的,反而是一種啟蒙主義者理性的反思性思維的體現。
無獨有偶,諾瓦利斯在他的小說《塞斯的弟子們》中亦構建了運用感性手法對理性做深刻關照,并通過理性的思辨對浪漫化的想法進行深刻反思的典型意象。其講述了男主人公夏青特在得到一本難以解讀的書后,為了尋找“伊賽斯”——生命圣潔女神,與自己的愛人洛森綠蒂告別,踏上了漫長征途。歷經諸多磨難之后,最終找到了這位象征著自然的女神。而揭開女神面紗的儀式性行為成為故事的高潮,面紗下等待著夏青特的既是自然女神伊賽斯,也是他的伴侶洛森綠蒂的形象。女神與愛人合二為一的戲劇性結局充分體現了浪漫主義式的對“愛”的美好想象。
而故事的反思理性又從何處體現呢?故事主人公夏青特(Hyazinth,即風信子石)與女主人公洛森綠蒂(Rosenblüte,即盛開的玫瑰花)之名形成了礦物與植物的鮮明對比。在不少浪漫主義詩歌意象中,礦物可以反映為堅硬、不可動搖的理性,而植物則是象征著自然、生命與熱烈的感性。這與諾瓦利斯的想法不謀而合:“男人代表認識與追求、理性、分裂、隔離,相反,女人則體現真理的所在、全面的智慧、整體與自然。”[5]男性對女性的追求,從深層語義的角度加以分析正是理性對智慧與真理的追求,這與其他浪漫主義詩文中對理性的批判大不相同,這就體現出諾瓦利斯對浪漫主義的反思。由此,我們便可將故事中夏青特對洛森綠蒂的個人情愛上升到啟蒙主義式的對真理與知識的愛方面,而夏青特對洛森綠蒂起初的離開亦可以被認為是諾瓦利斯對浪漫主義思潮中過度浪漫化現象的反思。總之,在諾瓦利斯的創作過程中,自我被“浪漫化”地抬升到了與自然平等的地位,但其思想內核依然沒有脫離18世紀所規定的啟蒙目的論與通過理性改造世界的思想框架,浪漫化的表達中仍是對真理的渴求,是運用理性對浪漫的反思性思考,是對理性及客觀世界不斷完善的愿望,并以此讓自我獲得在現世的幸福。這是諾瓦利斯詩學的意趣,更是啟蒙主義者對現實生活想法的真實反映。
諾瓦利斯作為德國浪漫主義詩派的代表人物,他試圖通過詩歌的形式探索人類內心的感性體驗和存在的意義,同時也關注邏輯、語言和思維的問題,將理性的知識與浪漫主義的情感和想象相結合,從而呈現出一種別具一格的個人創作特點。其在詩歌創作中多樣的意象選取與復雜的情感,充分體現出德意志民族重思辨、重內涵的理性思想內核。此外,他在某種程度上引領了德國詩歌的轉向,其深入“心靈”進行深刻剖析的創作方式,將描述客觀世界的詩歌導向內心與自我,拓寬了詩歌的主題,并對浪漫主義進行了反思,將詩歌與理性充分結合在一體,形成了德國浪漫主義的獨特風格。
四、結語
由上所述,德國浪漫主義詩派并不是同傳統觀點所認為的那樣與理性分道揚鑣,而是對理性進行批判地繼承。他們對福柯所言的“理性即酷刑”中的單純的工具理性進行猛烈反抗,而對理性中的合理科學成分進行了充分吸收。浪漫主義者雖然將理性的太陽拉下了神壇,讓感性重新回到了人們眼前,但他們仍舊讓二者得以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讓充滿理性思辨的浪漫主義文學在歷史的舞臺上大放異彩。時至今日,德國浪漫主義的回響仍在我們耳邊縈繞,其呼喚著我們對感性世界的追求和對工具理性霸權的警惕,而這對今日的社會發展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