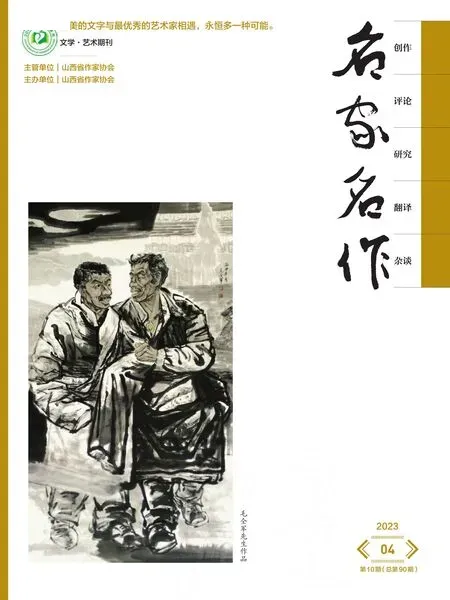村上春樹《開往中國的慢船》中的中國形象建構
康 嬌
《開往中國的慢船》作為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的處女作,藤井省三評論道:“自從村上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開往中國的慢船》以來,他持續書寫以中國歷史記憶為主題的作品,例如《尋羊歷險記》《發條鳥編年史》《天黑之后》。如果省略中國不提,就無法討論村上文學。”[1]可見該小說中的中國形象對村上春樹后來的創作影響重大。而比較文學形象學是以研究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為主要內容的一門學科。著名比較文學家伍依蘭則將形象學具體地解釋為:“ 形象學研究的是一國形象在異國的文學流變過程,即它是如何被塑造、被想象和被利用的,分析他國形象之所以產生的深層社會文化背景,并由此剖析投射的異國形象,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他國,以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整合。”[2]
文本的卷首和卷尾都引用了《開往中國的慢船》的歌詞,為什么要選取這首歌作為題眼?文本中是如何塑造中國形象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為何說這里的中國只是他想象中的中國,他的剖白又有怎樣的意義?對此,田中實意味深長地指出,日本人去中國,其實去紐約或者克里姆林宮都可以[3]。田中實將文本中的中國僅僅當作一個單純的符號來界定,此見解為我們研究村上春樹的中國認知拓展了新的思路,對我們深入文本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但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文本中是如何塑造和理解中國形象的,如何分析中國形象背后隱含的作者的文化心態和認知心理。本文將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出發,從歷史記憶和中國情結、中國的形象以及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三點切入,探討中國形象的塑造體現作者的創作意圖。
一、戰爭記憶和中國情結
在小說的卷首村上春樹就引用了一首美國人桑尼·羅林斯在1951年演奏的歌曲 On a Slow Boat To China——“無論如何,都想讓你搭上開往中國的貨船,船已借完,僅有兩個人”,與卷尾的“朋友!朋友!那遙遠的中國”相呼應,使得文本在一開始就打上了一種惆悵和失落的情懷。
小說伊始敘事者就站在現時點上發出“我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么時候,1959年抑或1960年”的疑問。繼而提出了到底誰會對“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的正確日期感興趣這個問題。文本作于1979年,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被稱為冷漠一代,作者的追問表達了他對年輕一代消極冷漠態度的否定。作者說自己的記憶含糊不清、前后顛倒,所以需要查閱新聞年鑒,在此的追問恰恰表明了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深不可測的關系。
這一章敘事者在追溯自己第一次遇到中國人的時間時,并沒有第一時間就想起與中國人的交往,而是想起了約翰遜和帕特森這個重量級拳擊冠軍的那場拳擊比賽,約翰是一名美國著名的拳擊手。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日本系列改革被稱為戰后民主改革,而“我”的小學時期正是在美國占領下的戰后民主主義時期,二戰中慘敗的日本淪為美國的殖民國。《日美安保條約》的簽訂使得日本從此喪失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完整。1959—1960年發生了大規模的反對安保條約改訂的安保斗爭。因此,1959年和1960年在 “我”的記憶中就是“丑陋的雙胞胎兄弟”。
整個小學時期,戰后民主主義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個晨昏,我們可以從學校的棒球比賽中一窺這種感情的深刻內涵。作者用了四個模糊來形容自己的記憶,而敘事者“我”也是個不可信賴的對象,敘述呈現出不可靠性,又用確切來形容自己記住的兩件事。小說正是通過在事實與關于事實的評判之間的差異,顯示出敘述者對于中國人和棒球比賽連段記憶的深刻性。棒球是從美國傳過來的風靡日本的運動,而戰敗后的日本少年吃的是美國供給的面包,接受的是美國式的戰后民主主義教育。而敘事者“我”打棒球時撞在籃球架上引起了腦震蕩,在昏迷時說了“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作者在追溯自己第一次遇到中國人的時間時,并沒有第一時間就想起與中國人的交往,而是想起了1959年和1960年的拳擊比賽以及棒球賽暈倒后掉落面包的事,以及那句“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這種屈辱的記憶就算過了20年卻還在敘事者“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這是日本人難以忘卻的戰敗后的屈辱體驗。
屈辱的近代化體驗,讓“我”開始考慮人存在的意義和未來,而對于人存在的思考的終點就是死,死使“我”想起中國人的臉。為什么死會讓我想起中國人?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以及2019年出版的《棄貓》中都有所提及。村上春樹的父親參加過二戰,并親赴中國戰場,親眼見過日本人殺害中國人的慘狀。父輩的戰爭記憶以非語言的形式完成了代際的傳承,父輩的戰爭創傷也轉化成了“我”內心難以治愈的記憶創傷。“我”繼承了父輩的彌漫著死亡意味的戰爭體驗,并以文字的形式將這段記憶語言化,中國這一他者形象承載著日本人的民族歷史記憶以及村上春樹的家族記憶。
二、中國人的形象塑造
村上春樹在日本港都神戶長大,在神戶有著名的中國城,中國對于村上春樹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正如張月所說:“異國形象是形象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但是這種形象并不是異國形象現實的復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創造出來的。”[4]文學中作為意識形態形象的他國形象,其實有著非常豐富和多變的表現形式,可能是人物、事物、景物,也可能是思想觀念、文化氛圍等。而在文本中敘事者就選擇了以在他人生的三個階段遇到的三個中國人來構建中國形象。如果說第一個中國人給“我”的印象是無奈的誠懇,第二個中國人是被迫的耐心,最后一個高中同學給“我”的印象則是他者境遇下的磨損。他們就如同鏡子,鏡中照映出了小學、中學和大學時期三個不同的“我”的影子。
“我”遇到第一個中國人是在我的小學時代。在去參加小學會考的路上,“我”看見中國的小學生在陡坡上排著隊朝一個方向行進,低著頭默默走路。讓人壓抑的孩子們的身影也代表孩子們在日本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生活,他們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被整個日本社會他者化了。第二個就是大學二年級那年春天打工遇到的中國女友的故事,雖是中國人,卻沒回過中國,一起打工的她干活非常熱心,但這種熱心類似于生存的緊迫感。在這里刻畫了一個被排斥、戰戰兢兢的中國女孩的形象。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她在日本社會中面臨的巨大壓力。“我”和她跳完舞后,本來可以順路把她送回家,但卻把她送上了相反的電車,等到她返回車站時已經過了門禁的時間,她認為這種行為是對她的一種不懷好意的捉弄。
然而“我”又陰差陽錯地犯了第二個致命錯誤,幾個小時以后我才發現把寫有她手機號的煙盒隨手扔掉了,導致之后“我”與她徹底失聯,她從“我”的世界消失了。如果說第一次送錯電車確實是“我”的無心之失,那第二次隨手扔掉聯系方式不得不讓人認為這是出于某種故意或者惡意。正如女生所說的:“即使你真的弄錯了,那也是因為實際上你內心是那么希望的。”“我”并沒有承認,也沒有反駁,只是嘆息,相當于默認。這使女孩更加確認了自己所承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的原因就是她是一個中國人,而“我”卻沒有否認,由于國家和民族差異以及戰爭問題造成的兩國之間的鴻溝,如今現實地橫亙在這兩個年輕人中間。而中國女孩也感受到“我”的這種無意識的惡意,所以從“我”的生活里徹底消失了。
第三個遇到的中國人是“我”高中時的同學,他沒有固定的工作,只能走街串巷地向中國人推銷百科字典。“我”見到他時卻沒有認出他,他認為“我”是想要忘記過去的事情,所以才記不起他。“我”的遺忘和他的牢記產生了鮮明的對比,“我”在內心里潛在地想要忘卻,想要逃避過去的記憶。而“我”的種種表現表明了忘卻不只是個人層面的,也是當時日本政府和國家對于戰爭問題的回避態度的真實寫照。而“我”的遺忘代表著日本不愿面對戰爭歷史、回避責任,企圖以遺忘為借口開脫歷史罪責的故意。直到他申明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我”才猛然想起這位高中同學,由于他在日本社會中的他者身份,連他的工作都被限制為只能賣給中國人,靠著一點同胞情意在日本勉強維持生存。最終,“我”只能用沉默結束了這次見面。
這三個中國人的形象寫出了敘事者“我”對于中國人的負罪感,但相比于負罪感而言,更加直觀的是“我”對中國人融合著熱情和冷漠、接近和疏遠、遺忘與記憶的復雜心態,而中國人在日本扮演的是備受歧視和傷害的他者角色。村上用緘默的口吻和同情的筆桿講述著這些在日本生存的作為他者的中國人。在小說中多以第一人稱“我”來敘事,對作為他者的中國人遭受的傷痛進行敘說。
三、“自我言說”的中國形象
在山手線的列車里,“我”又想起女孩的話,開始感悟到“我”和那位中國女生一樣,“這里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里沒有我的位置”。日本日益現代化和城市化,經濟的高速發展對人生存環境的擠壓,使人成為城市機械化生活中的一個齒輪,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喪失了存在的自由。而在山手線上的“我”所看到的情形,則是借他人的眼光完成自我認識和自我定位。中國作為一個他者的存在,成為日本進行自我認識、自我敘述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比較文學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即國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5]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經濟飛速發展,逐漸邁入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不斷擴張,使得人們更加功利化,人與人的關系漸漸疏離,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分離,精神家園變得荒蕪不堪,高度發展的后工業帝國帶給人們的是壓抑和苦悶,是精神的束縛和價值觀的崩壞。而“我”在這樣一個“無限膨脹的中介帝國”也變成了一個邊緣化的個體,失去了自我認同感和存在感。在山手線的列車上“我”又一次想起那個中國女孩的話:“這里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個被疏離的中國女孩的形象內化成“我”的形象。“我”在列車上看著這個咖啡果凍一般的城市,使“我”真切地體會到了被疏離的痛苦,只是女孩是因為國家民族和戰爭遺留等問題被迫被隔離在日本社會之外,而作為日本社會一員的“我”卻是出于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自發地認識到自己被社會隔離,感受到失去自我認同感和存在依托的痛苦。正因為如此,村上春樹才構建出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中國,是唯“我”一人能讀懂的中國,是只向我一個人發出呼喚的中國。
異國形象具有“言說自我”和“言說他者”兩種功能,用中國的烏托邦形象塑造實現了“言說自我”的功能。“對于他者形象的描述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我形象,這是因為作家在對異國異族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導致對自我民族的對照和透視。正如狄澤林克所說:‘每一種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時伴隨著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形象生成時,一定會伴生出一個自我形象,他者形象猶如一面鏡子,照見了別人,也照見了自己。”[6]他國形象的塑造在自我—他者的關系中相比于表現他者,更加注重表達自我。在他者言說中認識自我、反觀自我,從他者關注轉向自我審視。敘事者的主體意識更為重要,或者說,探究他國形象的構建,歸根結底是為了探究敘事者作為他者對于異國的理解和闡釋。沒有到過中國,但有著強烈的中國情結的村上春樹,曾經閱讀過大量中國的書籍,了解中國文化,所以他將中國描繪成一個烏托邦式的國家,表達了他對中國肯定的態度和向往之情,他創造出的中國形象是理想的烏托邦。它已經消解了地圖上中國的具體形象,成為敘事者內心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烏托邦具有“社會顛覆的功能”[7],敘事者將遙遠的中國作為自己想象的終點,并借助這一異國形象實現了對20世紀80年代日本現實社會的背離和顛覆,表達了對日本發展的迫切渴求和對未來殷切的期望,描摹了日本未來發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