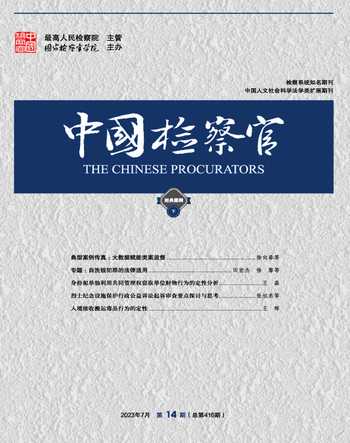入境接收搬運毒品行為的定性
王暉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某、黃某某均為香港居民,兩人均供稱在香港實施過多起毒品犯罪。2019年4月上旬,張某某(香港居民,另案處理)以30萬元港幣的報酬,雇傭何某某幫其到內地接運并處理一批毒品。4月13日,張某某指使何某某租下某小區C棟1603房(以下簡稱“C1603房”)和A棟1805房(以下簡稱“A1805房”)。4月14日,何某某聯系黃某某從香港入境到深圳,按張某某的安排,駕車到惠州市惠陽區,從一輛商務車接下四個藏匿有毒品的大箱子,搬到C1603房存放,后將數量發信息告訴張某某。4月20日至4月24日,何某某、黃某某連續三天從香港入境,打開之前存放在C1603房的四個大箱子,取出其中的“木塊”,分批次拉到A1805房,使用鉗子、螺絲刀等工具進行拆卸。經拆卸,每一塊“木塊”均拆出兩包相同規格包裝的毒品,每包重約250克。
4月24日,兩被告人準備返回香港時被公安機關抓獲。公安機關當場繳獲C1603房和A1805房鑰匙,并在2套房內共繳獲377塊(袋)毒品,凈重93681.92克,每塊(袋)均檢出可卡因成分,含量為66.24g/100g—80.53g/100g不等。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于2019年4月26日拘捕張某某,查獲約60千克可卡因,并以販毒罪起訴張某某,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審理。一審法院判處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走私、販賣毒品罪。被告人提起上訴。二審階段,檢察機關通知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需證據材料。公安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5條開展個案司法協助,但未提取到張某某的供述和其在香港犯罪其他證據材料。
二、分歧意見
被告人何某某、黃某某從香港入境內地接收、搬運、拆卸毒品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47條規定無爭議。但是,根據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三)》(以下簡稱《立案追訴標準(三)》)第1條,刑法第347條是選擇性罪名,對同一宗毒品實施了法條中的多種犯罪行為,并有相應確鑿證據證實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犯罪行為的性質,依次選擇適用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罪名。對于本案中,認定何某某、黃某某的具體罪名有五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走私、販賣毒品罪。兩人受張某某雇請,均從事過毒品犯罪,知道本案涉案毒品是張某某將運往香港進行販賣的。兩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實際上是張某某走私、販賣毒品中的一個環節,應與張某某團伙走私、販賣毒品犯罪進行整體評價,而不應割裂開來。
第二種意見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罪。兩人除了實施上述走私、販賣的行為外,還實施了接運毒品到某小區并搬送上下樓的行為,毒品發生了位置移動,還應當增加認定構成運輸毒品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運輸毒品罪。兩人拆卸、搬運毒品的目的,只有主觀供述,尚未付諸實施,不能將還未發生的目的行為,當成認定走私、販賣毒品罪的理由,故只能對搬運行為進行評價。
第四種意見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販賣毒品罪。兩人明知毒品數量巨大,且知道實施的搬運、拆卸行為是販賣行為的一個部分,屬于牽連行為,不單獨評價,故定販賣毒品罪。
第五種意見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兩人明知毒品運送到香港販賣,依然受雇入境,實施接收、搬運、拆卸毒品的行為。兩人實施的行為,是張某某共同販賣毒品犯罪中的一個部分,且接收搬運毒品應當單獨評價。
三、評析意見
上述五種分歧意見,爭議的焦點是如何認定本案的具體罪名,即現有證據證明的具體接收、搬運、拆卸行為,應當定性為刑法第347條中的哪種行為。爭議的焦點既涉及走私、販賣、運輸三種犯罪行為的證明和認定標準,還涉及行為之間的牽連吸收、共同犯罪等問題。本文認同第五種意見,分析如下:
(一)不構成走私毒品罪
根據《立案追訴標準(三)》,刑法第347條中的“走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將其運輸、攜帶、寄遞進出國(邊)境的行為。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走私進口的毒品,或者在內海、領海、界河、界湖運輸、收購、販賣毒品的,以走私毒品罪立案追訴。有觀點認為,何某某、黃某某兩人從香港入境處理毒品,且明知毒品可能運往香港,可以據此推定構成走私毒品罪,更何況兩人是張某某犯罪團伙成員,張某某在香港遙控操控犯罪,應當與張某某犯罪團伙進行整體評價,共同構成走私毒品罪。筆者認為,現有證據雖然能夠證實兩人與張某某實施了共同犯罪,卻無法將共同犯罪認定為走私毒品罪。
三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但無法證實是走私毒品的犯意。張某某直接雇請何某某處理毒品,黃某某受何某某糾集參與本案,兩人均知道受張某某雇請入境處理毒品,被承諾給予報酬,均承認曾在香港幫張某某實施過拆卸、運送毒品可卡因的犯罪行為,并且在拆卸、搬運等處理過程中,看到拆卸出的袋裝可卡因,進一步知道處理的是毒品。兩人明知處理的是毒品,依然受張某某雇請實施系列毒品犯罪行為,張某某、何某某、黃某某已經達成毒品犯罪的犯意聯絡,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但是,這種處理毒品的共同故意,既可以狹義理解為搬運、拆卸毒品的故意,也可以進一步解讀為販賣、運輸毒品的故意,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是走私毒品的故意。并且,目前在案證明走私故意的證據只有兩人供述,其中不乏猜測語言“可能運送往香港”。兩人雖然具有概括或者放任毒品出關到香港的隱約故意,但是卻不知道如何過關、通過何種途徑出境,故意的內容不明確,達不到確實充分的證明程度。
三人實施了共同犯罪行為,但無法證實是走私毒品行為。一是兩人的具體行為,不能直接認定為《立案追訴標準(三)》法條中走私毒品罪的三種具體行為。兩人雖然進出邊境,但并沒有攜帶毒品一同進出邊境,毒品依然存放在內地;在案證據也無法證實涉案毒品的來源,無法確定是走私進口的毒品,更無法證實兩人支付對價收購毒品,毒品存放地也不是內海、界河等國邊界地區。二是三人的共同犯罪行為,不能證明為走私毒品行為。張某某在香港被抓獲,但是未移管內地,既缺少指揮毒品出境香港的供述,也未收集到證實內地被查獲毒品正在被運往國(邊)境外的證據。兩人在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支配下,入境后實施了一系列中間行為,這種單純的接收、搬運和拆卸行為,無法證實是為了出國(邊)境做準備,即使未來可能會有走私毒品行為發生,但現階段還不能證實已進入準備或者正在實施階段,連犯罪預備階段都達不到。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更沒有證據證明存在走私毒品犯罪行為的前提下,不能憑兩人入境實施毒品犯罪,且知道毒品可能運往香港的隱約故意,進行客觀歸罪來認定構成走私毒品罪。因此,目前證實搬運、拆卸用來走私毒品的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程度,不宜認定構成走私毒品罪。
分歧意見中,認為兩人的行為應當作為張某某犯罪集團的一部分整體評價,具有合理性,但是認定構成走私毒品罪,必須準確審查證明標準是否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
(二)構成販賣毒品罪
根據《立案追訴標準(三)》,刑法第347條中的“販賣”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的行為。兩人被張某某雇請,從香港入境實施一系列毒品犯罪行為,但并未直接實施銷售或者購買的行為,只是明知毒品用來販賣,是否可以認定為販賣行為?厘清此問題,需要從規范和證據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規范層面看,可以根據犯罪“目的”來推定販賣毒品。從販賣毒品罪的定義可知,除了直接非法銷售進行販賣外,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買毒品行為也應當認定販賣毒品。為了販賣而購買毒品也是販賣,此處的“為了販賣”就是犯罪的目的。對于用“目的”來推定販賣,司法解釋性文件也有多種不同形式的規定。一是直接推定販毒人員關聯場所查獲的毒品為販賣。根據 《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法〔2015〕129號,以下簡稱“武漢會議紀要”)第2條第(一)項,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販毒人員后,可直接推定查獲的毒品也為販賣,明確規定從販毒人員住處、車輛等關聯場所查獲的毒品,一般推定為販賣的毒品。即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過販賣行為,被認定為販毒人員,除非有明確相反的證據,這些被查獲的毒品直接可以推定是用來販賣的。二是被查獲大量毒品的吸毒者、代購者、接收寄遞者,有證據證明犯罪目的的,則按“目的”定罪。武漢會議紀要規定吸毒者在購買、存儲、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毒品被查獲,毒品數量達到較大標準,沒有證據證明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可以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條文中采用目的性的“為了”表述,指出有證據證明毒品的目的用途,即“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應當以“目的”認定查獲毒品的性質,證明不了“目的”才退而求其次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毒品犯罪行為的“目的”成為證明和定罪的關鍵。因此,刑法第347條規定的四種行為,販賣行為認定有著有別于其他三種行為的特殊規定,可以用證明犯罪“目的”來認定販賣。分歧意見中,第三種意見認為販賣毒品罪不能以證據證明的“目的”來認定行為性質為販賣,與規范性文件的解讀相矛盾。
第二,從證據層面看,能夠確實充分證明構成販賣毒品罪。理由之一是現有證據證實兩人具有販賣毒品的“目的”故意。何某某、黃某某均供述是明知毒品為了販賣,屬于直接供述的已經知道用來販賣的明知;且根據監控視頻、現場勘查記錄等證據,證實兩人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搬運轉移毒品和拆卸毒品,屬于根據《立案追訴標準(三)》第1條第8項可以認定“應當知道”的推定明知。根據前述規范性文件分析,販賣毒品的主觀方面,已經達到證明兩人用來販賣毒品的證明標準。理由之二是現有證據證實兩人在販賣的主觀故意下,實施了接收、搬運、拆卸毒品等具體犯罪行為。理由之三是張某某在香港被檢控販毒罪,雖然是在不同的法域內被檢控,根據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1]原則,最終認定的罪名還需要經香港法院審理判罪后才能確定,但是檢控的罪名還是從側面印證了犯罪團伙的罪名。上述三個理由,根本的理由是第一個、第二個理由,第三個理由雖然還要面對最終判決罪名考驗,以及內地與香港不同法域販賣毒品罪犯罪構成的差異,但還是可以作為定性的重要參考。
(三)構成運輸毒品罪
根據《立案追訴標準(三)》,刑法第347條中的“運輸”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攜帶、寄遞、托運、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運送毒品的行為。兩人受雇接收、短距離運輸、在同一小區不同樓宇不同樓層之間的搬運毒品行為,是否達到運輸毒品犯罪中的運輸行為認定標準?分岐意見當中有不同看法,既有意見認為構成運輸毒品罪,也有意見認為被其他行為吸收,不單獨評價。對此,既要將接收、搬運行為與前述拆卸行為一并放到共同犯罪中考量,還要從運輸毒品本源含義進行分析。
筆者認為,運輸毒品罪中“運輸”的內涵,關鍵不在于從其一般含義上的位置改變,特別是位移距離的遠近去理解,更多地應該從運輸毒品罪中“運輸”所包含的刑法含義——具有使毒品流動、擴散的功能上去理解,即從其在刑法中所應發揮的規范作用和應承載的社會功能上去考量。運輸毒品行為直接使毒品從生產環節或者持有的靜止狀態,進入到流通環節,增加了毒品的擴散性風險,客觀上對毒品的非法交易和消費也具有促進作用。因此,認定運輸毒品行為,不在于移動距離的遠近,而在于因位置移動增加流通、擴散的風險。比如說,在販賣、走私、制造毒品犯罪過程中,不以擴散、流通為目的的短距離移動毒品,甚至短距離攜帶毒品到約定地點進行交易,一般不單獨認定為運輸毒品罪。
從本案來看,兩人接收、搬運毒品,既有平面空間的接運,又有立體空間的上下樓搬移。這種搬運行為,雖然距離較短,且屬于同一小區內的位置移動,但是兩人實施此行為,是為了在認為相對“安全”的空間,將毒品從完整的木板當中拆卸出來,進而實施走私、販賣等流入社會的行為,不是無意義的短距離移動,而是已經成為一種有刑法意義的、促成整個犯罪完成的毒品位置轉移行為,應當單獨進行評價,構成運輸毒品罪。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公安機關及時收網,本案接收、搬運的巨量毒品可能已經流入社會。第一種意見和第四種意見沒有看到接收、搬運行為特殊“價值”和“意義”,沒有正確將此行為評價為具有刑法意義的行為。
此外,運輸毒品行為也不應當被走私、販賣、制造三種行為吸收。首先,刑法第347條當中的四種行為,社會危害性不相上下,不存在“主行為吸收從行為,重行為吸收輕行為”情形。其次,刑法第347條規制“制造”以外的其他三種行為,旨在對促進毒品非法流通的每一環節予以規制,這三種行為都是在幫助毒品從源頭向消費終端擴散。司法實踐中,犯罪分子為走私、販賣毒品而制造毒品,為走私、販賣、制造毒品而運輸毒品,以及為了制造毒品而走私、販賣、運輸“成品”“半成品”毒品的情形并不少見。正是由于刑法第347條設置了選擇性罪名,使得這種目的與手段的牽連行為,不再需要運用牽連犯理論予以解釋,而是直接依照實行的行為確定罪名。因此,第四種意見認為存在牽連行為、販賣行為吸收運輸行為,是沒有準確把握四種具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綜上,本案何某某、黃某某接收、搬運、拆卸等行為的性質,雖然應當適用共同犯罪的罪名來認定,但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構成走私毒品罪。兩人短距離搬運毒品行為應當作為運輸毒品罪單獨評價;從規范和證據來看,本案還構成販賣毒品罪。
最終,二審判決采納第五種意見,即二審出庭檢察員的意見,改變一審判決走私、販賣毒品罪的定性,認為何某某、黃某某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被告人何某某死刑立即執行、被告人黃某某死刑緩期2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