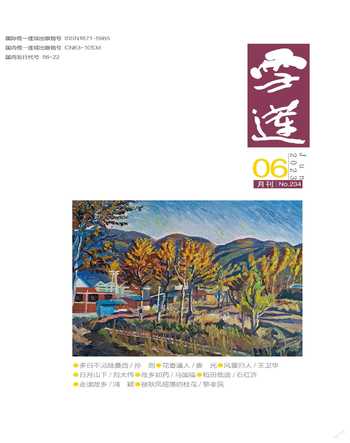月光深處的背影
月光,也許是太陽入睡后對白天的回憶或沉思。月光下的大地,朦朧中透著一份飄渺的鄉愁和淡淡的清香,猶如舒伯特的小夜曲,掠過清澈的圩鄉溝渠,激蕩起一縷美麗的念想,穿過黑夜,飄落在微微搖動的一棵棵梧桐樹的樹梢,隱約,又清亮。
梧桐樹下有兩排青磚平房,這就是圩鄉中學的教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這里,我與它結下了三年情緣,終生難忘。
學校是當地一座最大的祠堂——唐家祠堂改建的。唐家是大戶,圩鄉有所謂“丁半邊,劉半邊,中間一個唐包心”的民謠。祠堂自然不會小。祠堂的東邊有一口大塘,水面頗為遼闊,東風拂來,煙波激蕩。塘的東面和南面與圩內溝渠相連,便四通八達。中間有一土墩,土墩上一座瓦房。我們在學校讀書時,那是作為公社副業隊的辦公場所,常看到有男男女女劃船出出進進。
塘,名曰書墩塘。墩,又叫烏龜墩。據說是唐家祠堂的風水塘,土墩上原有一座石亭。相傳,唐氏族長“大先生”唐石亭,和國民黨要員湯志先曾在書墩塘畔以對聯相譏,口耳相傳,成為鄉里人茶余飯后的談資。湯志先手指烏龜墩說:“烏龜塘(唐)石亭”。“大先生”隨即應道:“王八湯至鮮(志先)”。唐石亭1921年任安徽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的監學。其時,惲代英、肖楚女在學校任教,章伯鈞是校長。后曾任望江縣縣長。湯志先,五四運動是安徽省學生運動骨干,后留學日本東京大學讀政治經濟科,曾任國民黨安徽省省政府代理主席,1985年病逝于美國洛杉磯。二人都曾從這里走過,也都已走進了時光的深處。
一
對于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書墩塘的一汪碧波給我們留下的是許多快樂的時光。
塘畔有一排翠綠的楊柳樹,中午,大家打完飯就喜歡端著飯碗,在樹下邊聊邊吃。清風徐來,浪拍塘岸,岸邊是一層厚厚的殘磚斷瓦,被水洗得干干凈凈,有的長著一絲青青的苔蘚。吃完飯就把茶缸往水里一丟,迅速舀一缸水,蕩一蕩,喝一口漱漱口,用力向水面噴去。水面上漂浮起一層一星兩點的浮油。此時,三五成群的小魚也游過來,仿佛也來趕我們這一場午飯。
我不住校,中餐在食堂打飯吃,飯票是用帶去的米換的,菜票就要用錢買了,一般是五分錢的菜,也是食堂賣菜的最小單位。燒菜的工友姓楊,有一條腿有點跛,走路一歪一歪的,眼睛卻有點高高在上,不怎么搭理學生,讓大家感覺他有點兒冷漠,所以有的學生私下里就叫他“楊截子”。一天中午,端著缸子打完飯,到楊師傅處排隊打菜,輪到我時,我從口袋摸出僅有的一張菜票,發現是兩分錢的,夠不上買一份菜,臉刷的紅了,窘迫地看了看鐵鍋中熱氣騰騰的青菜豆腐,猶疑著縮回手,準備吃白飯去了。楊師傅看也沒看,舀了一勺子菜湯,沒等我轉身,把勺子傾了一下,倒出一些湯水,說:“好了,兩分錢。”話沒落音,“啪”,一勺子菜已倒進了我的飯缸子。
直到今天,閉上眼,我依然能感受到那鐵勺與飯缸的輕輕一碰的震顫。那震顫中所發出的余音掠過食堂里的嘈雜聲久久地回蕩在我以后的紅塵路上,那么清晰,悅耳。
吃完了,不走。大家在清涼的樹蔭下聊著天南地北的故事,也有的學著吹口琴,吹笛子。有認真的,離得遠遠的去背書了,那是極少數,大家反而向他投去鄙夷的目光,說假認真。直至上課鈴響起,大家才一溜煙鉆進教室。
有時,翻撿起岸邊的瓦片,比著打“片遞子”,看誰扔出去的瓦片子在水面漂得最遠,留下的圓圈最多。于是,那一塊快因毀于某次戰火或天災,沉積了多少年的殘碎瓦片,又幸運地被我們撿起,閃爍著刀鋒的銳利,在柔和的水面拼命地向遠方切去。可無論漂得多遠,終究又沉浸于更深的水底,不知何時再重見天日。
悠悠的碧水對我們圩里的少年永遠充滿了無盡的誘惑。一個初夏的中午,暑熱已顯。我們幾個同學在樹蔭下無聊地聽著知了的聒噪。有人提議游到書墩塘上去看看。好奇心驅使我立即脫下外衣,走入水中,游了一會兒,回頭一看,居然只有我一人。他們穿著短褲站在水中朝我咧著嘴笑。游到深處,藍天白云相映于水中,水天渾然一體,一潭清水便顯得更加深邃,幽遠。孤身一人,一絲怯寒之意從腳底蔓延上來。可我又不甘回頭,硬著頭皮游了下去。上了岸,不敢再游回來,就悄悄地用公社副業隊的小船劃了過來,居然沒有被發現。
后來,聽說楊師傅調到縣城去了,再也沒有見過他。但那一碗菜湯,仿佛化作了一張芯片置入了我的心間,常常影響著我對這個世界的判斷和行動。
二
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師就是王石林老先生。
我們那屆學生可以算王石林的關門弟子。他是整個學校中年齡最大的老師,在學生中有一種神秘感。我們學生當然無從知曉王老師云蒸霧罩的真實來歷,也不會真的去探究那些,只知道他的英語水平是杠杠的,教書也是貼著心認真地教。我們的學長中有一批英語高材生,好幾個考上了國內一流的外語學院,都是他的學生。
王石林老師教我們時,早過了退休年齡,已與學校定好了第二年回懷遠老家。他在第一節課上就和我們說,要站好人生的最后一班崗。
教室走廊的盡頭過一個廊道就是他的家。每一個早讀課,他都要邁著蹣跚的步子來到教室,帶大家讀英語課文。也許是敬畏王老師,也許是那時候記憶力好,早讀課,溫習前一天的課文,每次提問,我都能背出來。記得他很喜歡我,課上提問我也多。
其實,后來我并沒有認真地學英語。這一輩子沒有把英語學好,也是辜負了王老師的一片希望,有些事,實在不好回頭再來,十二三歲的年紀也是太少不更事,冥冥中就是讓人在回憶中陡增一份傷感,這就是人生。
記憶中,從沒有看到王老師高聲地批評哪位學生,總是那么和風細雨。有一次,對一個學生的表現實在不滿意了,他居然拿下了滿口的假牙。他說,為了帶好你們這幫學生,保證發音準確,假期中我專門換了這口假牙。當時,看到他取下牙套后癟瘦空洞的嘴巴,只是覺得好玩,全然不能領會他為了教好這最后一班學生的拳拳之心。
少年的心事,最牽掛的就是玩耍,哪里能體會老師的那番苦心。
人往往就是這樣,以眼前的利益和感受為行動的導向,注定是浮淺而渺小的。所以即使現在,我們也不能說比當時進步了多少,更不能說這種基于現在的判斷,一定就是正確的。關鍵是遠見,遠見來自卓識,即諸法唯識。識從何來?修煉。人生就是一個不斷修煉的過程,卻不能從頭再來。
那時,王石林老師年事已大,基本是不出校門,到半里路外的東塘村小店買醬油食鹽等事,基本交給了學生代勞。我們跑得快,一個課間休息就把醬油幫他打來了。當然能安排此殊榮的一般是他喜歡并信得過的學生。
初一那一年,幫他打醬油,幾乎是我包了。
后來我聽王述圣校長說,他曾是復旦大學的高材生,民國時期曾任省人事廳干事,因把一批檔案完好地交給了新四軍,有功于人民。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灣沚中學教書。1957年暑假,他參加防汛,面對圩堤管涌險情,臨危不懼,身系麻繩下到湍急的河水中,順著圩堤摸漏洞,并順利地堵住了缺口,冒著生命危險換回了圩堤的安全,受到宣城縣政府表彰。1970年被王校長請到我們學校來教書。
人的記憶力確實很神奇,最近所遇之事往往過后就忘,昨天的事情,今天回憶起來還要想半天。幾十年前,王老師有的課上問我的問題,依然如在眼前。其中有些課文,仍能星星點點地能拼寫出來。如此,腦子里的外語板塊,衰草凄凄一片荒涼中居然還能冒出幾粒英語種子,便是王石林老師當時撒下的了。
可王老師已走了好多年了。
三
如果說在人生的漫長行旅中,我與王石林老師的遇見只是轉瞬即逝的驚鴻一瞥,那么劉宗寶老師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卻是留下了兄長般的關愛。
劉宗寶老師到雁翅中學教書時,我已是畢業班的學生,快要離開這個學校了。我們數學老師請假,他代了兩天課。在他眾多的學生中只能算有相識之緣。倒是參加工作后他于我更像一位亦師亦友的兄長。
我參加工作時,他已由中學的教導主任崗位調任鄉教辦的輔導員。一天,根據工作安排,他下午兩點到我所在的學校聽課。那天,雨下得很大,道路泥濘,我在辦公室望著外面的瓢潑大雨,心想,也許劉老師今天不會來了。此時,劉老師走進了我們那間大辦公室,一分鐘也沒遲到。原來他叫了一只小船直接劃到了我們學校。身上已濕淋淋的。其實,作為全鄉的教辦輔導員,他完全可以調整當天的行程,改一個時間。畢竟當時圩鄉的交通很不方便。
上完課,我自覺比較拘謹,沒有平時發揮得好,忐忑不安。沒想到點評時,他對我的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渾身張揚著激情的表揚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讓我對我的教學風格更有了信心。
那時,他雖已調到鄉教辦工作,家還在書墩塘畔。一次,我從街道辦事回家,經過他家門口,他一定要留我在他家吃飯,加上師母史老師也就三五個人。他能燒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糖醋排骨。他的糖醋排骨很明顯不是圩鄉本地菜系的傳承。不管是他照葫蘆畫瓢從外地學來的,還是他的創新,他的菜一下子觸動了我的味蕾,也把我們的距離拉得更近了。從此,我便成了他家飯桌上的常客。我們的交流也從工作蔓延到生活乃至思想。
有一次吃完飯,他突然要送我回家。從書墩塘邊沿著溝岸有一條蚯蚓般的小路蜿蜒到我家,中間要穿過一面垾子,兩個村莊。月光下,我們不知不覺走到了龍字垾的盡頭。
龍字垾傳說是一塊龍形寶地,它四面環水。僅兩條壩埂與外面的大路相連,垾子的龍頭處埋了許多墳墓,都是當地人占的,想占住風水寶地。小時候上街,走到此處,從一個墳穿過另一個墳,渾身汗毛直豎。后來大多數墳塋已平去,種上了莊稼。那天晚上清風涼爽。田野正綻放的油菜花散發著一縷淡淡的清香,我們行走在那油菜花中,沿著那溝岸小路,一路暢談。全然沒有顧及那花叢田野間稀疏的孤墳。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就快到我家門口。我又把他送回去。最后我們還是在龍字垾的田埂間分手。那時,我身在圩鄉偏僻的村小,人生徘徊期,已萌生了辭職轉行的念頭。記得分手后,我久久地凝視著他遠去的背影,猛然醒悟,他是在鼓勵我,激起我的勇氣。
這一幕,至今猶在眼前。月色迷蒙,青蛙在田間鼓噪,夜幕下的大地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畫,一個清澈而充滿激情的人影行走在畫卷中央。此情此景,卻漸行漸遠。
一個夏天,劉老師拿到了教辦宿舍的鑰匙,他就把家從中學搬到了街道。他專門通知我劃了一只小船去幫忙。東西也不多,大多是一些日用品,一船就搬完了。記得我們沒讓史老師參與,兩個人輕輕松松就搞定了。船行水面,突然起暴了,天空的云仿佛離地面很近,狂風刮過,烏云翻滾,大有橫掃天地之勢。小船在風浪上顛簸,搖搖晃晃,我劃著船,努力控制著船向。他穩坐船頭,淡定地說,這是風暴,不要怕。果然,一會兒,風漸漸地小下來,我們順利地劃到街道,搬完了家具。
他在新家燒了兩個菜,吃完飯我就劃著小船回家了。哪知那是我最后一次吃他燒的菜。
至今,我還一直精心地保留著我們的一張合影,一張我們唯一的合影。記得那是他來學校檢查工作,正遇上我帶的畢業班學生照畢業照,我和數學老師小劉一道請他和我們合了一個影。蔥綠的麥苗間我和小劉蹲在前面,他蹲在我們身后,雙手搭在我們的肩膀,臉上露出一片慈祥。他的身后綻放著一片金黃的油菜花。那花開得廣袤而深遠,云煙氤氳,直至遠處疏淡的村莊。
一年后,他在宣城開會,路上橫遇車禍,英年早逝。扳著指頭一數,竟然已有28年了。
今天,我再一次來到中學校園,校園長高了,長大了,長得花枝招展。校園內的荷塘翠柳,綠茵草坪,綜合樓、教學樓、圖書館、教師宿舍……布局有序,相互映襯,透著一分與生俱來的靜謐。夕陽橫掃進校園,校內的所有建筑都閃爍著淡淡的金色光芒。荷塘中的荷花正綻放在碧蓮之間,宛如青春的歌聲輕輕地洋溢,靜待著熱烈奔放的明天。微風吹過水面,清香徐來,伴著夕陽的余暉,仿佛哪位少年在這兒淺唱低吟……
今日的校園,已非昨日的校園。猶如校園天空的云彩,絕非是昨天絢爛的抄襲和復制。日子難以重返,那光怪陸離而無憂無愁的年少時光,伴著微風已從這兒滑過。滑過一灣溝塘,滑過了一片金黃的田野,滑過了兩排梧桐凄雨,滑過了溝旁輕拂水岸的柳絲翠葉……
離得越遠,圩鄉深處,那月光下的背影,越是常常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野徑埋香,風月琳瑯,如水的記憶,在每一個紅塵渡口,滋潤著情懷,豐盈著生命,風雨難摧。
【作者簡介】時國金,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2020年始創作圩鄉系列散文,發表于《人民日報》《鐘山》《清明》《散文百家》《翠苑》《雪蓮》《中國鐵路文藝》《安徽文學》《青海湖》《西湖》《太湖》《青春》等幾十家報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等選刊轉載。多篇文章入選《母親河的回憶》《碧水沃野》等散文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