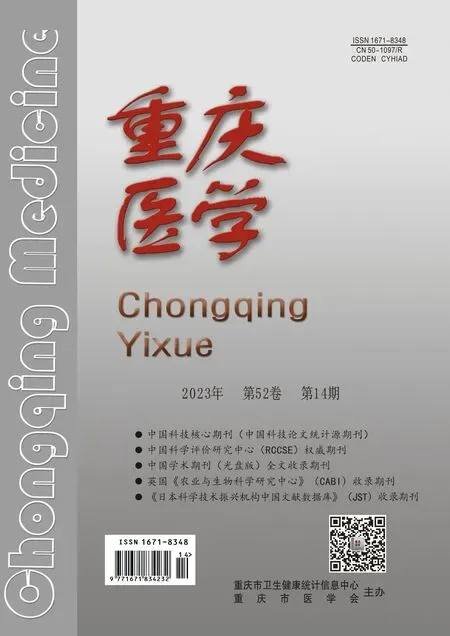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抑郁癥患者的相關影響因素分析*
劉興蘭,周小艷△,黃雪萍,彭祖來,薛 毅,吳清培
(1.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金紫山院區心理科 401147;2.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醫務科 401147)
非自殺性自傷通常被定義為沒有自殺意圖的、故意的自我傷害身體,除外公認的行為(如穿孔等)[1]。國外兒童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的終身患病率和年患病率分別為22.1%和19.5%[2]。我國初高中學生非自殺性自傷患病率為22.37%,一生中自傷發生率為14.5%,6~24個月的自傷發生率為23.3%[3]。自傷除了本身具有危險性外,還可能是未來自殺行為的危險因素[4]。近年來,青少年的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抑郁與自傷行為呈正相關,且抑郁明顯正向預測自傷行為[5]。臨床上,不少確診為抑郁癥的患者伴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目前的研究多側重于在社會層面(如學校、社區)篩選樣本,本研究旨在探討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抑郁癥患者的相關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1月至2022年5月本中心門診和住院的200例抑郁癥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年齡13~25歲,性別不限;(2)符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3)自愿參與研究并獲得知情同意書,未成年人還需獲得監護人的知情同意書;(4)溝通無障礙,能獨立或在協助下完成問卷。排除標準:(1)患有除外抑郁癥的其他種類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精神發育遲滯等;(2)患有嚴重的軀體疾病、腦器質性疾病等;(3)近2周內有嚴重自殺企圖及自殺未遂行為;(4)經研究者判斷,遵從研究要求的能力差或其他不能完成研究者。根據是否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分為研究組(111例,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和對照組(89例,無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本研究通過倫理委員會批準[2020倫審醫字第(021)號]。
1.2 方法
采用以下量表對研究對象進行評估。(1)自制問卷:收集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組合方式、居住地、首次發病年齡、住院次數等。(2)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Ⅱ,BDI-Ⅱ-C)[6]:評估過去2周內抑郁癥狀的嚴重程度,包含21個條目,每個條目為0~3級評分,總分0~63分,該量表在我國青少年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兒童期創傷問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7]:共28個條目,每個條目為1~5級評分,共5個維度。只要滿足情感虐待≥13分,情感忽視≥15分,性虐待≥8分,軀體虐待≥10分,軀體忽視≥10分其中1項即為中重度的童年創傷者,本研究視為有童年創傷;而同時滿足維度情感虐待<13分,軀體虐待<10分,性虐待<8分,情感忽視<15分,軀體忽視<10分的患者視為不伴任何形式的童年創傷。(4)Barratt沖動性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11)[8]:共30個條目,包括運動沖動性、認知沖動性、無計劃沖動性3個維度。每個條目得分1~5分,但無計劃和認知沖動性維度的條目均為反向計分條目。得分越高,沖動性越強。(5)父母教養方式量表(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EMBU)[9]:共66題,每個題目下又分為父親和母親2個條目,父親的養育方式包括父親情感溫暖、父親懲罰、父親過分干涉、父親偏愛被試、父親拒絕否認和父親過度保護 6個方面,母親養育方式包括母親情感溫暖、母親過分干涉、母親拒絕否認、母親懲罰嚴厲和母親偏愛被試 5個方面。采用1~4級評分,第20、50、56 題反向計分,其余皆為正向計分。
1.3 統計學處理

2 結 果
2.1 基本情況
研究組自傷次數0~3次20例(18.0%),>3~10次32例(28.8%),>10次59例(53.2%)。兩組年齡、性別、發作形式、住院次數、首次發病年齡、受教育程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2.2 CTQ、BIS-11、EMBU評分比較
研究組兒童期創傷率為87.4%,對照組為93.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89,P=0.169)。兩組CTQ中情感虐待、軀體虐待、情感忽視維度評分,BIS-11總分和各維度評分,以及EMBU中父親情感溫暖、父親懲罰、母親情感溫暖、母親拒絕否認、母親懲罰嚴厲維度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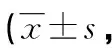
表2 兩組CTQ、BIS-11、EMBU評分比較分)
2.3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參數納入logistic回歸方程,結果顯示性別、年齡、住院次數、情感虐待、無計劃沖動性是抑郁癥患者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表3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 論
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可以作為一種癥狀出現在各種類型的精神疾病中,如抑郁癥、邊緣性人格障礙等。SERRA等[10]研究發現,伴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抑郁癥患者自殺意念、情緒失調、抑郁癥狀及焦慮癥狀均明顯高于不伴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抑郁癥患者。情緒調節、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與抑郁癥患者的自殺風險存在相關性,自傷水平越高,自殺風險越高,情緒調節對自傷、自殺風險的間接影響明顯[11]。因為不良的情緒調節可能通過干擾認知和行為抑制控制而出現不好的適應性反應,加重負性厭惡的情緒狀態,從而增加自殺的風險[12]。
研究組年齡小于對照組,年齡每增長1歲,出現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概率將降低20%左右,低齡與抑郁癥患者的自傷風險增加有關[13]。兩組女性所占比例均明顯高于男性,且研究組女性達82.0%,與以前的研究結果類似,女性出現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比男性高2.85倍[14],女性性別是自傷行為的危險因素[15],在制訂有關干預措施時需要考慮到性別的差異性。研究組絕大多數有多次自傷行為,有自傷行為患者的住院次數高于無自傷行為,且住院次數越多的患者發生自傷行為的風險增加1.2倍左右。有研究發現[16]約1/3的青少年在至少2次評估中有自傷行為,43%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在13~20歲至少住過1次綜合醫院,22%的17~20歲自傷青少年被送入精神病院,13~20歲有自傷行為者至少使用了1次精神衛生服務,其使用服務的主要原因是有抑郁、自傷或自殺念頭。
與抑郁癥青少年自傷行為相關的主要社會心理因素為童年虐待[17]。本研究中所有參與者絕大部分都遭受了中重度的童年期創傷,研究組情感虐待、軀體虐待評分高于對照組,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抑郁癥患者可能遭受了更嚴重的情感和軀體虐待,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8]。這可能與患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長期不利的生活刺激,導致沉默信息調節因子2相關酶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2 related enzyme 1,SIRT1)基因啟動子區CpG5位點的甲基化水平異常,從而導致自傷行為的發生、發展[19]。
大部分自傷行為為沖動性[20]。研究組BIS-11總分及3個維度評分均高于對照組,有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患者沖動性嚴重程度更高,無計劃沖動性患者更容易出現非自殺性自傷行為,與大腦成熟導致的情緒反應和沖動有關。情緒調節失調和沖動合在一起,二者得分高可預測非自殺性自傷行為[21],且沖動是青少年故意自傷行為的獨立危險因素[17]。有自傷行為的患者在執行任務時的反應時間更短,而較短的反應時間所反映的行為沖動與額葉功能障礙有關[22],如額葉體積或灰質厚度的減少,導致邊緣系統的抑制受限,從而出現沖動行為[23]。
父母是青少年健康和發展的主要貢獻者[24]。一些父母特征與青少年的自傷行為存在關聯[25]。父母情感溫暖低、懲罰、拒絕否認可能會使青少年感到自己不被關心、愛護、不安和沮喪,他們可能會利用自傷行為來緩解不愉快的情緒。消極的育兒方式與自傷行為、重復自傷和嚴重自傷行為有關[26],而積極的育兒方式會減弱這種風險[27]。雖然兩組比較存在著差異,但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發現所有的因子均未進入回歸方程,可能與兒童期創傷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重疊有關,可進一步擴大樣本,細致區分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
綜上所述,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抑郁癥患者的相關影響因素可以幫助心理衛生從業者更加有效的識別、診斷和治療。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本研究為病例對照研究,所有的變量都是通過研究對象的回憶所得,為主觀評價,可能存在信息偏倚,導致夸大或減弱對既往經歷的印象。(2)本研究選取在專科醫院就診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在一些指標上可能高于一般人群,研究結果的適用范圍有一定限制。(3)研究的樣本量偏小,未對自傷的具體行為特征(如頻率、時間)、抑郁的嚴重程度等進行分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