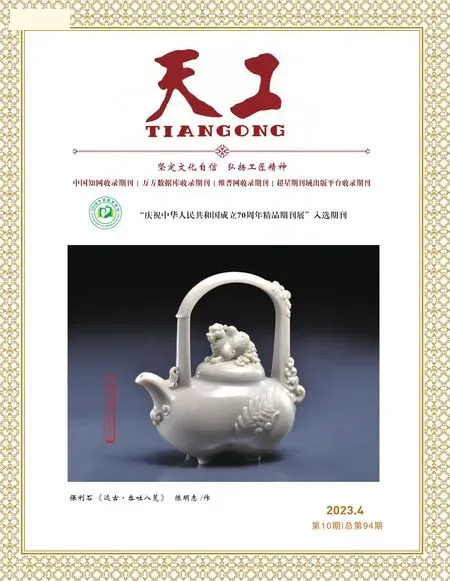木刻藝術的延安道路
張 妮 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
一、引言
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各行各業都加快了發展的步伐。快節奏的生活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靈感,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藝術創作過分追求形式美而忽略思想的表達,以及藝術創作與大眾生活脫節等。雖然這并未成為普遍現象,但需引起重視。革命戰爭年代,木刻藝術以其獨特的社會價值為中國人民追尋民族獨立與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因此,本文試圖從挖掘木刻藝術的創作背景出發,探尋延安時期木刻藝術的成長之路,并探討在當前社會背景下,藝術作品注入思想性、教育性的思路與方法。
二、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創作的時代背景
(一)延安時期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為木刻創作提供了沃土
同水深火熱的國統區相比,陜甘寧邊區處于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尤其在中國共產黨自由民主政策的倡導下,延安成為知識分子向往的熱土,這為木刻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沃土。
(二)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為木刻創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在延安時期,奔赴延安的青年達四萬余人,他們中不乏木刻工作者。同時,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干部培養,重視知識分子的先鋒與橋梁作用,于是創辦大量干部學校吸收知識分子。魯迅藝術學院便成為藝術創作的重要陣地。1939 年,中共中央出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提倡科學知識,歡迎科學藝術人才,獎勵自由研究,給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充分的保護與鼓勵。
(三)延安時期不斷發展完善的文藝理論為木刻創作提供了理論指導
延安時期,共產黨人選擇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延安文藝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1942 年5 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延安文藝的發展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論指導,不僅解決了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完善了黨的文藝方針,同時為日后延安文藝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綱領性的保障。
三、延安時期木刻藝術的發展
(一)木刻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植根于中華文明,淬煉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我國木刻版畫藝術發展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唐代因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版畫隨即產生,屬于古代復制版畫。由于魯迅先生新興木刻運動的倡導,20 世紀30 年代的新興木刻成了我國版畫創作的發端。魯迅先生曾在《新俄畫選》小引里提道:“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2]之后這種藝術形式與我國國情相結合,在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美術工作者奔赴延安,他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陣地,從中汲取養分。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他們克服困難,結合實際進行創作,將木刻藝術推向新的高度。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藝術家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創作出一大批優秀的木刻作品。延安時期,木刻版畫不受階級、地域、文化程度的限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宣傳教育職能。
(二)木刻藝術的內容與形式:走向大眾化、民族化
延安時期,木刻作品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類。其一是以古元為代表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內容更多反映邊區的民主建設。如《冬學》《離婚訴》等,展示了中國人民勤勞、勇敢的形象。其二是以魯藝木刻工作團為代表,他們的作品內容更多反映戰爭。工作團成員因直接經歷了戰爭中最殘酷的階段,所以創作出大批戰爭題材的作品。如彥涵的《當地人搜山的時候》《不屈的人們》,羅工柳的《馬本齋的母親》等。通過木刻藝術,“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里的人民是怎樣生活著的,以及武裝了的人民又怎樣和敵人戰斗著的實況,也能夠藉此得到一些了解”[3]。
延安時期的木刻藝術在形式上逐漸擺脫歐洲的影響,更多地考慮百姓的審美,探索出符合民眾需求的創作方向。初期,魯迅先生將歐洲版畫引入國內,并多次舉辦展覽、木刻講習會等供大家交流學習。因此,在木刻版畫創作的萌芽階段,藝術家潛移默化地受到歐洲版畫的影響。力群1941 年創作的木刻版畫《飲》(見圖1)塑造了健美的勞動人民形象,傳遞出對百姓的贊美。除去作品的內在表達,從它的形式語言上不難看出受到歐洲人物刻畫手法的影響。江豐、古元等藝術家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受到歐洲、蘇聯版畫的影響。

圖1 《飲》 力群/作
藝術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使創作風格、創作形式逐步發生變化。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為了更進一步適宜群眾的欣賞習慣,木刻從黑白趣味向明快的單線發展,從而誕生了一大批充滿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作品。力群的《豐衣足食》(見圖2)便巧妙植入了老百姓的審美喜好,更多使用陽刻的藝術手法,減少了對三維空間的塑造,盡量把所有物象整合到一個平面內,使得作品的形式語言有了很強的群眾基礎,同時在尊重客觀繪畫規律的基礎上融入中式審美,添加民族元素,更加符合老百姓的閱讀習慣。

圖2 《豐衣足食》 力群/作
四、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影響
(一)強化政治宣傳與動員
延安時期,文藝工作緊緊圍繞著黨的中心任務,舉旗幟,聚民心。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宣言》中提到,“它的成立,是為了服務于抗戰”,“使得藝術這武器,在抗戰中發揮它最大的效能”[4]。因此延安時期,版畫家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創作出大量木刻作品,充分發揮了木刻版畫的宣傳、動員作用。
(二)推動文化發展
陜甘寧邊區原是一塊文化荒漠[5],邊區人民難以突破封建愚昧思想的禁錮。為此,邊區開展了自上而下的教育普及運動。版畫家積極配合掃盲運動,創作藝術作品。力群的《聽報告》、古元的《冬學》都描繪了這場文化教育運動。《冬學》刻畫了莊稼人利用冬閑的時光,在院里埋頭學習的畫面。作品傳遞了人民的翻身不只是解決溫飽,真正的翻身是教育的翻身、文化的翻身的主題。延安時期的版畫家通過版畫歌頌與贊美勞苦大眾,以改變外界對老百姓的認知,也默默推動著邊區文化的發展。
(三)助力生產動員
1939 年,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極端困難的時期。為了克服困難,陜甘寧邊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版畫在這一時期自然而然地發揮了宣傳政策、動員生產的重要職能。沃渣的《開荒突擊隊》、王式廓的《開荒》、戚單的《防旱備荒》,從這些敘事性極強的木刻作品中不難看出木刻藝術對邊區生產建設的推動作用。
(四)引領社會新風尚
為維護社會的穩定,樹立良好的社會新風尚,1939年4 月,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以此保障邊區婦女的合法權益。古元對這一題材進行了深入挖掘,創作了《馬錫五調解婚姻訴訟》《結婚登記》《離婚訴》等作品,這些作品都是推動社會治理、引領社會新風尚的佳作。
五、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對當代藝術創作的啟示
(一)藝術作品應追求藝術性與思想性的統一
延安時期的版畫作品兼具藝術性與思想性。藝術創作好比廚子做菜,好的作品既要好看又要好吃。“好看”顧名思義是指它的形式是美的,需重視藝術性。而“好吃”則表明了思想內涵的重要性,二者相輔相成,好的藝術作品需要實現藝術性與思想性的統一。延安時期的版畫家也正是這樣做的,因此創作出了大量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
(二)藝術創作應學習民族傳統,探求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解放區的木刻工作者致力于對中國民間美術的搜集與研究。魯藝木刻工作團在對傳統年畫挖掘的基礎上,在前線開展了新年畫運動。木刻團的成員拜老百姓為師,利用傳統年畫的形式,植入新的內容,創作了一大批新年畫,例如《保衛家鄉》《軍民合作》等。新年畫深受百姓喜愛,老百姓親切地稱之為“翻身年畫”。延安時期剪紙藝術也受到高度重視。1943 年,魯藝師生搜集剪紙素材,并編輯成冊、出版發行。藝術家還創作了兼具剪紙元素的剪紙木刻。羅工柳的《衛生模范 壽比南山》、古元的《民兵》《自衛軍》都是經典案例。藝術家從民間藝術寶庫中汲取養分,在傳承和創新方面邁出重要一步。
(三)藝術創作應深入生活,聯系群眾
人民是藝術創作的源泉,也是藝術前進的動力,只有貼近群眾,才能真正地了解他們的生活,才能創作出與百姓同頻共振的藝術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大批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向人民大眾學習。1940 年,古元被分配到碾莊鄉擔任文書一職,同老百姓同吃同住,這段經歷使他真正懂得百姓的喜好。古元說:“我的木刻畫是在農民的炕頭上‘展出’的,周圍的老鄉們就是我的觀眾,也是我的老師。他們把我送給他們的木刻畫張貼在炕頭上,每逢勞動后歸來,坐在熱炕上,吸著旱煙,品評著這些畫。”[6]碾莊的生活促使古元的創作發生了改變,這段經歷也生動地詮釋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的深刻意義。
(四)藝術工作者應肩負社會責任感
面對殘酷的抗日戰爭,一向以民族責任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投入抗日戰爭中。古元說:“我作為一個革命的版畫戰士,希望創作出來的作品能鼓舞人民前進,給人民美好的精神食糧,為人類的正義事業,為共產主義事業做一點一滴的貢獻。我將堅持這個信念,努力不息。”[6]在高度責任感的驅使下,一幅幅鮮活的版畫誕生了。它們記錄了歷經艱苦磨難,付出巨大犧牲的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艱辛歷程。雖然我們身處和平年代,但是文藝工作者肩上的責任感不該被遺忘。
延安木刻植根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產生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實踐中,是新興木刻運動在延安的繼承和發展。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發展對當代美術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在新時期,弘揚時代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延安時期版畫創作的道路與經驗是根,啟迪當下、昭示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