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聲和淚水里的悲喜人間
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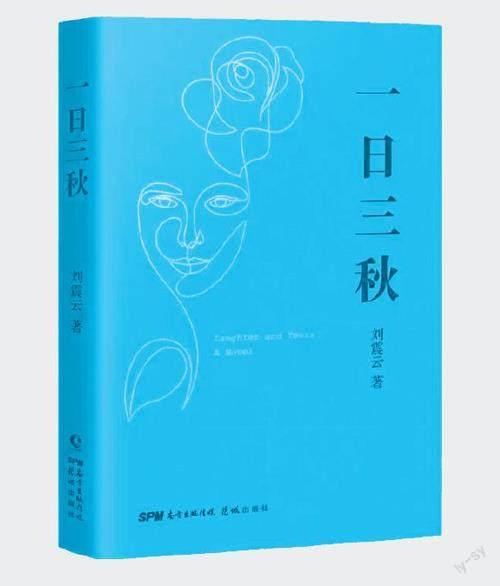
劉震云,出生于1958年5月,河南延津人。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90年加入中國作協。現為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委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等,中篇小說《官場》《新兵連》《頭人》《單位》《溫故一九四二》等。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這是一本讓你笑的書,也是一本讓你哭的書,歸根結底,是一本關于命運的書。人生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本想盡力折騰,奮力生活,活出人樣,活出精彩,卻無奈總是活成個笑話。
《一日三秋》是劉震云2021年推出的魔幻現實主義新作,一本小說,話盡普通百姓的一日三秋。可謂人生如夢,夢如人生;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小說借鑒經典名著《紅樓夢》以神話故事來統攝全書的敘事手法,只是《一日三秋》引入的是流傳在延津的民間故事——花二娘“夢里夢外”的傳說。花二娘按約定前來延津渡口等她的花二郎,可等了三千年也沒等到,后來變成了一座望郎山。望夫不得的花二娘,從此就成了喜歡闖入延津人夢里找笑話的妖怪,笑話講得好便獎勵一個紅柿子,講得不好就變成一座山把人給壓死。所以,每個延津人在睡覺前都會準備一個笑話,以備不測,這就成了延津人幽默的緣由。但延津人都知道花二娘為何等不到她的郎君,因為花二郎有一次進食,在聽一個笑話時被魚刺卡喉而死。尋找別人講笑話的人,本身也就成了一個笑話。花二娘在夢中尋笑話以及延津人夢外講笑話的故事,構成了小說的第一層結構。
小說的現實故事則以“我”(敘事者)記憶中六叔的畫作為母本,這“畫里畫外”的故事構成了作品的第二層結構。六叔原來在縣劇團拉弦、畫布景,后來劇團解散,六叔也幾易其職,但始終沒有放下畫筆。六叔繪畫的題材,有現實中延津人的悲歡離合,也涉及延津的歷史和傳說,因此有些畫作非常寫實,而有些經過六叔的變形和夸張,匪夷所思。六叔死后,“我”就用文字把這些本來沒有關聯的畫作串聯起來,于是這部小說就成了一部集寫實與變形于一體、穿越生與死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
有了這兩層故事的架構,小說的主體故事是由“戲里戲外”的第三層結構引出的。延津縣豫劇團排演了一出拿手好戲《白蛇傳》,飾演法海、許仙、白娘子的三個普通人陳長杰、李延生、櫻桃及其后人,這兩代人將四十年中戲里戲外的生活與情感糾葛在一起,上演了一場場人間悲喜劇。作品中法海、許仙、白娘子共同唱段中三人握手同嘆的部分,“奈何,奈何?咋辦,咋辦?”構成了《一日三秋》眾多人物命運的主要基調。
這樣,作者為讀者營造了神話傳說、繪畫故事以及現實生活這樣三層故事框架,小說中一個個人物,包括仙女、鬼魂等就在這三層故事結構中登臺亮相、來回穿越。《一日三秋》主要演繹了小人物的眾生相。掃大街的郭寶臣、賣羊湯的吳大嘴、搓澡的老布、燉豬蹄的老黃、算命的老董、開公交的樊有志、包糖紙的胡小鳳、賣身的馬小萌、菜市場經理孫二貨等等,五花八門,沒有哪個光鮮亮麗。就算陳長杰、李延生、櫻桃三人,出場時有“角兒”的光環,但因劇團解散而很快就成了凡夫俗子。作品中唯一一個略顯發達的人是陳長杰的兒子、中年后的陳明亮。經過二十幾年的底層打拼后,明亮的生活不再窘迫,出手有時也很豪闊,但他依然是個小人物。作者塑造這些小人物的重點也不在他們的世俗成功,而是通過他們不可控的命運之輪和人生巧合,道出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處世哲學。小人物的日常人生往往身不由己,他們最能體味人生的艱難,即便是萬般掙扎,最終也可能是徒勞一場。天地不仁或時運不濟,一切都仿佛命中注定,令人無計可施。作品中的眾生只能嘆:“奈何,奈何?咋辦,咋辦?”但是這種認命的處世哲學,顯然不是消極逃避、坐以待斃,而是直面苦難,忍耐妥協后的寬容和悲憫。
除了對小人物悲劇命運的深切關注,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是表達對故鄉的復雜感情。延津是劉震云的現實故鄉,更是他的精神故鄉。作品筆下的延津并非現實的、具體的延津,它是中國傳統文化根系和當代生存狀態的樣本。中國人安土重遷,不是迫不得已,都不愿意離開家鄉。從時空維度來看,《一日三秋》主要寫主人公兩代人在延津—出延津—回延津—再出延津的故事。陳長杰因妻子櫻桃為家庭瑣事而自尋短見,無奈之下,帶著兒子離開家鄉,到武漢謀生,重組家庭。而兒子陳明亮因思念母親,融不進父親組建的新家庭,他又回到延津,在家鄉摸爬滾打、長大成人,又立業成家。但是他的妻子馬小萌因為不愿出借辛苦賺來的錢,被閨蜜抖摟出不光彩的過往經歷。無奈之下,陳明亮不得不帶著想要自尋短見的妻子離開家鄉,到西安謀生,最后闖出了自己的天地。但他不忘本,經濟寬裕之后經常反哺家鄉。小說寫兩代人帶著怨恨離開家鄉,又因為種種原因不斷返回,這種被命運牽著的出走與返回,是破繭而出的需要,也是對生命之根、文化之根的眷戀。
書名“一日三秋”可作多解,《詩經》中的原義是因為愛情,但在此書中更多的卻應作為悲情來理解,即“度日如年”,《一日三秋》可謂道盡了人間苦澀。不過,在故事結尾,作者筆鋒一轉,用“不在話下”化解了略顯頹喪的無奈與悲哀,豁然間轉向通透與超然。在小說《前言》中,敘事者就告訴讀者把書中的故事當個玩笑。在這個玩笑故事中,笑話成了人人自救的辦法,人人也都活成了笑話。或許只有以談笑的姿態,方能抵御人生的孤獨、苦澀與荒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