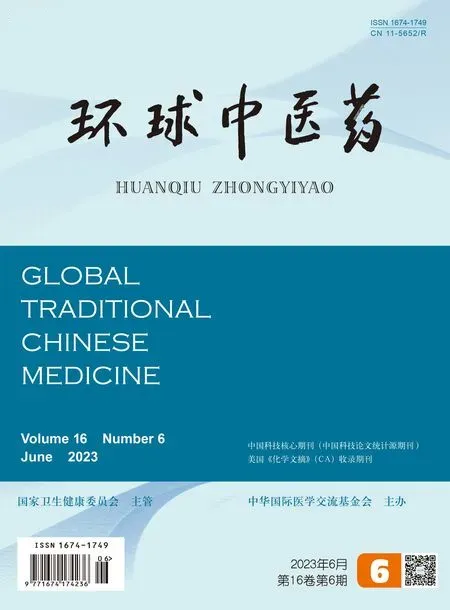虛勞病內涵與外延演變的理論研究
王赫 李成衛
虛勞作為一類疾病,現代通行的定義為慢性虛弱性疾病的總稱,以《中醫內科學》為參考,書中認為虛勞是以五臟虛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疾病,虛證是組成虛勞病的基本單位[1]。而《金匱要略》(以下簡稱《金匱》)所載虛勞指因虛損所致的多種疾病,臨床重點關注患者表現出的虛弱狀態,因此其范圍相對廣泛[2]。由此發現,不同時期對虛勞的理解各不相同,這一系列的差異不僅影響了歷代醫家對虛損類疾病的治療,也反映了不同時期醫學思想的變遷。鑒于此,筆者將對虛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進行梳理,以期還原仲景時代虛勞的真實含義,進而明確這一疾病的臨床意義。
1 虛勞病的本意與新意
1.1 《金匱》虛勞病本意

1.2 現代通行觀點的虛勞病
現代醫家對虛勞的論述可以《中醫內科學》為參考,書中將虛勞定義為“以五臟虛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多種慢性虛弱證候的總稱”[1]。整篇以氣血陰陽為綱,五臟虛損為目,分別論述了不同類型虛損的證治,并以益氣、養血、滋陰、溫陽作為基本治法。以氣虛為例,肺氣虛宜補益肺氣,方用補肺湯加減;心氣虛宜益氣養心,方用七福飲加減;脾氣虛宜健脾益氣,方用加味四君子湯加減;腎氣虛宜益氣補腎,方用大補元煎加減。


2 漢唐時期:以癥狀為診斷依據的特定疾病概念
漢唐時期,中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受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哲學思想的影響,醫家對疾病的認識以主體感知的現象為主,并衍生出通過觀察外部癥狀賦予內臟功能的藏象理論[5],同時也產生了以臨床癥狀作為疾病分類依據的診斷模式。
這一時期,虛勞的內涵為具有虛弱癥狀的一大類疾病,診斷以此癥狀為主,病性不作為主要診斷依據。除《金匱》中記載多種局部主癥各異的虛勞外,孫思邈《千金翼方·虛損》中也記載:“凡人不終眉壽或致夭歿者……正氣日衰,邪氣日盛。”孫氏認為凡正氣虛弱,邪氣流連者皆屬虛勞范疇,治療時倡導虛則補其子,如“心勞病者,補脾氣以益之;肝勞病者,補心氣以益之”,同時也創制了補瀉互參的治法,如虛損羸瘦的主方大薯蕷丸中用干漆、大黃等活血化瘀消積;治療五勞、七傷的腎瀝散用干漆化瘀消積[6],既注重虛損的補益,也注重邪氣的祛除。
而此時虛勞的外延范圍相對廣泛,如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所載虛勞七十五候,將許多慢性病后期歸入其中,包括骨蒸、傳尸等傳染性疾病[7]。該候所載虛證不足一半,多數的病證以虛實并見為主,如虛勞積聚候記載:“虛勞之人,陰陽俱損,血氣凝澀,不能宣通經絡,故積聚于內。”范行準[8]認為,由于當時的醫家還未在病因學概念上分類疾病,所以將久病不愈、思慮過度、失眠噩夢及身體羸瘦等以虛弱狀態為表現的疾病均歸到了虛勞的范疇。
此時的虛勞,主要以患者全身的虛弱狀態為診斷依據,凡臨床表現為這一癥狀的疾病均可納入虛勞范疇,對于病性的認識和病因的分類并不明確,從其內涵及外延的角度均可明確這一觀點。
3 宋金元時期:癥狀到病機的轉換
北宋時期,作為大方書的《圣濟總錄》仍沿用漢唐時期的分類方式,將虛勞分為五臟勞、六極和全身虛弱為主的虛勞,如虛勞痰飲、虛勞積聚、虛勞骨蒸等,并對每一勞均有詳細論述[9]。但是,隨著醫學的發展及病因理論的提出,因、機、證、治、方藥的治療體系逐漸成型,并成為雜病的主要診治體系[10],虛勞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
金元時期,在理學的影響下,醫門分戶,各家學說逐漸興盛起來,這一時期醫學體系的改變對中醫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述而不作的傳統思想被打破,新理論不斷發展,病因病機理論、臟腑辨證學說相繼成熟。其次,部分醫家援儒入醫、援易入醫,提倡以新思想解釋經典,闡發新說,并形成了觀點各異的學術流派,這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時期建立起來的“因機證治方”診療模式的應用。與此同時,藥物治療學理論也在這一時期有了新發展,張元素《臟腑標本藥式》創制藥物與病機相對應的敘述模式,該模式與“因機證治方”的診療模式相呼應,組成了理法方藥相對完備的新型診療體系。此時醫家對疾病及方藥的論述,也逐漸過渡到這一體系之下。
對于虛勞而言,醫家們不再僅以虛弱狀態作為診斷標準,而將著眼點放在了病因病機上。同時,內傷病因的理論創新,使醫家對虛勞的關注從外邪致病轉移到五臟與氣血的虛損上[11],治法由祛邪為主過渡到扶正兼祛邪。在新體系的影響下,醫家由癥狀確定臟腑虛損的病機,再由虛損病機確定治法的診療模式逐漸成型。
在這一轉變的影響下,虛勞的內涵變為了以臟腑虛損為病機的一類疾病,病性以虛為主。如劉完素[12]《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虛損論篇》提出的虛損因虛而感寒熱:“感寒則損陽,感熱則損陰。”在治療方面,以五臟虛損為前提確定治法和方藥,如“治肺損而皮聚毛落,益氣可也;治心肺損及胃,宜益氣和血,調飲食;治腎損,宜益精;治陽盛陰虛,脾腎不足,宜養血益腎;若形體羸瘦,無力多困,未知陰陽先損,夏月地黃丸,春秋宜腎氣丸,冬月宜八味丸”。
李東垣[13]《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篇》記載“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既脾胃虛弱,元氣不足”,指出虛勞的病因在于勞役,病機為脾胃虛弱,提出了“脾胃虛損,百病由生”的觀點。并根據《內經》“虛則補之”“勞者溫之”的論述,確定了甘溫補中的治療大法和一系列方劑。而脾胃虛損的病機也因東垣的演繹,成為后世治療虛勞的重要理論支撐。
朱丹溪[14]《金匱鉤玄》記載“癆瘵主乎陰虛,痰與血病。虛勞漸瘦屬火,陰火銷鑠,勞病,四物湯加人尿,姜汁”,將虛勞分為癆瘵與虛。對于癆瘵的治法提出以大補為主;對于諸虛,重視脾腎的虛損,創制了大補丸、補腎丸、補血丸、補陰丸等方劑。另外,丹溪“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學術觀點,也影響了后世部分醫家對虛勞的認識。金元四家對該病的認知,代表了當時大部分醫家的學術觀點,虛勞的虛損病機概念也逐步成型。
外延往往隨內涵的變化而改變,由于這一時期虛勞的內涵以虛損病機為主,所以原屬于漢唐時期的虛勞病,大部分因診療體系的細化而歸屬到了不同的疾病中,虛勞的外延在新體系的影響下逐漸縮小了范圍。原記載于虛勞范疇的虛勞痰飲、虛勞積聚、虛勞癥積等疾病,在這一時期分別確定了不同的病因病機,進而歸屬到了不同的疾病篇章中,或獨立成為一種新疾病。盡管其全身癥狀仍表現為虛弱狀態,但由于虛勞的性質變為虛損性疾病,所以這一類虛實夾雜性質的疾病不再從屬于虛勞病的范疇。
從以上所論虛勞內涵和外延的變化來看,這一時期的虛勞,將重點放在臟腑虛損病機的論述,并由病機確定了補虛的基本治法,癥狀僅作為分析病機的依據。經過醫家對疾病更系統的認識,虛勞逐漸變成了以臟腑虧損立論的內傷疾病。
4 明清時期:虛損病機理論成熟
明清以降,溫補學派興起,經由命門學說的影響,五臟皆有氣血陰陽的人體模式建立,醫家對人體和疾病的認知更加復雜。
這一時期虛勞的內涵在金元時期的認識上有所增加,主要體現為醫家將金元時期臟腑虧損的病機拓展為五臟虛、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的病機,并對虛勞的病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由于眾多醫家開始注意虛勞、虛損和癆瘵病名概念異同的辨析,也產生了對于虛勞的不同觀點及諸多專著。
張景岳為明代溫補學派代表人物,其《景岳全書·雜證謨·虛損》記載:“但凡虛損之由,俱道如前,無非酒色、勞倦、七情、飲食所致。故或先傷其氣,氣傷必及于精;或先傷其精,精傷必及于氣……故凡損在形質者,總曰陰虛”“氣虛者,即陽虛也;精虛者,即陰虛也……凡治此者,但當培其不足,不可伐其有余”[15]。張氏認為虛損主要在于真陰虧損,治療以陰陽虛實為綱,并創立了陰中求陽,陽中求陰的治療法則及左歸丸、右歸丸、大補元煎等為代表的方劑。這也表明了當時醫家對虛勞的認識已逐漸將臟腑的虧損與氣血陰陽的虛損聯系起來。何炫《何氏虛勞心傳》作為虛勞專著的代表,認為虛勞之癥,無外邪相干,皆由內傷臟腑所致,尤重腎陰,治法強調補腎陰,培脾土,慎調攝。《醫宗金鑒·雜病心法要訣》載虛勞治法:“后天之治本氣血,先天之治法陰陽。腎肝心肺治在后,脾損之法同內傷。”[16]此時的虛勞,更加注重對氣、血、陰、陽虛損的分類和補益,醫家對于“虛證”的認識更加詳細。
虛勞的外延也變成了以五臟與氣血陰陽虛損為主要病機的疾病,其病性仍以虛為主。如沈金鰲[17]《雜病源流犀燭》記載:“虛損癆瘵,真元病也。虛者,氣血之虛;損者,臟腑之損,虛久致損,五臟皆有。”不論是從何臟腑與氣血陰陽作為出發點認識虛勞,此時的虛勞已經與病機中的“虛證”聯系密切。
由此可見,經過醫學體系的演變,虛勞的分類和治療更加詳細。明清醫家在金元時期塑造的醫學體系之上對病癥進一步分類,虛勞也在這一分類中變成了病機理論指導下五臟與氣血陰陽虛損的代名詞。
5 現代虛勞:整體觀下的虛損
中國建國后,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作為中醫特色被寫進教材中,并成為綱領性內容指導臨床。現代中醫對疾病的認識,也因整體觀的影響,形成了過分關注人的全身,而忽略局部辨證的局面,這一認識,雖強調了人整體的一致性,但忽視了整體與局部的差異性[18],因而局限了部分疾病的治療。
就虛勞而言,現代虛勞的內涵多指以臟腑虛損,精血不足為主要病理過程的疾病,其全身虛損與局部的臟腑功能虛損須保持一致。這一改變,一方面源于古代醫家對虛勞認識的不斷改變和創新。另一方面,在整體觀與辨證論治應用于中醫學診療體系后,這一話語體系下的虛勞,已經不允許有“非虛證”的存在。即是說,現代醫家對虛勞的認識,是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整體觀的提出促進了現代虛勞變為純虛性疾病的歷史進程。
虛勞的外延也因此變成了對慢性虛衰性病證的指代,只有全身與局部病機均屬虛損的疾病,才可被稱為虛勞。
由此可見,經過不同時期醫學體系的演變,虛勞的概念逐漸等同于虛證,其內涵擴大為臟腑與氣血陰陽的虛損,而外延隨之變為全身與局部均屬虛證的慢性虛衰性疾病,內涵的擴大影響了外延的適用范圍,并隨其擴大而逐步縮小。
6 明確認知差異的臨床意義
理論的概述最終要落實到臨床治療中。明確全身局部具有差異性的虛勞病機,可以更好地理解虛與損的概念及區別、虛不受補的治略以及全身局部虛實夾雜的臨證處理策略,幫助醫者更清晰的認識該類疾病,使臨證處方的決策思維更加完善。
6.1 明確虛與損的區別
現代醫家對于虛與損的區分并不明確,常常虛損并稱。通過對整體與局部的分析,可以理清二者之間的區別,使虛損理論更貼近臨床。吳謙[16]《醫宗金鑒·雜病心法要訣》記載:“虛者,陰陽、氣血、榮衛、精神、骨髓、津液不足是也。損者,外而皮、脈、肉、筋、骨,內而肺、心、脾、肝、腎,消損是也。”由此看出,古代部分醫家對虛與損有著不同的理解,虛指氣血、津液的不足以及臟腑功能的減退;損指器質性損傷和五臟功能的異常,可以認為虛代表全身狀態,損表示局部狀態,明確這一區別,可以更好的理解并指導虛損類疾病的治療。如馬桂琴[19]從“形壞”的角度認識虛損,認為現代疾病中的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謝性疾病、肺系虛損的肺脹證、腎功能衰竭等均可因“形壞”而歸屬于虛損的范疇,其基本病機多為正氣不足,進而導致疾病發展過程中形體與功能受到損傷。并針對這一概念提出以調補之法治療虛損,緩緩建功,攻補兼施,方可恢復其“形壞”。
6.2 虛不受補的治略
對于虛不受補的理解,大多數醫家認為其主要病機為脾胃失司或濕熱久據,導致藥力發揮不暢,反加重濕熱,克伐脾胃,故在治療時常選擇性加入健脾消導、化濕之品[20]。筆者認為,通過整體局部觀理解虛不受補更加妥當,即全身虛損狀態下,有局部實邪的存在,這一認識可使虛實夾雜的病理狀態更加具體化。以《金匱》中的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為例,該方證指代對象主要為年輕男女[2],條文概述了失精家因失精而致一派腎氣虧虛之象,同時兼有清谷、亡血、男子失精,女子夢交的相火妄動的癥狀,此相火屬于局部的實邪,與整體虧損的性質相反,故治療時不可一味峻補。仲景選用桂枝湯調心陽以安相火,加入龍骨、牡蠣斂陽固澀,君相安位則邪可去,正可安。若根據腎氣虧虛的全身狀態直接采取峻補之法補腎填精,恐易加重其妄動之相火,過勞而致虛損更甚。
6.3 全身局部虛實相反的處方策略
通過對以上全身局部虛實異治的認識,可以發現臨床大部分慢性病、虛損性疾病均符合這一病機。以現代疾病中的肺間質纖維化為例,現代醫學認為該病原因不明,以彌漫性肺泡單位慢性炎癥和間質纖維化為主要病理變化,最終導致纖維化為特征的彌漫性肺間質疾病。現代中醫學多以“肺痿”“肺痹”等病名認識該病,并應用《金匱》肺痿的主方麥門冬湯治療,取得了一定效果[21]。
試根據全身局部虛實異治的處理策略分析該病:肺纖維化患者隨著病情發展,疾病后期常伴有消瘦、全身虛弱、呼吸衰竭等虛弱表現,此表現屬于全身癥狀;其肺組織結構遭到破壞,常表現為肺通氣和換氣障礙,導致呼吸困難,痰氣阻滯,此表現則屬于局部臟腑形損而致的邪實。從整體局部的虛實差異分析麥門冬湯治療該病的處方策略:對于全身的虛弱狀態,選用大劑量麥冬益氣養陰;對于局部的痰氣阻滯,選用半夏化痰散結;人參可助麥冬補益津液;粳米、甘草、大棗顧護脾胃以培土生金。由此觀之,該方符合全身虛、局部實的病機以及全身局部虛實相反的處方策略,且與肺間質纖維化一病所表現的臨床癥狀相符。另外有實驗研究表明,麥門冬湯可能通過改善氣道周圍纖維化區域的間質增生來發揮藥效[22]。
通過虛勞概念的演變進一步引申出全身局部觀的認識,這一認識超越整體觀對人體和疾病的局限,對臨床復雜難治性疾病的治療具有啟發意義。
7 總結
現代醫書在論述疾病歷史源流時,習慣將理論源頭追溯到經典中。如對虛勞病的論述,普遍將其理論淵源追溯到《黃帝內經》的“精氣奪則虛”“虛則補之,損者益之”以及《難經》的“五損”理論中[23],認為該病的發展是線性的延續。實際上,這忽視了不同時代背景下醫學體系的改變對醫家個體的影響,正是這一影響,導致了認知差異的形成。
經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的醫學思想和虛勞的內涵與外延的梳理,可以發現中醫界對虛勞的認識主要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漢唐時期,醫家以病人的虛弱狀態作為診斷依據,病種多樣,病性復雜,囊括的疾病種類繁多,治療時既注重虛損的補益,也注重實邪的祛除;宋至清,在理學的影響下,醫家對疾病的認知逐漸細化。盡管不同流派和醫家對虛勞的認識有所差異,但逐步形成了以五臟氣血陰陽的虛損為主要病機的觀點,對虛證的認識更加細化,虛實夾雜類疾病不再屬于虛勞的范疇,治療方面也逐步側重于臟腑虛損及氣血陰陽的補益;及至現代,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提出后,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原屬于虛勞中的虛證與實證被分開論述,虛勞逐漸等同于虛證,且整體與局部需保持虛損的一致性。與漢唐時期以癥狀為主要診斷的醫學模式相比,醫家對虛勞的認識變為以病性為主,這一認識也進一步反映了醫家對疾病診斷的細化和醫學體系的改變。
因此,虛勞的內涵與外延經歷了從癥狀到病機,從包含虛實夾雜狀態的疾病到純虛疾病的演變。理清這一演變的歷史原因,可以明確仲景所論虛勞的真實含義,同時認識到整體觀的局限性,進而將全身局部觀的決策思維更好的應用于疾病的臨床診斷與治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