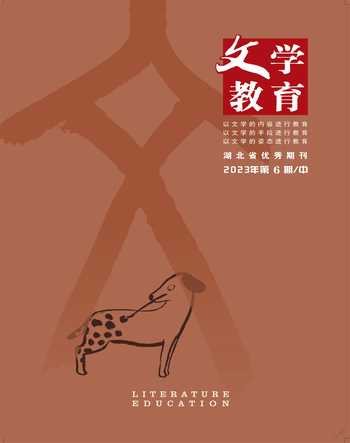魏晉士人的精神嬗變及當代啟示

驢鳴、長嘯、談玄、打鐵、縱酒佯狂、顧影自憐,這便是魏晉,是宗白華先生所謂的中國史上最混亂和最苦痛的魏晉。魏晉易代之際,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時代的夾縫割裂了士人的道德和行為,他們的理想人格發生了從君子到名士的轉型,他們醉心于清談、飲酒和吃藥,無論在朝在野,只為保家,不想衛國,只為明哲保身,不想造福百姓。史學家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士族,做人以行如畜生為通達,謀職以不走正道為才能,當官以不負責任為高尚。官場里充滿奔走之士,朝堂不見讓賢之人。”[1]P108可見魏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畸形、扭曲的,這是士人在對黑暗現實審時度勢后的選擇,是魏晉世界觀的心靈外現,盡管消極墮落卻體現了當下的人格理想和務實精神。
一.病態自由與矛盾人心
曹魏篡漢,司馬氏易代,如出一轍的殺戮使魏晉充滿了血腥。儒家的道德規范失去了約束力,獨尊的儒術也失去了原始生命力,華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倒塌了。于是士人開始追求新的人生體驗:回歸自然與人性,在及時行樂中實現自我。這是玄學的心靈外現,也是魏晉士人痛苦內心的外化。就連曹操都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憂患和感慨,更何況士人崇尚自由、任情放蕩、不拘禮節。然而他們所追求的自由是病態的,病態的主要表現是吃藥和酗酒。
吃藥的風氣始于何晏。何晏曾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世說新語·言語》十四)于是在他的影響下,五石散廣泛流行。五石散有毒且藥性燥熱,食用者須以飲酒或快走的方式散熱解毒,于是魏晉便出現了一群衣衫不整、散發狂奔的男子。不僅如此,長期食用五石散會使皮膚敏感,一撓即破,難以愈合。因此,魏晉士人大多寬衣大袍,且不敢沐浴,就算身上長了虱子也不以為然。“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晉書·王猛傳》)這便是“捫虱而談”的來源。然而這些行為在當時卻被競相推崇和追慕,甚至有人佯裝藥性發作,寬衣倒地,抓耳撓腮地裝出抓虱子的樣子,這就是魏晉的時尚。然這一時尚也有其意義:68歲位高權重的王戎就是在危急時刻假裝藥性發作,跳進茅坑裝瘋賣傻才得以保全性命。
魏晉士人不僅吃藥還酗酒,如“竹林七賢”中的劉伶。據《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經常乘坐鹿車出門,一邊喝酒,一邊前行。隨行的仆人扛著鋤頭,準備將醉死的劉伶就地掩埋。有一次劉伶甚至赤身裸體地躺地上飲酒,對于旁人的譏笑他反駁:“我以天地為棟宇,房屋為裈衣,諸軍何為入我裈中?”(《世說新語·任誕》六)酗酒是劉伶的生存之道,對于司馬政權,劉伶不想像嵇康那樣公然反抗,也不愿像阮籍那樣委曲求全,面對司馬氏他借著酒勁撒潑狂言,答非所問,流露出百無一用的樣子,最終得以壽終正寢。劉伶為避禍而酗酒,阮籍亦然。為了拒絕與司馬昭聯姻,阮籍醉飲兩個月。正如阮籍所說的“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詠懷》四十一),既然誰也飛不出魏晉這一彌天大網,那就飲酒作樂,明哲保身。然而,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就像王大所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需酒澆之”(《世說新語·任誕》五十一),所以阮籍嗜酒如命。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世說新語·言語》七十六)支道林放鶴歸去。這是出于對向往自由的感同身受。同樣渴望自由的還有“與豬共飲”的阮咸、“曝裈當屋”的劉伶、“顧影自憐”的何晏。他們在醉生夢死或藥性發作的時候享受自在,于是狂放和墮落。但這只是士人在苦中作樂中自欺欺人而已,因為那樣的自由是虛幻和病態的。病態的同時,他們的人生還充滿矛盾。據載,王述在做王導的屬官時,經常與同僚聚會暢談。見大家對王導極盡阿諛奉承,王述說:“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世說新語·賞譽》六十二)這是王述的率真。率真的王述還很貪財,剛上任不久便收受賄賂。面對批評,他回答:“足自當止。”(《晉書·王述傳》)但后來做州郡長官時他卻將俸祿和賞賜散發給親朋好友。王述的口無遮攔與大言不慚正如當代青年對率真而不扭捏,真誠而不造作的想象和追求。難怪簡文帝評價他“直以率真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世說新語·賞譽》九十一)而謝安“掇皮皆真”(《世說新語·賞譽》七十八)的評價說的便是王述的善隱真意。
魏晉士人的率真猶如孩子的純真,但也不盡相同。孩子的純真是未經世俗影響,沒有濁氣沾染的“不懂事”,而士人的率真是主動扭曲的所謂個性,有時近乎“癡”。因人以為“癡”,才能保全性命,這是時下的生存之道。然而,無論是雪夜訪友后“造門不前而返”的王徽之(《世說新語·任誕》四十七),失子后“豁情散哀,顏色自若”的顧雍(《世說新語·雅量》一),還是侄兒大敗前秦依然“意色舉止,不異于常”的謝安(《世說新語·雅量》三十五),都無非是“長于自藏”罷了。(《世說新語·賞譽》四十四)可見,士人的率真只是喜怒不形于色的隱忍,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能力。
“竹林七賢”中王戎讓人印象深刻。據說他富可敵國卻一毛不拔,送給侄兒的結婚禮物隨后又要了回去,為了不讓別人占便宜竟將李子核逐一鉆孔再賣,但父親死后他卻拒收帛金。讓人不解的還有阮籍。在“男女不雜坐”的禮教下,阮籍醉臥美人旁;對嫂子不僅有辭行之禮,還親自護送;聽聞母親去世的消息后仍繼續下棋,守孝期間還盡情飲酒吃肉。不僅如此,“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晉書·阮籍傳》)的阮籍竟以青白眼示喜惡。“稽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晉書·阮籍傳》)王戎、阮籍皆是時代的縮影,他們的率真不一定是真實,畢竟“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追求真實,這本身就是悖論。因此,魏晉對核心價值的種種追求,就只能變態畸形,充滿糾結。”[2]P159可見,魏晉士人集奮發和墮落,灑脫和執拗,漂亮和丑陋于一身,矛盾又統一。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非常痛苦。”[3]P105
“竹林七賢”的政治態度分歧明顯,但除了嵇康被殺,其余六人皆壽終正寢。因為阮咸虛浮,王戎裝瘋,劉伶賣傻,向秀見風使舵,阮籍委曲求全,而嵇康嘲弄權貴,公然反抗。嵇康的死改變了很多人,向秀從隱居深山到官至黃門侍郎,阮籍從酗酒避親到醉寫《勸進表》。情感的流露雖然可受外界的影響,但“哀而不傷”的自我節制還需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顧雍“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世說新語·雅量》一)阮籍葬母后“因吐血,廢頓良久。”(《世說新語·任誕》九)魏晉酗酒吃藥正如當代的享樂主義,都是放縱逃避的心理體現。當代青年沉溺于網絡,缺乏對現實世界的正確認知,于是消極、墮落,甚至自殘、自殺。因此,當代青年應以魏晉為鑒,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分析矛盾,解決問題,摒棄及時行樂和“朋克養生”的矛盾心理,不斷在社會現實中改造自我,實現自我。
二.審美情趣與傷逝情結
魏晉愛美,男人更甚。男子重儀容、以陰柔為美是魏晉的審美情趣。生性殘暴的石勒在誅殺王衍時,因不忍看到美男死后的慘狀,竟讓人推墻活埋這一“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的男子。(《世說新語·賞譽》三十七)魏晉唯美,士人不僅追求容顏之美,更追求情志的美好體驗。因此,既能美容又能使人亢奮的五石散便讓士人義無反顧,哪怕將全身潰爛或血管爆裂而亡。這獨特的審美讓本已充滿殺戮的魏晉更增添了一道血染的風采。
魏晉唯美,美在自然。魏晉時期儒學走向教條和僵化,玄學開始大行其道,備受推崇。玄學以崇尚老莊為根本,魏晉的山水詩始終不離老莊思想。無論是“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嵇康,還是“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的謝靈運,都將自然與玄理相滲透,藉山水以體玄理,在山水中追求清靜無為,清微淡遠,清高自賞。自然山水第一次成為文學獨立的審美對象。正如徐復觀說的:“由莊學而來的魏晉玄學,可以說是‘清的人生、‘清的哲學。”[4]P269“清”作為人生哲學的至高境界,是魏晉士人自然美與人格美,審美理想與人生理想的圓融和統一。然而“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阮籍《詠懷》五十三),士人唯自然之美的同時也悲憫人生,憂患生死。正如王戎所說的“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世說新語·傷逝》四),魏晉之人是極重情的。王濟生前喜聽驢叫,孫楚吊唁時便學驢叫為其送行。顧榮好琴聲,死后,張翰為其彈奏琴曲,放聲慟哭后竟“不執孝子手而出。”(《世說新語·傷逝》七)哭友情尚且如此,哭親情更是悲切。王徽之和王獻之晚年相繼病重,王徽之竟愿折壽以換其弟性命。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余年代之。”(《晉書·列傳》五十)后來王獻之去世了,王徽之悲痛萬分,一個多月后便也死去。
魏晉士人多傷逝,為他人也為自己。王濛病重時搖動著手中的麈尾感慨:“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世說新語·傷逝》十)他所惋惜的是自己的才華和容顏。而嵇康死前遺憾的則是廣陵曲的絕響。嵇康的人生向死而生,面對招安他屢次拒絕,態度強硬,言辭犀利,最終枉死。比起嵇康,阮籍更加長情,因為阮籍愛哭。他為失去母親而哭,為才貌雙全卻紅顏薄命的兵家女而哭,最后他“車跡所窮,轍慟哭而返。”(《晉書·阮籍傳》)阮籍最后的慟哭既為嵇康也為自己的窮途末路,但真正讓他嚎啕大哭的是盡管日暮途窮、孤獨無助卻還要活下去。最終,在嵇康死后幾個月阮籍抑郁而終。
魏晉重情,就連“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世說新語·尤悔》十三)的桓溫也有柔情的一面。桓溫攻蜀時,軍中有人捕獲一只小猿猴,母猴一路追趕哀啼,最后斷腸而亡。桓溫得知后“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黜免》二)不僅如此,一介武夫的桓溫還多愁善感。有一年北伐路過金城,見到自己曾種下的柳苗已成大樹,于是感慨:“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然后扶著柳枝潸然淚下。(《世說新語·言語》五十三)可見,盡管魏晉多屠戮,而士人仍重情。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獨立自主、仁義禮信等人格品行逐漸缺失,人際關系逐漸淡漠。而魏晉士人崇尚自然、重情愛人的情懷將啟迪我們對人生價值的觀照和思考:個人存在于社會,個人的價值和利益影響著社會,更影響著個體的進步與發展。只有秉持愛人與愛物之心,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統一,才能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
三.傲慢人生與務實精神
魏晉的門閥制度保障了士族成為上品官宦的世襲特權,于是士族有了“貴族”的氣質和傲慢的性情。雖然東晉政權是倚靠士族建立的,士族在經濟和政治上也曾與皇權相抗衡,但皇帝依然可以對其懲治甚至滅族。在魏晉,決定士族身份地位的是本世族的門第和名望,而非皇帝的寵愛與恩典,因此對于士人而言,光耀世族便能享千秋之榮華。于是士族們企圖在談玄論道中展現自我,以此提高本族世家的名望和地位,清談于是成為魏晉的另一時尚。空談玄理,不論政治,不問百姓,魏晉士人沉醉于玄學中自命不凡。然而,當殘酷的現實與理性的思辨背道而馳時,迷茫、恐懼、無助和絕望便籠罩著士人的心。盡管如此,他們仍要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清高和豪邁給后人留下回憶。(左思《詠史八首》其五)正如蘇力教授所言:“一個群體的長期‘愚蠢,從功能主義視角看,很可能就是他們在生存的具體情境中被逼出來的唯一選擇,因別無選擇,所以是智慧。”[5]P3個人可以愚蠢,人類則不會,群體的長期“愚蠢”定是當下的智慧。而魏晉兩百年間無論清高還是驚俗,豪邁或是風流,皆是當下的務實和別無選擇的智慧。魏晉的智慧體現在處世之道、人格精神,更體現于言語。魏晉清談常以高妙的品題和精彩的辯論彰顯個人的思辨能力和語言藝術,談玄者每到濃烈之時盡管通宵達旦仍感意猶未盡。然而,除了談玄,士人有的聚斂錢財、比財斗富,有的驕奢放縱、腐朽墮落。他們也曾有濟世之志,卻又在現實中執迷不悟,如王徽之、謝安等人。他們一邊享受著朝廷的高官厚祿,一邊又在山水的閑散和自由中流連不返。這就是士人務實的表現,正如羅宗強先生所評價的:“而其實入世之深,機心之重,亦莫過于晉人。”[6]P181
自古中華文化注重現實,崇尚實干,即所謂“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王符《潛夫論》)。然而只有權貴顯要才能不尚空談,德高望重才能致力實干,魏晉則不然。因為務實的前提是求真,魏晉的“真”是分裂割據與謀朝篡位,門閥傲慢與皇權虛偽。于是士人寄情山水,談玄論道。他們以傲視古今、狂放叛逆的姿態直面現實,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這種不為外物所累、實現自我、以“人”為本的人生觀和務實精神在當代仍有其意義。在社會急劇轉型、經濟迅速騰飛的今天,我們一邊享受著科技帶來的智能化體驗,一邊承受著被工具化和模式化的壓力。網絡技術的發展更滋長了孤獨、焦慮和敏感等情緒,影響了當代青年正確人生觀的形成。在此重壓下,我們需要“慮周流于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于四運,翻翱翔乎八隅”(阮籍《大人先生傳》)的人生理想,因為只有心靈自由才能不滯于物,自信自強才能立足于世。
魏晉士人一生充滿矛盾,他們因儒家的入世觀走上仕宦之路,而后儒學式微了。于是他們放縱出格,有悖禮制,積極避禍,消極抵抗,哪怕茍延殘喘,也要實現自我,這是魏晉士族最深沉的悲劇和最強烈的苦痛。如今的我們處于長期的和平時代,即便有著身先士卒的情懷和濟世救國的抱負,只要不置身于刀光劍影的社會現實,是很難理解古人的思想和行為的,無論是避世或者背叛。而實際上不僅只有消極和墮落,魏晉士人肯定自我、實現自我、追求自由、熱愛自然等精神仍值得我們學習。不僅如此,魏晉的文學與文化對后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由于對文學的重視,文學題材的開拓,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魏晉這一文學自覺的時代。自覺的除了文學還有人。魏晉士人在亂世中覺醒,他們以獨樹一幟的目光和姿態批判社會、警醒世人,以煥然一新的理念和價值體系重塑人生。在藝術文化上,魏晉的門閥制度使音樂、繪畫、書法、詩歌以世家的形式傳承下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起了重要的作用。魏晉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魏晉的人格精神、文化藝術、審美追求將穿越千年成為新時代的序章,引發我們啟迪和思考,供我們借鑒和學習。
參考文獻
[1]謝圣明,黃立平.《白話二十四史》第五冊《晉書·孝愍帝紀論》[M].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
[2]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II·魏晉風度[M].浙江文學出版社,2016.
[3]李澤厚.美的歷程[M].三聯書店,2009.
[4]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作者介紹:許小婷,泉州華光職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