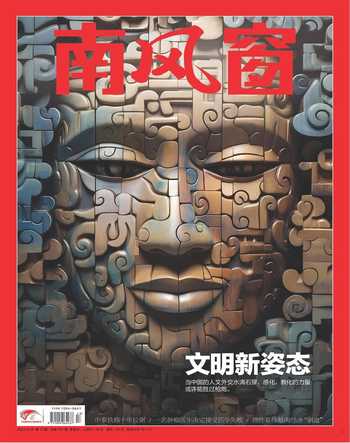如何預測“不可預測”的未來
郭曄旻
《未來大歷史》

或許不少人都做過彩票中獎一夜暴富的“白日夢”,也都幻想過自己能夠擁有特異功能,提前預知在未來開出的彩票號碼。不過,現于悉尼麥考瑞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大衛·克里斯蒂安為這種想法潑了一頭冷水:“想要弄懂未來可能有點像是想要抓住空氣。”不過,這樣的情況并不是沒有好處:“生活中的戲劇性和興奮感大多來自對未來的無知,而這也給了我們選擇的自由,以及去深思熟慮的道德義務。”
或許,正是出于這種“道德義務”,大衛·克里斯蒂安撰寫了《未來大歷史:如何建立未來思維》。所謂“大歷史”正是克里斯蒂安本人創造的名詞,用以探索從宇宙大爆炸到現代的歷史。
從學術意義上說,“大歷史”是一個新興領域,它使用多學科方法研究從宇宙大爆炸到現在的歷史。研究“大歷史”所需的“跨專業”特征,倒是正與大衛·克里斯蒂安的人生經歷相符。他在牛津大學讀博時學的是哲學,后來專攻俄國史,1984年還寫過一本關于俄羅斯農民的歷史著作,題為《面包和鹽》。
為什么著眼“過去”的“大歷史”會與“未來”聯系起來?克里斯蒂安有自己的解釋:“關于未來,我們僅有的線索都來自過去,這是最奇怪的一點。這解釋了為什么生活會感覺像是一邊盯著后視鏡一邊開賽車,也難怪我們有時候會撞車。”但也正是因為“我們也是在回望過去時步入了未來”,“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用過去照亮可能的未來”。
關于“可能的未來”,他給出了令人感覺有些沮喪的結論:“我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基于“未來無法確知”這一前提,克里斯蒂安在書中給出了兩個概念,“未來思維”與“未來管理”。前者用來囊括對于未來的各種各樣的思考,后者則描述“那種試圖把控或者按自己意愿調整未來走向的嘗試”。
對于人類而言,“未來管理”又可以分為三個步驟:找到一個目標;尋找并分析所在環境里的趨勢,搞清楚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么;然后行動,或者用書中的字眼,“下注”。這個詞倒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羅馬的愷撒揮軍渡過盧比孔河時所說的名言,“骰子已經擲下了(Alea iacta est)”。
這本書用了相當大的篇幅描述單細胞微生物、多細胞微生物、植物以及動物的“未來思維”與“未來行為”。對于動物而言,這些功能是通過“神經元”實現的。譬如,果蠅的大腦里有差不多20萬個神經元,而章魚的神經元則多達5.5億個。身為“萬物之靈”,人類大腦更是包括了大約1000億個神經元。
神經元傳遞信息的速度其實很慢(27.4米/秒),比已知的宇宙最快的光速(30萬千米/秒)低了不止一個數量級。但克里斯蒂安也指出,神經元傳遞的信號是“無損”的,如同通過地下電纜傳輸的電話信號一樣,所以腳趾上的疼痛感傳遞到大腦的時候并不會減弱。這種“信號無損”的特征,以及強大的并行運算能力(同一時刻有數以百萬級的神經元同時進行運算),使得“大腦在某些方面仍然比最頂尖的計算機更為強大”。這種說法顯然會讓一些恐懼“AI”的人大大松了一口氣。
盡管“對于大多數像我們這般醒著的生命而言,未來思維皆存在”,但人類的未來思維自有其獨到之處。首先,這是因為人類在地球生物中擁有相對最大(按大腦尺寸與身體大小的比例)的大腦。更重要的是,人類具有“集體學習”的能力。在書中,克里斯蒂安指出,“許多物種都存在某種形式的文化,因為它們有語言,也能分享信息與想法”。已然劃入人科的黑猩猩與大猩猩自然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然而,“唯有人類在分享信息時可以如此高度精確”。“集體的知識儲備隨之增長并代代相傳”,“我們的技術、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巨變”,“越來越多的知識儲備讓我們駕馭周圍環境與生物的能力越來越強”。
這樣“巨變”的表現,就是各個歷史時期人類的“未來思維”有所不同。在農業時代,占卜是很常規的做法。“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對先知與占卜者的尊敬可一點不亞于對醫生、領航員或是將軍的尊敬”。書中提到,古希臘的占卜師會觀察鳥群,也會研究獻祭動物的器官,聆聽人們講述的夢境,并對征兆做一番解讀。這自然是有根據的。這方面有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為了與斯巴達爭奪霸權而遠征西西里島,幾經交戰,仍舊失利,最后不得不撤軍。公元前413年8月27日夜里,正當雅典準備撤軍的時候,忽然發生了月蝕。統帥聽從了預言家的警告,下令過三個9天后再撤。這就使敵軍有時間訓練和改進海軍,把一度不可一世的雅典艦隊打得一敗涂地。
以此而言,克里斯蒂安感嘆“在現代人的眼中,流行于農業時代的未來思維,從方方面面來看都非常古怪和幼稚”。他同時指出,“驅使人們占卜的是巨大的焦慮感,是大多數人生活中的極度不穩定和不安全感”。這句話用來評價今日世上的一些怪象,仍舊是恰如其分的。
但就整體而言,當代人類的未來思維顯然與農業時代有了巨大區別。他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因果關系。“理解了事情為什么會發生,我們在思考未來時就能有更強的能力來察覺趨勢并將趨勢加以運用”。其二,或然性理論,“當無力確定何為真理的時候,我們應該追隨最可能為真的那個”。其三,數據收集與統計。“我們對概率變化趨勢的察覺、分析、理解和計算能力都會隨之增強。”最后,信息技術與計算機科學。這一點其實與第三點緊密相關,“現代計算機科學讓我們對統計信息的儲存和分析達到以前無法想象的規模,其速度和精確性也是空前的”。
當然,如今的“未來思維”距離完美二字還相差甚遠。基于過去數據的邏輯歸納其實并不可靠。“對真前提的歸納推理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在這方面,書中提到的“農場主假說”就是如此。一只火雞觀察了將近一年,發現每天某時總有人前來喂食,因此總結出了這個時間會有食物降臨的結論。不幸的是,這天是圣誕節,農場主把火雞宰了吃了。有趣的是,劉慈欣在《三體》提到了這個著名的假說,而克里斯蒂安在《未來大歷史》也提到了《三體》這本書。
但當代人類在“未來管理”方面還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強大能力。如果愿意,人類可以輕易滅絕地球上任何一種大型野生動物,也可以通過開鑿運河、建設水壩,改變地表景觀……這就使得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自己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未來。
克里斯蒂安顯然是個普世主義者,在他看來,“當我們意識到彼此依賴度增強的時候,我們就能為地球這艘飛船的美好未來達成廣泛的共識”。但作為一位理性的學者,他對人類的未來仍然給出了小心翼翼的警告:“回望過去的幾百年,活在今天世上的大多數人,看上去像是危機之前一幫飽受眷顧的家伙—可以隨意享用化石燃料革命成果的最后一批人。”
“在最糟糕的情景中,人類社會會在饑荒、戰爭、政治與經濟的崩盤以及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夾擊中轟然到底。”
“在多數的未來情景中,小型的、開拓性的人類殖民地將在21世紀末遍布太陽系,而機器人太空艙也將踏上前往其他星系的征途。”
太極端的預測或許聽上去有些不太靠譜,克里斯蒂安自己也為此打上了補丁。“從實際層面來看,不管是哪種場景都不大可能以純粹的形式上演。最終呈現的未來將是一個綜合體。”“當未來來臨時,它的混亂程度一定不輸過往。”這段話倒是令人聯想到古希臘“神諭”的特征—“為了有趣且合理,它有足夠的細節,也不會太過籠統以至于空洞”,“這些答案涵蓋了大多數未來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本書的最后,克里斯蒂安甚至提到了“多重宇宙”的概念,在這個概念里,各種未來的可能性在不同宇宙得以實現,也讓書中早先提到的觀點似乎不再正確:“除了一種可能之外的所有未來都消失不見了,留給我們的便是獨一無二的現在。”
而這樣的結論,等于把又一個嚴肅的問題拋給了讀者:假若“現實”的唯一性在“多重宇宙”里不復存在,“現實”究竟還有什么意義?如同整本書里的做法一樣,大衛·克里斯蒂安沒有提供確定的答案或預測,而是鼓勵讀者對未來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考—科學問題的盡頭,變成了一個哲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