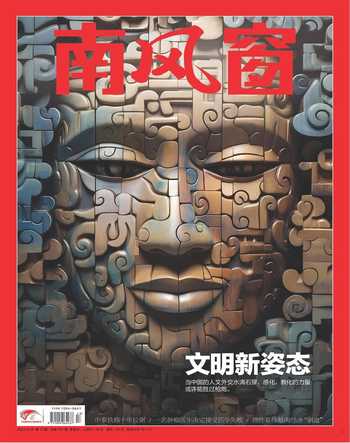導演王沐,拍一段精神受困者的愛情
何焰

殺青那一天,演員王子文哭得很慘。那是2020年泉州的冬天,她正結束電影《溫柔殼》的拍攝,將趕往《三體》遠在東北的片場。那一晚,她向人訴說對這部電影的不舍,她說,是這部電影好像將她洗了一遍。
《溫柔殼》中,王子文確實有一雙像被洗過的清澈雙眼。不止是她,還有男主角尹昉。他在一間亮室中奔跑,直到人群之中的那個女孩也笑了,才結束一場惡作劇。三十多歲,在演員中也罕見的,一派天真。
王子文演覺曉,尹昉演戴春。他們在一間精神受困者的療養院里,開始了戀愛。—這部名叫《溫柔殼》的電影,在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一口氣拿下了三個獎項,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和費穆榮譽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是王子文,最佳男演員是尹昉,而最佳導演的獎杯,是王沐的。
王沐是一名中年男性,大連人,微胖、不脫發、講話慢,性格直率。《溫柔殼》是他的處女作。
拿了獎,但其實是一股忐忑,貫穿著王沐過去的五年。從2018年籌備劇本,2020年冬天拍攝完成,再到今年5月26日電影《溫柔殼》在全國院線上映,這個漫長的戰線,已經拉了整整五年。
還好,口碑不錯。
這五年來,世界幾乎天翻地覆般地改變,王沐的生活也一樣,他有親人離世,也迎接了一個嶄新的小生命,他振作又受挫,受挫又振作。但還好,五年前起草、三年前拍完的電影《溫柔殼》,仍舊在2023年受到了認可。
6月伊始,王沐導演接受了南風窗的采訪,講敘了他因為拍攝電影《溫柔殼》所窺見的精神受困者的愛情與世界的一角。王沐承認一部處女作的局限性,但也愿意告訴觀眾,自己如何用人生的一個五年,來決心平視一群人。
他們是精神受困人群,也可能是我們的朋友、戀人、家人,甚至是我們自己。
推開門
“過年好。”2018年的盛夏,大連國禮醫院里,一個男孩反復對剛進來的王沐打招呼,“過年好。”
王沐禮貌回復:“你也過年好啊。”對方狡黠一笑,轉身就向同伴炫耀。—好壞。原來他是來試探王沐的。王沐也笑了,但突然就被撫平了緊張。
這是一家精神專科康復中心。這一年,王沐因為決心要拍攝一部精神受困者的愛情電影,托了朋友,得以進入精神專科康復中心的住院部采風。
這也是王沐走近精神受困者的第一天。
這一天的故事,從一扇門開始。
國禮醫院的一扇大鐵門,沒有上鎖。王沐在猶豫:是等院長來接,還是直接推門進去?他好奇為什么這里不鎖門,也沒有人從里面跑出來。王沐站在門外打量著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偶爾回看他。
他推了門進去。
進去之后,王沐慢慢放松下來。在今年5月底電影上映后,王沐寫下一篇長文《溫柔之必要》,講敘了許多自己采風第一天的經歷。
而《溫柔殼》電影的男女主角原型,就來自王沐在國禮醫院見到的一對女孩和男孩。
那一天,王沐推開鐵門,在人群中看到了那個女孩,“她身后一直跟著一個男孩,健康的膚色,眼神專注堅定,他永遠和女孩保持著固定的距離,從來不打擾她的生活”。
國禮醫院是男女分住的,但院長告訴王沐,這里經常會有人談戀愛。“他們并不避諱,也不會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這里的工作人員,便不會多加干涉。“不過這樣的戀情總是短暫的,一旦有一個人出院了,這種關系也就戛然而止,他們似乎很難得到家人的認同,盡管這些家人,大多數時間從未來看過他們。”
探訪國禮醫院之后,接下來的十幾個月里,王沐持續著采風工作。他看了十幾本相關書籍,走訪了五家相關機構,拜訪了一些心理學和精神科的專家。
在一年多時間的采風里,王沐有一些發現:相比于過去“精神病院”這種粗暴的稱呼,現在的機構名稱要溫和、五花八門得多。有的叫心理醫院,有的叫第幾人民醫院,有的叫康復中心,有的叫療養院。甚至有一些地方的福利院里,也居住著許多精神受困者。不同的名稱可能對應著不同的環境,王沐印象中,叫療養院的地方往往環境會稍好一些,但這些機構都有著一個共同點,就是:護工總是不夠,“1比8甚至1比16。”
院長告訴王沐,這里經常會有人談戀愛。“他們并不避諱,也不會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王沐去過的機構里,居住環境是很參差的。一些機構給王沐留下的印象是溫暖的,“似乎永遠能感受到有陽光透進來,有人很平靜地在其中生活,吃飯和散步”。而另一些機構,有封閉生活的場景,8個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還有沒有遮擋的衛生間,能夠看見里面的每一個坑位,也給王沐留下深刻的印象。
環境的參差,也在電影《溫柔殼》中有所呈現。
男女主角相愛的療養院,選址在福建泉州的鯉城福利院,那里的環境是溫和的,大門是敞開的,住在那里的人也幾乎沒有攻擊性。福利院里的真實住戶和工作人員也在電影中出鏡,大多數人的狀態平靜,神色天真;
而電影里,男主角精神受困的父親,他所居住的則是民間經營的無名收納所。那里房間狹小,收費便宜,有著被數倍放大的“老人味道”。
雖然從一開始,《溫柔殼》便定位是一部愛情電影,即便選定了“精神受困者”這個群體,王沐也從沒有野心要為這部電影做一個縝密的社會學田野調查,但他仍舊花了很多時間去親近他們,試圖在電影里放進一些生活的細節。
在忐忑中
其實是一股忐忑,貫穿著王沐拍《溫柔殼》的這幾年。
從2018年初決定從編劇轉行做導演,并選定要拍精神受困者的愛情故事開始,身邊就有人告訴王沐,這是一個勇敢又危險的決定。
一方面是個人發展上的忐忑,一方面是關于電影的忐忑。
《溫柔殼》制片人告訴南風窗,中國的電影圈似乎有一個怪事。攝影轉導演、執行導演轉導演、演員轉導演都很常見,但是感覺一個編劇轉行做導演的爭議就有很多,因為大家常說:“寫劇本和鏡頭呈現,完全是兩件事。”
但是王沐想轉行,原因不是別的,他只是想表達。
在轉行之前,王沐曾經跟國內非常知名的導演合作過劇本,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而擱淺,作品無法和觀眾見面。寫一個劇本將近一年的時間,作品中承載著他的情感和一個人生階段的感悟,連續兩三輪合作踩空之后,一個青年編劇的兩三年努力都變成無用功。
在沒有產出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王沐都很焦慮。“恨不得自己去做一點手工。至少是看得見的,有一個東西擺在我面前。”
想要表達,被看見,三十出頭的王沐一股沖勁兒,決定干脆自己拍。
拍什么呢?
最開始,王沐只是有一個模糊的想法,“要拍一個愛情故事”,最后錨定到精神受困者身上,王沐說是“命中注定”。
2017年他身邊有一位編劇前輩因為抑郁癥輕生。“只是一個短暫的工作接觸,大概兩個月,我覺得他身上似乎有無窮的精力,他很酷,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我想要成為的人。”但是有一天,王沐突然聽到,這個人離開了人世。
這件事對王沐產生了沖擊。
他開始去關注精神疾病的話題。慢慢地,他發現原來身邊有這么多的人都有精神困擾或者情緒困擾。這些朋友的遭遇,在王沐的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
那年年底,王沐逛書店,恰巧看到一本五年手賬。那是一本有趣的日記本,每一頁上都可以看到五年今日,這樣的安排讓王沐對時間的流逝有了實感。他突然產生了一種好奇:“我從想拍一個電影,到它拍出來,再到它上映,將會用多長時間?”
一個普通人想拍電影的夢想,一部電影從出生到與人見面,這一段歷程有多長?王沐真的很想知道。
十幾年沒有寫過日記的他,買下了這一本手賬。
但當時的王沐并沒有預料到,這一本日記,將會伴隨他整整四年。伴隨他去精神專科康復中心采風,伴隨他拿到2019年平遙國際電影節的創投獎金,伴隨他又去海南電影展拿下電影的啟動資金,伴隨著他的孩子出生,伴隨著疫情三年電影行業的持續蕭條,伴隨《溫柔殼》開拍……而到他停筆封本的那一天,這部電影才剛剛定剪。
王沐本想接著寫的,按照原計劃,把日記寫到電影上映那一天。
但王沐害怕了。
他擔心—這本五年手賬如果不夠用怎么辦?為了一部電影的誕生,這一本日記中已經記滿了他的忐忑和努力,如果寫到最后一頁,電影還沒有上映怎么辦,“會不會顯得我太可憐了?”
王沐決定封存了它。
再一次打開這本日記,是2023年5月24日。《溫柔殼》的首映禮結束之后。
五年多時間過去了,電影終于上映了。
在沒有產出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王沐都很焦慮。“恨不得自己去做一點手工。至少是看得見的,有一個東西擺在我面前。”
這一天,伴隨著一部電影從0到1,王沐在豆瓣寫下那篇長文:“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
得的什么病
直到今年6月初,接受南風窗采訪的時候,王沐說自己仍舊在這種忐忑之中。
而王沐最大的忐忑就是:“如果我沒有做好,可能會冒犯大家。或者說他們會誤會我在消費一個群體。”
當南風窗詢問王沐,他內心是否有一個答案,《溫柔殼》要做到一個什么樣的標準,才算不冒犯精神受困者人群呢?
視頻對話框里的王沐,立刻表現得有點無奈。一部電影出生之后,評價的權利就交由給了他人。導演沒有辦法。
如果非要有一個辦法,王沐的辦法是“平視他們”。
如何平視一個精神受困者,在王沐的生活中,或許他從自己的大姨的身上學習到了一些。
從王沐記事起,他的大姨就已經被診斷出有精神障礙。她的臉上總是掛著一股笑,處在一種不太清醒的狀態。家里長輩對大姨的病因,向來諱莫如深。“因為當年受刺激,似乎是和姥姥有關系。”
成長的過程中,王沐也只是遠遠地看著自己的這個親人,和她鮮少接觸。
直到2019年9月,姥姥在大連去世。王沐作為家中這一輩唯一的男性,回家給姥姥主持葬禮,在葬禮上,他見到了大姨生的兩個女兒,自己的表姐們。
表姐告訴王沐,在葬禮的前一天,才敢讓大姨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
但大姨似乎比想象中更冷靜。她只是說:“那以后再沒有人給我打電話了。”
原來,在姥姥人生的最后兩年,她每一天都和大姨保持著通話。
王沐無法不去想象那個畫面,春夏秋冬從眼前劃過,一個年邁耳背的老人,和她語速很慢的大女兒,每一天聊天的樣子。
王沐甚至會想:最后這兩年,大姨和姥姥是不是以這種方式和解了?但他又覺得,對于生活在“故事”中的家庭來說,不管是精神受困者,還是精神受困者的家人,“和解”這個詞,都太輕簡了。
王沐似乎走近了大姨一點,也更貼近了自己的電影《溫柔殼》一點。
他似乎也把從大姨身上感受到的情感、對親情的體悟,盛放在了自己的電影中,放在了電影主角的親子關系上。
從編劇轉行而來的導演王沐,在片場很少對演員講戲。如果他哪里覺得不對,他會去和演員講故事。他用一個故事去向演員溝通,請對方體味故事中的情感,由演員自己來發揮飾演。

為了把真實的經歷勾出的情感,灌注到電影中。王沐還找了兩個朋友,他們幾乎和電影中覺曉、戴春有著一樣的經歷。王沐請他們念一遍電影的臺詞,錄下來,送給王子文和尹昉聽。讓演員去感受,現實中有類似經歷的人,在這樣的場景下,會是這樣講話的。
王子文聽了錄音,問王沐,她說這個人聽起來怎么不像是生病了。類似的提問王子文也在一些采訪中講過,她說她問過導演,覺曉到底生的什么病?
王沐說:“覺曉沒有病。她只是不高興。”
這樣的問題,南風窗記者也追問王沐,男主角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
《溫柔殼》要做到一個什么樣的標準,才算不冒犯精神受困者人群呢?
王沐最開始不想回答,他說他不理解,“為什么你們看到一個人,不是看他愛什么,想做什么,要解決什么困難,而是一直追問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但后來追問著追問著,王沐告訴南風窗,最開始他也想要設定清楚,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但是他看了很多書、電影之后發現,同一種疾病可能在不同的書上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同一種病人在兩個不同的電影里會有兩種面貌。而幾乎探訪過的每一個專業的醫生也都告訴王沐,精神障礙患者通常是千人千面的。
后來,王沐索性不想在電影里講戴春生了什么病了。
“這部電影不是要為戴春治病的。我要寫的只是兩個人,他們相愛、就業、結婚、生育。他們的愛很美,很珍貴,和我們一樣。”王沐維護他們,或許已不單是一個導演維護自己的作品,更像是維護一個老朋友。
王沐打定了主意,《溫柔殼》要講兩個精神受困者的愛情故事,但要講他們身上更貼近普通人的那部分。
為覺曉和戴春這樣的人去維護一份普通的愛,其實更難,更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