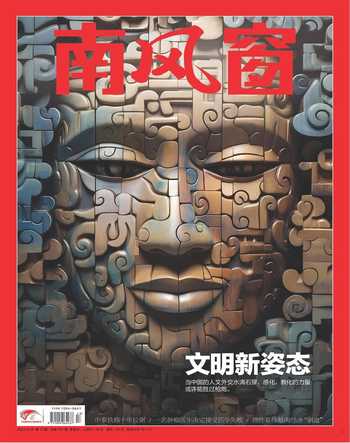土耳其轉向,尋找文明的背書
榮智慧

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緊張局勢一觸即發。穆斯林的齋月與猶太人的逾越節同時到來,近日有28萬穆斯林進入了以色列布控的東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兩個月前,這里有數百人遇襲。曾經三大宗教和諧共處的圣地耶路撒冷,如今紛爭不斷緊張兮兮。
七國集團峰會不久前在日本廣島落下帷幕。《時代》恭維稱,首相岸田文雄將日本帶回了國際舞臺,成為解決世界各地沖突的決策者。岸田文雄最近主動曝料稱,正與北約磋商在日設聯絡處。古老的東瀛文明,不期然成為西方遏制戰略的亞太前哨,還自鳴得意。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綽號“埃蘇丹”的埃爾多安第三次贏得總統大選。他甚至高歌一曲《給那些聽不到的人》:“唱吧親愛的,讓所有人都聽到……我愛你!我愛你!”土耳其近年來偏離親西方世俗主義,卻在外交上“左右逢源”,于國際舞臺備受矚目。
上述非西方軸心文明的國家和地區,各有其現代化轉型的高光時刻和問題成堆的落寞時分。相比于用一時的經濟發展指標來衡量,文明轉型的歷史經驗或許更具有超越視野。
地處東西方文明的交匯處,土耳其歷史上曾被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統治,有著前后13個不同文明的歷史遺產,比同樣層疊了東西方文明的耶路撒冷和日本更具歷史厚重感。
如今,告別奧斯曼帝國政治遺產、選擇“樞紐國家”定位的土耳其,能否像歷史上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融合了古代希臘、羅馬和印度的文化,為西歐文藝復興奠基那樣,對人類文明傳承創新有較大貢獻?
“民族牌”的土耳其模式
5月底的土耳其第二輪大選中,埃爾多安贏得52%的選票,隨后第三次出任總統。執掌中東大國20年的埃爾多安,加速締造一個野心勃勃的土耳其。他所青睞的“新奧斯曼主義”,是會繼續春風得意馬蹄疾,還是會挑起新的“文明沖突”?
問題的答案,還得從土耳其人的“民族認同”那里尋找。
埃爾多安率領的“人民聯盟”,勝選原因正如“隊歌”《冬不拉》所唱,“你的力量來自國家和民族”!反對派“民族聯盟”,本來大打經濟牌,然而第一輪大選后處境被動,不得不也轉向“民族牌”。
即便再次連任,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模式”也漸失光環。
土耳其現為世界第19大經濟體,人均GDP約1萬美元,相當于十余年來原地踏步,外債卻超過了GDP的一半—離“2023愿景”中GDP世界前十的目標很遠。2018年后,里拉價格跳水,通脹率一度升至85%的水平,迄今仍在50%左右。今年的大地震和大洪水,更使經濟復蘇舉步維艱。
匯率大跌,物價暴漲,主要由“埃爾多安經濟學”所賜。埃爾多安連續辭退央行行長,嚴格推行低利率政策,增加貨幣供應,以此促進中低端制造業發展,吸引外匯。反對派大發詰難,年輕人“吃不起肉,找不到好工作”。
但最新的大選證明,土耳其選民更看重主權和安全,經濟問題反而排在后面。
庫爾德工人黨成立于1970年代末,從1984年開始便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交界地帶發動襲擊,尋求獨立建國。雖然埃爾多安曾解除對庫爾德人的身份限制,也曾和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展開談判,但通過放大“恐怖組織”的“恐怖”、“包裝”反對派的縱容,他成功調動起支持者的同仇敵愾,鞏固了對土敘邊境地帶的控制。
土耳其高調介入利比亞內部沖突,作為北約成員卻謀求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還在非洲、中國、南亞、東南亞和高加索地區積極投資,顯現出不拘一格的地區強國姿態。
“漸別歐盟”也有民族主義成分。庫爾德人問題、敘利亞難民問題,以及土耳其與歐盟成員國希臘、塞浦路斯的歷史糾紛,都是歐盟拒絕土耳其的因素。12年前,阿拉伯變革潮摧枯拉朽,許多阿拉伯強人倒下;此后不少阿拉伯國家的青年,將埃爾多安視為伊斯蘭世界的理想領袖,超過一半的土耳其人對歐盟印象不佳。
地緣政治上的“向東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大轉變。土耳其號稱北約排名第二的陸軍強國,其海軍力量增長亦十分迅速,艦船頻頻出現于東地中海,勘探油氣資源。土耳其高調介入利比亞內部沖突,作為北約成員卻謀求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還在非洲、中國、南亞、東南亞和高加索地區積極投資,顯現出不拘一格的地區強國姿態。
特別是俄烏交戰以來,土耳其“左右逢源”:為烏克蘭提供無人機、集束彈藥和電子戰系統,同時不肯參與西方的對俄制裁。埃爾多安多次于伊斯坦布爾接待俄烏和談代表,更促成《黑海糧食協議》,令困于烏克蘭港口的谷物運往海外。
總結起來,“土耳其模式”不外是,在一個伊斯蘭國家,溫和的保守主義政黨長期執政,重視民生,堅持民主化,積極融入全球化,同時在世俗主義框架內打打擦邊球,盡量滿足保守選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獨立自主,尤其強調歷史性的身份政治符號。
文明傳襲方向之爭
“土耳其模式”還有一個名字:新奧斯曼主義。
2020年上半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圣索菲亞博物館改回清真寺,不僅再度掀起輿論詰問,也催生出圍繞“圣索菲亞”背后奧斯曼帝國“記憶與遺忘”的爭議。

關于奧斯曼帝國榮耀的回憶從未消失。自圣索菲亞清真寺被改成博物館以來,要求恢復為清真寺的呼吁就沒停過。在一些特殊的節點,比如1953年奧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500周年時,聲量最盛。
恢復清真寺的理由,并不來自宗教本身。伊斯坦布爾也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亞博物館對面的藍色清真寺,一直沒有多少人做禮拜。這一事件的理由是政治的,也可以說是利用宗教情感和歷史記憶的“宣傳操作”—歷史上,“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法提赫在這座清真寺舉行周五聚禮,紀念對西方和基督教文明之戰的勝利,該儀式持續了5個世紀。
埃爾多安擅長將自身的政治行為“嫁接”到帝國歷史之中。宗教圣地的恢復,本身就是“新奧斯曼主義”強調的榮光復興的核心。2020年5月29日的“征服紀念日”講話中,他特意提到:“我們要留下一個讓我們的祖先法提赫滿意的土耳其。”
“新奧斯曼主義”很難說是世俗主義的倒退,更多是埃爾多安對帝國歷史記憶的調動和操弄,以便服務于當下的政治氛圍。同樣,它也不屬于“文明的沖突”范疇。
在東地中海,土耳其也非常注重喚起奧斯曼帝國長期稱霸該地區的歷史記憶。其海軍艦船中,有一艘勘探船叫“奧魯奇·雷斯號”,顯然是為了紀念16世紀第一代“巴巴羅薩”海盜奧魯奇。除此之外,土耳其海軍還有三艘潛艇以奧魯奇·雷斯命名。
16世紀,奧斯曼蘇丹蘇萊曼大帝任命北非海盜王“巴巴羅薩”為“海軍總司令”。數十年里,幾代“巴巴羅薩”領導的奧斯曼海軍獨霸地中海,歐洲人甘拜下風,奧斯曼人也由此得到了北非的長期控制權。
“新奧斯曼主義”總被視為“凱末爾主義”的反面。
土耳其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凱末爾,打造出了一個世俗、進步、開明的土耳其。“凱末爾主義”的本質,是分離了突厥民族的原有傳統和伊斯蘭教法,然后與整個帝國的奧斯曼主義做切割,強調主體民族的獨特性,將草原習俗轉化為土耳其民族主義。建國精英使用拉丁字母創造新文字,完全學習西方制度。在民族主義壓力下,伊斯蘭教法開始退出國家政治、經濟領域,“現代”土耳其得以建立。
反之,“新奧斯曼主義”被西方視為宗教的、倒退的、保守的,負面評價較多。
其實,1980年代以來,土耳其第三共和國的諸多問題,促成了“新奧斯曼主義”的興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貧富分化加劇,城鎮化制造了大量的貧民區,為平民主義、保守主義和政治伊斯蘭提供了土壤;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一家獨大;議會制變為總統制;教育中的伊斯蘭和民族元素不斷增加;庫爾德問題、教俗之爭成為身份政治的焦點;與西方的關系陷入瓶頸期。
在一個99%的人口為穆斯林的國家和社會,如何安放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精神世界,顯然并非凱末爾的激進世俗主義所能完全解決。
“新奧斯曼主義”背后的保守主義群體,主要來自1980年代以來借全球化和私有經濟崛起的“安納托利亞小虎”中產階層。這一代人的成長環境,還是凱末爾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他們的主張依然以凱末爾主義為框架,同時,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總體上溫和實用,和伊朗教權國家的道路并不相同。
“新奧斯曼主義”很難說是世俗主義的倒退,更多是埃爾多安對帝國歷史記憶的調動,以便服務于當下的政治氛圍。同樣,它也不屬于“文明的沖突”范疇,就像臨時阻止瑞典加入北約那樣,更多是地緣政治上的見招拆招。
不過,包括反對“新奧斯曼主義”的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在內,人們對早已灰飛煙滅的“奧斯曼帝國”標簽的敏感,也足以說明帝國揮之不去的文化遺產的豐厚。
輸出何種政治影響?
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轉向,與埃爾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總設計師”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緊密相關。理解其戰略思想,方能理解土耳其的“大國夢”與轉型之路。
作為“基辛格式的外交家”,達武特奧盧以著作《戰略縱深》(2001),給 21世紀的土耳其規劃了新路線圖。正義與發展黨恰于2002年上臺執政,將“戰略縱深”的要義—加強土耳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發揚光大。
達武特奧盧認為,21世紀的土耳其已經成為地區性的“樞紐國家”。冷戰時期,土耳其只是一個北約的邊疆成員國,充當西方遏制蘇聯的南大門;冷戰結束后,土耳其被看成溝通東西方的橋梁國家。但是,土耳其應有同時在多個區域發揮影響力的能力,不能滿足于做橋梁,更要做“樞紐國家”,為鄰近地區提供安全、秩序與穩定。
而“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和歷史遺產,也使土耳其成為一個樞紐國家”。
“樞紐國家”的特征,就是輸出“政治影響力”。
今日的問題在于,一旦民族主義力量衰退,土耳其將走向何處?如果伊斯蘭教政黨在大選中勝出,伊斯蘭教法會否重返政治、經濟領域?
2010年底開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也門接連發生政治動蕩。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專制世俗政權被推翻,各色伊斯蘭主義政治力量泛起,且爭先效法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黨上臺,利比亞“過渡委”以伊斯蘭教法為法律依據,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一度掌權,敘利亞的穆兄會也支持“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自身也有意擴大其影響力。在納卡沖突中,土耳其積極支持“一個民族,兩個國家”意義上的兄弟國阿塞拜疆。
實際上,自20世紀初,土耳其就已經是亞洲各國的效仿對象。繼日本“維新”之后,列寧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稱為“亞洲覺醒”的重要部分,其現代化成就也曾令中國知識精英心向往之。
土耳其的現代化成就,往往被總結為三點:民族國家,憲政—代議制,工業化。其中“民族主義”是土耳其轉型的最重要推動力。
1930年代,土耳其民族構建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土耳其史觀”:數千年前生活在中亞的短頭顱民族,曾在中亞的內陸海創造了燦爛的文明,當內陸海干涸,他們就離開中亞,四處遷徙,向東到了中國,向南到了印度,向西到了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朗、安納托利亞、希臘和意大利。
在這一史觀的持續推動下,土耳其走過凱末爾主義的激進世俗民族國家建設時期,團結(民族主義)和進步(世俗主義)成為社會共識。有此共識,土耳其多黨民主政治得以運轉,同時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得以被規訓。妥協和務實之下,伊斯蘭主義政黨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力量,進而形成了目前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基本形態。
說到底,土耳其轉型模式,就是靠強有力的民族主義來“反傳統”。相比之下,伊朗就沒有強有力的民族主義,一旦引進現代制度,與伊斯蘭教法割席,馬上就會失去政權正當性,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正因此爆發。
而今日的問題在于,一旦民族主義力量衰退,土耳其將走向何處?如果伊斯蘭教政黨在大選中勝出,伊斯蘭教法會否重返政治、經濟領域?以土耳其為“榜樣”的那些伊斯蘭社會,在現代轉型的十字路口,又該如何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