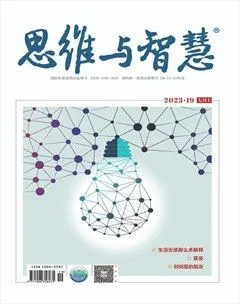時(shí)間里的朋友
姚文冬

去朋友家做客,遇見(jiàn)一人,覺(jué)得面善,聊了一會(huì)兒,也十分投緣。日后越想越蹊蹺,心里一激靈,這個(gè)人,曾經(jīng)是我一位朋友啊!——多年前因公務(wù)相識(shí),隨之有了私交。那年,時(shí)興搞第二職業(yè),記得他在夜市開(kāi)了個(gè)大排檔,老板、廚師、服務(wù)生一人兼,炒完菜,端著盤(pán)子在桌椅間飛步穿梭,像一個(gè)雜技演員。我常去閑坐,見(jiàn)此情景給他鼓掌加油,他干得更歡了。夜市散了,我倆在路燈下小酌,感嘆掙錢(qián)不易。
曾經(jīng)那么親密的朋友,幾十年后面對(duì)面,竟不認(rèn)識(shí)了?但不管怎么說(shuō),我們的友誼已中斷幾十年,是什么時(shí)候、什么原因?一概想不起來(lái)了。
人到中年,感覺(jué)身邊的朋友在變少——有的緣盡,“自然”走散,有的因有隔閡、裂痕,逐漸冷淡、疏遠(yuǎn),終成陌路。前者讓我感嘆歲月無(wú)情,后者讓我感到人情無(wú)常。
人生就像走路,從起點(diǎn)到終點(diǎn),與相遇的人并肩走過(guò)一段,然后各走各的。所謂朋友,就是曾經(jīng)并肩走路的人吧。走得太慢的,一回頭,不見(jiàn)了;走得太快的,趕不上了。無(wú)論快與慢,都漸行漸遠(yuǎn)。那些從身邊走失的朋友,都去了不同的地方——這個(gè)“地方”,包括空間,也包括時(shí)間。是的,時(shí)間也是一個(gè)去處。譬如我去上海,就能見(jiàn)到上海的朋友;那么,我“去”2008年,當(dāng)然也能見(jiàn)到2008年時(shí)的朋友。這個(gè)開(kāi)大排檔的人,就是這樣一位時(shí)間里的朋友。記得那年是1999年,在1999年的記憶里,我們的友誼仍栩栩如生。
朋友做不成了,彼此盡量回避空間的相遇,所以,不要試圖挽回失去的友誼,但要記住,他們都成為了時(shí)間里的朋友,以另一種形式永恒地存在。
少年時(shí)打工,那么多打工仔,唯獨(dú)我倆情投意合,我們還去照相館合影(那年代去照相館是一件隆重而奢侈的事,見(jiàn)證著友情的深度),后來(lái)工廠倒閉,就各奔東西了。去年懷舊,百轉(zhuǎn)千回弄到他的電話(huà),自報(bào)家門(mén),學(xué)名、乳名,甚至綽號(hào)都報(bào)了,他仍想不起我是誰(shuí),直到提起那個(gè)工廠。然后就是見(jiàn)面,互相請(qǐng)吃飯。我請(qǐng)他,他對(duì)我?guī)サ呐笥驯葘?duì)我更熱絡(luò);他請(qǐng)我,我感覺(jué)與他的朋友交流更放松。唯獨(dú)我倆,雖并肩坐著,卻拘謹(jǐn)、尷尬,找不回當(dāng)年的感覺(jué)。
后來(lái)就沒(méi)再見(jiàn),只是成了時(shí)髦的“微信好友”。再后來(lái),他可能改了微信名,我沒(méi)及時(shí)備注,就又找不到他了(多半是提不起查找的興致)。但少年的他、少年的友誼,每每回想,既親切,又感動(dòng),而在空間重逢的他,與時(shí)間里的他,就仿佛不是同一個(gè)人。
失去的朋友,住在不同的時(shí)間段里,如同空間的朋友,住在不同的城市或小區(qū)。而時(shí)間優(yōu)于空間,抵達(dá)空間要跋山涉水,抵達(dá)時(shí)間卻是跳躍性的,來(lái)去自由,只需閉目神游。
(編輯 吹優(yōu)/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