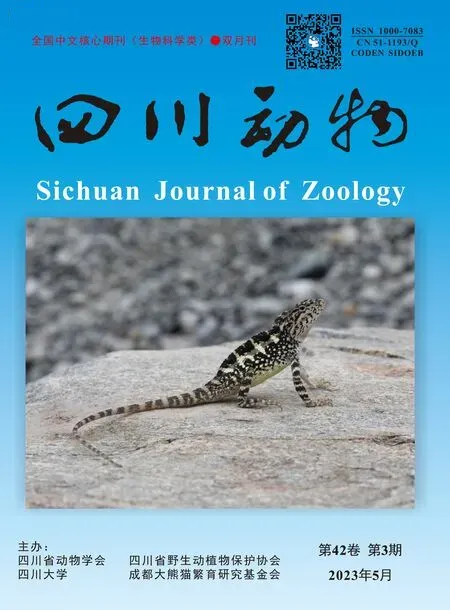金沙江上游2 種近緣龍蜥物種逃逸行為比較研究
李凌,向以華,劉帆,文宇浩,郭鵬,董丙君,吳亞勇*
(1.沈陽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沈陽 110034;2.宜賓學院農林與食品工程學部,四川 宜賓 644000)
逃逸行為是動物對周圍環境現存和潛在捕食風險的一種行為反應(Dimond & Lazarus,1974)。通過逃逸可有效規避被捕食風險,增加自身和后代的適合度(Treves,2000;Bednekoff,2001;Beauchamp,2014)。但逃逸是一種高耗能活動,包括奔跑(或飛行)過程本身的耗能及覓食時間的減少導致個體能量獲取的減少(Dowling & Bonier,2018),因此,動物需根據捕食風險,對逃逸行為策略進行權衡,只有當捕食壓力增大時,才可能選擇逃逸(Childress & Lung,2003;車燁,李忠秋,2014)。為降低逃逸成本,動物也可能通過信號展示的方式警示捕食者,如一些蜥蜴物種面對捕食者時的俯臥撐或抬腿等動作,可達到降低捕食風險的目的(Leal,1999;Fontet al.,2012)。動物一旦采取逃逸策略,通常也會權衡捕食風險和逃逸成本,從而優化逃逸距離,以便在躲避被捕食風險和保持能量之間做出權衡(Ydenberg & Dill,1986;Cooper &Frederick,2007;張凡夢等,2021)。當前,國內外關于動物逃逸行為的研究多集中于鳥類和獸類,而對其他類群的關注較少,特別是移動能力較弱的類群(如蛇、蜥蜴等)。因此,開展動物逃逸行為研究可有效揭示動物反捕食策略,并評估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的影響程度,這對瀕危物種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車燁,李忠秋,2014;汪開寶等,2018)。
動物的逃逸行為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Vanhooydoncket al.,2007)、種群大小(Liet al.,2009)、年齡(Liet al.,2013)、捕食風險(Xuet al.,2013)和季節(Muposhiet al.,2016)等。雌雄兩性由于生理周期、身體條件和繁殖角色的差異,逃逸行為常主要表現為3 種模式:(1)雄性偏好采取高風險行為,即雄性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顯著短于雌性,如北美馴鹿Rangifer tarandus(Stankowich,2008)、雄性赭紅尾鴝Phoenicurus ochruros(Kalbet al.,2019)和麻雀Passer montanus(García-Arroyo & MacGregor-Fors,2020)等,可能是雄性通常比雌性膽量更大,身體更強壯,逃逸能力(速度、耐力等)更強,成功逃逸概率更大,這種趨勢在交配季更為明顯;(2)雌性偏好采取高風險行為,即雌性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顯著短于雄性,如澳洲南部石龍子Eulamprus tympanum(Schwarzkopf& Shine,1992)和扁石蜥Platysaurus intermedius wilhelmi(Lailvauxet al.,2003)等,可能是雌性在繁殖活動(如孵化、育幼等)中投入更多,逃逸代價更大,這種趨勢在懷孕個體中更為顯著;(3)雌雄逃逸風險程度差異不顯著,即雌雄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無顯著差異,如棱鱗隱耳鬣蜥Holbrookia propinqua(Cooper,2003)、普通壁蜥Podarcis muralis(Fontet al.,2012)等,可能是雌性在自然狀態下體色普遍更暗淡,環境隱秘性更強,被捕食者發現的概率更小,因此允許捕食者接近(Vanhooydoncket al.,2007)。此外,由于遺傳、表型的差異性,同一類群近緣物種間的逃逸行為也可能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如白腰雪雀Montifringilla taczanowskii的驚飛距離顯著大于棕頸雪雀M.ruficollis,這與2 個物種的體型差異有關(張賀等,2016)。M?ller 和Erritz?e(2010)發現,體型越大的物種常具有更大的驚飛距離;但Smith和Lemos-Espinal(2005)研究了生存于墨西哥的4 種角蜥Phrynosomatid 的逃逸行為,發現2 種近緣刺蜥(Sceloporus gadoviae和S.anahuacus)的逃逸行為具有較大的相似性。整體來看,關于雌雄兩性之間和近緣物種之間的逃逸行為的比較研究還需深入。
分布于我國橫斷山區的巴塘龍蜥Diploderma batangense和麗喉龍蜥D.formosgulae為探究近緣物種逃逸行為的種內和種間差異提供了很好的模型。這2種龍蜥為近年新描述物種,表型及遺傳差異較小,為典型的近緣物種(李操等,2001;Wanget al.,2021)。野外觀察發現,2 個物種頻繁使用動作信號(點頭、俯臥撐和擺尾)進行求偶、領地守衛等社會交流活動,但是否具有警示捕食者的功能還不明確。前期調查顯示,2 種龍蜥均棲息于金沙江上游的干熱河谷灌叢生境,分布區均極為狹小且緊密相連,屬典型的狹域性物種和鄰域分布物種(圖1)。金沙江上游水電站、公路設施的大量修建已嚴重威脅到這2個物種賴以生存的棲息地,其生存狀態受到極大挑戰,種群數量呈下降趨勢,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農業農村部,2021)中,巴塘龍蜥已被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因此,開展橫斷山區龍蜥物種逃逸行為研究,可有效評估其抗干擾能力,為龍蜥的保護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據。本研究擬解決以下科學問題:(1)2 種龍蜥的逃逸行為模式是怎樣的?(2)2 種龍蜥的逃逸行為是否存在種內和種間差異?(3)2 種龍蜥社會交流過程中頻繁使用的動作信號,是否具有警示捕食者的功能?

圖1 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的分布區域、研究位點及形態Fig.1 Distribution,study site and morphology of Diploderma batangense and D.formosgulae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研究位點位于金沙江上游(圖1),其中,巴塘龍蜥分布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蘇哇龍鄉(99.059 116°E,29.461 718°N,海拔2 412 m),麗喉龍蜥分布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羊拉鄉(99.119 812°E,28.954 233°N,海拔2 552 m)。研究位點均為2 種龍蜥的典型分布區,生境破壞較小,種群密度較大;屬典型干熱河谷稀疏灌叢草叢生境,裸巖較多;氣候炎熱少雨,年均溫20~23 ℃,年均降水量600~800 mm;優勢植物為岷谷木藍Indigofera lenticellata、兩頭毛Incarvillea arguta、戟葉酸模Rumex hastatusy和白刺花Sophora davidii等。
1.2 逃逸行為量化
以人模擬天敵勻速靠近目標蜥蜴,測量其在面臨捕食風險時的行為反應,量化2種龍蜥的逃逸行為(Qiet al.,2014;Donihueet al.,2021)。實驗由2 名測試者共同完成:當發現蜥蜴個體時,一人迅速架設攝像機(SONY HDR-PJ670;上海)聚焦目標蜥蜴,持續追蹤記錄其后續行為;另一人在距目標蜥蜴約15 m 處以0.5 m·s-1勻速緩慢靠近,當目標蜥蜴開始逃逸(至少移動0.1 m)時停止前進,并迅速用標記物1(白色塑料瓶蓋)記錄測試者當前位置(位置1);待逃逸至避難所后,用標記物2(紅色塑料瓶蓋)和標記物3(黑色塑料瓶蓋)分別標記逃逸初始位置(位置2)和逃逸停止位置(位置3)。用卷尺測量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精度0.01 m)。逃逸起始距離定義為蜥蜴開始逃跑時,捕食者(測試者)距離目標蜥蜴逃逸初始位置之間的直線距離,即位置1 和位置2 的直線距離;逃逸距離定義為蜥蜴逃逸初始位置與逃逸停止位置之間的距離,即位置2和位置3的直線距離(圖2)。

圖2 龍蜥逃逸行為測試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measuring the escape behavior of mountain dragon lizards
一般而言,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越短,表明個體采取風險行為的偏好性更強。為降低“捕食者”個體差異導致的蜥蜴行為偏差,所有“捕食者”均由同一測試者完成,且身穿黑色服裝。為避免蜥蜴重復測量,各實驗個體之間距離至少相距100 m。測試完成后,采用釣竿制作的套索工具捕獲目標蜥蜴,測量相關形態數據。形態指標測量完成后均放歸至原捕捉位點。野外工作時間為2020 年8 月 下 旬 至9 月上旬每天09∶30—12∶00,即龍蜥活動的高峰期采集數據。所有數據采集對象均為成體。
野外工作完成后通過視頻回放查看目標蜥蜴在面臨捕食壓力時的行為,量化目標蜥蜴的行為類型(信號展示、靜止觀察捕食者、逃逸等)和順序,并記錄最終是否使用避難所(洞穴或灌叢)。
1.3 形態測量
依據體色(雄性背部顏色鮮艷,有較寬的黃色顏色條紋;雌性背部顏色偏暗淡,無黃色條紋或條紋較窄),以及半陰莖有無判斷個體性別。使用游標卡尺和電子秤分別測量頭體長(精度0.01 mm)和體重(精度0.01 g)。
1.4 數據分析
由于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均不滿足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檢驗,因此,在進行種內(雌雄兩性)和種間比較時均采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test)。采用一元線性回歸方法分別檢驗逃逸起始距離、逃逸距離和使用避難所比例與頭體長和體重之間的相關關系;采用卡方檢驗分析避難所使用比例的種內和種間的差異。統計值均以xˉ±SD 表示,顯著性水平設為0.05。所有數據統計分析均在SPSS 26.0進行。
2 研究結果
共獲取95只龍蜥成體的逃逸行為數據,其中,巴塘龍蜥46 只(雄性25 只,雌性21 只),麗喉龍蜥49只(雄性27只,雌性22只)。
2.1 逃逸行為的模式
2 種龍蜥雌雄個體在面臨捕食壓力時,均展現出探視、調整姿勢和逃逸3 種行為:當捕食者(人)靠近時,立即停止先前的行為(捕食、信號展示或曬背等),并通過探視的方式(轉頭注視捕食者)觀察捕食者的后續行為;若捕食者繼續接近,則靜止并調整姿勢(如四肢站立,身體調整至朝逃跑方向,并轉頭注視捕食者),繼續觀望捕食者;若捕食者進一步靠近,捕食壓力增大,則迅速逃離至其他地點,繼續觀望或進入灌叢(或洞穴)(圖3)。

圖3 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逃逸行為模式Fig.3 Escape behavior patterns of Diploderma batangense and D.formosgulae
2.2 逃逸行為的比較
麗喉龍蜥雄性個體的逃逸起始距離為222.93 cm±112.22 cm(n=27),雌性為197.64 cm±132.82 cm(n=22),兩 性 間 的 差 異 不 顯 著(Z=-0.784,P=0.433),逃逸起始距離與個體頭體長和體重無相關性;巴塘龍蜥雄性的逃逸起始距離為216.36 cm±79.66 cm(n=25),雌性為206.62 cm±96.66 cm(n=21),兩性間的差異也不顯著(Z=-0.067,P=0.544),逃逸起始距離與個體頭體長和體重無關(表1)。此外,2 種龍蜥的逃逸起始距離之間的差異均不顯著(雄性:Z=0.165,P=0.869;雌性:Z=-1.021,P=0.307;圖4)。

表1 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雌雄兩性逃逸行為與體型大小的關系Table 1 Relationship of escape behavior with individual body size for both sexes of Diploderma batangense and D.formosgulae

圖4 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逃逸行為的種內(兩性)和種間(同性別)比較Fig.4 Intraspecific (both sexes)and interspecific(same sex)comparisons of escape behavior of Diploderma batangense and D.formosgulae* P<0.05
雄性麗喉龍蜥的逃逸距離為71.48 cm±45.50 cm(n=27),顯著大于雌性44.73 cm±31.86 cm(n=22)(Z=-2.785,P=0.005),但兩性的逃逸距離與個體頭體長和體重均無關;雄性巴塘龍蜥的逃逸距離為91.24 cm±61.90 cm(n=25),雌性為74.95 cm±64.92 cm(n=21),兩性間差異不顯著(Z=-1.346,P=0.178);兩性的逃逸距離也與個體頭體長和體重無關(表1)。2 種龍蜥雌雄個體的逃逸距離也均未表現出差異性(雄性:Z=-1.035,P=0.301;雌性:Z=-1.908,P=0.056;圖4)。
當捕食風險增大時,2 種龍蜥所有個體均會逃逸至新地點。麗喉龍蜥48%(13/27)的雄性個體、50%(11/22)的雌性個體,巴塘龍蜥56%(14/25)的雄性個體、52%(11/21)的雌性個體會直接進入避難所(洞穴或灌叢中),而其余個體則會靜止在新地點,繼續觀望。2 種龍蜥雌雄兩性使用避難所的傾向與個體頭體長和體重無關(表1)。2種龍蜥使用避難所的比例未表現出顯著差異性(麗喉龍蜥:χ2=0.001,P=0.979;巴塘龍蜥:χ2=0.017,P=0.897);2 個物種雌雄兩性使用避難所的比例亦未表現出顯著差異性(雌性:χ2=0.024,P=0.876;雄性:χ2=0.000,P=0.991;圖4)。
2.3 動作信號與反捕食
在面臨捕食壓力時,2 種龍蜥雌雄個體均未展示出點頭、俯臥撐和擺尾等動作,表明在社會交流過程中使用的動作信號不具有警示捕食者的功能。
3 討論
3.1 龍蜥逃逸行為模式
面臨危險時,動物成功逃逸可有效降低被捕食風險,顯著提升自身適合度(Beauchamp,2001)。逃逸活動主要包括探查、環視、探聽和逃逸等過程(車燁,李忠秋,2014)。由于逃逸是一個耗能的過程,只有當被捕食壓力足夠大時,動物才會選擇逃逸,以保證自身安全。本研究發現金沙江上游2種近緣龍蜥物種的逃逸行為與其他動物的逃逸行為模式相似性較高:當發現捕食者(人)時,龍蜥并不會選擇直接逃逸,而是采取觀望的方式關注捕食者的后續行為,并調整自身姿態;當捕食壓力逐步增大時,才會選擇逃逸至其他安全地點。這種逃逸行為模式是長期進化的結果,具有重要的適應性意義:一方面可有效規避捕食者的捕殺風險,提高自身和種群的存活率;另一方面,也可有效節省能量,減少非必要的逃逸耗能(Dial,1986;Cooper,2001)。
3.2 龍蜥逃逸行為的種內和種間差異
雌雄兩性由于生理、表型和繁殖角色的差異,逃逸行為常表現出差異性。就蜥蜴類群而言,雄性個體因具有更大的體型和更高的雄性激素水平,膽量普遍更大、逃逸能力更強,面臨捕食危險時,通常會采取更具有風險性的行為,即更短的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Lailvauxet al.,2003;Nobleet al.,2014)。但本研究未檢測到巴塘龍蜥雌雄兩性逃逸行為的差異;雄性麗喉龍蜥具有更長的逃逸距離,但逃逸起始距離和使用避難所比例也未表現出兩性差異。2 種龍蜥雌雄兩性逃逸行為的差異不顯著,一方面可能是雌雄兩性經歷了相似的捕食者驅動的選擇壓力,雄性個體雖然均具有更大的體型,但并未檢測到雌雄兩性的逃逸距離、逃逸起始距離和避難所使用比例與個體體型大小的相關性,表明體型并不是影響兩性逃逸行為的因素,這與早期青海沙蜥Phrynocephalus vlangalii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Qiet al.,2014)。另一方面,也可能與雌雄兩性的繁殖狀態有關,8 月下旬到9月上旬為雌性產卵季,雌性個體具有較高的雌性激素水平,面對捕食者時,膽量更大,可能會采取風險行為,以降低因逃逸帶來的能量損耗,因此,具有較短的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該推測已在部分蜥蜴物種中得到證實,如懷孕的雌性澳洲南部石龍子面對捕食者時比雄性和未懷孕的雌性個體膽量更大,逃逸起始距離和逃逸距離更短(Schwarzkopf & Shine,1992);Cooper(2009)研究條紋高原蜥Sceloporus virgatus的逃逸行為也發現,在面對捕食壓力時,有卵泡或懷孕的個體會顯著縮短其逃逸起始距離。本研究未測量龍蜥交配季的逃逸行為,無法比較不同繁殖狀態龍蜥個體逃逸行為的差異,后續將拓展補充相關研究。
近緣物種因選擇壓力的差異,往往會在形態、行為、生境選擇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Johnson & Wade,2010;Gabelaiaet al.,2018)。青藏高原同域分布的白腰雪雀、棕背雪雀M.blanfordi和棕頸雪雀的體型大小和逃逸行為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Geet al.,2011);分布于智利的花環樹鬣蜥Liolaemus lemniscatus和棕樹鬣蜥L.fuscus雖頭體長未表現出差異性,但逃逸行為策略卻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Jaksi? & Nú?ez,1979)。近緣物種的逃逸行為差異往往與體型大小有關,特別是鳥類(McLeodet al.,2013,張賀等,2016,楊愛芳等,2021),但在一些蜥蜴類群中未得到支持(Bulova,1994;Smith & Lemos-Espinal,2005)。本研究選擇了體型大小有一定差異的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作為研究對象,從種間層面比較了2個近緣物種的逃逸行為,但未檢測到逃逸行為的種間差異,這與Labra 和Leonard(1999)對3 種近緣樹鬣蜥的逃逸行為比較研究的結果一致。此外,物種的反捕食策略往往是長期適應性進化的結果,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均棲息于金沙江上游的干熱河谷灌叢生境,屬鄰域分布物種,環境梯度變異小,且棲息生境中天敵及食物資源也具有較大相似性,2 個物種面臨相似的選擇壓力,因此,推測2 個物種的反捕食策略(逃逸行為等)可能較為相似,該假說在安樂蜥Anolis cristatellus(Cooper,2010)和鳥類(T?tteet al.,2020)中也獲得了證實。
3.3 動作信號與反捕食功能
蜥蜴類物種頻繁使用的動態視覺信號(肢體動作信號)具有警示捕食者的功能,可有效降低因逃逸活動帶來的能量消耗,如安樂蜥的俯臥撐動作(Leal,1999)、普通壁蜥的擺腿動作(Fontet al.,2012)。本研究也關注了巴塘龍蜥和麗喉龍蜥求偶和領地守衛活動中頻繁使用的肢體動作(點頭和俯臥撐),發現這2 種動作并未出現在警戒活動中,可能并不具有反捕食的警示功能,僅僅是一種社交信號,這與青海沙蜥的研究結果相似,擺尾和甩尾動作雖然在社交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但與其反捕食策略無關(Qiet al.,2014)。
3.4 后續研究展望
龍蜥是橫斷山區干熱河谷灌叢區域的代表性物種,對于維持區域生態系統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隨著該區域人類活動的不斷加劇,各種道路、水利以及生活設施大量修建已較大程度影響了本區域龍蜥物種的繁衍棲息。后續將持續關注其逃逸行為和抗干擾能力,從單一物種比較(季節、年齡、干擾強度等)到多物種比較,探討在當前人類活動逐漸增強的背景下對環境干擾的適應能力,為橫斷山區龍蜥物種乃至其他類群動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