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新作《未婚妻》:追憶瑞昌似水年華
俞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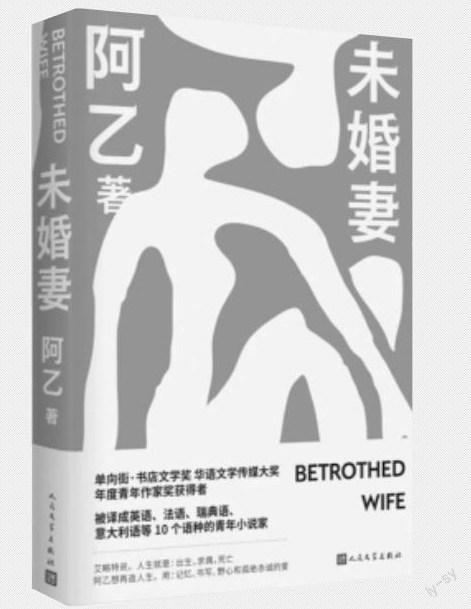
近日,青年小說家阿乙的最新長篇小說《未婚妻》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書中,中國式婚戀倫理尤為引人矚目。
《未婚妻》既是阿乙風格的延續,也包含著他更成熟的自我認知,有讀者稱“這是一部‘追憶瑞昌似水年華”。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高度評價《未婚妻》與讀者、與時代、與自我、與命運對話的特征,說這是一部帶有奧德修斯般反抗命運的英雄氣質和史詩氣質的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臧永清社長形容這種想象是“拿著放大鏡一般地在關注我們共同經歷的時代”。
從我出發,丈量世界
《未婚妻》從記憶入手,捕捉愛、醉、病、生與死的虛無,精微摹寫縣鄉中國波瀾壯闊的流動變遷。小說中,“我”作為小鎮警察,在一次公干時對一個女孩一見鐘情。然而,情感這種“形而上”的波動僅僅一剎那,接下來是情感變成婚姻的、無休無止的“形而下”。于是,縣城版的門當戶對被提上日程。“未婚”,這確定的又尚無結局的過渡狀態,讓阿乙的小說獲得了無盡的空間。
家庭和家人,其實一直是阿乙成為作家的內在驅動力。尤其是生病之后,阿乙對血緣、基因,自己與父親的相同與不同有了更深的體悟。在《未婚妻》里,出現了短暫的父慈子孝,因為他們要共同面對天大的“婚姻”。阿乙用抽象和具體、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往返穿梭,通過一次莊重且刻骨銘心的愛的回望與反芻,實現了多重和解,他激活了有限的自己,打開了“我”作為一個兒子、未婚夫、準女婿、準成人、前途無量的縣城青年的多重身份。在瑞昌,他是舞臺中心的,是天之驕子,如果不是出走到大城市,他不會成為“外省青年”。他用現在的自己想象那個留在原地的自己,用幸存于現在的自己想象那個被毀滅在縣城的自己。
在李敬澤看來,《未婚妻》是“一個曾經出走家鄉、現在要回鄉的奧德修斯,對一個從未離開過家鄉的奧德修斯的書寫和想象。”這書寫和想象帶有普遍意義,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城鎮化進程,我們幾代人都成了這樣的奧德修斯,我們每個人都有無數個自己被留在家鄉、留在原地,那些自己是我們永恒的鄉愁,“自己找自己”的鄉愁。
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涉及了一個同樣的問題——關于一個從縣城出發的“奧德修斯”如何去到廣大的世界中。現在阿乙把這個書寫的方向倒轉了過來。《未婚妻》實際上書寫了一個時代、幾代人的精神秘史。
激活記憶,再造人生
對成熟作家而言,閱讀一直是補充素材庫的重要途徑之一。阿乙對《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等經典著作的反復閱讀,都體現在《未婚妻》中,他甚至不惜為此加了很多注釋——讓一部小說像一部學術著作一樣,言必有據。
阿乙研究專家、文學博士徐兆正認為,阿乙在面對怪異的病和經驗被掏空的時候,用大量的經典閱讀提供的補給與療愈,緩和了寫作與經驗、重復與創新的緊張關系。他的閱讀書單當然不限于普魯斯特和喬伊斯,也不限于博爾赫斯、蘭波、福樓拜、托爾斯泰……
書中,阿乙宛如一個“時空穿越者”,通過對一段未完成的婚姻的描寫,通過對曾經名為“艾國柱”的小鎮警察的追憶,開辟出豐盈、充沛的精神國度,以及廣闊無邊的小說空間。他用記憶激活記憶、現實激活記憶、閱讀激活記憶,重現一個人業已失去的青春和安穩。他既面向經典,又再造經典。他用記憶、書寫、野心和孤絕赤誠的愛,酣暢淋漓地再造了一次人生。
“既然從未得到,又談何失去?”《未婚妻》里,有可擁抱的溫暖,也有無結局的虛無;它世俗、狡黠,也散逸、妖冶……這美好的、過渡的、曖昧的、永恒的“未婚狀態”,不正是像極了人體驗活著的全過程?生命,一如我們與造物主的美好約定,在結局到來之前,我們一直都在“未婚”的狀態,它是半浪漫半世俗的,也是半真實半虛幻的,更是半確定半懸而未決的……
阿乙說,《未婚妻》的續章《未婚夫》也在創作打磨中。真實經歷中,他的確有過一次縣城婚約,因為他的出走,這婚約成了人生遺憾。在小說中,他想讓“破鏡重圓”,讓這鏡子成為照亮自己完整人生的鏡子。“未婚”,這永恒的中間態,也正是包蘊著所有可能性的中間態,而阿乙“未完成時”的創作,也包含著無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