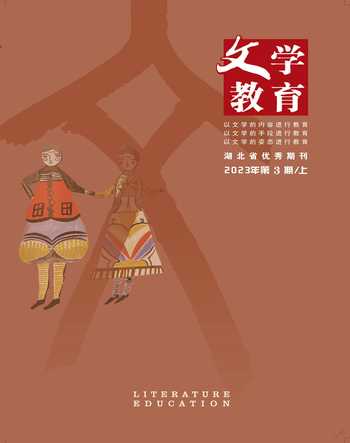李佩甫《生命冊》中離鄉者生存的多重困境
傅文琬
內容摘要:小說通過描述50年代以來的時代變遷,講述了在時代浪潮中知識分子在多種外部因素影響下的艱難探索過程。沉重的人情債讓吳志鵬無力承擔,拼命逃離家鄉;城市中的種種誘惑不斷擴充著人們的欲望,最終跌進了的無底的深淵;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寫出了在城市化進程不斷進化的過程中人們在其中產生的精神困境。李佩甫用現實主義的筆觸刻畫著人們精神狀態的異化過程,對當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進行了批判和反思。
關鍵詞:困境 李佩甫 《生命冊》 離鄉者
鄉村多占據著李佩甫創作的主題,作品中或直接描述在鄉村生活的人們,或描述在鄉村基層組織中的權力關系,或描寫從鄉村走向城市的這一批人精神世界的掙扎。當然,這與他長期的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他用一個土生土長的平原人的視角,講述廣袤平原大地上的花草樹木和風俗人情,進而揭示人們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生命冊》就講述了年輕人逃離家鄉,在城市當中生活的經歷以及精神世界的迷失與堅守,作為平原三部曲的收山之作,出版之后便斬獲多個獎項。這部作品是李佩甫“把幾十年對于平原的認識都砸進去”了[1],同時他也強調:“我這部長篇是用第一人稱獨白的方式來寫50年的心靈史,或者50年的記憶。用一個人的內心獨白寫他50年的心靈史、成長史。”[2]小說以吳志鵬的視角講述了一個知識分子背負著鄉土記憶漂泊的故事,對家鄉的逃離和對故鄉的回憶,將“老姑父”“梁五方”“蟲嫂”“杜秋月”“駱駝”等鮮明的人物形象串聯在了一起。
小說以50年代以來的時代變遷為背景,講述了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異,以及在時代浪潮中知識分子在多種外部因素影響下的艱難探索過程。李佩甫對于鄉村的景物和風土人情采用了大量的描寫,鄉村與城市相互交織,以樹狀結構書寫位于大平原上無梁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構成了他獨特的平原城鄉敘事。小說以“冊”命名,匯編了大小十幾個人物,選取不同人物命運的橫切面展示不同人物悲慘、苦難的人生命運,作者在敘述眾人不同的生存困境的同時也在探索救贖之路,表達了自己的人文關懷。巨大的人情交際網絡壓的吳志鵬難以喘氣,拼命逃離;欲望的不斷滿足讓人們迷失在城市文明的進程中;在城市和鄉村的轉化過程中,人們面臨著精神困境與生存困境的雙重挑戰。
一.難堪其重的人情之累
家庭是人情往來最初的誕生地,在生存、繁衍的加持下,家族網絡越來越龐大,人情的覆蓋面也隨之擴展,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則。在同一地緣范圍上的農村更容易產生人情上的往來,人們在生活、生產以及在交往活動中產生虧欠和償付的日常性人情較為多見。當個體處于陌生的環境當中需要尋求幫助時,首先會想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和同鄉,在人際關系網絡的交匯下產生所謂的熟人社會,通過這種人情往來的交際方式,我們的生活在有熟人的幫忙下似乎更加順利。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人情的存在充當著潤滑劑的成分,使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聯系的紐帶,日常生活也更加充實。鄰里、朋友、陌生人之間因為人情展開互助、合作、轉借等多種交往方式。人情關系加強了人們之間的溝通和聯系,雙方在互不損害對方利益的基礎下進行互助行為,促進了互助雙方之間的情感交流,對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關系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人情來往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占據著重要席位。費孝通說:“如果雙方相互不欠人情,也就無需要往來了。”[3]在經濟發展如此迅速的今天,往常通過人情交往來增進彼此之間感情的交往方式逐漸沾染上了利益的氣息,純粹的情感交流方式的模式被打破,到如今發展成為人們精明的計較利益得失的工具。人們談之“人情”就像是一種枷鎖,小說中的主人公“吳志鵬”也因這種人情的枷鎖被牢牢套住,讓他難承其重。
吳志鵬的母親在生下他之后就撒手人寰,父親也因煤礦瓦斯爆炸被埋在了礦井之下,就這樣,作為孤兒的吳志鵬由老姑父牽頭成為了無梁村人共同的孩子。他喝的奶是老姑父帶著他去每家的女人處尋來的;在他每次闖禍之后,也是由老姑父平息眾人的怒火的。吳志鵬在無梁村村民的眼中,就是一種“無名稅”式的存在,他吃的飯是一家家派的,而后在他上學期間,是每家出麥子或者玉米供養起來的,這種狀態持續了二十年。全村人把吳志鵬視為禍害,在推薦上大學時提議老姑父依靠以前的戰友給吳志鵬分到一個名額。可以說,無梁村的每個人都對他有著養育之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一種血脈上的聯系,也是一種地緣上的聯系,“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3]故鄉是人們在外最容易與陌生人建立聯系的橋梁,俗語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同一個身世出處拉進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吳志鵬從出生起就與無梁村的眾人建立了一種親緣上的聯系,“在這些親緣關系之間必然會產生情感交流或人情交往的日常生活現象”。[4]
在吳志鵬剛踏進城市的土地時,因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而無處可去,思來想去終于想到了“七不沾八不連”的同鄉吳有才。這也是一種人情關系的動用,“關系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人們是最離不開關系的”[5],吳志鵬就在寒冷的冬季憑著同鄉之間的關系找到了暫得以休憩的容身之所,而他同樣也在極其疲憊的狀態下與吳有才嘮著家鄉的體己話。如果說這時候是主人公在享受“關系”帶來的便利,這種因人情帶給他的束縛則是由一通電話開始的。第一個電話是國勝家女人的,因侄子考大學想讓吳志鵬幫忙錄取,他跑了十八趟招生辦公室,用他在省城靠微笑建立起來的脆弱關系網去打聽,最后事情也因這薄得像紙一樣的人情無疾而終;第二個電話是保祥家女人因丈夫農用車撞人扣在公安局,讓吳志鵬打個電話把他放出來的。而后這種來自無梁村的電話越來越多,難度也越來越大。吳志鵬努力的想把自己這株來自農村的種子移栽進城市,他隱藏著“狼”的野心,在準備許久的蟄伏下一步步走向講臺,依靠自己淵博的學識獲得了學生的認可。在原有的人生軌跡下,他會憑借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著名的學者,在本校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侶,成功的把自己打造成一顆城市的種子。而由于這不斷響起的電話,打破了吳志鵬原有的人生軌跡。為了幫鄉親的忙,吳志鵬四處借錢,到后來同事們見他就躲,生怕吳志鵬找他們借錢,這讓吳志鵬在同事面前逐漸抬不起頭來,對他照顧有加,給他爭取講師資格的老魏也對他失望,一句“農民習氣”將吳志鵬打回了原型,而他精心為自己改造成城市人的包裝也就此撕開,吳志鵬原本擁有大好前途的生活被電話攪得一團糟,讓其心力憔悴。終于在他接起幾百個電話之后,他的人情在一次次借錢當中,一次次托關系當中消耗殆盡,讓吳志鵬不堪重負。無梁村儼然成了沉重“包袱”,讓他產生了割斷這種關系的想法。但在吳志鵬漫長的一生中,他始終沒有掙脫掉這種人情的束縛,梁五方每次找他時手里都握著一張白條兒,兩張幫杜老師跑事的,三張幫劉玉翠打離婚官司的,七張推銷春才豆制品的,每一張“見字如面”白條兒的背后,都是吳志鵬背后的三千口無梁村人。
作為無梁村全村的孩子,吳志鵬無法拒絕她們,原因首先在于吳志鵬與老姑父之間毫無血緣的親情關系,老姑父與吳志鵬的聯系是最緊密的。從血緣關系上來講,老姑父并不是他的親生父親,但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老姑父占據了他重要的人生席位,吳志鵬喝的奶水是老姑父抱著他一家一家尋來的,上大學的名額是老姑父動用戰友情爭取來的。當老姑父張口時,多年的養育之恩使得吳志鵬無法拒絕,以至在后來的歲月中,無數張寫著老姑父字跡的“見字如面”的白條束縛了吳志鵬的一生。其次是這是一種地緣上的倫理關系,“一個人生在倫理社會中,其各種倫理關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圍了他,要他負起無盡的義務,至死方休,擺脫不得。”[6]主人公吳志鵬在村里建立的這種倫理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他是無梁村每個人的兒子,這就意味著要承擔起更多的義務,他是無梁村的一顆救命稻草,一旦有了困難,村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吳志鵬。當然這也與吳志鵬自身有關,他是一個得懂感恩的人,吳志鵬意識到無梁村人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賦予了他恩惠,從而在內心深處產生回饋的心理活動,并采取現實行動給予幫助,當他試圖做一回“狡猾”的狐貍要擺脫電話時,家鄉的回憶讓他產生了愧疚之情。在道德和情感的雙重作用下,就注定了他無法隔斷與無梁村的聯系,也無法擺脫這種人情之累。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人們處在社會的關系網中,必然離不開人情的動用,在吳志鵬上大學時,老姑父帶著禮品找到了在部隊時的戰友老胡將名額爭取了過來;厚樸堂藥業公司的上市“駱駝”找了很多關系去打通,以及后來生意場上的交際都涉及著人情往來的成分,但與吳志鵬的親緣關系的人情和老姑父的戰友情不同的是,駱駝動用的人情往來涉及到了金錢,是一種純粹的利益上的往來,這也就意味著它更為脆弱。經濟與科技的不斷發展,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已經逐漸演變為“生人社會”,人情的交際往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人們的感情交流,對社會穩定有著良好的影響;一旦這種人情消耗過度或者異化,就會帶來不良影響,例如因人情關系異化導致的腐敗現象。[8]
二.難以擺脫的欲望之困
“人類徹頭徹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無數需求的凝集,人類就這樣帶著這些欲求,沒有借助并且在困窮缺乏以及對于一切事物都滿懷不安的情形下,在這個世界生存上。”[9]叔本華認為,人的一生不斷在欲望和欲望所產生的成就之間不斷流轉,當現階段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就會產生倦怠、空虛、無聊、乏味的情緒,此時就需要新的欲求出現來重新調動個體生存的積極性。人類從呱呱墜地開始,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各種各樣的需求,最緊要的首先是一種生存欲望。其次,在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人們將會開始貪戀更多的需求,這些欲望大致可分為物質上的欲望和精神上的欲望,“不論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其最大特性是永遠追求滿足”[10],有人追求財富,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愛情,從根本上來講,都是為了滿足欲望。欲望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適度的欲望會激發人的活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尋求欲望的滿足過多,過重,就會產生不良影響,欲望的尋求者會在滿足中感受到無窮的痛苦,對社會秩序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人首先要保證自己生命的存在,才能逐步在此基礎上產生更多的需求,所以保證其最基本生存的生活欲望是最緊要的。對于吳志鵬來講,“錢”是他最重要的欲望,它保證了吳志鵬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他進城后作為一個大學講師,穩定的工作帶給了他穩定的收入來源,那他是什么時候感受到自己的貧窮了呢?第一次是在認識梅村后的第八天,成套的衣服,精致的皮箱,少見的絲綿被,各種各樣的在八十年代稱的上是奢侈品的物件沖擊著一個每個月只拿五十二塊錢助教的內心;第二次是找赫主任送禮,煙酒的寒酸;第三次是拿八百塊錢去公安局領蔡葦香,此時吳志鵬一個月七十九塊錢,他已經借錢借到同事們見到他都躲著走了;第四次是坤生媳婦難產生下的一雙患有腦癱的雙胞胎孩子,兩萬金額的治療費再一次沖擊著他。吳志鵬在一次次人情債中體會到自己的寒酸,感受到了因金錢帶來的自卑和窘迫。在金錢的驅使下,吳志鵬辭掉了他的工作,跟隨駱駝到北京做了一名“槍手”,同行四人,想要出古典文化的書籍名利雙收,但是,在書商的誘騙和金錢的枷鎖下,四人從“古典文化”的生產者淪為了“垃圾文化”的生產者,金錢利益的驅使帶領他們一步步走向了泥潭。誠然,這筆當“槍手”賺來的錢成為了吳志鵬和駱駝南下炒股的初始資金,在深圳和上海,他們倆靠著當時去蹭課學習的知識,在股市的浪潮里摸爬滾打,僅五年時間,吳志鵬就賺了四百二十八萬,駱駝比他賺的還要多。吳志鵬和駱駝對于金錢的需求有其合理化的成分存在,但是人的欲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當一個欲望達成之后,就會有新的欲望出現。就像駱駝和吳志鵬一樣,金錢的富裕讓他們感受到了高質量的生活品質,他們鉆進“錢眼”里了,心底的訴求更加旺盛。駱駝這個人物有著極為聰明的頭腦,對金錢有著異常靈敏的嗅覺,他們開起了公司,做起了老板,生意風生水起。“人是一種欲望的存在”[11],當欲望開始膨脹,人心也就開始迷失,吳志鵬感受到了駱駝的變化,在他的身上時不時會冒出“領袖意識”,他們收購工廠,造假包裝上市。此時對于金錢合理化的欲求開始變形,產生了畸形的欲望訴求,駱駝在金錢的誘惑下逐漸迷失自我,成為了金錢的奴隸,與吳志鵬漸行漸遠。這是一種因為金錢產生的利欲,“利欲慣性在生命力盲目的驅使下,會朝著非理性控制的方面發展,只要唯利心切,便會愈‘發展愈迅速,致為利欲膨脹。在膨脹的狀態下不可自拔,最后乃至無視規則,引來‘車毀人亡。”[11]這樣就可以解釋駱駝后期發生的一些變化以及他跳樓自殺造成悲劇結局的原因。
小說中對于人物在情感上的需求也不容忽視。首先是主人公吳志鵬,梅村是他心中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用吳志鵬的話來講,梅村是唯一讓他心痛,他唯一愛過的女人,是他心中白月光。梅村帶給了吳志鵬母親一般的溫暖,主人公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人物形象是缺失的,成年后亟待尋求一種情感上的慰藉,可能正是梅村像母親一樣的懷抱,在吳志鵬的心里印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以至于在多年后,他沒有放棄尋找梅村的下落,帶著承諾和九十九朵阿西比亞玫瑰。反觀梅村,梅村有著悲慘的童年經歷,母親的改嫁經歷以及很壞的繼父給她留下了很大的陰影,但是她對于愛情依舊存在著理想主義色彩,就像日記中記載的那樣,“我本期望著找一個我愛的人,一個靠在他的肩膀上,能說一說知心話的人……”[5]梅村要找到一個情感契合的人來彌補童年陰影。她在一次一次的尋找中并沒有達成心理上的情感慰藉,吳志鵬依靠著自己的才學吸引著梅村,悲慘的童年經歷也讓她產生了同情心理,梅村對吳志鵬的愛情也在不知歸期的等待中消磨掉了。而后,一個詩人——苦水,他徒步黃河的志向,寫給梅村的一百首詩征服了梅村,但當她發現這些詩是他抄襲來的,梅村的幻想瞬間就被打破了。離婚后的梅村覺得追了她四年的徐延軍是愛她的,第二次的婚姻也僅僅維持了兩年,徐延軍每天像審犯人一樣審問著梅村,她覺得這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愛情。她又嫁給了一個畫家,畫家可以發現她身上的美,但她不知道的是畫家是對美有一種欲望,但這種欲望并不針對梅村一個人。梅村一生都在追尋,追尋一份純粹的愛情,但她始終沒有找到,最終變成了一個充滿怨氣的女人,而這怨氣就是梅村對生活的不滿和發泄。
情感的欲求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演變成性欲。弗洛伊德認為性是一種本能,是一種每個人生來就有的能力,在這種本能的驅使下,人類進行一系列的活動。性本能說是弗洛伊德主義的支柱和基石。[12]小說中有許多關于性的描寫,但大多數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畸形、病態的狀態,最典型的莫過于春才。在性本能的驅使下,性意識在十八歲的春才身上逐漸覺醒,“對現代社會來說,最特殊的倒不是性被指定必須存在于陰暗之中,而是人們在把他作為隱秘的同時,沒完沒了的去談論它。”[13]正是在村民的調笑嬉戲中,春才對于“性”有了初步的認識,最初的春才只是“紅紅臉而已”,后來就直接蹲下了。由于缺乏正確的引導,他將這種本能進行了壓抑,從而選擇了“偷窺”這種不正當的方式來疏解這種欲望,一方面在眾人的談笑中不斷產生好奇心理,一方面又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恥,最終在這種折磨下選擇了自我閹割的結束方式。
在利欲、情感需求、性欲的誘惑下,他們在滿足欲望的過程中逐漸了迷失了自我,成為了欲望的奴隸,困于欲望牢籠。“執行意志,滿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譽,都是欲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終不變的。”[14]欲望在人們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的刺激下,可以激發創造活力,但是需要“超我”的約束,在道德的范圍內嚴厲的審視來自“本我”的各種欲望。當下社會欲望高度活躍,人們在欲望的沖擊下不斷追尋著滿足,精神意志遭受著侵蝕,個人欲望的釋放,并不是為所欲為的,它需要理智的調節和控制,才能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不竭動力。
三.進退兩難的精神之苦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耕社會,華夏人民生于土地長于土地,因此在文學的敘事傳統上,自然離不開鄉土敘事。在鄉土敘事的背后是作家們在現代進程的誘惑中,靈魂上無處依托以及找不到精神家園的痛苦喚起了內心深處對于故鄉的懷念,暗含著濃濃的鄉愁。上個世紀20年代,魯迅的作品《故鄉》喚起了現代作家對故鄉的回憶,以農民疾苦作為主要內容,創作了很多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的文學作品。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城市的范圍圈逐漸擴大。鄉村和城市作為人類生存的空間,“在當代文明中代表著相互對立的兩極”[15]。兩個空間彼此交融又產生著摩擦,兩者之間的沖突逐漸進入大眾視野。城市相比于鄉村來說,擁有著更多的機遇和挑戰,這種情況也就造成了農村人口的流失。城市的繁榮吸引著無數人的向往,希冀能在時代浪潮的機遇中大展拳腳。作家們也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創作了許多關于城鄉的作品,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作為一個獨特角度走進了文學視野。李佩甫的創作中也突出了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文本中寫出了在城市化進程不斷進化的過程中人們在其中產生的精神困境。
在小說當中,愚昧落后的傳統文化造成的一種群體上的精神壓抑讓人無法忽略。長久的精神壓抑必然會產生情緒上的集中爆發,梁五方就是一個典型的受害者。當然傳統文化有其積極的一面的存在,九爺與梁五方之間是一種師徒間的傳承關系,多種民間技藝在傳承的接力下得以延續。憑借著這種技藝上的傳承,梁五方找到了生活的立足之本。他身懷絕技,憑著自己的本領在方圓幾十里打響了自己的名聲,但因此被視為“越師”,師傅九爺將其逐出師門,讓梁五方自立門戶。梁五方年輕氣盛,依靠著自己的本領愣是在水塘之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子。這座房子沒有依靠任何人幫忙,可以說全憑梁五方自己的努力將自己的日子過得風聲水起,這自然讓村里人產生了嫉妒心理,覺得他太“各色”了,引起了眾人的不快。而眾人的爆發隨著“運動”的到來集中式的噴發。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黑羊效應”,特指一群好人欺負一個好人的情況。陳俊欽在《黑羊效應》中將其分為三種角色:無助的黑羊,持刀的屠夫和冷漠的白羊。[16]梁五方是“黑羊”,他憑借自己的本領卻引來村里眾人的妒嫉,群眾便是“持刀的屠夫”,“二十四條”罪狀給了眾人一個發泄口,一窩蜂地沖上去將梁五方淹沒,人們或打或擰,或踢或捶,肆無忌憚地發泄著怒火,這些人群當中,大多數與梁五方并沒有什么仇恨,甚至并沒有什么交集,但是在庸常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積攢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怨氣,長期精神上的壓抑讓他們無處發泄。梁五方作為一個發泄口的契機恰巧出現,讓無梁村的人們“瘋狂”的毆打他,“瘋狂于單個人是某種稀奇事,但于群體、黨派、民眾和時代則是常規”[17]。吳志鵬和蔡國寅等人作為旁觀者的白羊,對眾人的毆打并沒有及時采取相應措施,甚至產生了快意。在特定的壞境下,人們的怨恨和惡意是可以傳染的,在個體獨立存在時,是可以保持正常的價值判斷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的,一旦放入群體之中,從眾心理會驅使他加入群體行動,短暫的喪失行為對錯的辨析。而梁五方也在這次群體事件爆發之后變成了一個無賴式的“上訪者”,與當初充滿活力的奮斗者形象截然不同。
吳志鵬是一個精神上的漂泊者形象,無梁村沉重的人情負擔給他的精神上帶來了沉重的苦難,于是他“逃離”家鄉,輾轉游走在各個城市之間,企圖擺脫自己“農村”人的身份,在城市中尋找精神的棲息地。“燈”的意象在文本中多次出現,在寒冷的雪夜,暖黃色的燈光一方面溫暖著吳志鵬漂泊著的心,一方面又在提醒著他農村人的身份。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城市人,吳志鵬不斷修正著自己,學習城里人走路,買一些仿名牌的衣服,開始大量的閱讀積累對付城里人的新詞,努力縮短鄉村人與城里人的差距,讓自己這顆“移栽”進城市的種子努力生根發芽。北漂地下室“槍手”的人生經歷也給他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折磨。駱駝是吳志鵬人生路上的貴人,一方面來講,身上具有領袖氣質的駱駝帶著吳志鵬一起走上了人生的巔峰時刻;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在物欲橫流的城市之中精神異化者的形象存在,在關鍵時刻給吳志鵬豎起了警示牌。城市中散落著的各種欲望吸引著無數從鄉下進城打拼的年輕人,金錢、權力、地位給他們帶來了精神上的滿足,而物極必反,欲望的無底洞逐漸將他們的精神扭曲,在不斷追求的過程中迷失自己,就如駱駝一樣,他的精神困境有一部分時他的身體所帶來的,精神上的扭曲讓他沉淪在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最后造成了悲劇的結局。吳志鵬在城市中不斷游走,尋找著精神的家園,多年之后,他擁有了金錢和地位,像極了一個土生土長的城里人,但在人生的進程中,無梁村的各種畫面勾起了他藏在內心深處的回憶。城市中的生存法則讓他在精神上產生了困惑,而他拼命想要逃離的家鄉卻在他精神即將扭曲的關鍵時刻將他拉回。駱駝的死讓他明白自己精神上的根始終都是自己的故鄉,此時他要將自己的精神回歸,等他再次踏進無梁村時,多年的變遷讓他產生了一種疏離感,精神上呈現無處可歸的局面。吳志鵬與無梁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地緣和情感的雙重作用下,注定了他無法割斷與無梁村之間的紐帶,而當他意識到故鄉始終是他精神的棲息地時,故鄉早已物是人非。就這樣,逃離不得,回歸無門,吳志鵬就此陷入了逃離與回歸的兩難境地。
長篇小說《生命冊》描繪了廣袤的平原大地,展現了中原的人情風貌,章節開頭以植物喻人,暗指人物悲慘的生活和悲劇的命運。在語言的表述上,大量獨屬于中原的方言詞展現出了濃厚的平原氣息;平實細膩的心理描寫,形象又生動的表達了人物復雜的心理活動。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李佩甫塑造了很多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老姑父”、杜秋月、梁五方、“駱駝”……每個人物都有鮮明的特色,但他們身上多少都有悲劇成分的存在,通過這些人物形象悲劇命運的書寫,表達了作者對于人性的審視和生命的思考。獨特的敘事結構讓故事更加立體,在城市與鄉村的交叉敘述中展現了人情帶來的沉重負擔,充斥著欲望的城市給人造成的生存困境以及城鄉文明的沖突給人造成的精神上的異化。
精神漂泊是現代人生存的普遍現象,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經濟水平的提升豐富著人們的物質世界,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而人們的精神世界卻相對匱乏。李佩甫從人情、欲望和精神等多重困境書寫現代人在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批判“駱駝”一類人的墮落和沉淪,另一方面通過敘述吳志鵬的人生軌跡表達了自己對普通人的關懷和救贖。李佩甫坦言這是一部自省書,他將自己的生活背景融入到了創作中,用自己獨特的鄉土敘事堅守著對鄉土精神的追尋。在當代社會發展如此迅速的今天,現代化的變革在相當程度上便利著我們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腐蝕著我們的精神狀態。李佩甫用現實主義的筆觸刻畫著人們精神狀態的異化過程,對當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進行批判和反思,警醒世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時常審視內心,打破束縛自己的重重枷鎖,進行自我救贖,擺脫精神上的兩難境地。作品對于生存困境的描寫和人們精神狀態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亞麗.《生命冊》:中原的故事就是中國的故事[N].中國青年報,2015-10-23(11)
[2]王波.李佩甫:貧窮才是萬惡之源[N].中國青年報,2012-4-17(10)
[3]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中華書局,2013
[4]楊威.中國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質及其現代轉換[J].求是學刊,2000(03):29-34
[5]李佩甫.生命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6]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185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8]何旭明.論人情關系與腐敗現象[J].社會科學,2000(11):19-23
[9](德)叔本華.叔本華說欲望與幸福[M].高適,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55
[10]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敘述:20世紀中國的文學敘事與文藝精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3
[11]趙詣.意識學:生命欲望意識文化與教育——自然主義生命觀[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42、22
[12]宋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62
[13]弗洛伊德.性學三論[M].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14]陳獨秀.人生真義[N].新青年,1918:4卷2號
[15](美)帕克:城市社會學,宋俊嶺譯[M].華夏出版社,1987:275
[16]陳俊欽.黑羊效應[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
[17]尼采.善惡的彼岸[M].趙千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22
(作者單位: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