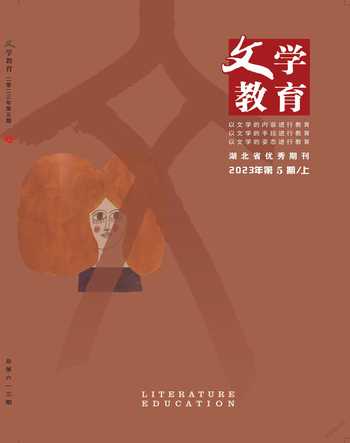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山鄉巨變》中女干部鄧秀梅形象探析
易舒悅
內容摘要:作為小說《山鄉巨變》中的主人公,鄧秀梅是一位帶著指導合作化運動任務而來到清溪鄉的女干部,并且在處理各類工作事務中,充分發揮其人格內部的雙重性別氣質。其中干部身份與性別氣質的互滲,使得鄧秀梅不僅實現了她的政治使命,又為“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建構出一種區別于一般干部的女干部形象。而這一“新形象”在被構造為合作化時期的政治想象和女性想象同時,其背后性別優勢的發揮也對當下女干部的性別與履職關系問題構成一種深刻的現實關照。
關鍵詞:《山鄉巨變》 鄧秀梅 農業合作社 農村基層女干部 “十七年”文學
在對新中國農業改造的講述過程中,“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塑造了諸多人物類型。其中,“農村女干部”多以正面的具備較高素養的基層干部形象受到學者的關注。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女干部形象研究極少與以男性為主的干部群體進行區別,而實際上,女性干部與男性干部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往往與不可回避的性別連結在一起。在人格上她們往往超越了一般的女性氣質,表現出雙性氣質的綜合,這一切又與其干部身份與政治使命直接地關聯著。因此,對“女干部”的性別氣質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存在潛在的意義。周立波在小說《山鄉巨變》中圍繞清溪鄉農業合作化過程,塑造出了許多不同階級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傳達出特定時代背景中的政治想象與女性想象,其中女干部鄧秀梅在性別氣質與干部身份上展現出獨特之處。本文嘗試以《山鄉巨變》中鄧秀梅這一女干部形象為切入點,結合現代性別理論,深入文本細節,對其干部身份與性別氣質的展現、“干部”成長的階段化歷程進行討論。并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知識與相關史料,對照兩種不同的歷史語境,闡述“鄧秀梅”這一女干部形象與改造時期的合作化政策和實踐的密切聯系,以及社會性別優勢的發揮可能對新時代女干部履職的有益啟示。
一.“鄧秀梅”的干部身份與性別氣質
一般地,性別氣質包括男性與女性氣質兩類。女性氣質泛指女性共有的心理特征與性格特質,如細心敏感、柔順感性等,而男性氣質與以其相反,表現為勇敢堅強、進取理性等。這種二元對立的氣質觀點長期存在于各種社會環境中,并被人們無意識地接受。而女性主義批評家貝蒂·弗里丹、弗吉尼亞·伍爾夫、凱特·米利特等人都曾對性別氣質展開討論,并提出“雙性同體”思想。弗里丹在《女性的奧秘》中主張男人和女人應該朝著“雌雄同體”的未來而努力,使得所有人在他們的精神和行為里融合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性格特點。①伍爾夫也認為性別應該是互通互融的,只有當男女兩性都擺脫了性別意識的糾纏之后,才能獲得了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和解放——“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男性頭腦中女性的一面應該發揮作用,女性也應該與頭腦中男性的一面交流,兩種力量和諧共處才是正常和理想的狀態。”②
小說《山鄉巨變》中,“鄧秀梅”是一位由縣委派到清溪鄉幫助指導鄉內互助合作工作的女干部。與一般的基層干部形象不同,女干部鄧秀梅在思想與行動上表現出明顯的對一般女性氣質的超越,這體現為鄧秀梅部分男性氣質的展現。同時鄧秀梅從未割舍她特有的女性氣質,并且借助強大的精神力量將這兩種性別氣質恰如其分地運用在繁雜的農村工作中,使兩種氣質在不同的方面展現出各自的優勢,構成一種互補關系。鄧秀梅這一形象正體現了弗里丹、伍爾夫等人所提出的“雙性同體”思想。作為兩種性別氣質的集合體,她能夠從傳統的性別氣質觀念突圍出來,而促成這一切的深層原因是她的政治理想與干部身份的要求。
具體地,干部身份使“鄧秀梅”展現出與所謂女性氣質相反的男性氣質,具體有以下幾點。第一,熱情誠摯、負責能干——作為初到清溪鄉的外鄉人,鄧秀梅懷著極高的工作熱情,首先向盛淑君、李月輝、陳大春等人詢問清溪鄉的各方面情況,這是為更好掌握清溪鄉的狀況與問題,方便之后實際工作的開展。第二,勇敢要強、有主見、擅長組織決斷和指揮調度——她堅持與鄉民同吃同住,生活上緊密聯系群眾,不搞特殊化;善于為干部或群眾分配工作任務,如囑咐劉雨生調查謝慶元的互助組、考察李盛氏家里狀況,她自己也身體力行,深入各家各戶,與基層干部一起面對、解決各家各戶的問題,為村民講解合作化生產帶來的好處。第三,在工作與私人情感上保持理性——鄧秀梅新婚不久就毅然投入到黨的事業中去,與丈夫分居兩地,而這份私人情感隨照片和書信被藏入抽屜中,從不會擾亂她的工作。而工作中的鄧秀梅一直保持著理智,極力排除一切情緒化因素。鄧秀梅表現出更多的“男性化”氣質,總是以基層干部所應該展現出的氣質或素質嚴格要求自己,達到基層干部的標準。當然文中也顯示鄧秀梅所不具備的部分男性氣質,如由于其本身數學不好,在匯報時說不清入社的具體比例而“當人爆眾,受了區委書記間接的搶白”③(115-116),相比于朱明書記,她對數字的敏銳度以及對數目字管理的嚴謹度還有所不足。
同時,鄧秀梅部分女性氣質在工作中凸顯并發揮作用,達到男性與女性氣質的互補。其女性氣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體貼耐心。與農民們交流時,她傾聽他們的生活瑣事與各種苦楚,表示理解并進行善意開導,交流的話題總會從家常入手,再過渡到入社的必要性,循循善誘,設身處地為農民們著想;第二,細心冷靜。對于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細節留心觀察,而這些細節的發現與掌握對于合作化工作的推進起到關鍵作用。如張桂秋、符賤庚二人謊稱只是趕牛“寄草”以掩蓋殺牛意圖時,鄧秀梅敏銳“發覺秋絲瓜(張桂秋)的左手總是躲著,偶爾抬起,也是直直的,肘子從來不彎曲”③(192)而生出疑心,并冷靜地告知其他干部,眾人才采取行動,搜出了張桂秋藏在袖子里的殺豬刀。鄧秀梅的細心冷靜不僅保障了一行人的人身安全,而且使張桂秋的計劃顯露無疑;第三,把握女性心理,重視婦女工作。鄧秀梅與婦女交流時總能準確把握女性的心理,推己及人,不僅傳達一些科學的婚戀經驗,而且激勵婦女參與入社宣傳工作。此外,鄧秀梅既察覺到盛淑君的戀愛心理及其變化,又預料到劉雨生與盛佳秀二人關系的走近,這也與文中所提到其具有從事婦女工作的經驗相對應。總之,女干部鄧秀梅在與農民的交流對話、細節的發現與處理,以及對于婦女工作這些方面發揮了女性氣質的優勢,通過自己的方式深入群眾生活與心理,做到了一般男性基層干部所難以做到的。
鄧秀梅兼具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同時她也將這些男性氣質、女性氣質恰當地運用在工作的不同方面,使理論知識成功地付諸于實踐。正是鄧秀梅與其他基層干部“并肩作戰”,清溪鄉才最終達到了入社指標并建成了常青社。更深層地,鄧秀梅形象中雙性氣質的融合是與基層干部身份相對應的價值理念通過超我力量外化的結果。相對于一般干部形象塑造的單一性政治隱喻,“鄧秀梅”所代表的干部新形象展現出了性別氣質與干部身份互滲的張力。弗洛伊德認為任何人都具有雙性氣質,可見擁有單一性別氣質的人(包括現實生活的人與小說虛構的人)則是遠離生活和真實的。而正是在這種性別氣質與干部身份的互滲中,鄧秀梅這一新形象帶有了當時“農業生產合作化”政策與農村出現新氣象的象征意味,這種象征不是神秘的,神圣的,而是生活的、真實的。
二.“鄧秀梅”前史:女干部的階段化成長歷程
小說《山鄉巨變》上下卷分別塑造了兩位女干部形象,主要在上卷提到的是受過組織訓練后由黨委下派到清溪鄉開展合作化工作的鄧秀梅,她是一位理論扎實的投身合作化事業的外鄉人;而另一位女干部形象則是主要在下卷講述(這里指正式投入工作時)的清溪鄉新婦女主任盛淑君,她是一位受到鄧秀梅的影響而選擇加入干部隊伍的本地人。地域差異并沒有在作品中過多的展現,但除此之外,二人同樣是可以進行對比的,這對比的可能性在于——在塑造與刻畫二人形象時,作者實際在表現人生階段上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盛淑君從一位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女轉變為能夠撐起社內“半邊天”工作的干部,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文本中所“缺失”的鄧秀梅成長為女干部以前的經歷。盛淑君是處在成長期的“鄧秀梅”,鄧秀梅則是處于成熟期的“鄧秀梅”,文中對二人的書寫能夠構成一段完整的農村女干部成長史。
鄧秀梅作為組織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女干部,已經徹底擺脫了盛淑君那種青澀苦悶的戀愛心理,是“新婚戀觀”的“過來人”,同時將所掌握的理論、政策真正與實踐工作相結合,沉穩冷靜地處理事務,真誠親近地對待農民。在文本結構上,小說以女干部鄧秀梅與“朋友們”道別、孤身前赴清溪鄉作為開場,而在“進入”后又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這個過程沒有用任何插敘去寫她受到組織培訓與積累理論知識的過程,而更多地是對其“現實”工作進行細致描寫——與上級領導、其他干部以及農民之間的交流與配合和對鄉里各方面問題的發現與解決等。
而文中對盛淑君的書寫,包括她的性格、出身、生活、戀愛等,有一個更加明顯的變化過程。在上卷前部分,盛淑君是一個永遠帶著笑意又具有雙重憂慮的少女形象。在身份上,團支書陳大春介懷盛淑君母親早年有過一些風流之事,而遲遲未決定其入團一事,因此盛淑君為難以加入團組織而憂慮。在愛情上,在意陳大春對自己的印象,二人關系也得不到實質性進展,因此盛淑君又為戀愛受到阻礙而憂慮。但是盛淑君并沒有沉浸在這些憂慮與苦悶中,而是選擇積極服從組織與安排,將青春與熱情投入在合作社運動的宣傳動員工作中。作為宣傳隊隊長,盛淑君面臨打擊與困難毫不氣餒,并且鼓舞其他姑娘們的“士氣”。同時在婚戀經驗上,聽取鄧秀梅的囑咐,處理好情感與工作的關系。
而在小說下卷開頭,戀人陳大春被調走后,而盛淑君做出了與鄧秀梅同樣的選擇——與戀人分處異地卻一起堅持為黨的事業而奮斗。即使感到不舍,但她還是留在了清溪鄉,幫助其他的基層干部開展工作,同時也正式擁有了政治身份——婦女主任。作為婦女主任,行動上,盛淑君與其他干部一起加入青年突擊隊,與單干戶王菊生進行作田比賽;制作跳板,解決了因泥塘地滑容易摔倒的問題;照料因勞累過度而暈倒的“競爭對手”王菊生堂客;組織召開婦女會,提出成立托兒站,使婦女們“騰出手來”參與勞作等。思想上,她循著鄧秀梅的精神品質,決心調動婦女的積極性;她反思鄉里的變化,提升對黨的認識。可見,盛淑君在行動與思想上逐漸成長起來,走向了成熟階段。
圍繞清溪鄉,鄧盛兩位女干部一個組織建社,一個推進生產,雖然她們面對的具體任務不同,但是在單純少女盛淑君身上,我們總能想象到成長時期的鄧秀梅;在婦女主任盛淑君身上,我們也總能尋找到成熟時期的女干部鄧秀梅的影子。文中也明確提到少女盛淑君在深夜里的多次向鄧秀梅傾吐煩惱,以及婦女主任盛淑君重回鄧秀梅曾經住過的房間時,“房子依舊,主人換了,盛淑君不禁想起鄧秀梅,忙從衣兜里挖出她的信,從頭到尾,又念一遍”③(355)。這里盛淑君對這封信的珍視暗含了她一直接受著鄧秀梅言傳身教的影響。二人的成長階段特征實際上也有不同,鄧秀梅是從“理論”到“將理論與實踐行動結合”,盛淑君是從“被動行動”到“主動行動,同時進行著思想的升華”,而盛淑君的政治思想的“啟蒙”正來自于鄧秀梅的指引。鄧秀梅早已成為盛淑君的精神力量,在事業與愛情上支撐著她一直向前走去。
鄧秀梅與盛淑君二人在成熟期實現了這種特殊的女干部形象的重合。總的來說,二人在婚戀、工作、愛情與事業的關系處理等層面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農村女干部的成長歷程,并且從成長期到成熟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化的特征。
三.干部與性別:“鄧秀梅”的本質與現實啟示
在《山鄉巨變》中,以鄧秀梅為代表的農村女干部形象不僅匯聚了男性與女性雙重性別氣質,而且也呈現出成長過程的階段化特征,而這些氣質與特征都與她們的干部身份與職責履行有著一定的因果關系。從本質來看,這些女干部形象的出現與新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產生著莫大的聯系。在創作上,拋開作者受到當時文壇構造“新中國想象”這一形勢的影響不談,女干部形象本質就是理想與現實的一種結合,而她們性格與人格特質也兼具理想性與現實性。
作為十七年文學的政治想象與女性形象的一種集合,鄧秀梅首先與合作化運動時期的婦女參政從政政策有關。鄧秀梅以推進湖南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女干部形象在小說中凸顯出來,她的性別屬性與政治身份必然地糅合在一起。作為現實的縮影,鄧秀梅這一形象反映了正是合作化時期農村中婦女從政的可能。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政策也確實對婦女從政問題有特別地涉及。1954年,全國婦聯發文強調,“應在農業合作社、互助組及基層婦女代表會議的婦女積極分子中,選擇積極勞動、政治思想進步,能聯系群眾、而又有一定能力的婦女,有計劃地培養她們成為各組織的領導骨干”④等。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確提出,女社員應該在合作社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里占一定名額。次年,《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將以上規定在人數上進一步具體化,“在合作社主任、副主任里面,至少要有婦女一人”⑤。這些指示與章程為這一時期的婦女參與合作化以及農村公共事務的領導和決策活動提供了重要依據,而農村女干部“鄧秀梅”的出現也正是這些政策性文件指導下的“結果”。
其次,鄧秀梅這一農村女干部形象也與《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下文簡稱《問題》)這篇報告對干部的要求有關。在合作化運動高潮來臨之際,1955年7月,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指出了合作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而關于農村領導干部,報告中主要強調了三個方面。一是抵制基層干部思想中出現“前怕龍后怕虎的態度”。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被派到農村中,要發揮好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的力量,建立起以當地干部為主,派去的干部為輔的管理方式;二是在群眾動員上,基層干部要系統地和反復地宣傳相關的政策與辦法,要解釋合作社的好處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三是注重建社的質量,反對“一刀切”或者單純追求數目字的偏向。除了《山鄉巨變》以外,其他的合作化小說也塑造了許多農村女干部形象,比如《創業史》中的青年團縣委干部王亞梅、竹園村互助組組長劉淑良、《三里灣》中的合作社副社長秦小鳳。雖然這些女性都同樣擁有 “農村女干部”這個身份,但是鄧秀梅在屬性與實踐上與她們有所不同,因為她是由黨派到農村去的、經過了“短期訓練”的、肩負著特定任務的干部,與《問題》中提到“派去的干部”相對應。在實踐上,鄧秀梅是現實性與理想性相結合的干部,她的工作任務主要針對于本地干部自身出現的問題與農民階級內部難以解決的矛盾,而實際上,這些問題與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僅與《問題》中所提出的三個方面極為貼合,而且幾乎都能在鄧秀梅的指導下得到解決。
因此,無論是與清溪鄉中的本地干部相比,還是與上面提到的其他女性干部相比,鄧秀梅都可以算的上是具有更高水平與理想色彩的干部,而且這位農村女干部在重振一方村莊的政治與農業事業的同時并沒有回避她的性別。那么對于現實中從政婦女看似尷尬的權力與性別 “對立”問題,實際上鄧秀梅身上所散發的優秀品質與她對各種工作的處理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地給予現實以反思。
新時期以來,女性參政從政狀況總體朝著積極樂觀的方向前進,但是女干部在走上領導崗位與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仍然遇到許多問題,而職責履行與性別屬性的關系是這些女干部首先要面對的。作為一種身份,“女干部”從賦予女性身上后就開始積極發揮起作用,而且在具體的工作與權力的行使中,她們往往表現出與傳統女性氣質相差別的性格特征。借助斯托勒的社會性別理論來說,正是管理與領導權力模式的變化,使得這些女性的社會性別特征在自覺或不自覺中轉變了,她們具有了強烈的事業心、獨立的性格、頑強的意志以及從政在崗應有的能力與素養。而“鄧秀梅”為女干部帶來的一些啟示更多是對生理性別限制的超越,從發揮社會性別優勢的角度出發來解決她們在履職中的性別顧慮。
一是運用對“人”的注意力與溝通能力。鄧秀梅善于與人溝通,而她的表達和溝通技巧的運用往往與對對方的觀察聯系在一起。相比男性,“女性注意多定向于人,在人上的注意穩定性較好,持續時間較長”⑥,而領導干部在各項工作中必定離不開與人打交道,因此女干部們更應該發揮注意力的偏向優勢,在與群眾、領導以及同事溝通時,通過注意力的集中來感知對方的情緒態度,及時調整自己的語言表達從而有效推進工作。第二,把握女性心理,強化“她力量”。鄧秀梅多次與婦女進行對話,或耐心聆聽,或循循善誘,心與心的親近促使農村婦女發生思想的新變。女性在性別上具有“天生的”優勢,能夠細致入微地把握女性的心理,因此女干部應發揮這一優勢,將其運用到婦女工作中,引導婦女擺脫舊思想舊觀念的束縛,積極從事生產勞動以及參與政治生活。
新時代的女干部履行職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于解決她們的性別與履職的“矛盾”需要從內外兩方面著手。在外部層面,應對女干部生理上的特殊性給予應有的政策關懷,通過各種方式營造良好從政環境,竭力消除男性同事與領導的歧視等,而內部層面還得從女干部自身入手,應主動化“劣勢”為優勢,自覺培養各種能力以適應工作與競爭的需要,扭轉女干部的干部身份與性別生理“看似矛盾”的困擾,使“能頂半邊天”這一理想得以真正實現。
女干部鄧秀梅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在《山鄉巨變》中所要著力塑造的,但這一形象對于整部作品的意圖表達、十七年合作化小說的人物類型研究、十七年作家對農業改造這一歷史現實的考察、以及當下女干部的性別履職問題反思與啟示都產生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鄧秀梅所代表的女干部形象不僅是雙重性別氣質與政治身份權衡的“結果”,承載著合作化小說、十七年作家以及當時的社會與時代對于理想干部的一種綜合的想象,而且更是對于對當下現實中的女干部在履職與性別關系處理方面做出了一種實驗性的示范,具有跨時代的回應于歷史、作用于現實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周立波.山鄉巨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3]柳青.創業史: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美)貝蒂·弗里丹著;程錫麟等譯.女性的奧秘[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9.
[5](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賈寧譯.性學三論[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5.
[7]史敬棠,張凜,周清和,畢中杰,陳平,李景崗.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 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
[8](美)克萊爾·A.埃塔,(美)朱迪斯·S·布里奇斯著;林磊,桑標譯.心理學關于女性第4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9]河北省婦女問題研究會編著.女性職業角色與發展[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
[10]葉忠海.女性人才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1]楊燕.職業女性生涯發展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2001.
[12]張小莉.社會性別視角下當代中國女性黨政領導人才職業發展研究[D].遼寧:遼寧師范大學,2014.
[13]彭瑤.超越性別:《奧蘭多》的女性主義思想[J].名作欣賞,2006(4).
[14]常明明.農業生產合作社干部研究(1954—1956年)[J].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28(3).
[15]許薇.從《創業史》女性形象塑造看柳青的女性觀[J].昌吉學院學報,2017(2).
注 釋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245.
②彭瑤.超越性別:《奧蘭多》的女性主義思想[J].名作欣賞,2006(4):96.
③周立波.山鄉巨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④全國婦聯.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關于當前農村婦女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報,1954-7-31(3).
⑤史敬棠,張凜,周清和,畢中杰,陳平,李景崗.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219.
⑥葉忠海.女性人才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5.
(作者單位: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