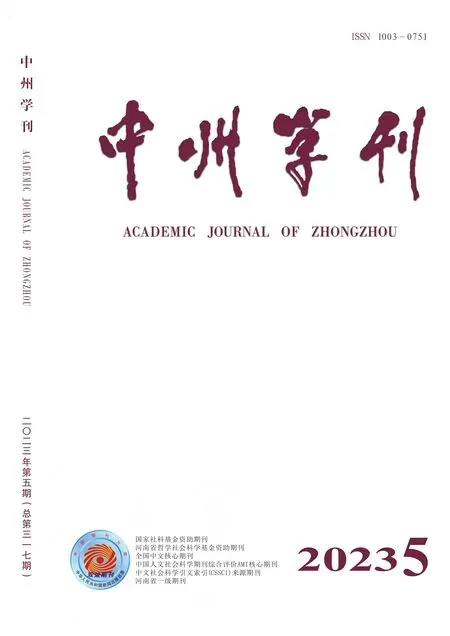儀征胥浦漢墓竹簡《先令券書》未釋縣名辨析
鄔文玲
關于漢代輿縣的治所位置,以往學者們根據文獻記載、考古調查和考古發現作過一些研究,大體認定其在江蘇儀征胥浦鎮境內。蘇文先生認為漢代輿縣故址在今儀征胥浦儀征化纖廠內,當地百姓稱之為“佐安城”[1]。印志華先生認為江蘇儀征老胥浦鎮路南蜀岡上的“霸王城”即是漢代輿縣的治所所在地[2]。所謂“佐安城”和“霸王城”,根據明代《隆慶儀真縣志》記載,所指區域大體相當[3]。雖然兩位先生提供了較為有說服力的理據,但由于沒有確鑿的文字材料佐證,難免有些美中不足之憾。不過,這一缺憾有望通過重新辨識當地早年出土的簡牘資料予以彌補,從而為尋找漢代輿縣城址提供有用的線索。
1984年江蘇省揚州市儀征縣胥浦101號漢墓出土的竹簡《先令券書》,是我國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遺囑抄本,自公布之日起,便備受學界關注。學者們從文字釋讀、簡序排列、內容解讀等方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取得了不少研究進展①。有些爭議得到了解決,有些問題仍存異見。特別是其中有一處較為關鍵的簡文,雖然墨跡清晰,但卻有多家不同的釋讀意見,至今尚未達成一致,還沒有較為合理的說法。實際上,這處簡文也關涉輿縣地望問題,十分重要。本文嘗試對此再作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昃”字釋讀爭議
為了討論方便起見,先按照李解民先生的釋讀和排定的簡序,將《先令券書》的釋文移錄如下:
1.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昃,高都(1)
2.里朱夌廬居新安里,甚疾其死,故請縣、(5)
3.鄉三老,都鄉有秩佐,里師譚等,(3)
4.為先令券書。夌自言有三父子男女(2)
5.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6)
7.吳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長實。(10)
8.先令券書明白,可以從事。(7)
9.嫗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為姓,遂居外,未嘗(16)
11.弱君等貧毋產業。五年四月十日,嫗以稻田一處、桑(11)
14.各歸田于嫗,讓予公文。嫗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處、(14)
15.桑田二處,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賣田予他人。時任(13)
16.知者:里師伍人譚等及親屬孔聚、田文、滿真。(8)
根據李解民先生重新排定的簡文和研究可知,這組竹簡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文件。其中1—8號簡為第一個文件,該文件的主人公為朱夌。其性質是朱夌在病重時立的一份書面遺囑,自名為“先令券書”,旨在交代六個子女與各自的生父。9—16號簡為第二個文件,該文件的主人為嫗,記載了嫗關于家產分配的交代。兩個文件的時間坐標不同,內容不同。第一個是確認六個子女生父家次的先令券書,第二個是交代五個子女家產分配的口述記錄。后一個文件不能視為先令券書的內容。兩個文件的主體稱謂不同,在場證人也有所不同。兩個文件的簡文字體、書寫行款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兩個文件的書寫時間存在一定的間隔。而兩個文件的主人朱夌和嫗,實際上是同一個人[4]450-453。
對于《先令券書》1號簡“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昃”之“昃”字的釋讀,歷來多有爭議。以往諸家提出了幾種不同的釋讀意見。
一是釋作“亥”而存疑,為發掘者所首倡[5]。陳平、王勤金先生亦持此說,并作了進一步的說明:
疑為亥字,但只是形近或是,于義可做辛丑日的亥時粗略可通,而無大把握。李學勤先生提議釋為定字,以為于形既近于義又可作建除十二辰之定辰解。我們在查對了《云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書中《秦簡·日書甲》第743至754簡簡文后發現,九月的丑日值平而不值定。張政烺先生又以后唐同光四年(926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及寶祐四年(1256年)三部歷書對稽,九月皆建戌,九月的丑日當值平而不值定。故元始五年(5年)九月的丑日不大可能值定,此字也不大可能是定字。查《漢書·地理志》,今儀征所屬漢之廣陵國轄縣,亦無縣名與簡文此字相近者。故此字亦非縣名。此字的釋讀,暫時存疑。[6]
二是釋作“仄”。為陳奇猷先生所首倡,他指出以往釋作“亥”不妥,亥時為三更時分,是半夜,一大幫人在半夜三更為此《先令券書》,不合情理。他根據后世有把“平仄”之“仄”寫作“夨”形的例子,主張將其釋作“仄”,認為“仄”為“昃”之省文,《后漢書·薛宣傳》“躬有日仄之勞”,以“仄”為“昃”可證。《說文》“昃,日在西方時側也,從日仄聲,《易》曰日昃之離”,《易·豐》“日中則昃”,是昃為日過中午,即下午之時。此《券書》“辛丑仄”即辛丑日下午[7]。這一釋讀方案得到胡平生、李天虹[8]和李解民[4]等先生的贊同,并將其徑直釋作“昃”。

四是釋作“□”,作為不識之字處理,為李均明、何雙全先生所首倡[12]。
五是釋作“乃”,為馬新先生所首倡[13]。
六是釋作“乞”,讀為“訖”,意為寫定,為劉奉光先生所首倡[14]。得到陳榮杰、張顯成先生的贊同。他們指出陳雍先生將其釋作“今”字,不僅形體不相符,而且文意也不順暢,因為先令券書中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已經表示日期,再用一個“今”字重復時間沒有意義。進而對其字形和文意作了進一步分析,贊同劉奉光先生的意見釋作“乞”,認為“乞”當是上面兩筆和下面的“乙”連筆草書而成。“乞”通“訖”,意為寫定。元始五年九月辛丑寫定該先令券書也是說得通的[15]。
二、“昃”應釋作“與”
上述諸家釋讀意見,不論字形還是文意,皆有未安之處。首先從字形來看,其與“亥”“定”“仄”“昃”“今”“乞”諸字,都不能完全吻合。從文意來看,釋作“亥”“仄”“昃”“今”“乞”“乃”中的任何一個字,于文例皆不相符,于文意也不夠順暢。因此,不論字形還是文意,皆需重作考慮。


表1 字形對比
因此,跟以往所釋的“亥”“仄”“昃”“今”“乞”“乃”諸字相較,將“△”釋作“與”,字形更為契合。
其次,從文例和文意來看,釋作“與”,皆可講通。“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高都里朱夌廬居新安里”,交代了立券時間和立券人個人信息兩部分內容,立券時間為“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年月日皆具,非常明確;“△高都里朱夌廬居新安里”,則系交代立券人朱夌的狀況,“廬居新安里”,表明她當時居住在新安里,“△高都里”則是交代她原本的籍貫。“高都里”為里名,其前的“△”,應為縣名。
漢簡中有大量表述個人籍貫的資料,通常都是采用“郡名+縣名+里名”或者“縣名+里名”的形式,且縣名之后往往不綴“縣”字。比如:
張掖郡居延通澤里大夫忠強,年三十。(居延新簡E.P.T17:27)
戍卒河東郡北屈務里公乘郭賞,年廿六,庸同縣橫原里公乘閑彭祖,年卌五。(居延新簡E.P.T51:86)
戍卒東郡東阿高樓里公乘孫光。(居延新簡E.P.T52:571)
戍卒東郡清世里鞠財,有方一完。(居延新簡E.P.T51:111)
戍卒魏郡鄴安眾里大夫呂賢,有方一完,櫝一完。(居延新簡E.P.T51:113)
戍卒潁川郡許西京里游禁。(居延新簡E.P.T51:385)[18]
田卒淮陽郡扶溝反里公士張誤,年廿七。(居延漢簡514.31)[17]
這些簡文屬于戍卒名籍,記錄了戍卒個人的籍貫、爵位、年齡、姓名、擁有的武器狀況等信息。對于籍貫的記載,皆符合“郡+縣+里”的格式。在契約文書中,對于當事人籍貫的記錄,也同樣采用這種格式。比如:
戍卒東郡聊成孔里孔定,貰賣劍一直八百觻得長秋里郭稚君所,舍里中東家南入,任者同里杜長賓,前上。(居延新簡E.P.T51:84)
僅采用“縣+里”格式記錄籍貫的例子也很常見:
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臨仁里耐長卿貰買上黨潞縣直里常壽字長孫青復绔一兩,直五百五十,約至春錢畢已,姚子方(居延新簡E.P.T57:72)
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廣漢縣廾鄭里男子節寬意賣布袍一陵胡隧長張仲孫所,賈錢千三百,約至正月□□任者□□□□□□□(敦煌漢簡1708A)[19]
正月責付十□□。時在旁候史長子仲、戍卒杜忠知券齒,沽旁二斗。(敦煌漢簡1708B)
不論采用哪種格式,里名之前皆為縣名。因此,“△高都里”之“△”無疑亦是縣名。實際上,早年間,陳平、王勤金先生已經考慮過此處應為縣名,但因為沒有找到可對應的縣而放棄了:“查《漢書·地理志》,今儀征所屬漢之廣陵國轄縣,亦無縣名與簡文此字相近者。故此字亦非縣名。”[6]蘇文先生曾說《先令券書》上提到“輿縣”,但未作過多申論,不知其是否已有將“△”釋作“輿”的想法,也有可能他是意指同墓所出“赗賻”木牘中所提及的“輿縣”④。現在根據字形可確定“△”當釋作“與”,“與高都里”,即與縣高都里。《漢書·地理志》中雖無“與縣”,但有“輿縣”,屬臨淮郡。臨淮郡為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置,新莽始建國元年(9年)改為淮平郡,領有二十九個縣:徐、取慮、淮浦、盱眙、厹猶、僮、射陽、開陽、贅其、高山、睢陵、鹽瀆、淮陰、淮陵、下相、富陵、東陽、播旌、西平、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平、海陵、輿、堂邑、樂陵(其中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平、樂陵皆為侯國)[20]1589。其中的輿縣,據《續漢書·郡國志》,東漢時期改屬廣陵郡[21]。據《晉書·地理志》,西晉時期仍屬廣陵郡[22]。
“與”“輿”二字常通用。比如尹灣漢墓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的統計包括兩大類,一類冠以“乘與”字樣(另一類無冠字):
[乘與]弩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一
[乘與]素木弩檗五十
[乘]與弩弦卌六
[乘]與弩糸緯卅八
乘與弩矢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五
乘與弓矢五百一十
(中略)
·右乘與兵車器五十八物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16]103-106
李均明先生研究指出:
上述牘文為皇室兵器、車馬器統計。“與”通“輿”。“乘與”即“乘輿”。“乘輿”指皇室擁有的器物,蔡邕《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秦簡·秦律雜抄》:“傷乘輿馬,夬(決)革一寸,貲一盾。”整理小組注:“乘輿馬,帝王駕車的馬,《漢書·昭帝紀》注:‘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史記·呂太后本紀》:“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集解》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托于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據上文兵車器集簿所見,則所有的各類皇室器物皆冠“乘輿”二字,可證蔡邕《獨斷》所解甚確。其余未冠“乘與”字樣者則為庫存非皇室器物的統計。根據此庫的官員配置與器材統計皆未見于尹灣6號漢墓1號牘《集簿》、2號牘《東海郡吏員簿》、3號牘《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4號牘《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5號牘《東海郡屬吏設置簿》,說明此庫不屬于東海郡直接管轄,可能是漢朝設于東南地區的大武庫,受朝廷直接管轄。[23]
除了“乘輿”和“乘與”可通之外,在地名中也可見到“與”“輿”二字相通的例證。比如秦封泥中有“方輿丞印”[24]:

最初有學者認為方輿可能與方輿地圖有關,故將方輿丞理解為主管地圖的職官[25]。后經學者們的考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方輿,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縣。馬王堆帛書《式法》“心尾箕掩,東井與鬼復”“牽牛角亢,東井與鬼”之“與鬼”,傳世文獻通作“輿鬼”。《左傳·昭公十四年》:“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漢書·古今人表》庚與作庚輿。《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經典釋文》:“輿本又作與。”可證與、輿相通,“方輿”即文獻中的“方與”。《史記·春申君列傳》:“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铚、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史記·高祖本紀》:“于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未戰。”“周市來攻方與。”《史記·陳涉世家》:“秦嘉等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史記·曹相國世家》:“將擊胡陵、方與”,“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清一統志》卷一百八十三:“方與故城在今(濟寧州)魚臺縣北,秦置方與縣。”秦方輿縣故址在今山東省魚臺縣西⑤。漢武帝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封劉髆為昌邑王,方與屬昌邑國。居延漢簡149.19+511.20“昌邑方與士里陳系,十二月癸巳病傷頭、右手,傅膏藥”。漢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國除,更名山陽郡。
因此,《先令券書》1號簡中的“△”應釋作“與”,讀作“輿”,首句釋文應改作: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與(輿)高都里朱夌,廬居新安里。
表明立券人朱夌雖然暫居新安里,但她的籍貫為輿縣高都里。
三、輿縣城址當在胥浦101號漢墓附近
從《先令券書》前后文來看,訂立先令券書的地點可能是在暫居地新安里,因此特別交代其原籍為輿縣高都里。而在說明其暫居地新安里時,并未綴縣名,表明新安里與高都里一樣,皆屬輿縣之地,故無須綴縣名。同墓所出簡牘中,有一枚隨葬衣物疏:
這枚衣物疏中開頭所言“高都里朱君”,應是墓主人,也即先令券書的立券人朱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高都里”之前并未冠以縣名,表明該衣物疏的制作地在輿縣之內,故無須綴縣名。根據發掘簡報,101號墓為夫婦合葬墓。甲棺內尸骨保存較好,棺內出土簡牘、銅鏡、鐵刀、木劍、紗面罩、骨笄、石琀、耳塞等遺物,乙棺內尸骨已朽,出銅鏡、帶鉤、鐵削等少量遺物[5]。雖然發掘者未明言甲、乙棺主人的性別,但根據尸骨腐朽程度和出土帶鉤可知,乙棺主人應為男性,下葬年代更為久遠,很可能是朱夌的第一任丈夫朱孫。李解民先生根據西漢時期夫婦合葬墓南女北男的排列葬俗,亦推定乙棺的主人為男性[4]454-455。從先令券書來看,朱夌和第一任丈夫朱孫,養育了四個女兒。朱孫去世之后,妻子朱夌繼承了戶主身份和全部財產。根據目前所見秦漢時期戶籍資料來看,在登錄戶籍時,妻子一般冠夫姓。據此,則朱夌亦當是冠夫姓,原本不一定姓朱⑥。也可推測,其第一任丈夫朱孫的籍貫即為輿縣高都里。死后葬于當地,且為朱夌預留了墓地。雖然朱夌后來再嫁了兩任丈夫,但并未遷走戶籍,死后仍與第一任丈夫合葬。朱夌的第二任丈夫名衰近君,為吳縣人;第三任丈夫名病長實,為曲阿縣人,吳縣和曲阿縣其時皆屬會稽郡[19]1590—1591。從朱夌在遺囑中向子女們交代各自的生父,以及對財產擁有完全處置權來看,當時她的三任丈夫很可能均已離世,且與后兩任丈夫很可能是“入贅婚”。
同墓所出簡牘中,還有一枚賬簿木牘:
公文取子方錢五千于廣陵。
又船十二枚直錢萬四千四百于江都。
又取錢千六百于江都。
又取布六丈褐一匹、履一兩,凡直錢千一百卌。
又取錢千于江都。(正面)
又取縑二匹直錢千一百于輿。
又取三千錢罷木用為衣。
又取錢九千于下呂。
又取錢二萬于輿。
又取長襦一領直錢千三百。
凡直錢五萬七千。(背面)
這件木牘被整理者定性為“赗賻木牘”。從內容來看,記錄的皆是公文從各地領取的錢物數量。第一行記錄“公文取子方錢五千于廣陵”,意即公文從廣陵城領取了子方錢五千。以下各行則僅言取錢多少于某地,很可能是承前省略了公文和子方。根據《先令券書》,公文應為朱夌之子,子方為朱夌之女、公文之姐。《先令券書》說“嫗予子真、子方自為產業”,表明子方有一定的產業和經濟實力。從木牘來看,公文取錢物之地涉及廣陵、江都、下呂、輿四個地方。江都和廣陵,屬于廣陵國;輿屬于臨淮郡;下呂,可能屬于楚國的呂縣⑦。從木牘賬簿來看,公文“取縑二匹直錢千一百于輿”“取錢二萬于輿”,兩次從輿地所取的錢物價值二萬一千一百,高于其余地方。如果這確實是“赗賻”記錄的話,表明墓主人與輿地的關系可能更為密切。
總之,諸多證據表明,將先令券書中的“△高都里”之“△”釋為“與”,讀作“輿”,表示“輿縣”,意思順暢,也符合文例,是可以成立的。亦進一步證明,江蘇儀征胥浦在漢代曾為輿縣之地,胥浦101號西漢墓所在地即為輿縣高都里。又《先令券書》提及訂立遺囑的見證人有“縣、鄉三老”“都鄉有秩佐”“里師譚”,也即包含了三老、鄉吏、里師三種身份的人。其中鄉吏為“都鄉有秩佐”,表明訂立遺囑之地屬都鄉。因此,可以進一步明確朱夌的籍貫為輿縣都鄉高都里,胥浦101號西漢墓所在地即為輿縣都鄉高都里。
眾所周知,都鄉通常為縣治所在之鄉,墓葬區一般不會距離縣城太遠。金秉駿先生根據山東、江蘇、湖北、河南、四川五省發現的漢代墓葬與縣城遺址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后,認為西漢時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縣城附近,墓葬距離縣城的平均距離大多為2至6千米。鑒于墓葬與聚落之間的距離,這就意味著西漢時期相當數量的聚落位于縣城內或分布在距離縣城非常近的地方[26]。如此,則輿縣城址也應當在距離胥浦101號西漢墓所在的輿縣都鄉高都里附近不遠的地方。

史書中較早涉及晉代廣陵郡輿縣城址的信息,見于《晉書》所載桓彝和徐寧交往的故事中。據《晉書·桓彝傳》,桓彝因才華出眾、能力超群,短期內多次獲得升遷,官至尚書吏部郎,一時間名顯朝廷,受到當時專擅朝政的王敦的猜疑和嫉恨,為了自保,桓彝稱病辭官。他曾路過輿縣,與縣宰徐寧相遇相交,大為賞識,認為徐寧堪稱海岱清士,將其推薦給庾亮。徐寧由此得到重用,歷任顯要官職[29]1939-1940。《晉書·徐寧傳》中則記載了更為豐富的關于徐寧和輿縣衙署的細節:
徐寧者,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桓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29]1955-1956
由此可知,徐寧是東海郡郯縣人,年少時即成名,擔任了輿縣縣令。廷尉桓彝善于鑒識人才,他辭官之后,曾到廣陵去尋親訪友,返回的途中,遇到大風天氣,在水上滯留多日,心情郁悶,于是上岸散心,見到一處房宇,看起來像是官署。經訊問,得知是輿縣衙署。于是前去造訪,與徐寧相遇,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停留多日才離開。回到都城后,即向庾亮舉薦徐寧,徐寧由此迅速得到升遷,歷任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等職。
針對《徐寧傳》中對桓彝的旅行路線和所見輿縣廨署的記錄,清代焦循認為:“輿縣在廣陵之南,故彝從廣陵還都過此也。在大浦之旁,室宇有似廨署,則輿縣似無城郭,浦所以控潮,則瀕于江矣。”[30]關于輿縣的地理環境,在其他史書中也有一些線索,比如《宋書·符瑞志》載: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征北長史、廣陵太守范邈上言:“輿縣,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濁。自比以來,源流清潔,纖鱗呈形。古老相傳,以為休瑞。”[31]印志華先生指出,浦是通大河大江的水渠,胥浦河是儀征境內最古老的通江大河,也符合浦的含義。從大浦上岸即為輿縣廨署,說明晉代輿縣城池即在胥浦河岸邊[32]。這些信息當也有助于確定漢代輿縣城址的位置。
注釋
①揚州市博物館《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率先介紹了出土簡牘的情況。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錄了這批簡牘的釋文。有關《先令券書》的研究,見陳平、王勤金:《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楊劍虹:《從〈先令券書〉看漢代有關遺產繼承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陳雍:《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補釋》,《文物》1988年第10期;陳平:《儀征胥浦〈先令券書〉續考》,《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2期;陳平:《再談胥浦〈先令券書〉中的幾個問題》,《文物》1992年第9期;劉奉光:《西漢墓〈先令券書〉復議》,《邯鄲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李解民:《揚州儀征胥浦簡書新考》,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張伯元:《“先令券書”簡解析》,《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廖群:《〈先令券書〉與〈孔雀東南飛〉悲劇釋疑——兼論中國古代婦女的“夫死從子”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陳榮杰、張顯成:《儀征胥浦〈先令券書〉再考》,《文獻》2012年第2期;陳榮杰:《也論揚州儀征胥浦〈先令券書〉》,《歷史文獻研究》第31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鄭金剛:《胥浦漢墓〈先令券書〉釋讀問題補議》,《文獻》2014年第4期;范博軒:《〈先令券書〉反映的漢代遺囑繼承問題探討》,《大觀(論壇)》2020年第4期,等。②黑白圖片出自連云港市博物館、揚州博物館、每日新聞社、(財)每日書道會:《江蘇連云港·揚州新出土簡牘選》,美術出版設計中心,2000年。③“與”字簡體作“與”,為了便于字形比對,本文皆用繁體“與”。④蘇文:《從考古資料看兩漢時代的江蘇經濟》,《東南文化》1989年第3期,注釋112:“漢代輿縣故址在今儀征胥浦儀征化纖廠內,調查時城垣已不清楚。在城址內出土大量的磚、瓦構件和陶井圈。城郊西南高地上又發現大量的漢至六朝墓葬。地方志書和當地農民稱該城址叫佐安城。然漢代在江蘇境內無佐安縣建置、而其地理位置與漢代輿縣地頗合。同時,城址附近六朝墓磚上有‘輿縣’字樣的銘刻。在此發掘的胥浦101號墓隨葬《先令券書》上亦提到‘輿縣’。所以我們認為這座城址實際就是漢代的輿縣縣治遺址。本注部分考古資料承南京博物院張敏同志提供。”⑤參見陳曉捷:《學金小札》,《古文字論集》(二),“考古與文物叢刊”第四號,《考古與文物》編輯部,2001年;周天游、劉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簡讀》,《文史》2002年第3期;傅嘉儀:《秦封泥匯考》,上海書店2007年版;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⑥根據當地發現和清理的幾座同時期墓葬中出土的文字資料信息,陳平推測包括101號在內的這些墓葬是漢代何姓的家族墓,《先令券書》中的“嫗”可能是何氏之女。101號墓同出的“何賀山錢簡”文云“[女?]徒何賀山錢三千六百,元始五年十月□日何敬君、何蒼葛書存[文]君明白”,即涉及何賀、何敬君、何蒼葛三位姓何之人。參見陳平:《儀征胥浦〈先令券書〉續考》,《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2期。⑦參見班固:《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38頁;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