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赫胥黎
——從文學家到哲學家的精神之旅
王 坤
阿爾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是享譽世界的英國作家、思想家和開明知識分子,其《長青哲學》一書集中呈現了長青哲學傳統的思想樣貌。每一種文化體系都有其大傳統與小傳統、主流和非主流;正是在這種多元并存的巨流中,一個文明體系始成其豐富與活力,人的精神也于此間得到多個向度的激發、延展和安頓。長青哲學,作為西方思想傳統中的重要一支,歷經漫長歲月以來,一直不斷地得到闡釋,在二戰之后尤其備受關注。其著眼點為人類的終極目的(Final End),關心所有宗教及文明系統表面差異下共通共同的“神圣本原”(Divine Ground)。關于長青哲學更精確的定義,赫胥黎這樣告訴我們,“長青哲學主要關注的是萬物、生命與心靈的大千世界背后那個神圣的實在”,它也是關于形而上學、心理學、倫理學等所探討的現象背后的“神圣的實在”,亦即萬物內在而超越的本原的學說。
遠不止是文學家
阿爾道斯·赫胥黎生于以高度智力成就聞名的赫胥黎家族,其祖父是著名生物學家、進化論支持者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被稱為“達爾文的猛犬”),堂外祖父則是同樣享有盛名的維多利亞時代詩人兼評論家馬修·阿諾德。赫胥黎曾讀于伊頓公學,后就讀于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下半生在美國生活,1937 年移居洛杉磯直至1963 年逝世。他天資異常,受到良好教育,對人類的生存處境具有超人的洞見力。他曾想做醫生,然而一次眼疾幾乎讓他視力全失。學習盲文后,他逐步開始寫作,先后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并在20 世紀20 年代成為一個明星人物,以小說和散文名于世,也出版電影故事和劇本。通過寫作,赫胥黎充當了社會道德、標準、理想的追問者和批評家。不得不說,他是一個卓越的人文主義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赫胥黎對靈性主題如超個人心理學、長青哲學也情有獨鐘,并于1938 年與吉杜·克里希那穆提結為好友。在其人生的最后階段,赫胥黎在學術圈被公認為現代思想界的精英,位居當時最杰出的知識分子行列。其名著《美麗新世界》(1932)暢銷不衰,其他著名作品有長篇小說《鉻黃》(1921)、《男女滑稽圓舞》(1923)、《光禿禿的樹葉》(1925)、《旋律的配合》(1928)、《加沙的盲人》(1936)、《幾個夏季之后》(1939)、《時間須靜止》(1944)、《天才與女神》(1955)、《島》(1962)等,另有短篇小說集、詩歌、散文和戲劇,一生為人稱道的著述計五十余本。《長青哲學》一書則成為整個長青哲學傳統中的當代扛鼎之作。
赫胥黎生而孱弱聰穎,一向富有創見。他的堂兄格爾瓦斯(兼有同窗之誼)說,赫胥黎自小與眾不同,擁有開啟自己內心堡壘的鑰匙,他時常進入其內,以逃離學校現實的折磨和苦難;他機敏,也參加同學們的笑談,然而不知怎的,同窗們總感到赫胥黎“與其他人走在一個不同的層次上”[1]。
從伊頓到牛津:喪母、失明與戰爭
1908 年9 月,14 歲的赫胥黎進入伊頓公學。正在春風得意少年時,一個重大打擊不期而至,他的母親因病驟然離世,年僅45 歲。在葬禮上,赫胥黎啜泣不止,其長兄朱利安描寫他這位14 歲的弟弟“痛苦但面無表情地”站在墳墓旁邊,其姨母漢弗萊·沃德夫人家的表姐多蘿西則回憶道:“這個伊頓公學的小孩非常易感、神情沮喪、面色蒼白,深深地——但是一言不發地感受著痛苦。”[2]在這樣的年齡,對于一個深情而敏感的人,喪親之痛很容易引發生命無常、死生事大之思。“當后來赫胥黎在《加沙的盲人》(1936)中寫到安東尼·比維斯在校學習期間因母親去世而感到的孤立和悲傷時,格爾瓦斯認為,‘他是在運用他自己的痛苦經驗’”;而“在《灰色的卓越》(1941)中,赫胥黎寫到另一位歷史人物在10 歲那年失去了父母之一:‘在他心里留下的是一種揮之不去的空虛、無常,一切僅有的人生幸福朝不保夕的感覺——這種感覺平時處于潛伏狀態,但卻時時會浮出表面’”[3]。這種喪親而致的無常感流露在其文學作品中,可以推知也一定促使他進行心靈上的宗教和哲學求索,潛在地成為他日后關注長青哲學的一樁因緣。我們注意到,母親朱莉婭在病榻上給赫胥黎寫過一封信,這封信他終其一生都帶在身邊。朱莉婭在信中囑咐道:“別做太多的判斷,而應該多愛一點。”
許是天妒英才,兩年后,這位天才少年又遭受了另一重身心災難:他在一次軍訓中感染眼疾,后終生視力受到影響。1957 年,赫胥黎在美國接受一次采訪時回顧說:“發生那事的時候我大約是16 歲半,我得了角膜炎,一只眼睛大約十分之九失明,另一只眼睛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將近兩年我無法讀任何書。我不得不離開學校,不得不請私人家教。我學習閱讀盲文,甚至盲文樂譜,那是很難的。后來,差不多兩年之后,我可以用一個度數非常高的放大鏡讀書了,借著它讀完了大學。”[4]可以說,這場災難是他早年生活中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影響了他一生的走向。幾近失明使他遠離了體育運動,也遠離了與同齡人社交的諸多尋常渠道。這確實刺激了他“性格中所固有的一種傾向,一種離群索居,也許是沉思冥想的傾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事件確定了這些事實”[5]。這次失明事件促使他終生沉思心智、德性與肉體的關系:“離開生理判斷的心理判斷和道德判斷是多么無意義呀!”他在1933 年對其終身好友內奧米·米奇森說:“當然,我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視力缺陷。點狀角膜炎塑造了我,現在也在塑造我;而我反過來在過去和現在都利用了它。”他在《夜里的音樂》中寫道:“人們利用他們的疾病的程度,至少相等于他們被疾病利用的程度。”[6]而失明對于當時赫胥黎的一個直接影響就是他在伊頓公學的求學生涯宣告結束,他不得不輾轉各地嘗試改善視力。1929 年,他回憶道:“由于使得我在一段時間幾乎失明的眼睛感染而中斷了教育……我獨身無依,凡事只好靠自己。”在1911 年至1913 年之間,赫胥黎的教育事實上中斷了,直到他借助一只放大鏡通過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的入學考試為止。同時,這次失明事件也使赫胥黎免于和同齡人一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而得以在牛津繼續其智識積累;但這對于當時的他,似乎并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慶幸,反而是一種打擊。他不能出于愛國主義情懷參與戰爭,也不得不中斷在牛津剛剛建立起來的許多深刻友誼。他再度意識到自己的孤獨:“我總是對光亮感到一種強烈的渴望。”[7]這種表達既是其視力不佳的生理和心理現實,也可看作是一種深廣的比喻。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探索光明、探索自己,盡可能地去理解同時代的人。這種智識上的雄心,使得他遠遠超越散文、小說的藩籬,進入了歷史、宗教、哲學的探索。
在牛津求學的歲月,赫胥黎全心全意投入讀書,盡管視力極為不佳,卻能夠借助放大鏡堅持一天閱讀七八個小時。赫胥黎的研究者公認,他“畢其一生是一位熱切尋找最佳作品和‘經典作品’的人”[8],不肯浪費一丁點時間和視力。過人的閱讀量、卓越的頭腦和平易近人的友好態度,使他迅速成為貝利奧爾學院知識分子群的中心,他的房間變成同齡人的聚會之所。然而,素以活躍的政治氛圍著稱的貝利奧爾學院的這批精英,似乎并不熱衷于時政,他們更為關心的是藝術、文學、歷史、宗教、哲學這些廣泛的人文修養和超上之眼。
在同窗好友都奔赴前線之時,赫胥黎與有限的幾個“殘缺不全者”(他們的自嘲語)留在冷清的牛津。這期間,他幾乎只能不斷讀書,并到風景勝地度假,期冀優美的風景和靜謐,有助于將友人正死于戰爭的悲痛緩和成為一種平靜的聽天由命的悲傷。在赫胥黎的思想上,一個新的面向開始發端,即探索某種更廣大、普遍的真理,并漸漸朝向某種有機的統一。他通過書信說與友人:“當一個人處在這個美麗的國度時,他強烈地感覺到,他是一個遍及一切的宏大靈魂的一部分。”[9]這種心路變化和探索結果,后來集中呈現在《長青哲學》一書中。

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
作為一名作家,赫胥黎被人們看成是冷眼旁觀、不留情面的,他似乎對人類的愚行厭惡至極,但敏銳的讀者會發現,他的字里行間始終流露著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感。他有著一顆儲藏豐富的心靈,且對人慷慨。他是生態運動的早期鼓吹者,提醒人們注意核武器、人口膨脹、自然資源枯竭、軍國主義以及狹隘民族主義的危險;他警覺廣告的洗腦作用和現代消費資本主義及學術極度專門化;他取笑教授們,即便在他成為一名訪問教授時仍然如此;他不膜拜某個領域的學術權威,認為無論怎樣高深的學科,對于自己都沒有隔膜。羅莎蒙德·萊曼稱他為“一種光輝的智力化身”。他一生興趣廣泛,涉獵領域幾乎涵蓋20 世紀人類的各個方面;他學識淵博,厭惡大眾文化和傳媒娛樂,在其諸多犀利的批評性散文及小說片段中,對廉價的電影倫理和庸俗的商業音樂毫不留情地冷嘲熱諷。我們不應忽略一個事實,這就是“他的思想一直以某種方式傾向于有機的統一,試圖在表象的世界里尋找出本質的意義”[10]。
1915 年10 月,赫胥黎回到貝利奧爾學院,這是他在牛津就讀的最后一年。思念往昔同窗、細數好友的傷亡,他經受了一種創痛的深切心靈體驗。戰爭越是拖下去,赫胥黎越覺憎惡,他譴責戰爭影響了平民生活,侵蝕了公民自由,軍國主義引起“英國文明的崩潰”。他對戰爭后果的看法非常悲觀:“我對于這一切所產生的后果,不可避免的美國對世界的主宰感到害怕……我們都將被殖民化;歐洲將不再是歐洲。”[11]他對戰爭深層動因和影響的反思,三十年后這樣呈現在《長青哲學》里:“旨在超越時間者,施政往往和平,執迷過去未來、執持保守記憶和烏托邦夢想者則會制造迫害和發動戰爭。”[12]他將政治與宗教心理統合在一起進行觀照,認為“過度的特權和權力會誘發傲慢、貪婪、虛榮和殘暴,壓迫帶來恐懼與嫉妒,戰爭導致仇恨、苦難和絕望。所有這些負面情感對于靈性生命都是致命的”[13]。他警覺:“為強權政治辯解、袒護戰爭和軍事訓練的哲學(無論政客和戰爭發動者的官方宗教是什么)永遠是對國家、種族或意識形態進行偶像崇拜的某種極其不切實際的學說,由此必然會生出優等民族的觀念和那些‘沒有律法的賤胚’[14](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15]
從嘉辛頓社交圈到中學教師
與此同時,赫胥黎進入嘉辛頓社交圈。需要說明的是,嘉辛頓莊園當時是莫雷爾夫婦的府邸(1915—1927),這對夫婦熱衷主持文化沙龍,吸引了大量文藝界人士,嘉辛頓成為20 世紀初英國文學藝術生活的一個傳奇式空間。在此,赫胥黎與勞倫斯締結了深刻的友誼,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而與艾略特等其他文學家、藝術家、政治人物及思想者的交往,也對赫胥黎大有心靈慰藉和思想激發之功。他說:“莫雷爾家是我所知道的最愉快的家庭之一:那兒一直有饒有趣味的人和有益的談話:我常常從牛津到那兒去拜訪他們。”[16]而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1916 年赫胥黎大學畢業,開始經歷從充滿智識樂趣的豐富生活轉到乏味殘酷的職業現實的“粗暴過渡期”。他受聘于雷普頓學校的一個臨時教職,從而不得不離開氣氛活躍的嘉辛頓和牛津,在教工宿舍寂寞地接受不斷傳來的友人陣亡的消息。他感嘆“恐怕在攻勢結束前還得死更多的人”,“人們在死后繼續生存的一個方式是活在他們所歸屬的社交圈里,特別是在他們的朋友中間”。而他只能咀嚼著往事不堪回味的傷痛:“一個人必須朝前走。記住他們的最好的方式不是沉浸在過去之中,而是著眼于未來。”[17]
1916 年8 月,赫胥黎擺脫了雷普頓學校的臨時職位,回歸并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嘉辛頓社交圈,甚至搬到嘉辛頓農場居住,歡愉地勞動,直至1917 年4 月。在這里,赫胥黎“發現了他將在整個一生中繼續發現的東西—— 一個由智慧的人們組成的小小的然而高雅的圈子,這些人激發了他,反過來又被他所激發”[18]。更炫目的一筆是,1916 年夏季,22 歲的赫胥黎遇到小他四歲的愛侶瑪麗亞·尼斯,并在三年后結婚。瑪麗亞在赫胥黎一生中扮演了無與倫比的重要角色——妻子、秘書、管家,直至她1955 年病逝。可以說,她向赫胥黎獻出了全部的身心,有一次甚至宣布,她死在赫胥黎前頭是不對的,“因為他視力差,她無休無止地讀東西給他聽,即便閱讀的材料使她厭煩得無法相信也是如此。她駕車帶他在整個歐洲和美國行駛了好幾千英里的路——在旅館的登記本上將她的職業填寫成‘司機’”。瑪麗亞曾就學于劍橋,秉性聰慧,富有文化教養,真可以說,她是赫胥黎“視聽人類世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的眼睛和耳朵”[19]。
田園牧歌的生活無法長久,1917 年伊始,赫胥黎面臨兩項他自知當時無法逃脫的選擇:要么當個寫評論的雇傭文人,要么成為一名學校教師。其所經歷的謀生之艱難,似乎不讓于今時的我們。赫胥黎曾于1917 年3 月31 日的《泰晤士報》個人欄中登載了這樣一則求職廣告:“年輕男子,22 歲,公學及牛津學歷,一級榮譽畢業,希望從事文學、秘書或其他工作。”[20]他最終謀得航空委員會的一個文職,從1917 年4月工作到7 月。此時的赫胥黎尚未完全依賴自己的一桿筆謀生,在嘉辛頓所享受的那種貴族式的悠閑也如舊夢遠去了。職是之故,他被卷入一種社交漩渦中,并稱之為“東奔西竄”,“這種東奔西竄僅僅是一種狂熱,一種麻醉劑,令人興奮而容易忘卻”[21]。然而同時,歷經所有這些急促的聚會、暢飲和社交活動之后,再次回到書籍,又其樂無窮。
同年9 月,赫胥黎回到母校伊頓公學任教。伊頓公學是英國上層社會培養年輕一代的中心,身處其中,赫胥黎經日目睹對真正精神層面漠不關心的貴族派頭:“而經過數年之后到了那個年齡,這種裝腔作勢就變得幾乎是自然的了。這是一種特有的國民習慣。”[22]他畢生反對這種國民習慣的生硬與刻板。赫胥黎自認為天生不是一塊“教育孩子們的料”,在知識傳授上需要“進行簡縮”,而受教的學生們卻對他敬愛有加。學生倫西曼追憶,起先大家感到他的口音有點矯揉造作,“不久我們有些人就試圖模仿它了”,因為這個口音說出的話往往是發人深省的。他不是“一位狹義上的好老師”,而是“一位廣義上的教育者”[23],他帶領學生進行理智探索,擺脫事物的羈絆,讓學生瞥見此中的極樂。這可說是對一位老師極高的禮贊。
全職寫作生涯:旅行、創作與探索
不容忽視的是,赫胥黎的生命和文學探索都是在戰爭背景下進行的,而他似乎是天生的作家。他多次表示:“我實在比什么都迫切希望的是,能有一年除了寫東西以外什么都不做。”“我從來沒有感到我是在履行一種真正的道德行為,除了我在寫作的時候。在寫作時,而且只有在這個時候,才不是在浪費時間。”[24]
1919 年年初,赫胥黎回伊頓去上最后半學年的課,他已決定開啟全職的寫作生涯。英國大學教職無望,美國作為選擇的可能性凸顯出來,其新增的吸引力是,美國“是不會爆發革命的唯一地點”,而赫胥黎“一心一意致力于營造一個寫作的空間,不希望自己被卷入政治動亂和革命之中,因為它們干擾‘頭腦的自由運用——而說到底,這種自由是世界上值得擁有的唯一的東西,而能夠適當運用頭腦的人是僅有的一些值得最低限度的尊敬的人’”[25]。妻子瑪麗亞也同樣意識到這種獨立思考和自由寫作的價值,她能夠欣賞赫胥黎并終身用行動支持和成就他。她表示“寧可做任何事情”,也不愿意迫使丈夫“為了我的緣故放棄他自己的一些時間和游歷來賺錢”[26]。瑪麗亞身上體現了一種奉獻、犧牲的道德觀。他們度過了長達35 年的幸福婚姻。婚后第二年,兒子馬修出生,同時赫胥黎的文學創作已在英國文學界小有名聲,耳際響著贊揚。他在擔任《雅典娜神廟》的編輯職位和《威斯敏斯特報》的戲劇評論員之外,又分身在切爾西圖書俱樂部工作,還說服出版人支持自己編輯了一份名為《貴族》的時尚雜志。而這種評論、新聞和廣告寫作注定是階段性的。出于經濟和健康考慮,1923 年至1925 年,赫胥黎與妻兒曾旅居意大利,其間游歷佛羅倫薩、羅馬,發現建筑、雕塑、繪畫的樂趣,而“意大利的缺點是沒有圖書館,以及缺乏消息靈通和高智力的社交圈子”[27],由是在倫敦與意大利之間幾度輾轉,多部小說在安頓的間歇問世。1925 年至1926 年間,赫胥黎夫婦在突尼斯旅行兩個月,在印度、東南亞和美國旅行11 個月。令人高興的是,在紐約時他們得以投身于美國的文學界。幾個星期的時間內,赫胥黎夫婦會見了形形色色的名人,包括后來成為好友的卓別林和盧斯。美國的豐富與多元帶給赫胥黎不小沖擊,在離開時,他“因為得到許多體驗而更豐富,因為許多信念的破滅而更貧乏”[28]。

赫胥黎文學隨筆集:Complete Essays
1933 年,長達五個月的墨西哥之旅也同樣延展了赫胥黎的經驗和視野,促使他深入思考文化和種族差異,得出的結論是:“時下在法西斯歐洲流行的人種優越論是一派胡言,而人種純潔的觀念也只是一種幻想。”“任何人種都是一個寬大無比的滾輪的截面。”[29]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的幾年,赫胥黎夫婦在巴黎、倫敦及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城市鄉野之間暫住或遷徙。無論何時何地,赫胥黎一直保持著瘋狂閱讀的習慣,讀物涉及各個知識領域,從文學到科學,從宗教學到心理學。“他承認他更喜歡榮格而不喜歡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后兩個人僅僅是‘偏狂者’。”[30]榮格反對弗洛伊德自然主義的傾向,更強調人類精神的崇高性,認為人的夢境和精神病人的幻想、妄想是建立在自古以來的神話、傳說、故事等共通的基本模式上的,提倡所謂“原型”的觀點,并以此為基礎,廣泛著眼于全世界的宗教,反對歐洲中心主義。
宗教哲學與和平事業
文學高產獲得的稿酬使生活寬裕了許多,這客觀上為赫胥黎的心靈探索之旅提供了更為有力的支撐。在讀了杰拉爾丁·科斯特的《瑜伽和西方心理學》一書之后,赫胥黎對長兄朱利安說,瑜伽可能是一條前進之路,“我一直覺得,對人們來說,找到一條自身發展之路是十分必要的”[31]。他認為,只有取得心靈和精神上的成長,人們才能從完善的社會政治、繁榮的物質經濟及發達的科技手段中真正獲益。
在戰爭的背景中思考與寫作,赫胥黎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無比珍視與摯愛和平,并在30 年代成為“保障和平聯盟”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在和平問題上,赫胥黎的思考和主張可謂發乎深遠,他對西方“人道主義”有深刻反思,認為人道主義容易導致一種民族主義的宗教,而后者仍是和平的破壞者。可惜的是,“除了赫胥黎的幾位知己以外,同時代的人并沒有認識到和平理想主義者的危機”[32]。在和平議題上,赫胥黎引入了一種精神的或說宗教性的標準:“剩下的只有精神信仰了,而每個人都能接近獲得這種信仰,達到人人團結一致,這樣的一種信仰為和平主義創造了最佳的形而上學的環境。”[33]他發現,和平問題在根本上是宗教性的問題,也就是人的終極精神安頓的問題。從此,赫胥黎開始了通往終極哲學的不可阻擋的旅程。在以后的歲月中,他成為“長青哲學”闡述者的同時,還開始呼吸法門、節食、冥想等各種身心鍛煉法的實踐,一則為改善欠佳的身體狀況,二則為開展精神探索。“到1936 年初,赫胥黎無限歡欣地宣告,他戰勝了失眠癥和疲勞癥(他如今可以每天工作八小時,而不是四小時),血壓正常了,身心失調癥消失了,多年的痼疾兩塊濕疹不見了,皮膚光澤改善了,慢性鼻腔黏膜炎不復存在了。”[34]在這幾年中,從某些科學和理性主義者那里,“他獲得了輕信江湖騙子的‘美譽’,而他本人卻毫不懷疑這種理療法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35]。
赫胥黎幾乎可以說著作等身,是什么動力催生了這些作品呢?當然遠在對稿酬的希求之外。在1936年為“人人圖書館”叢書撰寫的前言中,他說:“我寫書是因為我想寫,因為狼就站在門口,我必須寫,是因為寫作是一種自我探索和自我教育的形式,是因為我想閱讀我要說的事情,這幾本書的寫作過程是一次次令人愉快的經歷。”[36]這一時期,赫胥黎持續參加和平保障運動,和一群思想家組成一個名叫“經濟學研究綜合技術中心”的團體,這些人后來逐漸成為勃魯姆[37]政府中非官方的智囊團成員。值得注意的是,“在赫胥黎的余生中,他被諸如此類的男男女女所吸引,如心理學家、科學家、工程師、社會學家、生理學家、經濟學家,概言之,即人類社會各個領域內的專家,這些人對他的吸引力要超過文學界的人”。《赫胥黎傳》的作者N.默里認為,至此,“赫胥黎身上的超脫世俗的知識分子主義結束了,從現在起,他認識到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存在于與解決實際問題辦法的合作之中,而不是沾沾自喜地妄加推斷”[38]。有研究者評述赫胥黎這種轉向類似于佛教的“回小向大”,即從書齋著述到積極參與入世,從小乘阿羅漢到大乘菩薩。
旅美、二戰與人類精神秩序重建
1937 年,赫胥黎夫婦赴美旅行,本以為“這次赴美旅行只是又一次漫游而已,會像以往那樣地去演講、去考察,他們很可能在年底返回英國,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這次在美國的旅居將是永久性的”[39]。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歐洲淪為戰區。他一邊密切關注和憂心著歐洲局勢,一邊開始更認真地對待“東方智慧”,他越來越轉向從宗教中尋找慰藉和出路。“幸存的英倫三島和一些體面國家的漸漸墮落”使他極度苦惱和失望,“為了能找到一種包羅萬象、囊括一切的哲學,不僅僅只是涉及人類肉欲的哲學,那么,就必須研究宗教哲學”[40]。因為他認識到,只有根除產生戰爭罪惡的思想和感情,才能制止此類暴行。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宣布參戰。同期,赫胥黎在對宗教作整體研究和對神秘主義作專門研究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像20世紀西方持不可知論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求助于東方,孜孜探求宗教思想和自己所從事的和平事業之間的關系。“赫胥黎開始挑戰‘時髦的’或謂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經濟因素決定政治事務。由于顯而易見的理由,他想求助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思想——特別是挑戰世俗的現實政治的現實主義思想——是否同經濟一樣的強大有力。”[41]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上用力頗深,觀點也日漸成熟,幾年后也在《長青哲學》一書中作了系統闡發。
1942 年,赫胥黎寫了一封信給兩位記者,這位處于神秘主義理論探索中的思想者這樣評述這個階段的自己:“我是一個有點文學天賦的知識分子,體質略弱,沒有過分的強烈情感,對實際事務不感興趣,對慣常的程序沒有耐心;我不善交際,常常喜歡離群索居,偏愛獨自一人的自由自在,這些欲望使我持續不斷地努力避免受制于他人,同時也使我產生了對強權和高位的冷淡,因為一切事情都遭受到強權和高位的奴役……作為一個中青年人,我最最關心的是知識、是理想的實現、是文學藝術、是繪畫和音樂。但是,迄今幾年以來,我對這些東西都感到有些不滿意,覺得即便是最偉大的杰作也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之處。最近,我開始明白了,應該怎樣評價現實和像藝術和常識之類事情之間的關系。鑒于這些東西的自身不足,這些精神活動只有從神秘主義的優勢觀出發去看待,才能觀察到它們的真實遠景。”[42]他認為,在認識世界上,神秘主義是有其優越性的。他訴諸密友作家瑪麗·赫金森:“在減緩人世間痛苦的事情上,一個人能做的實在是微乎其微。除了神秘的宗教書以外,我幾乎不讀其他方面的書。我現在只對這一方面感興趣,而且我相信,它是解決世間問題的唯一希望。”因此,“應該有一個諸教共存的地方,神秘主義是滿足各種需求的唯一東西”[43]。
1944 年年初,赫胥黎在洛杉磯的比弗利山開始《長青哲學》的引文選錄與寫作,他全心全意地投入這樁醞釀已久的工程,因他已充分認識到,長青哲學“蘊藏于世界上一切偉大的宗教和玄學的體系之中”[44],只有內心發生改革、實現內在和平,真正有益的政治變革和世界和平才有希望。此時,二戰已近尾聲,赫胥黎的主張可謂代表了世人的愿望:“編纂這樣一本書應該是與世有益、恰逢其時。”[45]赫胥黎知道,“戰爭結束之后,有許許多多的人想‘做點事情’,他們需要正確的知識并以此作為行動的基石”[46],這促使他加快手頭的工作。他沉浸在閱讀神秘主義的典籍之中,他感到遺憾的是,教育系統漠視了這方面的經典著作:“我們的教育體制是多么古怪啊!英國文學專業的學生必須閱讀斯梯爾[Steele]和艾迪生[Addison]優雅的報刊文章,需要對笛福[Defoe]的次要小說和馬修·普賴爾[Matthew Prior]的辭章點綴了如指掌,不認真閱讀這樣一個偉人(威廉·勞)的著作卻能以滿分通過所有考試——這個人不僅是英語散文大家,而且也是當時極為有趣的思想家以及整個圣公會歷史上最受喜愛的圣人之一。”他接著說:“我們目前對勞的忽視再度表明,20 世紀的教育家們已經不再關注終極真理或意義的問題,(除了單純的職業訓練)僅僅關心淺薄的無關緊要的文化傳播,以及愚蠢而冠冕堂皇地培養為學術而學術。”[47]赫胥黎認為那些卓越的神秘主義者對于教育的意義,在于他們現身說法、知行合一,從而實現了更高的認識,成為了更好的人。“如果一個作家‘把所有的經歷都花在寫作上而不是遵照他所學的知識去提高完善自身,那么,他的知識就決不會“更上一層樓”了’。”[48]
《長青哲學》囊括了赫胥黎的諸多見解:其一是長青哲學的理論建立在神秘體驗的事實之上;其二為“自我是一種厚厚的幾乎不透明的媒介,阻擋了絕大部分來自實在(Reality)的光線,歪曲了它允許透過的所剩無幾的光線”[49],要發現永恒的真理、合一認識神圣本原,須去除我執、消泯自我。赫胥黎認為神秘主義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擺脫了教義的宗教,而五花八門的教義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健全基礎上的非本質的東西和隨意解釋的事實”[50]。他深信,沒有神秘主義之光照耀的世界必定是“一團漆黑、愚蠢荒唐”的。
一般而言,宗教社會學家也會非常關注特定的神秘主義組織;從這個角度切入,西方神秘學研究不知不覺變成了“新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研究,主要關注在西方神秘學信念系統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大小小的宗教組織,比如神智學會、人智學會,等等。《長青哲學》一書乃是赫胥黎想為戰后人類的精神重建作一點專門貢獻。二戰后,他越來越醉心于用神秘主義或者說宗教的辦法來重建世界,當時美國有許多宗教機構和“身心靈團體”,然而赫胥黎本人似乎并沒有考慮與這樣的團體實際生活在一起,只是對其思想感興趣。根據我們掌握的現有資料,未見赫胥黎與特定的神秘學組織有隸屬聯系。
“赫胥黎先生的心聲”
1948 年,赫胥黎夫婦回到故鄉歐洲,游歷意大利、英國,耳聞目睹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情狀與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數月后返回美國。赫胥黎借創作的文學形象之口大聲疾呼:戰后,歐洲傳統的價值觀消失了,“遺留下來的真空被進步和民族主義的愚蠢之極的夢想所充塞”,科學家“不再是人,而成了專家”[51]。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赫胥黎“變得越來越圣潔”,“像一個圣徒的形象,一個真正的圣徒……帶著超凡的沉靜和圣潔,那聲音是如此的莊嚴、如此的柔和、如此的優美,令人神經震顫”[52]。其間,赫胥黎一直在醞釀一部以意大利天主教神秘主義者為題材的小說《錫耶納的圣凱瑟琳》,為此幾度走訪錫耶納。1950 年6 月,赫胥黎返回英國探望兄嫂和親朋故舊:“所有這些20 年代和30 年代的親朋故友都已經上了年紀了,謝頂了,腹部凸出了,給這位加州流亡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嘆喟‘誰也逃脫不掉似水年華’。”[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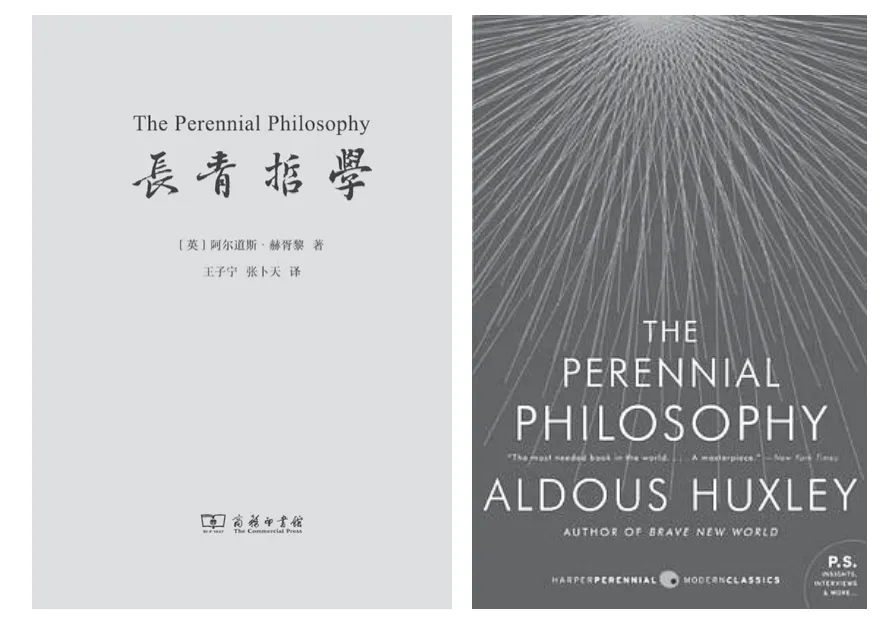
赫胥黎:《長青哲學》(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赫胥黎
作為一位文學家,赫胥黎可以說天性敏銳善感,其涉足的精神疆域也遠比同儕豐富、遼闊和深刻,而這一點是由眼光和探索精神決定的。如王六二先生所言,哲學家關心宗教似乎天經地義:“一個哲學家,即使沒有宗教思想,至少也有自己的宗教觀點或對宗教的看法。”而一個文學家關心宗教則似乎略顯奢侈:“盡管文學家都要談人生觀,但大多達到形而上的層次就打住了,至多有點哲學味。不過,大文學家都是奢侈的,他們不僅要談人生觀,不僅要把人生觀談到形而上的層次,而且還要談到世界和人生的終極性質。”[54]這樣的大文學家無疑非常可貴,王六二先生這段文字褒揚的是毛姆,不過用在赫胥黎身上也完全合適。1948 年,代表《圖畫郵報》采訪赫胥黎的西里爾·康諾利說:“如果你看看他的臉,首先會得到一種巨大才智的印象,但是在藝術家中,這種印象并不少見。更加值得注意,而且幾乎是他所特有的是他的臉上煥發出來的安詳、慈愛與和藹;你不再感到‘一個多么睿智的人啊’,而是感到‘一個多么好的人啊’。”[55]而這位記者素以冷靜著稱。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對赫胥黎的普遍看法已趨圣化,認為他已超凡絕塵,精神支柱已脫離了這個世界,但其遺孀勞拉·赫胥黎(第二任妻子)則強烈表示不同意這種看法,她堅定地認為,他是非常入世、放松和快樂的:“我無法告訴你這個人是多么文雅和溫情:又容人,又溫情,又體貼。”[56]赫胥黎去世后,朋友們致的悼詞與勞拉的看法倒是一致。
作為一名長青哲學思想家,赫胥黎在語言和宗教方面具卓越學識,并富有創見。N.默里認為可以這樣概括赫胥黎的哲學:只有改善我們自己,才能改善世界。在《旁觀者》雜志書評中,歷史學家C.V.韋奇伍德稱《長青哲學》是“赫胥黎先生的心聲”,這本書“無可爭辯的是一位思想家的著作,書中浸透著的始終如一的正直是寥若晨星般的一把精神火炬在黑暗中燃燒”[57]。
梁漱溟則說,學問是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學問乃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休斯頓·史密斯告訴世人,我之所以回溯世界偉大的智慧傳統,主要是為了對我自己無法回避的問題有所幫助。徐梵澄堅稱,治學,應是為了人生。“我們不是為學術而學術,卻是為人生而學術”(Non scholae,sed vitae discimus.),這句箴言在西歐學界人們耳熟能詳。赫胥黎的探索和著述,可以說是這種學問態度的典型體現。我們研究長青哲學,回溯赫胥黎的精神之旅,根本而言,也是在研究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