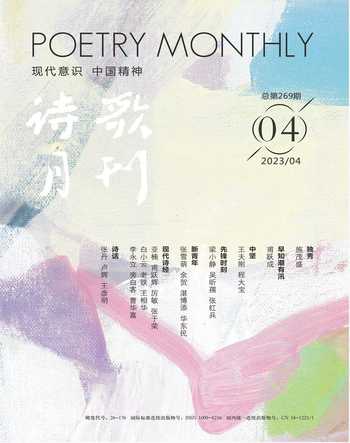那朵偽裝成雪的云(組詩)
吳昕孺
長沙荷園,兼贈草樹
荷花池,注定要變成
荷園,花已隱入漢語內(nèi)部
茶,舊成紅墻。酒,白成幻境
你拈須而成的每個字
掉到那像一張密紋唱片的
水井蓋上。今夜,必有盛大的
餐桌——明月這首圓滿的詩
被完全拆分
許多詞,意義已被用盡
盛宴往往也是劇終。一本書
同時昭示著鑼鼓和沉寂
守夜。你蘸著最后一抹晚霞
點燃長明燈。你不理解光的含義
唯有背負所有屋頂
在語言的祠堂里繼續(xù)修行
汨羅桃林寺鎮(zhèn),兼贈李卓
想起桃林古寺內(nèi)那尊關(guān)公塑像
他手持青龍偃月刀
頭側(cè)豎一匾,上書:你來了,莫瞞我
你瞞著所有人,唯獨
沒能瞞過父親:你像稻穗那樣飛揚
或像紅薯根那般深潛
有時躲在油茶花里
被那只皸裂的手輕輕拈起
不知用了多少年,父親
將自己活成一座祠堂
而待你出世,曾經(jīng)巍峨的殿宇
早已內(nèi)化為骨骼
越來越狹小的眼眶,日益向內(nèi)開拓
以便風浪驟起時,供你容身
張家口太舞鎮(zhèn),兼贈李凌芳、羅趙華
八月,太舞鎮(zhèn)的雪藏在玉石梁
呼呼的山風里
草是真正的滑行者,它們
身姿單薄,仿佛
隨時都會消失,卻不可思議地充盈
我們的眼眶,并生擒了天際
那朵偽裝成雪的云
北方構(gòu)筑遼闊的殿堂,讓雪和草的舞蹈
皆為奇跡。正當我們嘆服
那輕靈躍過群山的
漫坡青綠,蹲下身來,又忽然
聽到一棵草的呼喊
石河子,兼贈曲近
在那里,陽光濺到枯黃的草莖上
發(fā)出金屬的聲響。石子的隊伍
幻化成光的河流。空氣中
所有糖分,都跑向飽滿的水果
城市像一群剛剛破土的竹筍
從巖縫里迸發(fā)出來。而更大的奇跡
是那風格獨特的博物館
鑲嵌著一個詩人單薄的背影
許多江南口音,染綠寥廓與蒼涼
春風過了玉門關(guān)之后,由白云
一路護送至戈壁灘。胡楊在遠處呢喃
像一朵蓓蕾在夢里偷偷溜出
被月光嚴加看守的花園。你跑遍
整個西部,才把它找回
石河子,無數(shù)人花一般的歲月
才堆積成你如花似玉的容顏
翠湖,兼贈敏華
道路泥濘而曲折,撲向相聚的地點
速度依然顯得那般緩慢
時間沃土過于松軟,兜不住磨得發(fā)亮的腳步
不得不為對方注射大劑量
凝視與獨白——用寧靜的藥水
泡著孤寂的粉末,我們才得以不斷享受
疲倦之后的美妙停頓
那是我們自產(chǎn)的花和果,當發(fā)現(xiàn)
翠湖不惜干涸自身
賜予我們內(nèi)心不可窮盡的大海
我們已經(jīng)變成了
湖邊的一棵樹——一同舉起粗壯的枝干
和密不透風的枝葉
蒼翠消弭了距離,同時設(shè)置界限
日漸消瘦的秋水,薄如鋒刃
削除冗余的夢
湖邊的每顆石子
都是聳入天際的高山。靈魂爬到樹巔
變成一只鳥巢——它讓我們
徹底放棄對風和云朵的模擬,唯獨癡迷于
擁有之物,恰如光對光的渴慕
南湖漫步,兼贈劉創(chuàng)、楊厚均
南湖縮攏成一個酒盅,在我們
嘴邊傳遞。那一種醉意
不知來自李白的詩句,還是
錦繡般波紋里淌出的蜜
它無限擴大的時候,盛唐
這只蜜蜂,趴在平行宇宙的墻上
嗡嗡作響。南湖是那么透明
它的外殼僅有一層薄薄的時間
循著我們的足跡,不覺走到天外
風正一點一點地,擦去
云與水的界限。但湖里的荷花
在暗處,依然開得明艷奪目
從未覺得自己如此輕快、干凈
從未如此獨占這一份靜美
我們說著,笑著,流連于時間的表面
波光的折縫,永不能結(jié)束這一天
南湖藏書樓,兼贈余三定、朱平珍老師
庭前,一株高高的銀杏
一株圓圓的丹桂
雖然沒有靠著,卻可以看到它們
互相依傍——一種融洽無間的遺世獨立
給南湖以重新定義
密集的枝葉在空中吟誦,鳥語在云上
書寫,經(jīng)由微風刪改
被波光一一裝訂成冊。各種姿態(tài)的漢字
匯成清泉或巨瀾,沖洗庸俗的面目
和迷障的壁壘
我揣著心的迷宮而來
終于帶走一個長著蘭蕙的出口
在絢麗多變的南湖,藏書樓
用令人驚異的樸素標注了恒常的秘訣
就像庭前那兩棵樹
經(jīng)歷無數(shù)風雨,依然靜靜地
花開花落。一本書打開,一本書合上
整整六萬冊
排列成人類靈魂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