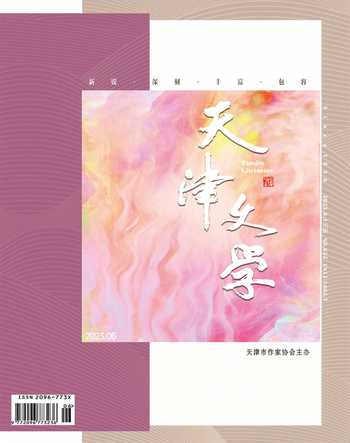新鮮的生活與新鮮的力量
在我們的《改稿會啟動和實施方案》中,編輯部提出了45歲以下占比50%的要求,可見我們對于挖掘年輕新人新作的決心,這一限定也使得我們在兩個區作協報送上來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尤其是西青區報送的小說與詩歌作品、河北區報送的詩歌作品中,年輕作者占了大多數,其創作潛力不可小覷,這的確是本次改稿會的一大亮點。另外,我們也看到了在平時投稿中所熟悉的作者,這一次報送了自己的新作,也得到了編輯部一致的肯定。我們依據“文學性、探索性、開拓性”等等要求對于來稿進行評判與衡量,從而確定了最終入選改稿會的名單。總體來說,稿件的質量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也發現在工作之中一直以來會面對的一般性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個人尚需提升與改進的地方。在接下來一對一的改稿中,作者可以聽到編輯對于這些作品的具體指導意見。
下面開始正式的改稿環節。鄭皓文的小說一共報送了兩篇——《腥湯》與《山火》。鄭皓文年齡雖小,16歲,但是作品卻顯出了超越年齡的成熟氣質。鄭皓文的小說有一種詩意,由種種神秘的意象“金魚”“棺材”“血紅的女人”或者是充滿神秘感的敘事場景“族長的死”“圍觀的人群”“隨時響起的尖叫聲”構成。題目《腥湯》就可以看到小說意識與味道是非常濃的,信息量大,一個“腥”字就有了小說張力。但是小說的問題也比較明顯:
首先是語言問題。短篇小說要有力度,同時也要清晰表達。鄭皓文的語感很好,小說的文學味道足,比如“父親把魚包起來烤,用筷子一塊塊捅進肚子里”這個描述就很有趣味也很生動,但年輕作者容易陷入對文字表達的迷戀之中,形成一種文學腔或學生腔。語言本身應是為小說服務的,在寫作過程中應該有意識避免對自己文字的過分強調而顯得油滑。鄭皓文的語言也是因為過分強調這種文學感覺,有時候是刻意為之,反而給人一種生澀的感覺,將簡單的問題敘述得復雜化了,在閱讀上會給人形成一定的障礙,這個還需要多加訓練,盡量避免陷入對文字的顧影自憐。
其次是情節推動問題。鄭皓文的語言是截斷式的,一節一節的,情節也是跳躍的,幻燈片似的。應該通過情節連貫性的敘述訓練,加強小說敘事連貫性的表達。現在故事或者說是一個小說念頭的轉化還是碎片式的,不夠完整。
第三是視角的轉化問題。比如《腥湯》的第三段,前面還在說父親伸展身體,后面又要以主人公章化為主視點作為敘述。要注意在一個段落中或者章節里盡量避免視角不停轉化,會給讀者一種混亂的閱讀體驗。
最后說說小說的主題。鄭皓文的小說其實呈現了一個逐漸迷離和瘋狂的現場,最后血腥味非常濃。作者其實呈現出的是一種具有先鋒意識的寫作風格,主題并不明確,當然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成長母題,這一母題在青年寫作中身上并不鮮見,他們逐漸成長,開始有意識地反抗長久以來在成長中父權的壓制,于是在文本中以各種隱喻的方式呈現一種撕裂的反抗。但這樣貌似具有隱喻性的寫作雖可作為階段寫作的成果,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求學并步入社會,作者應該更深入生活現場,透過現在看似深奧與深刻的“寓言”看到生活的真實面貌,改變二元的思考方式,切實了解生活本身的面貌,使真正的生活成為筆下的主要對象。當然對于這個年齡且呈現出這樣寫作風格的作者來說這樣的要求還太早了也太高了,但是我相信隨著作者閱歷不斷豐富,若他依然保持著對待文學創作的熱情,一定會寫出更多令我們感到驚喜的作品。
鄭皓文另一篇小說《山火》,語言非常輕松灑脫,這是我非常喜歡的。比如小說開始兩人對話,在節奏的把控上就很節制和有分寸。“我給你開開燈,給你發個電報。她笑了幾聲……”這個對話和人物動作之間的空隙穿插很自然,對于成熟的寫作者都是比較難得的。還有“她說,你把語音掛了,我給你錄一段。不會啊這么明顯。”這樣生活氣息濃郁的對話,與《腥湯》對比就輕松自然很多,這兩個作品不知道哪一個寫得更早一點,但《山火》顯出一種更放松的寫作狀態。不過,《山火》存在與《腥湯》相同的問題,就是作者有時候會忽然停頓下來描寫某個場景或者心情,可能是作者本人興之所至吧。但興致不能作為一個完整作品的寫作標準,寫完作品需要反復修改,與小說本身無關的細節描寫再精彩也要學會放棄。
這篇小說依然是一個充滿著實驗色彩的先鋒小說,鄭皓文試圖在小說之中再創造一個故事,是關于小說的小說,我們會稱之為“元小說”。在小說里鄭皓文提到了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阿萊夫》,我估計作者也讀了很多這位阿根廷小說家的具有獨特空間意識和思維路徑的小說,顯然在他自己的小說里也采用了一種先鋒小說敘事策略。但我們深究這個故事,除了它敘述方式的獨特性——故事中套著故事,與一個名為“幽靈”的人進行思想對話,故事中引用典故等之外,其核心情感依然是青春題材的。這個現象很有趣,就是作者本身的生活經驗就這么多,但他開始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派作品,于是他借用了這樣一種形式來寫自己的生活。這樣的寫作方式當然是被允許的,也是很多人剛開始寫作時會采用的方式,但其實也是曲折的甚至是徒勞的,其實就是沒有必要。作者目前只是看到了西方先鋒作品形式的新鮮,卻沒有看到形式本身是要與內容相聯系的,現在呢,被割裂了。我在這篇小說里只看到了敘述本身,沒有看到更多的東西,這是遺憾的地方。西方現代派的形式也依然是要為內容服務的,比如說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寫法,現在很多寫作新人還在模仿,但是學一個形式看似是容易的,卻沒有意識到這一文學敘述形式其實是普魯斯特在表達他自己對于時空的特殊認知,而不是單純的一個散漫的形式再將自己的任何東西裝進去。以上是我對鄭皓文小說的看法與建議,總的來說,鄭皓文是一個非常有天分與潛力的寫作者,我相信,如果他未來還有寫作的愿望,一定會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現,這是一定的。
下面我來談一談吳春笑的創作。《驢伙計》是一個篇幅比較短的小說,但是可以看出作者豐富的寫作經驗和成熟的寫作技巧,我認為這也是年輕作者們應該學習的。作品非常完整,結構很工整,詳略得當,實際上是一篇幾乎沒有修改余地的作品,但也是因為這樣,這篇作品才有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故事沒有大的波瀾與起伏,功能落腳在抒情上,它顯得更像一篇散文,而不是小說。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應該是可以將一個在日常生活中業已熟知的主題煥發出生機的,是要找到平凡主題中新的敘事角度的,當然,這是很不容易的,但這正是一個作家得以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短篇小說應該是喚醒讀者沉睡的壞死的日常經驗,它面向的是人類精神性的考察。我說了這么多,并不是說不能寫像《驢伙計》這樣主題的作品,而是我們要找到文中所講述的人與動物情感密切連接的新的敘事可能,現有的這個故事并沒有超越我對生活的一般的認知經驗,它是可被預期的,也就沒有那么高的審美價值了。
另一篇小說《老高的瓜田》,其實也有相同的問題,但仍可以看出吳春笑本身的創作實力,沒有短板,也沒有硬傷,起承轉合處理得嚴絲合縫,高低起伏也都是精心設計過的,呈現一個完整故事的能力是具備的,但欠缺的是更吸引人的素材和進入素材的新穎視角。平鋪直敘地將一個故事講完是容易的,但沒有真正打動人的點,于是再有力的表現、再堅實的地基,可能也淹沒在一個相對平庸的故事構造里,這是讓人遺憾的。我給吳春笑的建議與前面年輕人的意見相反:他們需要收著寫,吳春笑需要放開了寫,大膽地寫,瘋狂地寫,跳出自己固有的寫作思路與方法,將一個故事推向一種極致,或許能夠呈現一種全新的寫作面貌。
接下來我來說說孟憲華的稿件。孟憲華是《天津文學》的老作者了。這次改稿會孟憲華送審了兩個作品,一個詩歌、一個散文,我放在一起說說感受。首先,散文《中秋,情滿故鄉》開頭的詩歌“搖著輪椅,畫出一個大大的圓”“母親是我的故鄉,我是母親的月亮”等都是很有詩意的,這是孟憲華詩歌功底的一個呈現,但進入到散文的正文,問題出現了——孟憲華的散文更像被是她稀釋過的詩歌。詩歌的抒情性在語句與語句中間連接自有的一種情感的節奏、韻律,但她的散文空有情感的語句,成了一個空殼,情感無法附著,顯得輕薄沒有說服力。我們一直都說散文是“形散神不散”,但顯然孟憲華這篇散文神也散了她想在這篇散文中表達一種家鄉的新變,這種姿態和意識是向上的,應該予以鼓勵,但沒有尋找到一些可供依附的日常意象來進行描寫,空泛的感情表達是碎片化的,空喊口號,也沒有獨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表達。近幾年編輯部常會收到一些寫景抒情的散文,散文以家鄉風物或是親情回憶為主,在這些散文中,尚可發表的是一些在語言表達或者內容上還算有些趣味、看頭或者是有獨特經驗的。“真實表達”只能作為散文寫作最一般性的要求,相較于小說,散文貌似寫作門檻低了一些,但其實,這一文體對于寫作者自身的情感與文化底蘊的要求更高,寫出一篇與眾不同的散文需要穿透人生經驗,直抵精神和靈魂的深處,在沒有戲劇沖突(當然也可以有戲劇沖突)的文字中間,我們要看到一種全新的表達、新的認知,這就要求散文寫作者,不能僅將目光停留在生活的表層描寫生活中可觸及的東西,更要試圖去挖掘那些不可觸及的、深邃的、尚未為人所知的認知。寫散文不能偷懶,寫景抒情只要有一定文字基礎都能做到,但怎樣脫穎而出,怎樣寫出不一樣的情感,這是需要我們反復去思索的。很多散文作品寫得太老實了,本本分分,無功無過,這反而才是最大的問題。在這次改稿會收集上來的作品中,也幾乎都是這樣的問題,寫景散文寫得像景點的說明文字,這其實恰恰說明了在散文寫作中,我們欠缺智性的思考與生活的沉淀。散文的主題可以有很多,生活的種種都可以進入散文寫作,它考驗我們的思考力與鑒別能力,考驗我們對生活本身的轉譯能力和駕馭能力,需要閱歷,更需要仔細的觀察,許多作者都與經驗有著豐富的寫作經驗,欠缺的反而是寫作能力與經驗之外的更深入的思考與大膽的嘗試。
孟憲華的詩歌《打卡魏氏莊園》我認為比散文要好。在孟憲華的詩句里,其實總能發現一些閃光的句子:“當人煙和時光已經離去建筑還在說話”“今日,我要省略一場雪趕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霧霾前再把莊園的每個角落審視一遍找到那熟悉又陌生的笑聲”。但是,問題也很明顯,題目和詩句都有一種不穩定的感覺,俗與雅并存,不協調。比如題目中“打卡”這個詞很當代和隨意,但是詩歌本身的風格卻典雅的,題目拉低了整體的閱讀感受。比如《第二次踏進魏氏莊園》中“莊園的故事高懸成門口的紅燈籠照亮我們的背影。是在告訴我們大起有大落還是財與才哪個重要”也是這個問題,前半句與后半句有落差之感,詩歌語言要凝練更要講究。《生活在魏氏莊園的紫藤》中這一句“多好啊,能在一起生活下去”,這種口語式的寫法就好一些,雖然仍然淺白,但是顯得自然。寫作詩歌應該好好打磨與凝練字句,所以寫作過程要緊張起來,要“繃”起來,也就是寫作的時候要肌肉緊張,不要過于松弛,不然會給人漫不經心的感受。這一組詩歌我認為思路是好的,從不同角度寫了一個地方給你的感受。《天津文學》曾經發表過女詩人安琪的一組寫文物的詩歌《文物記》,從取材的思路上有相似的地方。但相比孟憲華可以更深入素材內部,而不是簡單地將物與情聯系起來,要把這個地點作為一個支點,撬動更多的靈感,而不是就事論事,和你的散文創作一樣,不要太依賴切身的某些感受,要充分發揮想象力,要讓詩句飛翔起來。再回頭看看我認為寫得靈動的詩句,就明白其中的緣由了。
河北區報送的龐駿是一位年輕作者,其詩作很冷峻、尖銳,詩歌有畫面感,也有敘事,有自己的風格。他的詩歌有智性的書寫,顯然是有文學專門訓練的,比如開頭就寫:“將敘事進行下去已經毫無意義了”,這首先就否定了敘事的可能,那么他的詩歌就沒有敘事了嗎?不僅沒有還相當豐富,“他倚著黑暗中的一面墻,手指像蛇一樣一圈圈纏在打火機上,我敲了敲他的手指,火熄了”這顯然都是敘事。我認為這是一個詩人應具備的也是可以保留的,但龐駿的問題出在,他掌握了大量的或抽象或智性的語詞,他過于信賴這些語詞了,詩歌中出現這些語詞,會對他的詩歌的深度與獨特性造成破壞——“不安”“不祥”“神像”“靈魂”“欲望”還有各種神話中的典故等等。龐駿在國外求學,應該會讀到很多西方的詩歌作品,于是他的詩歌里有翻譯腔,也會使用很多抽象的高級的詞語,這些詞語本身就帶有很多精神性的含義,但這些含義限制了他的詩歌表達。如果用自己的母語寫作,就要重新梳理自己的語言表達系統,用母語體系去訓練思維方式,回到自己的語境中來,翻譯腔容易讓詩歌顯得有格調,但同時也會使詩歌空洞。要學會降低自己的身份,現在作品中的高級感都是詞語賦予的,不是詩歌本身的,要忘掉自己強大的知識背景,重新審視自己的表達,學習自己的母語,這是我對你的建議。
這次改稿會,令我非常驚喜的是看到區作協報送的小作者們的詩歌作品,清新、純凈、靈動。一方面是孩子們還處在成長階段,沒有過多受到外界各種聲音的干擾,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區作協在文學新人培養上的良苦用心。我簡單地點評一下小作者們的作品:一個是付婧翚的兩首詩歌,充滿詩意的想象,這肯定是寫詩歌最需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質。她的詩歌并沒有追求刻意的押韻,但在韻律和節奏上卻有著天然的語感,這可能是本身的天分帶來的。“斜陽下的傍晚真好心寧靜得像一座小島”,這樣的詩句令我的心也寧靜了。付婧翚的語言是很質樸沒有雕琢的,也因此顯得很高級,但不同于成人寫作時要刻意追求一種質樸,但她的作品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首《晚風》用了重復的寫法,第一句“傍晚的風很柔很輕”這句話重復了三遍,當然不是不可以,但詩歌重復的寫法顯得像歌詞,詩意的濃度會降低,盡量減少這種重復性的手法。第二首《桂花香》,前五句都可以,保持著質樸的特色,但是像“縈繞”“芬芳”“春耕 夏耘 秋收 冬藏”這些詞語要盡量避免多次使用,《晚風》這首里面也有,這些本身就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使用得過多會落入一種范式的淺俗,拉低詩歌的格調,在作者這個年齡,學著盡量用自己的語言去描繪你眼中的世界。
楊顗諾的三首詩歌,因為年齡比付婧翚大,一下就看出她思考問題的深度了。第一首《我是什么》更像是一個小小少年不斷確認自己的身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宣言,我認為其作為詩歌的價值因此就立住了。再看其中的“我認為”“他們覺得”“你覺得”“有人說”“也有人說”“而我更希望自己是”等等,這種不斷的視角轉化相當精彩,也讓人耳目一新,尤其最后作者反而不愿意成為世俗生活中所認定的成功者,其實也反映這一代少年對于成人世界所謂的那套成功學的抵制與反抗。《耳朵》很容易就讓人想到了楊顗諾在這個年齡所要面對的成長問題,《氣味》則是她對于世界認知的一種個人視角——通過氣味來辨識。這兩首詩,一首是通過聽覺,一首是通過視覺,這是一個詩歌創作者邁向成熟所應對世界敏銳感知的表征,她都做到了。如果要對她提出建議的話,我認為是多讀書,打開視野,真正去感受世界,不斷歷練,如果寫作的動力能夠一直持續下去的話,生活的歷練會給她更多的素材與方法,她也會慢慢解鎖更多詩歌寫作的有趣的技巧、題材和情感表達,我對她的寫作還是充滿期待的。
于樹漫的詩歌,或許需要從另一個視角去審視,就是兒童的視角。但是,用于樹漫的詩歌與前兩位小作者的詩歌作對比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之處,作為一名成人寫作者無法再回歸到最原始的童真狀態,成人的想象是嫁接在刻意壓低的成人視角上的了。做個比喻,有點像家長和自己的孩子溝通時,刻意用那種孩子的聲音說話,這是這組詩歌給我的一個感受——就是它顯得有點過于壓低自己了,不自然了。比如《稻草人》:“稻草人,像個大哥哥……”這個像一個家長的口吻;《含羞草》里面的“你好啊你好啊”就是一個成年人在模仿小孩子說話;《天上的雪》“落啊落落啊落”這種重復的囈語,都顯得有點過于稚嫩了。與前面提到的一樣也要在詩歌中避免去刻意重復同一句話。于樹漫是一個很成熟的兒童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但我認為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需要一種勇氣,就是要提高難度,前面我們看到了14歲的孩子已經可以寫出這么成熟的詩歌,我們的成人兒童文學創作者也應該放開自己的手腳。孩子們現在起點很高,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早就需要更為深邃的知識與認知補充了。如果從非兒童文學編輯的角度來給這組童詩提意見的話,我認為還應該更松弛,更開闊,更有深度。不應拘泥于兒童視角,不要刻意去營造那種稚嫩的氛圍,比如《孤獨的云》,我認為這是一首很好的詩歌,但不一定非要以童詩的視角去看待它。
責任編輯: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