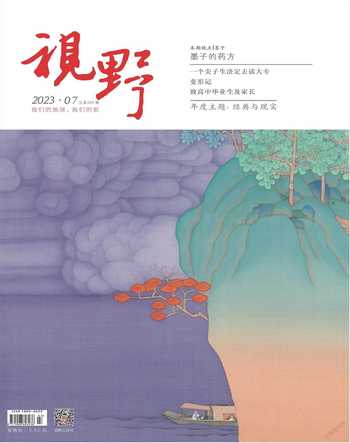最初的漢字
蔣勛

漢字有最少五千年的歷史,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尊,器表上用硬物刻了一個符號——上端是一個圓 ,像是太陽;下端一片曲線,有人認為是水波海浪,也有人認為是云氣;最下端是一座有五個峰尖的山。這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漢字,比商代的甲骨文還要早。
我常常凝視這個又像文字又像圖像的符號,覺得很像在簡訊上或Skype上收到學生寄來的信息。信息有時候是文字,有時候也常常夾雜著“表情”的圖像符號。一顆紅色破碎的心,代表“失望”或“傷心”;一張微笑的臉,表示“開心”“滿意”。這些圖形有時候的確比復雜啰嗦的文字更有圖像思考的直接性。漢字造字法中本來有“會意”一項。“會意”在漢字系統中特別可以連結文字與圖像的共同關系,也就是古人說的“書畫同源”。
人類使用圖像與文字各有不同的功能,很多人擔心現代年輕人過度使用圖像,會導致文字沒落。我沒有那么悲觀。漢民族的文字與圖像在漫長文明中相輔相成,彼此激蕩互動,很像現代數字信息上文字與圖像互用的關系,也許是新一代表意方式的萌芽,不必特別為此過度憂慮。
文字與圖像互相聯結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其實常常見到。例如廁所或盥洗室,區分男女性別時當然可以用文字,在門上寫一個“男”或一個“女”。但在現實生活中,廁所標志男女性別的方法卻常用圖像而不用文字:女廁所用“耳環”“裙子”或“高跟鞋”,男廁所用“禮帽”“胡須”或“手杖”;女廁所用“粉紅”,男廁所用“深藍”。物件和色彩都可以是圖像思考,有時候比文字直接。
我在臺灣先住民社區看過廁所用男女性器官木雕來區分的,也許更具古代初民造字之初的圖像的直接性。我們現在寫“祖先”的“祖”,古代沒有“示”字邊,商周古文都寫作“且”,就是一根男性陽具圖像。對原住民木雕大驚小怪,恰好也誤解了古人的大膽直接。山東莒縣凌陽河大汶口黑陶尊器表的符號是圖像還是文字,是一個字還是一個短句,都還值得思索。
太陽,一個永恒的圓,從山峰云端或洶涌的大海波濤中升起。有人認為這個符號就是表達“黎明”“日出”的“旦”這個古字。元旦的“旦”,是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一直到今天,漢字的“旦”還是有明顯的圖像性,只是原來的圓太陽為了書寫方便,“破圓為方”變成直線構成的方形而已。
解讀上古初民的文字符號,其實也很像今天青少年玩的“火星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數千年的漢字傳統一路走來有清楚的傳承軌跡,一直到今天的“簡訊”“表情”符號,并沒有像保守者認為的那么離“經”叛“道”,反而很可以使我們再次思考漢字始終具備活力的秘密(有多少古文字如埃及象形文字、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早已消失滅亡)。
漢字是現存幾乎唯一的象形文字,“象形”是建立在視覺的會意基礎上。我們今天熟悉的歐美語言,甚至亞洲的新語言(原來受漢字影響的韓文、越南文),大多都成為拼音文字。
在歐美,常常看到學童學習語言有“朗讀”“記誦”的習慣,訓練依靠聽覺掌握拼音的準確。漢字的語文訓練比較沒有這種課程。漢字依靠視覺,在視覺里,圖像的會意變得非常重要。圖像思考也使漢文化趨向快速結論式的綜合能力,與拼音文字靠聽覺記音的分析能力,可能決定了兩種文化思維的基本不同走向。
大汶口黑陶尊上的符號,如果是“旦”這個古字,這個字里包含了“日出”“黎明”“朝氣蓬勃”“日日新”等許許多多的含意,卻只用一個簡單的符號傳達給視覺。漢字的特殊構成,似乎決定了早期漢語文學的特性。一個“旦”字,是文字,也是圖像,更像一個詩意的句子。
漢語文學似乎注定會以“詩”做主體,會發展出文字精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短詩,會在畫面出現“留白”,把“詩”題寫在“畫”的“留白”上,既是“說明”又是“會意”。
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都是鴻篇巨制,詩里貫穿情節復雜的故事;古印度的《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達》動輒八萬頌十萬頌,長達幾十萬句的長詩,也是詭譎多變,人物事件層出不窮,習慣圖像簡潔思考的民族常常一開始覺得目不暇接,眼花繚亂。
同一時間發展出來的漢字文學《詩經》卻恰巧相反——寓繁于簡,簡單幾個對仗工整、音韻齊整的句子,就把復雜的時間空間變成一種“領悟”。漢字文學似乎更適合“領悟”而不是“說明”。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僅僅十六個字,時間的逝去,空間的改變,人事情感的滄桑,景物的變更,心事的喟嘆,一一都在整齊精簡的排比中,文字的格律性本身變成一種強固的美學。漢語詩決定了不與鴻篇巨制拼搏“大”的特色,而是以“四兩撥千斤”的靈巧,完成了自己語文的優勢與長處。
松下問童子,
言師采藥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處。
漢語文學最膾炙人口的名作,還是只有二十個字的“絕句”,這些精簡卻意境深遠的“絕句”的確是文化里的“一絕”,不能不歸功于漢字獨特的以視覺為主的象形本質。
(依依摘自上海三聯書店《漢字書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