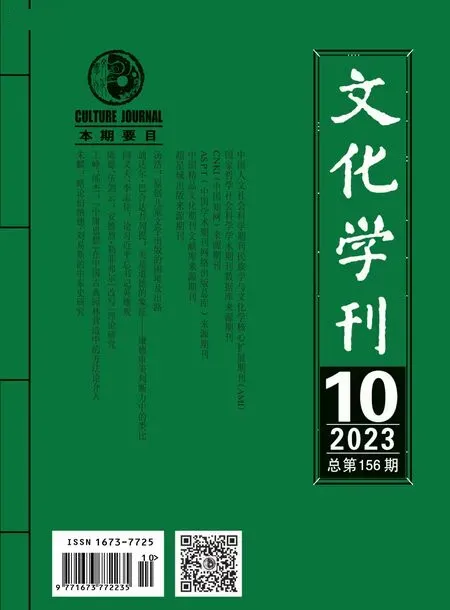略論伯納德·劉易斯的中東史研究
朱 麟
一、引言
“中東” ,是歐洲人對于地中海東岸廣大地區的稱呼,意思是距他們中等距離遠的東方。 現今稱為 “中東” 的地方,如果以耶路撒冷為圓心,大致可以包括四個圈層的國家。 最內層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向外是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然后是土耳其、伊拉克、沙特等阿拉伯半島諸國以及埃及,最遠的是伊朗。
中東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極具多樣性的語言、宗教、文化而著稱,同時也是當代世界政治經濟領域的焦點之一。 因而,西方史學界歷來重視對于中東歷史文化的研究。我國對中東史的研究自新中國初期就已起步,經過70 余年的發展,在研究機構建設、人才培養以及研究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隨著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尤其是 “一帶一路” 倡議的全面推進,中東在我國對外交往中將會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進一步加強對中東歷史文化的研究,不僅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世界史其他研究領域也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在開展自主研究的同時,多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視野、開拓思路。 從1789 年拿破侖遠征埃及算起,西方國家對中東的殖民滲透超過兩個世紀。 出于殖民滲透和統治的需要,其對中東的研究起步也很早,幾乎與殖民史同步,而且掌握了大量一手史料,成果可謂汗牛充棟。雖然西方學者的研究不乏西方中心論等傾向,但也有很多有益的學術成果值得借鑒。
二、國內對伯納德·劉易斯中東史觀研究的現狀
談到20 世紀西方的中東史研究領域,伯納德·劉易斯是位不得不提的人物。 劉易斯出生于英國倫敦的猶太人家庭,后移居美國。 他精通多國語言,一生致力于中東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是少數最早接觸奧斯曼帝國檔案的西方學者,90 多歲仍筆耕不輟,活躍在學術界。 劉易斯不僅著作等身,成就卓越,而且極富個性,對中東歷史文化有著自成體系且獨到的理解,堪稱學術大家。 一般認為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斯蘭史、奧斯曼帝國史以及西方與中東關系史這三個方面,但實際上就中東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幾乎所有重要的方面以及幾乎所有時期而言,劉易斯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論述。
國內中東歷史和文化相關研究中不乏引用劉易斯的著作和觀點,但真正對其著作、史學思想、研究方法等進行全面深入探討的則少之又少。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常玲梅2010 年的碩士學位論文《伯納德·路易斯的中東史觀》是目前國內專門針對劉易斯的著作及史觀進行相對系統梳理的唯一作品。 但如作者所言,由于篇幅有限,也僅能從文化史觀、政治史觀、民族史觀三個方面做論述,旨在對其史學成就作系統的梳理。 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義的《超越文明沖突論:伯納德·劉易斯的中東史觀》(《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6 期),從 “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 “奧斯曼衰落與土耳其革命” “文明沖突” “為歷史辯護” 幾個方面對劉易斯的史觀做了介紹。 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專業楊烔2021 年碩士學位論文《論 “東方主義” 之爭:以薩義德與路易斯為中心》從著名的 “東方主義” 之爭的角度對劉易斯的相關觀點進行了較為深入闡述,也是目前國內以比較方式較為深入地研究劉易斯史觀的唯一作品。 另有個別文章就其某一特定著作或特定觀點進行評述,包括吳冰冰的《學術與偏見——從〈錯在哪里?〉看伯納德·劉易斯的中東史觀》(《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1 期總第96 期),王宇浩的《試析美國伊斯蘭研究中的 “猶太因素”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1 月第1 期),《在美國研究伊斯蘭的猶太人》(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09 年3 月)。 吳冰冰和王宇浩并非專業的歷史學者,在評述的時候更多關注的是劉易斯的猶太裔背景,以 “其母校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本來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劉易斯也曾為政府部門直接工作”[1]50,認為其學術研究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因而從政治立場角度對其歷史著作和史觀予以批判,難免有失偏頗。 還有幾篇文章簡要介紹了劉易斯其人其作品,包括魯能的《從傳統到現代——〈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讀后感》(《華夏文化》2013 年11 月),羅秉祥的《文明的沖突,或無知的沖突? ——一個基督教務實論的評論》(《基督宗教研究》2004 年12 月)。 常玲梅在其碩士論文中曾表示,從整體上看,國內對于劉易斯中東史觀還處于介紹、引用階段, “總結、分析和深層探究是不夠的”[2]。 這種狀況在她的碩士論文發表十余年之后依然沒有改觀,至今能找到的國內介紹、評析劉易斯中東史觀的文章也幾乎只有上述寥寥幾篇。 劉易斯豐富的著述中,翻譯引進國內的也僅有《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新版本譯為《中東兩千年》)《歷史上的阿拉伯人》《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穆斯林發現歐洲》屈指可數的這幾部,這不能不說是遺憾。
三、伯納德·劉易斯中東史研究的特點
從劉易斯的著作中,可以初步總結出其中東史研究有如下特點:
研究結論和成果基于豐富的一手史料。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缺乏史料的歷史研究就好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第一手史料的缺乏一直是制約我國包括中東史在內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英國在中東長期的殖民統治使得劉易斯和他那一代的英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大量一手史料。 歐美、中東各國圖書館、檔案館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尤其是他曾花了一年的時間游歷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查閱史料。 其時,恰逢土耳其當局決定放寬對奧斯曼帝國檔案的查閱申請,劉易斯有幸成為少數最早接觸奧斯曼帝國檔案的西方學者之一。 作為西方歷史學家,他可能是第一個。 奧斯曼帝國檔案跨越數個世紀,包含上百萬份各類檔案和記錄,尤其是有大量地方性檔案, “這些檔案的開放不僅極大地改變了西方人對奧斯曼帝國的研究和理解,在更廣泛意義上也改變了對歐洲歷史的理解”[3]90。 正是基于豐富的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使得他的著作和觀點有著很強的說服力,令人信服。 也正是由于幾乎沒有學者能在中東史料的掌握上與劉易斯相抗衡,對于劉易斯史觀的批判大多只能就觀點本身從邏輯甚至政治立場等角度入手,這無疑降低了這些批判的力度。 劉易斯在史料整理方面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出版過中東史料集A Middle East Mosaic:Fragments of Life,Letters and History、Islam: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掌握阿拉伯語、突厥語、波斯語等小語種的研究人才的匱乏,是制約我國中東史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而與他那一代其他優秀的中東學或者東方學學者一樣,劉易斯對史料的解讀是基于其天才般的語言能力的。 根據其自傳Notes on A Century 的記述,除了作為母語的英語,他至少還精通或熟練掌握意大利語、法語、德語、俄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拉丁語、希臘語。 同時掌握東西方多種語言使得他能夠直接閱讀各國原始史料。 在廣泛查閱東西方史料的基礎上,不僅能夠從傳統的西方視角觀察中東,更能夠從中東視角觀察中東、回望西方、審視中東與西方的關系,從而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結論。 比如,他認為 “伊斯蘭教因征服而傳播” 這一說法是誤導性的。 雖然兩者在時間上平行進行,征服者也的確用諸如輕徭薄賦等形形色色的誘因來吸引征服地的民眾皈依伊斯蘭教,但并沒有用武力強迫他們入教, “阿拉伯征服者最原始的作戰目標,并不是借由武力來樹立伊斯蘭教信仰” 。 至于說阿拉伯征服者試圖將征服地的臣民同化為阿拉伯人則更是難以成立。 恰恰相反, “頭幾代的征服者,在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之間維持嚴格的社會分際,不容許新進的穆斯林和自己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享有完全的平等”[4]。
劉易斯的研究涉及中東幾乎所有的歷史時期以及所有重要的主題。 他的著作不僅有《中東兩千年》這樣的通史作品,也有《現代土耳其的興起》這樣的國別史作品,以及《歷史上的阿拉伯人》這樣的民族史作品,更有大量就具體問題進行研究探討的專題著作,涉及包括西方文明對中東的影響、東西方文化沖突、中東現代化、中東政治形態的演進、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伊斯邁爾教派、種族與奴隸、阿薩辛派、16 世紀巴勒斯坦城鎮的人口與稅收,等等。他甚至還寫過一本關于外交與政治阿拉伯語的小冊子。 劉易斯打破傳統的政治史觀,注重從社會文化史角度研究中東歷史,并在這些著作的基礎上構建起了一套自成體系的關于中東歷史和文化的解釋體系。 他從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推演出文明沖突論作為重要的解釋手段。 這一理論因 “9·11” 事件而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但也在很大意義上被流行化和簡單化了。 實際上, “同亨廷頓明顯的國際戰略指向不同,劉易斯在文明沖突論上的觀點更多地體現了一種對世界事務的先知性判斷”[5]。 而他關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衰落和危機的論述則被認為是對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貶低, “似乎有意忽視了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1]49。 但事實上,劉易斯從未否認阿拉伯或伊斯蘭文明的歷史貢獻,而是重在探究為何近代以來中東會落后于西方,中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以及從穆斯林應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能得出怎樣的結論。 這些探索和研究緊緊立足于歷史學,力圖在史料的基礎上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得出具有啟示意義的歷史學成果。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必要對劉易斯的中東史觀做全面的歷史學的研究和理解。
在研究方法上,從文化層面入手,立足于東西方文化比較,以文化的差異和沖突來解釋歷史是劉易斯中東史研究的重要范式。 劉易斯不僅對文化表象進行比較,更注重探究文化差異表象背后的歷史原因及其影響。 這使得他能在對歷史本身做出強有力解釋的同時,更有可能對現實政治做出睿智的洞見。 他的著作尤其善于從基本的概念解析入手,抽絲剝繭,由厘清差異而分析原因,進而探討差異和沖突的影響,可謂由微觀視角入手而照見宏觀景象。 比如,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方傳統認為宗教和政治權威,即教會與國家是不同的,可以而且應當分離。 這一原則可以追溯到《圣經》的教誨,即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基督教在其發展早期遭受羅馬帝國的迫害,使得更多基督徒相信這種分離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因而,中世紀以來,無論是爭斗還是合作,教會與國家在西方總是兩種不同的權威和機構。 但這種政教二分法概念,在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中東傳統看來則是難以理解的。 伊斯蘭教經歷了與基督教完全不同的發展歷程,其興起是伴隨著一個強大的阿拉伯帝國的誕生,帝國也因伊斯蘭教而更加興盛。 因此,在穆斯林看來,教會與國家是一體的,無法分割。 作為各自文化基礎的兩個宗教完全不同的發展經歷造成了兩種文化對于宗教與國家的關系完全不同的理解。 到了近代,這種文化差異的影響在于:當西歐各國已經普遍走上政治世俗化發展道路之時,奧斯曼帝國的現代化努力卻一直受困于如何處理伊斯蘭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 事實上這一問題也一直困擾著從奧斯曼帝國治下以及西方殖民統治之下獨立的中東各國。 在劉易斯看來,一戰后凱末爾領導下堅定世俗化的土耳其和1979 年革命后全面回歸伊斯蘭傳統的伊朗代表了現今中東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演進方向。
以史為鑒,從歷史關照現實是很多歷史學者的理念。 劉易斯也承襲了西方對中東研究的現實關照傳統。 作為中東研究領域的權威,劉易斯從不避諱表達自己對的觀點,無論是學術的還是現實政治的。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劉易斯與其他中東專家一起被邀請到華盛頓就局勢提供建議。當時,絕大部分專家認為美國即將投入的將是一場重大而艱難的戰爭,可能會是 “另一個越南” ,甚至可能 “開啟一個東西方關系的新時代” 。 劉易斯則持極其相反的觀點,認為這將是一場 “迅速、低成本且容易” 的戰爭[3]324。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9·11事件” 之后他的作品被封為中東研究的圭臬,他本人成為白宮的座上賓,各大媒體競相采訪他。 這些關注在為他贏得廣泛贊譽的同時也引來了不少非議。 2004 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指責他主導了小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尤其是入侵伊拉克。 他本人則在自傳中對此專門做了回應。 而他與賽義德關于 “東方主義” 的論戰,更是被稱為 “學術界的中東戰爭”[1]50。 但是,不論對現實政治的觀點如何,劉易斯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位歷史學者。 因此, “重新認識劉易斯的歷史學家身份,是中東研究的一個必要課題”[5]。
跳出具體的研究領域,劉易斯也嘗試站在更廣闊的視角審視歷史研究及歷史寫作本身。 與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劉易斯也追求蘭克式 “如實直書” 的真實性,力求用他的著作反映歷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的真實面貌。 然而,他發現這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 歷史事件從發生、記錄,到敘述、解讀,每個環節都可能造成偏差。 歷史學家尋找答案的過程不僅面臨重重困難,而且非常痛苦。因為人們總是會受到極大地誘惑,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而不是實際的情況去講述歷史。 劉易斯把歷史分為三種:文獻和傳統中記載的歷史,它構成族群的集體記憶,但常常受制于族群領袖的有意選擇。 學者發掘的歷史,即那些因學者的研究而重見天日的事件和人物。 第三種是為了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或民族主義目的而構建的歷史。 這類歷史主要取材于前兩種歷史,但圍繞其特定的目的對素材進行重新構建、解讀甚至是編造[6]。 通過對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本身性質的探討,劉易斯意在展示,歷史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記錄和理解,更是人類重塑自身命運的工具。
四、結語
劉易斯的中東史研究涵蓋領域廣泛,史料來源豐富,觀點鮮明犀利。 從歷史學術的角度將其研究成果更多地介紹引進到國內,并做全面深入的探討,取其合理可用之處,將有助于推動我國的中東史研究。 尤其是將其帶有很強社會文化史氛圍的研究成果與傳統的政治史研究相結合,將有利于中東整體史研究的開展。 方法論上,其多角度的研究視角、文化比較和沖突的解釋范式,對于我國世界史其他領域乃至中國史的研究也都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比如中國與西方關系史研究、中國與奧斯曼近代化比較研究等等。
從中東史學科建設角度而言,我國應在推動對外學術交往的基礎上,注重一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翻譯出版,為學術研究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 同時,應加強跨學科人才的培養,尤其是掌握多種語言的研究人才的培養。 鼓勵更多研究人員直接閱讀原始史料,從對原始史料的解讀中得出更具原創性的研究成果,為世界中東史研究做出中國貢獻,以高水平的史學研究成果服務于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構建和 “一帶一路” 倡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