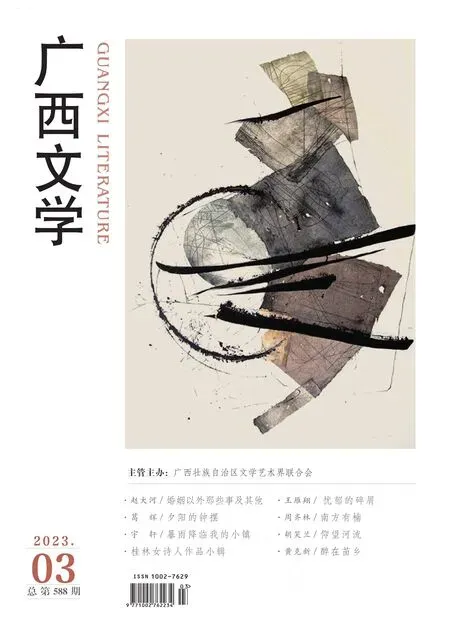遙想花山
潘 琦
我無數次去過花山,觀賞那千古崖壁畫。
20世紀70年代,我應朋友的邀請,乘坐木船第一次走近花山。清晨,太陽剛露出山頭,我們便從寧明縣城明江碼頭出發,沿江兩岸奇峰挺拔,峭壁對峙,草木蔥蘢,景色迷人。小木船慢悠悠地行駛了四個多小時才到達花山。我們來不及休息,便迫不及待上岸徑直去觀賞慕名已久的崖壁畫。順著一條小徑往花山走去。大概平時來的人不多,小徑雜草叢生,坎坷不平,四周靜極了,顯得有些冷落荒涼。走到花山前的一塊平地上,朋友說,這是看崖壁畫的最佳觀賞點。我舉目仰望,映進眼簾的是一幅幅用赭紅色顏料繪成的各種人物、動物和器物的畫像,畫面壯觀,圖形抽象,意境奇特,引人入勝。也許是由于我的一顆心完全沉浸在一種莊嚴肅穆的情愫中,在驚奇地仰視著每一個神秘的符號和畫面之后,和朋友拍了幾張照片,就心滿意足地匆匆返回住地了。事后回想起來感到十分遺憾,雖然走近了花山,看到它偉岸宏大的身軀,撫摸了它蒼老的面容,觀賞了那生動而古樸的神奇壁畫,但沒有從容不迫地詢問這千古壁畫究竟為何時、為何人、為何畫,用何顏料畫,畫的內容和意義是什么,等等,甚至沒有很好地觀賞萬山叢中花山巍嶷的整體景象和浩浩的左江賜予它的自然本色,沒有聽聽人們講述花山古老的傳說。
后來我查閱了關于花山的史料和諸多專家學者撰寫的論文,才知道花山崖壁畫有許多撲朔迷離的問題,人們還在不斷地探索,還未能輕而易舉揭開它那神秘的面紗。想想那時我是多么幼稚,只看到花山崖壁畫宏大的畫面,卻沒想到它遼遠神秘的歷史。不過,如果把花山崖壁畫比喻成一本書,我只看到書的序言,便在內心燃起一種刨根究底的幻想。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便迷上了花山,一定要找機會重覽花山,認真品讀花山,補上這一課。
機會像猜透我的心思一樣,20世紀80年代末,我調到南寧地委工作,花山就在身邊。那年,春暖花開時節,我們乘坐一艘游船順左江流水而下,從上游龍州縣巖洞山崖到下游的扶綏縣青龍山崖,實地考察沿江崖壁畫。喀斯特地貌使左江兩岸奇峰聳立,層巒疊嶂。連綿起伏的山峰,蒼松翠竹綠茸茸地遮了一層繡幕,一派雄偉的景象。近岸的懸崖峭壁上分布著一處處古代巖畫,大家不顧乘船的疲勞,仔細觀察每處巖畫,爭先恐后地拍照。一路上請隨行的專家為我們講解:左江崖壁畫綿延長達二百多公里,目前已發現崖壁畫分布于七十九個地點一百七十九處,形成一道規模壯觀、氣勢恢宏的崖壁畫長廊,被稱為“左江崖壁畫”。花山崖壁畫以其規模宏大、畫像眾多、種類齊全而舉世聞名,成為左江崖壁畫的代表。壯語稱崖壁畫為“岜萊”,意為崖壁上有畫像的山。花山臨江一面金字塔形的崖壁上,留存可辨認的畫像一千八百多個,以人物居多,小的人像只有三十厘米,最高的達三點五米,形體高大雄偉。據研究,花山崖壁畫是戰國至兩漢時期的壯族先民所創作、繪制的,距今已有兩千多年。崖壁畫用的赭紅色顏料,據現代科學方法鑒定、分析,是赤鐵礦粉,以動物膠調和,這和我國古代使用的顏料、黏合劑相吻合。至于這些畫像是怎么描繪上去的、具體內容等諸多問題,國內外專家學者仍在探討之中。
我坐在左江畔上,靜靜地看著緩緩東逝的江水,眺望著遠處綠樹掩映的村寨,聽江畔那肥壯牛羊啃草聲,山花盛開散發陣陣芳香,水光山色相互輝映……一切是那么寧靜、優美、古樸、和諧,令人仿佛進入了神話境界。我遙想花山遠古的景象:壯族先民們一代接一代地在左江兩岸生息繁衍。時而生產豐收,人丁興旺,生活平安;時而災禍降臨,生產歉收,饑寒交迫,家破人亡。人們長期生活在禍福難定、吉兇未卜的環境中,對于變幻莫測的大自然及社會矛盾又缺乏正確的認識,只有幻想祈求上天的恩澤保佑。于是便將幻想中能征服自然的英雄或能保佑人間的神靈及族群崇拜的圖騰繪制在崖壁上,作為祈求消災避難、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寄托與信仰,每年都在崖壁畫前舉行祭拜活動。這些巖畫歷經千年風吹雨打,依然保存下來。這些遙想帶有天真爛漫的色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花山崖壁畫和其他古老的藝術形式一樣,都是起源于人們的勞動實踐,是多彩的社會生活的積淀,壯族先民用聰明的才智、豐富的想象、真實的情感,繪制出來的藝術畫面,它是民族文化的歷史記憶,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結晶,是世界巖畫藝術上的奇跡。想到這里,我內心深處增添幾分自信與自豪。
歷史,謹慎地揭示著自己的秘密,章章節節地給人們上著深沉的課,留下無數不朽的珍貴遺產。為了解開花山崖壁畫之謎,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屆黨委、政府都非常重視對花山文化的考察與研究,先后組織了多次規模較大的考察研究活動。其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人數最多、層次最高的當屬1985年4月那次。當時,自治區人民政府邀請了全國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歷史、考古、民族、美術、民間文學等十二學科的八十名專家學者參加考察,歷時三個多月。這次考察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后來深入開展花山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之后區內外專家學者連篇累牘撰寫論文,紛紛對花山崖壁畫發表真知灼見。然而對崖壁畫所反映內容的解釋仍無權威性的定論。
前些年,我和廣西桂學研究會同人到云南考察民族文化。在麗江市我們參觀了納西族人的村寨。納西族是麗江的主體民族,他們的先民創造了一種介于原始圖畫文字和甲骨文等象形文字之間的“圖像形文字”,并用這種獨特的文字,書寫了數萬卷的納西本土宗教東巴教的經典,如今被世界十多個國家收藏,成為世界文明史上一幅幅壯麗神秘的人文畫卷。麗江以文為魂,如今成為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當地領導激動地說:“是文化成就了麗江。”這話打動了我們的心。
遙想花山,這塊凝聚著壯族先民創造力的文化瑰寶和南國壯美山水風光的圣地,卻無法引人注目、流連忘返,實在令人費解。歷史文化價值屬于可開發的人文旅游資源,花山文化具有集壯美、古樸、盛名、獨特及可開發利用于一體的綜合性歷史文化價值,為何沒有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癥結在于我們如何從研究、保護、開發、利用的層面去評估、宣傳、推介其文化價值,能給人們以吸引力、沖擊力和感召力。在喧嘩浮躁的今天,人們希望有一處僻靜之地,讓自己浮躁的心靈得以休憩,同時又得到歷史人文的熏陶。花山完全可以成為最佳的選擇。有專家認為,按照大文化的理念,自然風光是文化,文物古跡是文化,動物植物是文化,衣食住行、養生長壽也是文化,花山的文化資源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文化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空間將極為廣闊。文化遺產是在人與自然、社會等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文化遺產傳承既要強調保護,也要探索讓其發揮應有的作用,讓其融入當代人類的文化與生活。這些至理的論斷,值得決策者們參考。
在昨天、今天和明天組成的歷史系列中,只有今天才是實體。過去的存在,是歷史的現實,不忘昨天的歷史,就是把今天奉獻給明天。當我幾度肅立于花山腳下,凝視著它那氣勢雄偉、耐人尋味、百思不得其解的畫面,遙想它遠古的滄桑,依稀感到有些模糊含混,有些惆悵。遠古時代,嶺南開發遲緩,很多少數民族沒有文字,又歷經戰亂、劫難、遷徙。關于花山崖壁畫包含的社會內容,歷史文獻記載極少,可供查考的資料奇缺,就是已有的文獻記述和民間口傳心授,也是充滿著神秘的色彩,都不足以為論證的依據。要確切地有權威性、科學性地解釋花山崖壁畫的含義,絕非易事。今天我們在繼續開展花山崖壁畫研究的同時,加大對它的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的力度,把純史學研究變成現代經濟文化建設服務研究,提高它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和旅游價值,花山文化將因此閃爍新的光彩。
花山,極富浪漫而神秘的歷史文化色彩,它不僅誘發起史學家的好奇,也會撩拂起作家的靈感。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花山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層出不窮,從左江走出來的作家、藝術家英才輩出。花山是壯族文化的發祥地,是廣西民族藝術人才的搖籃。記得20世紀70年代初,《廣西日報》文藝副刊征集刊名,在眾多應征的刊名中,經評選“花山”列為榜首。我常常把花山視為廣西文化的根源與血脈。1996年5月20日,區黨委宣傳部為了集思廣益,研究廣西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文藝發展規劃和具體措施,邀請二十多名青年作家、藝術家在花山召開座談會。這次青年文學藝術座談會,后來被稱為“花山文藝座談會”,并認為是“拉開了振興廣西文藝的序幕”“廣西文藝以新桂軍的整齊陣營,邁開了跨越式發展的步伐,從花山腳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迎來了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繁榮昌盛的藝術春天”。我在后來寫的一篇散文《難忘這段情》中這樣記述花山會議:
初夏的南國,鶯飛草長,都說這樣的日子是郊區的最好時節。我和二十多位文藝青年一塊到花山壯族山寨召開文藝創作座談會。青年們的笑容如初夏的陽光一樣燦爛,如清朗的月亮一樣明凈。我們坐在寨前的草坪上,探討文學藝術的發展規律,商量振興廣西文壇的措施,勾畫八桂文學發展的藍圖,憧憬八桂文苑繁榮的前景。大家心情輕松愉快,暢所欲言,用心去思考,真誠地交流,仿佛在和秀麗的花山對話,與散漫的浮云攜手,隨滔滔的左江水奔流。
每當我回憶起與年輕的文學桂軍們相處的歲月,深深感到,任何感情只有在自然的時候才有價值,越是自然的東西,就越是生命的本質,越能牽動人至深的情感。
我習慣從文化的層面和文明的視角遙想花山。花山崖壁畫是壯文化的靈魂,它悠遠的歷史和神秘的色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寶。2011年廣西桂學研究會“廣西文化符號影響力調查”課題組,采用城市抽樣調查、高校抽樣調查和典型調查的形式進行問卷調查,在回收的三千四百多份有效問卷中,花山崖壁畫高票列為最有影響力的廣西文化符號。20世紀80年代,在花山崖壁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后,廣西區、地、縣便積極創造條件,申報花山崖壁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和積極申報,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四十屆會議上,花山崖壁畫成功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既是廣西,也是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重大突破,填補了中國巖畫類世界遺產的空白。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我好奇地閱讀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花山崖壁畫的評語:左右江巖畫符合《世界遺產名錄》項目列入標準第三、第六條標準,即“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一種創造性的天才杰作。能為一種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一種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讀完評語,我為中華民族文藝強大的創造力和創造的輝煌成就而驕傲,為人類以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和對未來的追求并創造的文明而自豪。不同凡響的創造和持之以恒的勇氣是值得尊敬的。
托爾斯泰說:“一個人只有在他每次蘸墨水時,都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才應該進行寫作。”如今,我已過古稀之年,記憶雖然漸漸飄逝淡忘,但生活在風云際會的時代,依然帶著欣慰和激動的情懷,不由自主地回首。文學就是懷舊,記憶是作家的眼睛,回首時,在霧里、云里,于朦朧處,依然看到燦爛的星光、火紅的太陽。于是我提筆寫下這遙想花山的情緒和粗淺的思考,只當為八桂文藝事業之繁榮發展貢獻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