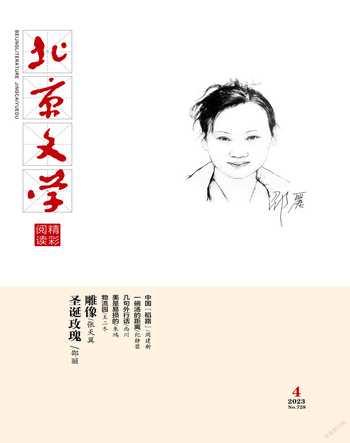如夢令
蔡勛建
我出生那年是甲午年,可謂“驚天動地”。
——歷史這樣記錄著:1954年6月中旬,長江中下游發生三次較大暴雨……長江出現百年罕見的流域性特大洪水。與我有關系的是長江中下游的一個支流華容河潰堤決口,整個兔湖大垸一片汪洋,才開鐮沒幾天金黃色的早稻和那些長得十分喜人的棉花、大豆、高粱都泡了湯。在一個叫五田渡的地方,靠華容河堤腳的一個土磚茅屋里,我的年輕的母親倚靠著一個木床痛苦地呻吟著,她很自信,她不管我愿不愿意也要拼命把我送到這個“水深火熱”的世界……
這一天是農歷六月二十一,一個考驗我們母子的日子。我似乎對這個世界有著最初的莫名的抵觸和抗拒,因此所謂“呱呱墜地”不屬于我,本應該屬于我的大喊大叫而沒有發生,這可嚇壞了母親,接生婆一只手抓起我的雙腳一把倒提起,另一只手在我的屁股上狠勁地拍打,我終于經不住這種“酷刑”,最終發出一聲長嘯,算是“回應”了眼前這個陌生的世界,還有那些陌生的期待的目光。
六月三伏天,最是火熱的時節,我來到這個世界。這歡迎的陣勢也太隆重太熱烈了。不久,水才漸漸退去。可有一天,我們家那土磚茅屋忽然起火,家里人和左鄰右舍都只顧忙著搶救家什物件去了,全然忘記了我的存在,我再沒有沉默,而對這個世界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吶喊……人們驚魂未定之際,我的母親回過神來霍然大喊一聲“我的兒吔”,沖進火海,把我從搖窩里搶了出來。母親的頭發被火燎得焦煳,她從火海中摟著我沖出來的一剎那,熊熊燃燒的房梁訇然倒塌幾乎砸到她的腳跟,我仍在驚恐萬分地哭號。我的左小腿已經被火神光顧過了,而且,從此給我永遠留下了一幅海島模樣地形圖。
我本屬馬,可鄰居街坊硬說我像牛。我出世了,我的麻煩也就來了。我母親的表姑媽我的表姑奶奶天天來瞧我,說我活生生一條牛犢(讀e,第三聲)子,索性就叫“沙牛”吧,她們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沒幾天我就“臭名遠揚”了。我們湘北華容邊鄙之地,叫公牛為牯牛,母牛為沙牛,你看這不是寒磣人嗎?當年我那大大咧咧的姑奶奶一句消遣涮我的玩笑話——我不知當年姑奶奶對我“男命女名”究竟是何“居心”——居然就鐵板釘釘地成了我的乳名小號,讓我苦不堪言,幾乎受用終身。后來,我發蒙讀書有了學名,長成甚至有了字號,可那個讓人哭笑不得的諢名就像牛皮癬一般死死地賴著,鏟之不掉,揮之不去。
我知道,名字對于一個人,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但我更深知一個讓人感到侮辱、羞辱、恥辱的符號,會對人造成多大的傷害與災難!少年慕虛榮愛自尊恐怕是天性,我又怎禁得那些挖苦、嘲笑、奚落等與我那綽號結伴同行,為了一個讓人站立不起、總是被別人“打倒”的名字,從小學到中學,我曾經恨不得鉆山打洞般地逃離……
許多年后,我都不敢面對故鄉,因為只有故鄉認得我,故鄉的人更熟悉我,就因為一個讓我尷尬讓我“痛”的名字。倘若回鄉下老家,遇見年長者一時認不出我來,偶爾回過神來他會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哦哦是沙牛回來啦!”那一聲驚詫不打緊卻是當著一大堆晚輩小孩的面,我頓時就像一個人贓俱獲的賊,滿臉通紅,一下子從耳根紅到腳跟。也有客氣的,他不當面叫你,卻在背后指指戳戳著說“沙牛回來了”,好像回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牛,一條走失多年的母牛。一個混賬名字,居然是我的軟肋我的七寸,有的人奈何不了我時,他會在一個讓我窒息的地方等著我——在我的乳名小號上大做文章。我有一個叫三九的小學同學,他“斗”我不贏的剎那或是向我挑釁的當頭,他的“殺手锏”和“殺威棒”就是扯起喉嚨喊歌來羞辱我:讀書怕過考喲,種田怕打草,奶豬仔最怕閹豬佬;癩子怕剃頭喲,沙牛怕牯牛……那種居心叵測的“兒歌”的殺傷力是極可怕的,那時候,我連鉆地坼縫的心都有。
1966年,我12歲,我人生的第一個“輪”。這年我考入縣最高學府華容一中,與“炮打”“火燒”熱烈邂逅,與“轟轟烈烈”“驚心動魄”欲罷不能。
九月初,極少挑擔負重在鄉下做裁縫的父親破例幫我挑著行李——一個木箱,一套鋪蓋,從華容河北端出發,走過新生大垸,翻過黃湖山,穿過黃湖山峽谷,從黃湖山西麓進入華容一中校園。那時學校周圍還沒設圍墻,唯見古木森森,松濤颯颯,父親放下行李擔,手撫龍鱗般的松樹對我說:“伢兒,你可是我們家第一個進華容學府讀書的人啊!”
父親的期待之殷,盡在這一意味深長的感嘆之中。按說作為農家子弟,我沒有理由不好好表現,刻苦讀書,可當時“文革”那種形勢場面讓我這個懵懂少年既是一頭霧水,更有滿腹困惑、迷惘和驚懼。這個初中我只混了兩年就輟學了,英語僅僅識得26個字母,俄語學會了“起立”“坐下”,代數只上到“有理數”,大白天開批斗會,晚上跳“忠字舞”,或者看高年級的學兄學姐們表演活報劇。
縣學府校園里的高音喇叭絕對是一流的,其分貝之高,讓方圓十幾里都能聽到喧囂,其功能之廣,讓學校幾乎所有活動都能在喇叭口解決,開批斗會召集人最是方便了。有兩首“革命歌曲”使用頻率最高,一個是《看見你們格外親》,一個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黃湖山東南麓,是一中的正大門,也是學校通往縣城的大道,那是一條煤渣路,那條道上寫滿了瘋狂與荒唐:被打成黑幫分子而頭戴黑高帽、掛著大黑牌子的老師們,在全校幾千學生排著長長的隊伍的簇擁下從那里走出校門,過華容大橋往河西,穿四牌樓至西門打轉,游街一個來回上十里地……
父親對我不放心,每周六我回到家里,他都要刨根問底盤詰:你沒有參加什么組織吧?我頭搖得像撥浪鼓,我說我是“逍遙派”。父親先是一愣,隨即睜大眼睛兇巴巴地問逍遙派是么子派?我說么子派都不是,父親馬上說:逍遙派好,逍遙派好!
學校食堂也仿若戰場。那時學生開餐吃桌席,一張四喜桌為一席,八個人吃一席,大概是四菜一湯,炒大白菜、炒白蘿卜片、青椒炒榨菜,還有個小葷菜什么的,湯是霉豆渣湯,每天每餐大同小異。大米蒸飯有兩盆,每盆一斤二兩,鋁盆。那種開餐的場面是盛大的,大飯廳平面擺放幾百桌,吃飯的動作也是神速的,簡直就像打仗,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戰斗。場面真是駭人,只要飯廳的大門一打開,那些早就擁在門口敲盆擊缶的學生們頓時如潮水般涌入,捷足先登者會搶先抓起一只鋁盆,用鋼叉或鋼勺把先將盆內米飯畫上一個十字,——雖然那十字就一橫一豎,但絕對不是公平準確的橫直兩根線,嚴重地傾向一邊,四個四分之一,是絕對不相等的——再用勺把順鋁盆內壁攪一圈(防止米飯巴盆),然后瞄準四個半月形的其中最大的一坨,用鋼叉撬起往自個兒碗里撂,接下來就是如何向菜進攻了。當然能這么干敢這么干的絕對不是我們這些使用竹筷子被稱為“鄉巴佬”的農家子弟,而是家住城里的“小霸王”所為。這樣的結果是非常尷尬非常難堪的,像我這樣的鄉里伢子,經常是吃上最小最小的那一坨米飯,那是名義上的四分之一,這還算是走運的,最吃虧的要數本桌的女同學,男生們殊死戰斗之時她們按兵不動,等到她們動手時已是一片狼藉,盤中所剩無幾,能吃上一小角兒米飯是幸運的,最后連霉豆渣湯都喝不上的往往就是她們。
1977年,我“將”了父親一軍,父親說那是“摳底將”——沒經過他同意我退伍了。我不知我觸到了他的底線。回到家那天,父親很不高興,黑著個臉。見到街坊鄰居也有些躲躲閃閃,好像有什么見不得人似的。老實說,我在部隊當兵六七年,本來是很有可能穿上四個兜兜的干部服軍裝的,不是我不努力,只是沒有想到最終壓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父親所謂的歷史問題。當希望總躲在絕望之后你看不見摸不著時,何去何從,你就要下決心了,于是我堅決地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向后轉”。回就回了吧,這倒沒什么,只是我心里還是有些難過,我用什么來安慰你,我的父親。自從1970年冬,16歲的我當上了汽車兵,第一次離開家離開他,他的眼睛就一直守望著我,哪怕千里萬里關山阻隔他也目不轉睛,其實那也是一種望眼欲穿——他巴不得我的肩上扛個星回來,可惜那年代還未恢復軍銜制。
我有兄弟四人,可能我是父親最寄予厚望的,我在部隊超期服役三年據說他曾在鄉黨面前夸下過“海口”。后來,父親知道了是他“影響”了我的前程,內心非常歉疚,看到我滯留在家,他心事沉重。其實,我才覺得壓力山大,一同退伍的戰友們一個個被市里縣里招工走了,有去運輸車隊的,有去機關單位開小車的,我卻一次次坐失良機,原來的那種“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青春自信和技術自信被一次次的招工失敗漸漸抵消。年齡在增長,青春在消磨,我真的要認真考慮再一次離家了,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再不走,我這個大隊小學代理校長就真的會“轉正”留下;再不走,我就真有可能留在大隊當干部——據說公社里那個抓黨群的副書記在黨員培訓班上已經“看”上我了;再不走,父親就真的會拿根竹棍來攆我了,他生怕我窩在家種田。我在父親的幻想與翹望中匍匐著,等待時機,我的前途似乎只有兩個詞四個字:“提干”“上班”——這都是多美好多體面的字眼!前頭那兩個字永別了,后頭這兩個字,對于我這個回鄉的汽車兵來說,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
這不,說走就走了。
我迫不及待,一步就跨進了縣城,目標是縣商業車隊,工作是卡車司機,屬性是“亦工亦農”。在那年月,亦工亦農是體制的一種產物,用勞動部門的術語說,就是一種計劃內的合同工,用社會“俗話”說,就是也工也農,工人職業農民身份,說白了就是一個吃“背背糧”的貨車司機。我真的是饑不擇食了,連一個幾乎就是一個臨時工的“空當”也不放棄了。
我的身份在車隊被嚴格地區分著。首先,你是個代班司機,就是駕駛員誰家里有事誰請了假,那你就去頂班,你要隨叫隨到。其次,你是一個沒吃“國家糧”戶口還在農村的合同工。食堂里掌大勺的劉師傅是個國家職工,他手中打菜的鋼勺從來只向那些正式職工傾斜,他的笑容從來不送給我。后來他退休了又留在車隊當門衛,退了休也不減威,有時為啥事也不忘記他國家退休職工的身份對我嚷嚷。在那個嚴格以“國家糧”給人定等級分尊卑的年月,我們這些吃“背背糧”在城里謀食的漢子,一個個把自尊藏得很深很深,生怕被人碰傷。
俗話說,黃土也有翻身之日。不知是我的執拗,還是我的幸運,終于感動了上帝,后來我不僅翻身招了工,還有了幾次身份置換。
調到商委工作后,我登了一次鼎山。鼎山在我心中相當于泰山,雖然海拔不高,卻也十分險峻。站在鼎山——我湘北家鄉版的泰山——之巔,遠望著人們手足并用氣喘吁吁從西北角陡峭處往上爬,不禁感慨萬端——人生何嘗不是在爬山?只是我有所不解,為什么越是陡峭險峻越是擋不住人們向上的步伐?
是的,我一直都在攀爬那座屬于我的鼎山。我不敢這山望著那山高,可我的遭際中卻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就在我左沖右突困獸猶斗折騰多年好不容易招工、解決糧食戶口,然后又獲機遇改行之際,又遇上了新問題。
時間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我賴以謀生的縣商委原本好生威武,管轄著糧食、商業、供銷、外貿、石油、煙草、鹽業、藥材等八大單位,忽一日,縣里宣布機構撤銷。一個偌大的機關、一支偌大的隊伍似乎隨著一聲哨響就地解散了。
這年三月,我被疏散到糧食局,沒想到報到當日就遇到了一道坎,當時糧食系統人事直屬省廳統管,下面進人必須先報省廳審批,由于事涉改革大局,當時也就“先斬后奏”了。我手里雖然捏著縣人事部門開具的介紹信,那不好使,真正進入還是要走程序,最后還是局長親自帶上一摞我在報刊發表的文學作品以“人才引進”為由申報,好不容易過了省局這一關。
前些年,我潛心于文學創作,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我是被人“發現”并推薦去縣商委工作的,先是借調,后來正式調入,主要是編輯《商業簡報》,寫寫材料,這讓我徹底告別職業開車生涯。由于不是干部,我的身份又以一個新名詞——“以職代干”——來確認。也有說“以工代干”的,就是干部崗位工人身份,也是體制的產物,那時如我這樣的“同行”不少。
我發現,一個單位人頭總是用所謂編制來控制的,問題是占了編制的人撇開什么背景不說,他可以不干事或者說他干不了,可錢照拿。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人沒占到編制但還得要“一顆栗子頂一個殼”地干,只能好好表現,尋找機會。我屬于后者。既不是干部,也不帶編制,那個日子就不好過了。好在局長開明也挺愛才,任命我為某股副股長,括弧,保留正股級。自然這也是對我最好的安慰,我自己也這樣想,我畢竟是“從上頭下來的”,可人家那老資格在局里待了幾十年的老股長不高興了,生怕你是來搶班奪位來了。給你一張辦公桌,整天面無表情,老人家自己忙得不得了,就是不安排你做事,你插不上手也就只能是每天幾張報紙一杯茶,日子過得那個憋屈得慌。
不久,局里成立政工辦,命我“主政”,實際上我也就是一個“光桿司令”,手下無一兵一卒,工作職能也很簡單。局長很期待地對我說,今后局里有關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事情就統歸你管。這就有事干了,那些年年年都評市級省級文明單位,政工辦可是重任在肩,責無旁貸。事實上干完這些本職工作之后,我更多的精力放在對本單位系統的宣傳上,就是外樹形象,用筆發言。大量的有分量正能量的紀實性報道走向媒體,有的則冠以“報告文學”在大報小刊發表,單位聲名鵲起,我的知名度也隨之提高。但有一件事你不敢想,那就是提拔,人要求進步這很正常吧,可你是個“白坯”身子——不是干部,沒門。每年縣委組織部門都會下來考察科局級領導班子推薦干部,說還是說“機會面前,人人平等”,可你還得要有那資格。我呢,那也就是“早谷米打糍粑——不夠格”,雖然早谷米也是米,但黏不上。
又一座大山擋在面前。不是干部,你提拔難,要提拔,你得先錄干。不是干部,更有尷尬的時候,那就是年度的公務員考核與崗位清理,你連干部都不是卻還占著一個主任的崗位,鳩占鵲巢,這哪成啊?這時候你還不要太著急,因為事情還都是要人去干的,更何況有些事兒未必是誰都能干得好的。末了,單位上領導出面向上報告保留幾個“以職代干”崗位,于是我們得以幸存。我們這些被保留下來的“人才”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報考國家公務員,一條是等待過渡(機構改革或上面下達轉干指標),報考我是不敢,就只能是等待過渡了。可等待是漫長的,不一定有結果,在這種焦灼的等待中,我還要解決好文憑問題,還得創造一些留得下站得住的理由。
1990年,50集電視連續劇《渴望》熱播,萬人空巷。我心里百感交集,也有一種渴望。
2014年仲夏。某日,收到一則短信,我大吃一驚。讓我吃驚的不是這短信的內容,而是發短信這種形式以及短信的語氣。這則短信正兒八經地通知我,根據某某部門指示要我準備辦理退休手續。語氣完全是居高臨下毋庸置疑的,發短信者是局人事科長,一個我曾經共事多年的“鐵哥”。鐵哥科長沒有給我打電話而是給我發短信,這讓我感到莊重嚴肅,公事公辦。
我要退休了,這是真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這不是真的,我以為這不過是時間跟我在開玩笑。因為在我看來我早已是“退”了“休”了的,所謂退休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給我“補辦”一個手續,然后發一個退休證。這有個說頭。
2006年三月,縣領導約我談話讓我“退線”,問我還有啥意見啥要求,還一再表示“今后待遇不變”。我說沒啥意見,反正是“船到碼頭車到站”,下唄,不過我得鄭重聲明,我的實際年齡離52歲“一刀切”還差四五個月。那次談話很簡單,沒幾分鐘就結束了離開了,我心里明白,結束的不只是職務,而是一種生涯;離開的不只是單位,而是一種舞臺。我提前幾個月“退線”,有人對我說干嗎不“堅持到底”呢?我說為什么呢?那人又說誰誰誰就表示“差一天也堅決不下火線”,硬杵著。我卻很坦然,那有啥呀,不就一個“帶蚌殼的”(括弧,享受正科級待遇)XX長嘛,那樣抗著杵著有意思嗎?
我很配合,也很快地騰出了辦公室,交出了鑰匙。按本地約定俗成的模式,你退線了,就可以不去機關上班了,換句話說你徹底自由了,放羊了,你快活了。老實說,這種日子并不快活,你很快會被邊緣化,越邊緣化越會有失落感,而且你還會有你意想不到的問題接踵而來。
果然,問題來了。首先遭遇的是以前每月的手機話費補貼給你取消了。平心而論,抹去這幾十百把元的補貼也在理,你不在領導崗位不辦公事還補貼個啥呀,問題是上面那位領導說的“不變”那話尚言猶在耳,這事兒雖小,卻也讓人憋屈,不是錢的事。
我原來那單位,全系統幾千人,曾經是人喊馬嘶,熱鬧得很,如今呢,門前冷落車馬稀了。這也是存在決定意識,作用決定存在。一個單位其作用淡出職能退化而日漸式微那是很正常的了。可人心不穩,局里一把手換過好幾位了,誰會愿意給一個沒事干守攤子的單位“站臺”呢,這不,又有一個局長沒來幾個月又調走了。沒多久,縣里決定我們局與某局合并,我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退線的,一退就是8年。整8年提前離崗徹底賦閑,工資開始是簽領的,后來就打卡了,這就越來越與單位組織沒有往來,不是自個兒“玩失蹤”而是生生“被遺忘”。所以說,退休手續是“補辦”的。
回到退休這個話題。這就很有些尷尬了。先是縣里主管部門一個按章辦事的電話提前通知局里人事科,某某某要辦退休了,于是人事干部就通知本人交兩張照片擬辦退休證用。到了退休時間——順延一個月,你就去領退休證,從此你的名字進入了另一個行列。而這個過程,沒有誰找你談話,沒有誰為你開會,沒有……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子(后來我覺得自己太自戀,這樣的比喻太美好了),自動地悄無聲息地從樹上掉下向地面滑落……
說來也巧,我拿到退休證那天,迎面正好碰到一文友,我想與他坐坐,沒想到這位主政某局的詩人局長謝絕了,理由是他要去參加本局老同志退休茶話會。這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哪壺不開提哪壺。是我“退不逢時”嗎?也對。我辦退休時,我那單位剛好宣布與某單位合署辦公,原機構雖撤銷,但一直貌合神離,“兩地分居”,名義上的局長有一個但基本不理這邊“朝政”,說不上是群龍無首,也不算是我人無歸屬……
那一刻,從我曾經的“鐵哥”科長手里拿到退休證的那一刻,從我有心邀請老朋友上茶樓遭婉拒的那一刻,我猛然驚醒了,人生的確如夢,退休了,就遠遠不是什么邊緣化了,而是要被滾滾紅塵徹底淹沒……那一夜我失眠了,我想我們“50后”這一代人經歷的事情太多太多,除了上述這些,還有諸如文憑問題計劃生育問題都曾讓我們十分尷尬。是的,我只能說尷尬,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尷尬,好在雖然說“尷尬”也是“坎”,但最終還是被我們“越”過去了。我一次次的身份置換,都無不見證著我在不屈不撓地穿過這些“尷尬之門”。
人生總在穿越,盡管人生如夢。
特約編輯 白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