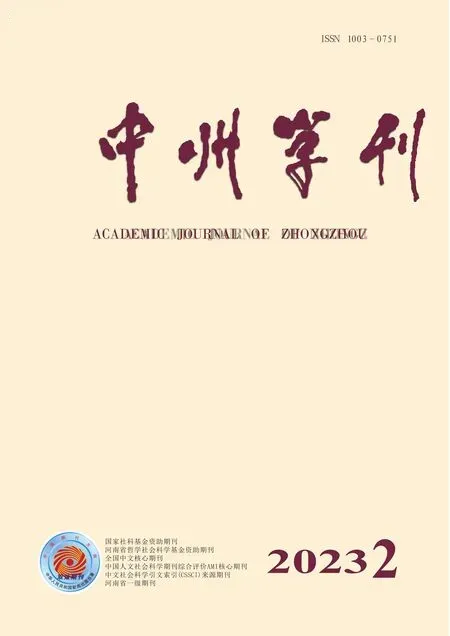先秦兩漢的文學身份批評及其發生
趙 輝 韓玲玲
身份是個體在社會各種關系中的定位,不僅規定了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權益、生產生活和行為方式,而且規定了個體的思想價值取向、知識體系、語言表達方式等。先秦兩漢的文人已注意到文人的創作“因事而作”時,不同行為性質的行為主體使用不同的言說身份,創作主體的不同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創作主體的言說身份和隱含身份對文學話語體系具有很強的規定性。在文學創作中,創作主體的身份關涉作品的內容、題材、表現方式和風格,因此,文學的身份批評在文學批評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學界研究先秦兩漢的文學觀念,絕少對這一時期的文學身份批評予以關注。本文試圖對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學身份批評意識試加闡釋,以引起學界對這一文學批評方式的關注。
一、先秦兩漢文學批評的身份視角
身份是個體在社會各種關系中的定位。復雜的社會生活形成了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體現在職業、人倫、經濟、地域、時代、學術、道德、民族、團體等各個方面。個體的身份定位也體現在眾多的社會關系之中,每個人都具有多種身份,是一個多種身份的集合體。先秦兩漢時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由復雜社會關系而形成的眾多身份意識已經產生。但那時文學創作多是政治和學術行為,禮樂等級制度帶來的人倫道德生活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用來進行文學批評的身份也主要是職官、地域、人倫道德、學術等。
1.職官身份批評
職官身份是指個體在國家政治機構中擔任的職務。從職官身份角度對某類文學作品進行批評,在先秦時期已經萌芽。如《周禮·大祝》說大祝掌六祝之辭,作祠、命、誥、會、禱、誄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1]1746-1747。這里雖然沒有明確說大祝這一王官身份確定了六祝之辭和祠命等六辭的內容、表現形式,但肯定了大祝和六祝之辭、祠命六辭的內容、表現形式的內在關系,包含著文學身份批評的核心內涵。《毛詩序》從創作主體身份的角度對一些詩歌的內容進行解釋,其中也涉及職官的身份。如說《小雅》中的《正月》《小旻》等,都是“大夫刺幽王”所作。
雖然《周禮》《毛詩序》都注意到了文學作品的職官言說身份,但都不曾指明職官身份對作品話語形成的制約作用。而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在闡釋諸子各個流派話語體系的發生時,從王官身份的視角,對主體的職官言說身份及話語特色都有明確交代。他認為諸子十家話語體系特征的形成,與流派始創人的王官職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司徒在周代的職守是“帥其屬而掌邦教”,輔佐帝王安撫邦國。故其出入六經,宗師孔子,宣揚禮樂仁義道德,強調效法堯舜文武。“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史官主管文書史記,明了歷史興衰,故其學術強調“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清廟之守,即管理太廟的官員,有著履行節儉體制、“養三老五更”“大射選士”“宗祀嚴父”等周代制度的職責,故其學說話語體系強調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羲和之官職掌天文歷法,故其話語體系強調“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理官即主管刑罰的官員,故其主張“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而“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故其話語體系“兼儒、墨,合名、法”,融合了各家學說。班固說各家學說發生的源頭出于王官職守雖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將諸子各家話語體系特征的形成與王官的職掌聯系在一起,去追尋各家學說話語體系的源頭,實際上已經尋找到思想和文學話語體系發生的關鍵因素。
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闡釋屈原詩歌話語體系時,充分注意到了屈原的“逐臣”身份對其作品話語體系形成的關鍵作用。他論述《離騷》時說,屈原曾為三閭大夫,深受懷王信任;后受上官、靳尚譖毀,被懷王流放。因其“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訴說自己放逐離別的憤懣和愁思。故《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不僅有濃郁悲憤和愁緒的抒寫,有對自己高潔品行的訴說,也有對自己才華的自我贊頌,還有通過對古圣賢帝王的向往表明自己理想信念的正確。在《九章》序中,王逸在闡釋屈原的寫作緣由時再次說到,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而寫下了《九章》,訴說自己履行忠信之道,卻不被楚王采納的憂憤。在論《遠游》的產生時,亦謂“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意中憤然”[2]163。王逸在闡釋屈原這些作品的產生時,不僅注意到了這些作品都在訴說屈原被貶謫放逐的悲憤,而且從屈原忠貞而遭受小人讒毀以致被貶放逐來闡釋這些作品產生的緣由。可見,王逸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屈原的“逐臣”身份與其作品話語體系形成的關系。王逸對屈原《離騷》等詩歌的闡釋,也采用了職官身份批評的方法。
2.地域身份批評
地域身份是指主體在一定地區文化中形成的特有特征。它表現于一定地區的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各種文化現象、風俗、意識等。先秦兩漢時期,人們已注意到主體的地域身份與文學話語體系的密切關系,如《毛詩序》已經從地域身份的視角解讀詩歌。如說《邶風·凱風》是因為“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國人作此詩以“美孝子”[3]635;《衛風·氓》是因為宣公之時“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3]684。《毛詩序》從作者的衛地的地域身份去論述《衛風》中這些詩歌的產生,開先秦兩漢文學地域身份批評先河。
班固繼承了《毛詩序》的地域身份批評方法,但較之《毛詩序》,他汲取了管子的理論,將自然地域對民情民俗的形成作用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融合在一起,去解釋《詩經·國風》話語體系地域特征的形成。他在《漢書·地理志》中說,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云。’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4]1652。陳地“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4]1653。在記述衛時說:“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4]1665在班固看來,自然條件不同,人們的生產生活經驗也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人們性格愛好的差異。《詩經》各《國風》創作主體的地域身份不同,這不同的地域身份使創作主體受不同地域文化風俗的熏陶,形成了地域文化及與之相適應的話語體系,發之于詩歌,就形成了各《國風》不同話語體系在內容和審美取向上的差異。稍后于班固的王逸,在文學話語體系的發生方面,繼承了班固的這一批評視角。他在談《九歌》這一組詩歌話語體系特征的形成時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冤結,托之以風諫。”[2]55這里也是以屈原的荊楚地域身份去解釋《九歌》的巫風話語體系特征的形成。
此外,鄭玄作《毛詩譜》,也是依據《詩經》十五國風和雅、頌作者的地域身份,從地域空間的角度,以其政治教化的歷時性,結合地域風俗去闡釋十五國風和雅、頌的話語體系特征的發生。如《陳譜》不僅說明了陳國的歷史,而且說明了陳地巫風盛行的原因:“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然后從政治的角度對《陳風》進行闡釋:“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3]799《毛詩譜》更多關注的是不同地域國風的政治傳統和現實,對各地的民情風俗注意不多。與《漢書·地理志》相比,這種從地域空間的角度對文學話語體系的闡釋,弱化了文學創作主體地域身份的內涵,但在闡釋《詩經》文學話語體系的發生時,注意到文學創作主體地域身份的作用,這是值得肯定的。
3.人倫身份批評
人倫身份是指個體在社會人際關系中的定位,如父母、兄弟、君臣等。先秦兩漢禮樂制度的本質是人倫身份等級,它的實踐主要通過倫理道德得以表現。因一些文學作品為人倫道德方面的言說,故人倫身份也被那時的人們用于文學批評。
先秦兩漢時期,人們已經注意到文體的功能、作者的身份以及內容之間的關系。如《禮記·祭統》曾說:“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5]3486從這段話看,“銘”是后輩對祖先的功業進行贊美、表示孝敬的一種文體,作者的身份當為先祖的子孫,比較明確地說明了主體身份與贊美祖先功業這一內容存在的內在關系。《毛詩序》在說明每一首詩歌的言說意圖時,有很多涉及主體言說的人倫身份。如認為《邶風·綠衣》及《日月》這兩首詩都是因為莊姜喪失“夫人”的身份,淪為“失位夫人”而作[3]625-628。又說《鄘風·柏舟》是衛世子共伯與共姜結婚后不久就去世,共姜堅守節義,但“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誓而弗許”,“作是詩以絕之”[3]659。
4.學術身份批評
學術身份是個體在不同學術思想中的一種定位,表現為個體一定的學術取向。戰國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思想流派,也形成了學術言說主體的學術身份。《莊子·天下》中已有學術流派的觀念,對諸子中一些流派話語體系的差異進行特別關注。《莊子·刻意》則注意到了這些話語差異是因主體的身份差異而形成。他將士分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按《莊子集釋》中成玄英的解釋,“山谷之士”即如申徒狄、卞隨之類的人,他們“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平世之士”即如孔子之類的儒家學者;“朝廷之士”即如伊尹、呂望之類的政治家;“江海之士”即“棲隱山藪,放曠皋澤”的人。這里雖是就不同的處世態度來確立他們的身份,但處世態度是其學術、思想的反映。如孔子是儒學創始人,隱逸思想是道家的標識。《莊子·刻意》認為“山谷之士”其言總是“怨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平世之士”發言吐氣不離仁義忠信;“朝廷之士”言行不離功名和端正君臣上下關系;“江海之士”則游處山林,閑散而不關世事[6]535。可見,言說身份不同,價值取向和行為、話語體系也大不相同。
漢代也有以內容來區分辭賦話語體系的。如揚雄將賦區分為“麗以則”的“詩人之賦”和“麗以淫”的“辭人之賦”[4]1756,認為“詩人之賦”雖然也有華麗的辭采,但華麗有度,內容不失雅正,具有《詩經》的諷刺精神。而“辭人之賦”“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但徒有華麗的辭藻,“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4]3575,如同俳優所說的笑話之類,只具有娛樂價值。而所謂的“辭人”“詩人”,也是具有學術思想身份的意義。
二、文學身份批評的內在邏輯
先秦兩漢的文學身份批評,核心是創作主體的言說身份決定文學的言說話語,即“是什么身份說什么話”。這一批評方法,反映了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因事而作”的核心觀念以及言說身份構成與身份知識話語內涵獲得的內在邏輯。
1.身份批評與“因事而作”
西周時期已經有了文章“因事而作”的意識。《尚書·洪范》開篇即說:“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這表明《洪范》是記周武王滅商后第13年拜訪箕子,向他請教治國的“彝倫攸敘”而作。這一意識被《毛詩序》繼承,其在解讀《詩經》的每首詩時,都首先交代該詩所作的緣由,以幫助讀者理解詩歌。如《綠衣》之序謂:“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3]625《狡童》之序說:“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3]723后來的賈誼在作《鳥賦》時,也作有自序告訴讀者此賦因何事而作:“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似鸮,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7]208。由此可見,文章“因事而作”是先秦兩漢人的共識。
文章既是“因事而作”,而事都是一定性質的行為,有著一定的行為主體。一定性質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行為目的。在行事的過程中,行為主體所有的行為方式都是為著目的的實現。因此,“因事而作”的目的并不是指向文本,而是指向事情的結果,文本不過是主體實現其行為目的的一種手段。從這一角度看,文本創作的價值并不體現在文本自身,而是體現于文本在這一行為中產生的作用和結果。作為行為手段的文本,都是圍繞著實現這一行為目的服務的,故文本的言說,自然也就被行為性質和目的所制約。
此外,一定的行為性質,也規定了行為主體的身份。也就是說,在一定性質的行為中,主體的身份不是隨意的,而是由事情的行為性質而確定的。每一行為主體都有眾多的身份,但這眾多的身份是通過不同性質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在同一性質的一個特定場合的行為過程中,行為主體一般不可能具有兩種身份。例如,球場上的裁判員進行裁判時,其身份只能是裁判員,而不可能是銷售員,所說的也只能是裁判話語。文章“因事而作”時亦是如此。司馬遷作《史記》是一種記述歷史性質的行為,其言說身份為史家,而不可能是父親、朋友等。而他作《報任安書》是一種回應同僚、友人請求性質的行為,其言說身份自然與他作《史記》時的言說身份不同。故其作《史記》時只能運用歷史話語,而作《報任安書》時則不可能去言說歷史,如同作人物傳記時那樣去書寫某人的生平。漢秦嘉作《贈婦詩》是問候妻子性質的行為,其言說身份是關愛妻子的丈夫,而非其黃門侍郎的職官身份,故其言說話語更多是夫妻間的情語。
可見,文章“因事而作”時,行為性質和行為主體的身份都限定著文本的言說內容和言說方式。因而,當人們確定文學為一定性質行為的產物時,創作主體的言說身份便與行為性質和言說目的及言說的內容產生了相對固定的對應:即行為的性質決定行為目的和行為主體身份,行為目的和行為主體身份又決定了行為主體的言說話語。
這一內在邏輯,在先秦兩漢的文體創作和批評中都有反映。如《禮記·祭統》認為,銘之所作產生于子孫祭祀先祖的行為,目的在于歌頌祖先,顯示孝道,作者的身份當為祖先的子孫,故其話語為“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這在劉勰的《文心雕龍》文體論中得到極為充分的表現。而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說屈原作《離騷》,是因為自己被放逐,“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也”[2]1-2。其目的是諷諫楚王,希望楚王覺悟而再次重用自己。根據王逸這段話,知屈原作《離騷》是因自己被放逐而諷諫楚王的行為,屈原的言說身份為“逐臣”,言說目的在于“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而非《離騷》創作自身。《離騷》的創作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方式。屈原作《離騷》的言說身份和言說目的,決定了《離騷》不可能像《洪范》去言說政治的“彝倫攸敘”,而不帶一絲的悲憤;也不可能像莊子《逍遙游》那樣去闡釋無己、無功、無名才能不被外物所驅使,從而達到人生的自由;而只能言說自己的悲憤、才華和對楚國的忠貞,“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可見,先秦兩漢的文學身份批評,與中國文學“因事而作”而確定的行為性質、目的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邏輯關聯。
2.身份批評與身份經驗及知識話語體系
先秦兩漢文學的身份批評,也體現著先秦兩漢人們以一定的身份經驗獲取相應知識話語體系的認知。春秋時期,人們意識到一定的身份具有一定的話語。人們將那些言行符合禮義的人稱為“君子”,并賦予其一定的話語特征。這一意識在戰國得到了普遍表現。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產生了不同的學術流派。每一學派內的人,都有了他們的學術思想標志——身份。而使他們獲得某種學術身份的,便是他們的學術話語。學術流派即學術身份不同,其話語體系也就不同。如《莊子·天下》以墨子、禽滑厘為一派,宋钘、尹文為一派,彭蒙、田駢、慎到為一派,關尹、老聃為一派,莊周為一派,并對他們學術思想的特點進行了總結。說墨子、禽滑厘派“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6]1072。關尹、老聃學派的特征是“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6]1093。這里以作為學術身份標志的學術思想話語,將不同學術家流派非常明顯地區分開來。《荀子·儒效》將學者分為俗儒、雅儒、大儒。這俗儒、雅儒、大儒也具有身份的意義。荀子對其學術身份的區分,也是從其學術話語著眼。他認為俗儒的話語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于墨子”。雅儒所強調的是“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9]。他們的話語體系各有不同,故有了學術身份的區別。
正是依據這一點,司馬遷有了儒、墨、法、道等學派之分,并指出其學術話語的主要特征。“儒者以《六藝》為法”,“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墨者亦尚堯舜道”,主張節儉。“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10]3290-3292。也因為如此,班固《漢書·藝文志》有了諸子十家的學術流派之分。
先秦兩漢時期,一定的身份除與先秦的職官制度規定每一職官都有一定的職掌和一定的話語特征有關外,也與主體以一定的身份經驗而獲取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密切關聯。人的每一種身份的獲得,都要經過這種身份的經驗去獲得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通過某種身份的經驗而獲得某種身份及其相應的知識話語的意識,最遲在春秋戰國已經萌芽。孔子曾多次談到怎樣才能成為君子,說君子應該務孝道之本,應該好學,強調“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11]115,“先行其言,而后從之”[11]57。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君子的行為標準,為仁就應當“克己復禮”,故要成為君子,就應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1]132。而這些道德的培養,又離不開對詩、禮的學習。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11]178君子的道德“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11]104-105,所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11]174。孔子認為,君子身份有著與其相對應的行為和話語,禮樂倫理道德的經驗是獲得君子身份和話語的唯一途徑。
個體地域身份,是個體在生活地域特有的自然環境中,形成的特有生產生活方式和人文風俗經驗的結果。司馬遷對此曾有充分論述。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中山地薄人眾,加上有商紂時沙丘的遺民,故“民俗懁急”,男人“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動則殺人剽掠,“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人“則鼓鳴瑟”“游媚貴富”[10]3263。南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等地“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10]3268。東漢應劭在《風俗通義·序》中說:“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12]和司馬遷一樣,他認為民情風俗因不同的自然地理而產生,這種民情風俗的不同,也帶來言語歌謳“或直或邪,或善或淫”的話語。它發之于文學,便形成了這一地域文學的地域話語特征。正是這些地域人們的地域生活經驗,使他們獲得了這些地域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其知識話語,導致了他們性格和話語的特點。
可見,先秦兩漢時期已經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和一方文學的觀念。人們已意識到了每一地域的人,通過這一地域的生產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民情風俗經驗,形成這一地域人的特有性情和知識話語體系。一定的身份不僅反映著與其相適應的經驗,而且反映著與其相適應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所以,在文學的言說中,主體不僅應該是什么身份說什么話,而且身份本應有的知識話語體系,也能夠讓他是什么身份說什么話。
3.言說身份與隱含身份
言說身份即行為主體在一定性質行為中被規定的身份,如前所說屈原作《離騷》的言說身份為“逐臣”。隱含身份即主體在言說過程中,隱含于言說身份之中而對主體言說起著某些次要的支配作用的身份。
在文學的言說中,除言說身份在支配主體“說什么”和“怎樣說”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身份也在對主體言說產生著一定的影響。先秦兩漢的文學身份批評中,也有專門從創作主體的隱含身份去進行文學批評的。如揚雄以“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去批評漢賦,并不曾涉及主體的言說身份。他曾批評“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4]3575。在揚雄看來,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就是“辭人”之賦,司馬相如應是以諫臣的身份創作《大人賦》的,但因其言說頗似俳優,以華麗辭采將仙境描寫得引人神往,致使武帝對神仙更加向往。司馬相如的“辭人”身份在《大人賦》的創作中為隱含身份,這一隱含身份也在很大程度支配著《大人賦》的寫作,使其具有了“辭人”之賦這一類賦作的特征。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和鄭玄的《毛詩譜》從地域身份角度批評《詩經·國風》,也都是從創作主體隱含身份的角度去闡釋某一類型作品特色的形成。
但先秦兩漢的文學身份批評,主要還是以創作主體的言說身份對作品進行闡釋。《毛詩序》和王逸的《楚辭章句》等,大都是從言說身份的角度去解釋作品話語的發生及其價值取向。但是,《毛詩序》和王逸的《楚辭章句》也已經注意到言說主體的言說身份和隱含身份對于作品的共同作用。《毛詩序》中的一些序,不僅交代所系之事,而且以“刺”或“美”某國、某位君主,去確定其地域和時代,具有交代其地域和時代身份的意義。如《衛風·氓·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3]684據此,知此詩的主體言說身份為色衰而被丈夫拋棄的棄婦。而在交代此詩作于衛宣公時,不僅交代了作者為衛人的地域身份,也交代了作者生活于衛宣公之時的時代身份。其批評將作者的言說身份和隱含的地域、時代身份結合于一體,體現出即人、即事、即地、即世的文學批評觀念,比較全面地揭示了《氓》這一話語發生的主體與地域、時代風習的內在關聯。
《史記》中很多文人傳記具有文學批評的性質,如《屈原賈生列傳》《司馬相如列傳》《老子韓非列傳》等。這種文學家傳記的文學批評,具有文學家評傳的性質。這種批評方式,將事與時代、地域文化對主體學術、思想的作用聯系在一起,力圖通過展示創作主體的生平與其創作之間的關系,去闡釋作品話語特征的產生。而對作者生平的展示,也是對他多種身份與其作品話語特征的內在關系進行闡釋。如《屈原賈生列傳》不僅交代了屈原的“楚之同姓”的國別地域和王族身份,而且涉及其“楚懷王左徒”的職官身份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職守,更突出了屈原職官身份逆轉的原因是“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以及他遭受貶謫、放逐之冤對《離騷》《九章》的發生及美學價值取向產生的深刻作用。因其為“楚之同姓”,故其“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因其曾為懷王左徒,原是“王甚任之”的寵臣,一下轉變為逐臣;本“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故“疾痛慘怛”而怨憤油然而生。所以他認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并依據由寵臣向逐臣身份的逆轉,闡明了《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10]2481-2485核心話語的產生。《離騷》的言說身份是逐臣,但其中又隱含了屈原楚人、王族、寵臣和戰國人等多種身份,其話語自然也包含著這些身份所獲得的相應話語。故《史記》的文學家傳記的文學批評,事實上是將《離騷》的言說身份與隱含身份結合在一起,去闡釋《離騷》話語特征的發生。
三、先秦兩漢文學身份批評的發生
先秦兩漢時期實行嚴格的禮樂制度,其核心是倫理等級。每個人所具有的倫理等級,就是其在社會中的身份定位,因此,先秦兩漢社會是一個嚴格的身份制社會。這種嚴格的等級身份,不僅規定著個體的政治、經濟乃至藝術等各方面的權益,而且規定著他們的生產生活行為方式、職守和使用的話語體系,甚至言說方式。先秦兩漢的文學,都是“因事而發”,是當時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呈現。故現實生活這嚴格的身份意識,不僅在文學言說中得以充分表現,也導致先秦兩漢文學身份批評方法的發生。
1.先秦兩漢的官制、職守與其話語規定
國家政治機構都設有不同機構的官員,不同機構的官員各有職守、等級,形成其各自的身份,也產生了相應的話語。《尚書·舜典》不可能是舜時的作品,但卻反映著遠古設有職官的狀況。如其載夔為樂官,掌管樂律和樂教。從商代的甲骨卜辭看,占卜也分別有專職人員掌管。卜人司“卜”,貞人司“貞”,占人司“占”,并有不同的話語。
根據《周禮》,可以看到周代官職眾多,等級嚴格,職守非常分明。六官之中,天官冢宰為治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治”[1]1375。地官司徒為教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教”[1]1501。春官宗伯為禮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禮”[1]1622。夏官司馬為政官之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1]1792。秋官司寇為刑官之屬,“使帥其屬而掌邦禁”[1]1873。冬官則為司空,掌管工程制作。他們的所屬官員,也都有明確而詳細的分工。如春官下屬的大司樂,掌管學政,以樂德、樂語、樂舞教育貴族子弟。大師掌六律六同,教風、賦、比、興、雅、頌六詩。這些官員的工作雖然都是維護國家政治運行,但因分工不同而導致各言其事,故有了各自不同的言說話語。
中國古代,一定的文體都產生于一定性質的行為。官員的職守不同,其行為性質也不同,故其所使用的文書的文體也有不同。如士師掌禁令、獄訟、刑罰,其所用的文書為用之于軍旅的誓、用之于會同的誥,用之于田役的禁和用之于國中的糾,用之于都鄙的憲[1]1889。太祝為掌管宗教禱祝的官員,負責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這六祝之辭的寫作;同時還要負責作祠、命、誥、會、禱、誄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1]1746-1747。“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1]1761-1762大史執掌禮法,其方式是對帝王言行和對官員違反禮法進行記錄,以“昭法式”。如趙穿在桃園攻殺晉靈公,大史記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他們使用的為“春秋”這一記事文體。這就是《禮記·王制》所說:“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5]2911《漢書》亦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4]1715可見,先秦不同職守的官員,不僅有著不同的職守話語,也使用著不同的職守文體。如章學誠所說:“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官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故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13]雖然不能說先秦就完全沒有私人的著述,但先秦兩漢的官員都有自己的職守、專門的政令和知識話語體系,卻是事實。這種國家機構職官身份和知識話語的對應,不僅形成了一定性質的行為產生一定文體的觀念,也很自然地形成了身份與知識話語體系對應的觀念。
職官的分工也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學術流派的區分,產生了學術身份。班固從職官身份的角度去闡釋諸子學術的發生,不一定全是事實,但有些學派出自職官的職守話語卻是不容懷疑的。如說農家出自農官,法家出自主持刑罰的理官,道家出自史官,也是有一定依據的。道家的始祖為老子,其思想的核心是主張順任自然,無為而無不為,反對以禮樂道德去異化人性。而這一觀念應該主要源于《歸藏》和《周易》。史家本兼有宗教職能,春秋時史家也熟知《歸藏》《周易》,而老子本來是周守藏室之史,故說道家出于史官并不是完全沒有依據。
2.先秦兩漢的人倫身份與其話語的規定性
禮樂制度的內涵是禮樂道德,諸如孝悌、仁義、忠信等。這些道德的實踐,雖不分等級身份,但具體到一定的等級身份,卻有極為嚴密的行為規范。如《禮記·曲禮上》說,為人子,出門回家一定要告訴父母;吃飯不能和長者同在一席,也不能坐中席;居處不能在年長者所居房子的西南角,不能走道路的中間,不能站門的中間。在路上遇到先生,要小步快走靠近,拱手正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平時要端正容貌,聽人說話必須專注恭敬。說話不能把別人的話當成自己說的話,也不能重復別人說的話,而且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曲禮下》多言政治倫理的行為規范,如說大夫私人外出、出疆必須請示,“反必有獻”。士私人“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5]27。可見,在禮樂制度下,不同的倫理身份,其行為方式是有嚴格規范的。
同樣,不同的倫理身份也有著不同的嚴格的話語規范。雖然孔子所說“非禮勿言”是普遍的要求,人們說話都必須符合禮的規范要求,如《管子·匡君小匡》說:“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14]但具體到不同的身份,包括稱謂、自稱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如兒女對于父母,臣子對于君主,下級對于上級,少年對長者,都有著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和話語規范。身份不同,所使用的話語也有很大不同。這在《禮記》的一些篇章中有詳細的記載。如稱謂,同為人婦,天子的妃子稱后,諸侯的配偶稱夫人,大夫的配偶稱孺人,士的配偶稱婦人,庶人配偶稱妻[5]2743。自稱如《禮記·玉藻》說:“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5]3217-3218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身份也會不同,其自稱也不同。如《禮記·曲禮下》說:“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兇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5]2742同一性質的事情,因身份和言說場合不一樣,禮也明確規定有不同的表述話語。如《禮記·曲禮下》載,同為死,“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5]2748。同為回答他人問兒子長幼,國君之子、大夫之子和士之子因身份不同,表述也不一樣。如《少儀》說:“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于樂人、未能正于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5]3279如此等等,不一盡述。
從《禮記》的這些記載看,先秦兩漢時期的這種人倫身份規范,遍布于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不僅在行事時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且在不同場合說話時也必須符合自己的身份。禮制中這種嚴格的身份規范無時無刻不在強化著人們的身份意識,并由此而在整個社會形成了強烈的身份意識。一旦某個人的行為和言說有違身份,便會招來責難與批評。先秦兩漢時期禮制極為嚴格,涉及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這種倫理身份的批評充斥于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學多是因社會生活之事而作,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倫理身份批評也因而順理成章地應用于文學的批評之中,對這一時期文學的身份批評起著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結 語
文學的身份批評是一種從主體在社會各種關系中的定位去考察其作品的創作內容、題材、表現方式、審美價值取向的批評方法。因主體一般以一定的身份去獲取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每一主體都具有多種社會身份及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主體的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身份的生產生活行為方式及知識話語的影響。因此,文學的身份批評不僅可以用來探尋具體作品的言說內容、題材、表現方式、審美價值取向的形成,而且可以發現其創作與時代、民族、地域、團體、職業、學術等方面的內在關聯,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并對其做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評判。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不同創作主體的同一言說身份,發現這一身份的創作在言說內容、題材、表現方式、審美價值取向上的趨同性;通過主體創作的隱含身份,探討不同主體、地域、流派、時代、民族之間創作的趨同性和差異性產生的緣由。因而,身份理論對中國古代文學及其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