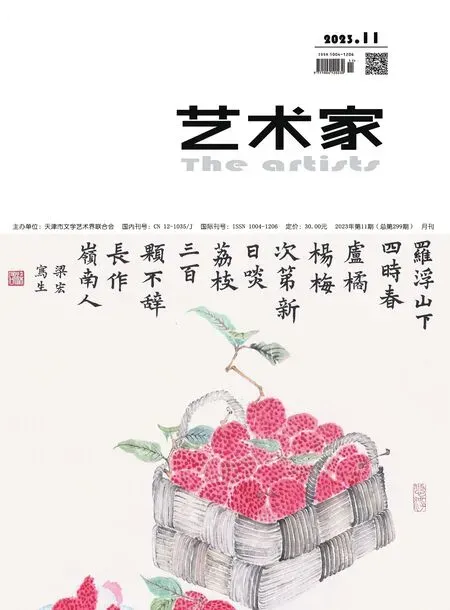現代性視域下閻連科小說的鄉村書寫
□羅雯靜
閻連科是21 世紀文壇上一位具有“土性”的作家,面臨傳統鄉土歷經現代性洗禮這一尷尬境地,他以干預現實的莫大勇氣真誠地書寫著鄉土文明遭遇現代性后鄉土文化的斷裂問題。閻連科采用荒誕手法演繹著“鄉土共同體”的土崩瓦解,現實“烏托邦”理想的幻滅。其“民族寓言”的宏大書寫中蘊含著啟蒙精神,苦心孤詣地道出社會轉型期間民眾生存困境;物化的世界里所折射出的鄉土社會倫理鏡像,淋漓盡致地展示著善惡雜糅的人性;耙耬世界里氤氳著人類生存夢想的現代性隱喻,追尋著安撫人類心靈的棲息地。
我國古代文化博大精深,關于“變”的智慧在我國古代思想中就有體現。中國古代史家認為“變”有三個級度:一曰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曰百年期的緩慢漸變;第三種變化并不基于時間維度,通稱“激變”或者“劇烈脫節”。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來我國社會文化的變革便屬于第三種。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現代性觀念開始在中國興起。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在啟蒙與救亡相交替、內憂和外患相交織的復雜局勢下朝現代化的道路上探索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顯著提升的背后也滋生了許多問題,如物質與精神不平衡的發展、畸形的物欲追求、環境污染等。在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乃至與后現代交替之時,鄉土作家閻連科面對傳統鄉土遭遇現代文明這一現實問題時,表達了復雜的文化心態。
一、荒誕手法與“鄉土共同體”的瓦解
現代性在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與科學技術革新的同時,也催生了導致人性的物質化、工具化的社會圖景。現代性席卷過后的人類社會面臨的是精神災難。現代性作為啟蒙時代以來“新的”世界體系的生成,與鄉土小說有著不解之緣。“鄉土小說”這一概念的產生與現代性密切相關:正是因為現代工業文明的到來,人們不再像以往一樣以鄉村為主要生活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成為人們生活和關注的中心,有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對立,所謂的“鄉土社會”和“鄉土小說”概念才得以誕生。對于傳統鄉土遭遇現代文明這一問題,鄉土作家閻連科在其小說中傳達了自己的立場: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封閉鄉土社會有著自己的運行法則,現代性的強行介入為異化現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對烏托邦狂熱追求的人們也在物欲、原欲等的誘惑下,人性承受異化和扭曲的折磨。
閻連科筆下描繪最多的是社會關系封閉的耙耬山脈,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邊緣群體人物,有著一套完備的權利法則、道德準則和倫理法則。人們起初都有熱烈而堅定的共同意志,堅決服從于同一個權力中心,圍繞著同一個既定目標,遵循同一套倫理道德共同努力奮斗。現代性涌入傳統鄉土社會,打破了鄉土社會表面的穩定、平衡。多元文化的滲透、個人主義的滋長、畸形欲望的生長等都為社會關系封閉的人們提供了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因而,當傳統鄉土遭遇現代文明之時,由于技術、欲望、市場等的輸入,鄉土社會里的農民在心理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瘋狂的幻想與美好的愿望、畸形的欲望與本能的渴望等都使鄉土社會的人近似瘋狂,人性開始異化,中國鄉土便由平衡、穩定走向嘩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的隱憂》中說:“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攜同現代性之名肢解自由、造成秩序混亂現象的情形十分相似。”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中,丁莊作為全縣城最窮的莊子,顯然傳統的農耕方式已經無法滿足丁莊人對物質財富的渴望,“三層高的青瓦房”成了丁莊人此生最大的追求。縣教育局高局長找到當地頗有聲望的丁水陽來動員丁莊人賣血,在丁水陽的鼓動下,窮困潦倒的丁莊人便開始了以血為商品的營生,上演了將血肉作為原始資本追逐財富的慘劇。丁水陽的兒子丁輝則是慘劇的罪魁禍首。他對金錢的過分追逐導致他人格的極度扭曲。丁輝建立的抽血站不符合衛生標準,重復使用棉簽和針頭致使丁莊爆發了嚴重的艾滋病。當丁莊被死亡的陰霾籠罩之時,更為荒謬可笑的是他卻發起了“死人財”。他與高局長二人相互勾結把國家免費發放給熱病患者的棺材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并且把這些棺材當成商品賣給那些將死之人。
閻連科采用荒誕手法敘事實際上就是演繹著“鄉土共同體”的土崩瓦解,“鄉土共同體”失序的原因在于人們對“烏托邦”的狂熱追求。閻連科的長篇小說《堅硬如水》把這種敘事手法展現得淋漓盡致。高愛軍和夏紅梅是具有現代思想的青年人,本想為鄉土社會的轉型貢獻自己的力量,但事與愿違,長期浸染于傳統鄉村宗法制度的村民排斥外來思想。高愛軍和夏紅梅的努力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人與人之間開始了鉤心斗角,原來富庶的土地產量銳減,高愛軍和夏紅梅也在鄉土社會的現代化浪潮中逐漸迷失自我。在二人的謀劃算計下,一心為百姓謀福利、求發展的趙秀玉和王鎮長被送進了監獄,趙秀玉在監獄里自殺,李林隊長則被村民們活活打死。原始的、傳統的鄉土社會在現代因素的浸染之下發生了嘩變,瓦解了鄉土社會的道德秩序,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們在心理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品的結尾處,高愛軍和夏紅梅在錯誤意識的引導下殺人毀寺,導致一切都走向了毀滅。所有的一切都伴隨著傳統鄉土秩序的解構、“烏托邦”理想的破滅走向了歷史的虛無。
二、耙耬世界與“民族寓言”的宏大書寫
當整個社會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的工業文明轉型,乃至后現代、后工業時代到來之時,知識分子對農村農民的精神狀態與生存狀況的關注頗少,鄉土淪落為逐漸被邊緣化的境地。閻連科用荒誕筆法所創造出的文學世界,實際上是對世紀末農村深切關注的“民族寓言”。閻連科以一種“民族寓言”式的獨特表述策略,采用西方式的價值與精神,含情脈脈地審視著匍匐于那片貧瘠的土地上“耙耬山脈”的蕓蕓眾生,苦心孤詣地給予民族歷史和命運深切的觀照。
“民族寓言”這一理論源于西方話語,詹姆遜在《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這篇論文中指明了“民族寓言”是關于以魯迅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學整體特征的名詞。詹姆遜認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詹姆遜以魯迅的《阿Q 正傳》為例說明“民族寓言”的巨大作用。阿Q 是寓言式的中國本身,而那些取笑玩弄阿Q 的可憐蟲在寓言的意義上也是中國。詹姆遜的這種“民族寓言”中所蘊含的對民族歷史和命運進行全方位關照的精神是存在著某種合理性的,更與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心理不謀而合。但是閻連科“民族寓言”式的寫作方式與魯迅相比則黯淡了不少,因為他關注的僅僅是20 世紀后期河南豫西那塊土地,以及匍匐于那塊土地上求生存的農民。土生土長的農村作家閻連科始終相信,從改革開放到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此浪潮下的農村和城市的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仍舊為了生計和疾病痛苦掙扎,因而為窮苦人代言成了閻連科文學創作中不自覺的追求,他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一隅之地,并逐漸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耙耬山脈”。
閻連科小說“民族寓言”的宏大書寫在空間的特異性和時間的不確定性上尤為突出。首先是空間的特異性,閻連科長篇小說《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是三個縣城交匯的村莊,然而三個縣城的縣志上均沒有有關三姓村的記載。依據他們代代相傳的說法,在明末清初之時,他們的祖輩為了躲避戰亂,藍姓、杜姓、司馬姓依次從山東、山西、陜西逃難至耙耬山脈深處,由于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便在這里安居樂業,繁衍子孫,因而形成了村落。《受活》中的受活莊是位于耙耬山脈深處的一個深溝,源自明王朝的大遷移。其次就是時間的不確定性,如《年月日》中故事發生的時間為“千古旱天那一年”,時間的模糊使讀者只能依靠文本的整體閱讀去猜測故事發生的時間。這兩種特質使閻連科創作了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世界——“耙耬世界”。在《年月日》《受活》《日光流年》《耙耬天歌》《耙耬山脈》等文學作品中的“耙耬世界”經過作者藝術的加工成了經驗世界與客觀世界部分相重合的獨特世界。因而,閻連科筆下的“耙耬山脈”、丁莊、受活莊、三姓村都是歷經現代科技文明、工業文明洗禮下鄉土中國的隱喻。三姓村人世世代代活不過四十歲的陰霾、丁莊爆發的艾滋病、受活莊里的殘缺人、“耙耬山脈”里莫名的災害,都寓言性地象征著處于社會轉型期間鄉土中國的苦難。由此可見,閻連科筆下“耙耬山脈”深處的村莊蘊含著極大的隱喻意義,以及在這些村莊里所出現的災難和疾病,既是一種“民族寓言”式的宏大書寫,在一定意義上又象征著處于社會轉型期間的鄉土中國。
三、物化世界與鄉土社會倫理鏡像
當現代性向后現代性過渡之時,由市場經濟所催發的消費觀念和價值理念的合理化,使處于世紀之交的人們沉醉在虛幻的商品經濟中,以城市為中心的欲望世界由此生成。閻連科對現代性的態度既有迎合又有批判。現代性的到來確實使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會制度得到完善;但是作為一位有著敏銳洞察力和理性思維的現代知識分子,閻連科發現現代性的高度膨脹導致社會局限,在浮躁、悲觀、迷茫的鄉土社會面孔下,人類利己主義的本能存在于一個物化的世界里,共同演繹出善惡雜糅、美丑并存的人性萬象。個體道德中的善良、邪惡、美好、陰暗全面折射出了鄉土社會倫理的表征,更凸顯了鄉村倫理秩序。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描寫了現代化浪潮下丁莊人對金錢的畸形追求及對生活的美好憧憬。丁水陽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了在這樣一個物化的世界里,作者仍對民間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給予肯定,對鄉村道德的重建給予了莫大的期望。
小說的敘述視角采取的是第一人稱的亡靈視角,以一個不在人世的12 歲的“我”來講述丁莊荒誕離奇的故事。生活在丁莊的人本是以種地為生的,他們逐漸發現傳統的農耕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對更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新的社會語境所誘發的物欲追求。于是,丁莊人拋棄了理性,用近乎癲狂的病態心理踏上了通往“美好生活”的路程。教育局高局長為了丁莊人賣血便找到丁水陽,丁水陽按照高局長的理論讓鄉親們認識到“血和泉水一樣,舀不干,越舀越旺”。大家抵不住金錢的誘惑便開始瘋狂賣血。丁水陽的兒子丁輝建立了第一個抽血站。丁輝對金錢的追逐致使他的人格極度扭曲,成了丁莊里最大的血頭。鄉民們出于報復起先只是毒害“我”家的雞鴨,最后失去理智毒死了“我”。畸形的物欲追求致使村民麻木不仁,忽視了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傳統鄉土社會的重義輕利、淳樸善良也因物欲的空前膨脹變得土崩瓦解。在這樣一個物欲高度膨脹的世界里,丁莊里上演了一幕幕倫理道德喪失、人性荒誕可笑的景觀。
丁水陽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現了作者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圍剿之下仍對傳統鄉土中的積極因素予以肯定。丁水陽有自己的道德準則和行為尺度,他試圖勸說兒子放棄這種營生并向全村人賠禮道歉。在勸說無果后,他便把患熱病的村民召集到村里的學校并貼心地照顧他們的飲食,希望可以控制村里疫情的蔓延。他宅心仁厚,擁有長遠的目光,為了使村里的孩子受到教育與瘋搶學校教學設備的賈根柱等人周旋,勢單力薄的他最終只能看著學校被搶劫一空。這位固守傳統道德的老者希望可以破除僵局,期盼村莊里的村民可以放下對兒子丁輝的仇視并和睦相處。但事與愿違,最后丁水陽選擇了一種極端的方式:一悶棍打死了自己的兒子。
閻連科是21 世紀以來一位獨特的作家,他對現代性的追問與尋思體現出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道義和責任感。他用自己的文學作品構筑理想的鄉土社會,建構人文精神。他采用荒誕手法敘事演繹著“鄉土共同體”的土崩瓦解;“民族寓言”的宏大書寫蘊含著作者對民族歷史和命運的深切觀照;鄉土社會倫理道德的失序,揭示出社會轉型期間鄉土人們在物欲的誘惑下潰不成軍的社會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