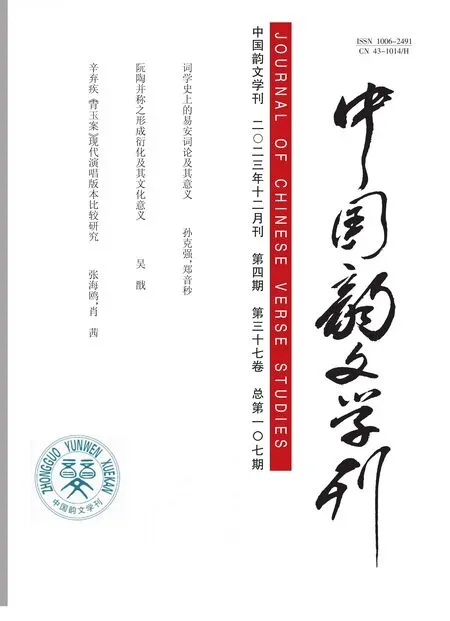以貧嘆拙:陶淵明詩歌“拙人”書寫的獨創意義
張思羽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2488)
陶淵明的詩歌書寫了拙于世事、任真自守的內心懷抱,詩人以“拙人”自視,在詩作中多角度地展現了身為“拙人”的人生體驗與世事反思;在創作手法上,陶淵明將“嘆拙”與“詠貧”相結合,通過“以貧嘆拙”的筆法,深刻呈現了“拙人”獨特的精神藝術內涵,創造了在詩歌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拙人”這一藝術形象。杜甫、白居易等唐代大家深入繼承了陶詩的“拙人”書寫,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新變,從而塑造出更為豐富立體的“拙人”形象。陶詩“拙人”書寫的創新及其詩歌史影響,對于認識中古詩歌的精神藝術價值有重要意義。
一 以貧嘆拙:陶詩的“拙人”書寫
陶淵明多借詩歌表現隱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文學題材時常伴隨著他對“拙”的詠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1)文中凡引陶詩皆據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22年版。[1](P74)。詩人自視為“拙人”,并進一步發掘出自身疏離于外部世界之巧偽的拙樸特質。這一“拙人”話語與其衣食困乏的貧居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確切地說,“嘆拙”與“詠貧”兩種鮮明的旋律始終回蕩在陶淵明的詩歌之中。前者主要表現為不通世務、拙于人情的自嘲,后者則指向對歸隱田園后貧窶之苦的嗟嘆。“嘆拙”與“詠貧”兩重思想表達相因相生,逐步交織成一種“以貧嘆拙”的獨特筆法,塑造出意涵豐富的“拙人”藝術形象,宣示了陶淵明對適性生活的追求及其對完足生命意識的領悟。
陶淵明集中言“拙”者凡七見: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
誠愿游昆華,邈然茲道絕。[1](P62)
(《影答形》)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1](P74)
[《歸園田居(其一)》]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1](P100)
(《乞食》)
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
平津茍不由,棲遲詎為拙?[1](P202)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1](P347)
[《雜詩(其八)》]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1](P368)
[《詠貧士(其六)》]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1](P425)
(《感士不遇賦》)
盡管在這些句子中,“拙”出現的語境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所傳達出的情感色彩基本一致,即一種高度的自我認同。這種自我認同意味著陶淵明主動順應其天生質性,選擇了一種在旁人看來未免窘迫的生活方式。他多次在詩歌作品中描繪自己衣食不完的處境:“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1](P106)、“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1](P202)等,但在客觀描繪貧窶生活的基礎上,陶淵明更多強調自己不以躬耕自食為苦的安然態度,這是由于他對自身質性中的拙樸本色有深刻而明晰的體認。這種拙樸不僅導致物質的困窘,亦是陶淵明見斥于官場的深層緣由。因此不難發現,陶詩的“嘆拙”往往伴隨著“詠貧”的思想主題一同出現。詩人并非以空談的口吻強調自己守拙的價值取向,而是依托于對“貧”的客觀摹寫,《歸園田居(其一)》《乞食》《雜詩(其八)》《詠貧士(其六)》等詩皆是從匱乏的現實物質條件敘起,再推及對自身質性之“拙”的堅守與追求,這一現象尤其值得深入探討。
陶淵明于義熙元年(405)辭彭澤令后幾乎完全退隱隴畝,主動拒斥“薄宦”所帶來的必然后果之一即是物質條件的拮據,此點已為人所共知。其日常吟詠多涉饑寒,如“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1](P301)、“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雜詩(其八)》][1](P347)等。上述詩文中所談到的“拙”既指向陶淵明的個性,也與其生活處境息息相關。詩人自知質性之拙難以改易,因此毫不猶豫地選擇“守拙”。然而與此同時,他失去官俸又不善生事,其生活的拮據是可以想見的。故在其表達中,“詠貧”與“嘆拙”實為一組互為表里的文學主題,他之所以能夠安于貧窶的躬耕日常,是由于其內心深處存在對“拙”的執著堅守,正是這種堅守使其超越了以往的“貧士”而能夠以“拙人”本色立身。
回顧此前的詩歌史與思想史,“詠貧”并非新鮮主題,書寫饑寒現實、暢言安貧樂道亦非由淵明始創。經典文本中的“詠貧”大致不出兩類表達:一是嗟嘆貧寒之苦,如《詩·邶風·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2](P103),曹植《贈徐干》“顧念蓬室士,貧賤誠可憐”[3](P63);另一類更加普遍,即源出儒家思想的安貧固窮之說,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4](P8)、“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4](P141)及“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5](P28)等。在此思想語境中,貧窶生活是作為君子之道、高潔之志的陪襯而存在的,真正受到推崇和吟詠的對象乃是安貧、樂貧的人生態度。(2)關于魏晉以來詠貧詩的主題呈現與涵容變化,可參魏念芳《魏晉六朝文人詠貧士詩研究》(華僑大學2021年6月碩士學位論文)。對主動摒棄仕宦之途的逸民高士而言,困于衣食乃是常態,如東漢的向長、與陶淵明同列《晉書·隱逸》的孫登、董京、郭文等(3)參見李生龍《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一書。書中第三章《隱士的經濟狀況》詳細列舉了隱士貧困的境況及其謀求自立的方式。除躬耕之外,漁、樵、屠沽、教書等亦為其謀生選擇。如作者所言:“因為貧窮之故,隱士多重視謀求經濟上的自立。因為如果不能滿足起碼的生活條件,他們就很難維持自己人格獨立的初衷。”(P62)“如果僅僅靠自食其力,隱士們即使再勤勉,充其量也只能自給自足,不可能致富。所以他們靠保持一種隱逸心態來維持隱逸之志,即甘于生活清苦而追求精神上的恬淡閑適。”(P60)[6](P60),趙壹更是在《刺世嫉邪賦》中借秦客之口直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7](P2631)。飽讀詩書的士人固守清高節操,不欲屈身事俗,難免落到身無長物的境地。也正因此,他們索性發展出一套安于饑寒處境的觀念,用“君子固窮”等思想消解衣食匱乏所帶來的苦痛。漢代以來,士人多仰慕恥食周粟的夷齊、簞食陋巷的顏回和茅屋不完的原憲,將他們視為安貧樂道、持身自潔的楷模。延及東晉,玄學思潮的影響又使得安貧思想進一步與少私寡欲、靜心修志等主張相聯系,如《抱樸子外篇·安貧》所言:
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于險途,澄精神于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臺鼎, 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 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8](P211)
這段話展現出一套與世俗物質富貴相對立的心靈富足標準。通六藝、揮翰藻,覽天地萬物之玄妙,便可從容自得,“與賈豎爭利”“與凡瑣競達”則會讓人迷失本心。自先秦至于兩晉,儒、道二家盡管在應世方式等具體觀念上存在分歧,當涉及“貧”的話題時卻往往不約而同地強調“憂道不憂貧”,不僅不以貧窶為苦,反而視之為遠世俗、秉素志的高遠境界。
然而,此類“詠貧”表達極少涉及對個人質性的討論,大體屬于一種非功利的、彰顯人格境界的道德追求,但這種追求仍然屬于向外的標榜而非向內的省視。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得知安貧、樂貧之舉是否合乎士人的本愿,他們在貧寒處境中真切的心靈狀態實則已隱沒于某種普泛的思想潮流之中。但在陶淵明筆下,我們看到了新的思想質素的加入。他嘗試從“拙”的角度理解前代貧士的出處選擇,將籠統的“詠貧”主題提升到身心相適的高度。這一思想傾向集中體現在其《詠貧士》組詩中。
貫穿組詩始終的是詩人對前賢平和、從容心境的著力刻畫,這正符合陶淵明“拙人”的心理投射。在他看來,安于貧窶乃是拒斥仕進、量力循性的必然結果,無須作憤世之語。所謂“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詠貧士(其一)》][1](P357),“量力守故轍”與“寒與饑”可謂順理成章。既以遵從本心為前提,那么貧窮的生活就并不構成一種阻礙。此處的“守故轍”與“守拙”其實有著相近的意涵,即強調“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歸去來兮辭》)[1](P452)。與其認為古代賢士是不得已忍受貧窮生活的苦楚,陶淵明更加深信他們與自己一樣深懷拙人之心,主動舍棄世俗名利而選擇保全身心自由:
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1](P362)
(其三)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1](P364)
(其四)
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1](P366)
(其五)
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1](P368)
(其六)
上述詩句都采用設問語氣,詩人一面提出質疑,一面代古人述志。詩中涉及貧窶之苦的描繪超越了對安貧精神的簡單謳歌,意在揭示貧士質性之外的“拙人”本色。這種對內心之拙的執守可作為理解貧士心中之“道”的重要切入點。陶詩提及的貧士長年過著“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其三)、“芻槁有常溫,采莒足朝餐”(其五)的生活,甚至于達到“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其四)的地步,那么他們該如何解決“貧富常交戰”的問題呢?詩人嘗試從順應天性的角度找尋他們甘愿置身其間的緣由,表述在詩歌中即是“茍得非所欽”“非道故無憂”“道勝無戚顏”“所樂非窮通”——在物質富足與精神充盈之間,他們舍前而取后,選擇遵從內心之“道”,這里的“道”也即不違背本性,為獲得飽暖而“矯勵”迎合世俗。至此,系于“貧”的哀嘆已消解于對“拙”的自覺認識之中。借助對自身固有質性的發掘,陶淵明與前賢達成了觀念上的共振。不合時宜、拙于人事的天性誠然使“拙人”難以在遍布塵囂的世俗空間內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正因拙于人事,個體索性得以從繁雜世事中抽身,免受俗務牽纏。身心自由與物質豐裕固難兩全,因而取舍之后的貧窶便顯得順理成章,無須作怨艾之態。理清了陶詩的詮釋邏輯,方能明確陶淵明思想貢獻的關鍵之處:他不再像前人一樣將安貧樂道看作一種外在的道德追求,而是真正從個體天性的本源上去探尋一條最適宜“拙人”生存的道路,這樣一來,安貧就成為一種發乎本心而非被外界賦予的自洽選擇。于是,只有不善應對人事、專注追求仁義之道的“拙人”,才能做到與先賢精神合契。陳引馳曾從現實政治角度闡釋陶淵明在人生觀念上的超越性:
陶淵明對于自己歸隱田園的種種自我詮說,從自然本性立說,承莊生玄學之緒,固然是其學問思理有以致之,實亦是現實中挫敗之人生經驗的轉化與提升。陶的自我轉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當時的現實和此后的歷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借文字而實現了自我的完成。[9](P26)
由此,我們也可以說,這種自我完成是在“詠貧”與“嘆拙”的深入融合中實現的。有別于大張旗鼓地宣稱自己“安貧樂道”,正是由于“人事固以拙”,方能真正與先賢合契,獲得超脫形骸的精神自由。歸根結底,陶淵明饑寒書寫的旨歸在于對“拙人”的體認與書寫。區別于從古以來對“貧”的強調,他另辟蹊徑地將“拙”作為賢士所共有的天性,指出順應天性與坦然接受貧窶的內在一致性,進而使其筆下的“拙人”超越了以往面目模糊、形象單一的“貧士”,成為立體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學形象。由貧窶設問,釋以從容樂道,陶淵明在異代知己身上找到了實現心靈自洽與完足的方法,即“轉而否棄外在征取,返歸內心,啟明本心,超越有形,表現為一種理想人格的修養,進入一種生命的自由境界”[10](P96)。陶淵明通過嘆拙來更新傳統的詩歌主題,并使得“拙人”這一文學形象得以在詩歌創作中逐步生成。
二 陶詩“拙人”形象的思想藝術創新
以順應質性之“拙”視角審視貧窶,使陶淵明能夠從容面對饑寒,不作怨艾之態,朗然宣告“守拙歸園田”的出處選擇。他不但以“拙”自命,還將這一“拙”的品格賦予前代貧士,最終促成“拙人”藝術形象的誕生,并使其進入新的文學文本。要理解這一點,首先應回到漢魏時期玄學思想盛行的大背景中。
陶詩中的“守拙”是當時士人清談與詩文寫作中的常見語詞,亦是兩晉玄風中的重要觀念,如潘岳《閑居賦》“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11](P1987)、庾純《大槐賦》“若其含真抱樸,曠世所希”[11](P1667)等皆是這一思想傾向的反映。還歸素樸、養拙、守拙等強調內心修養的重要意義,是對魏晉前期虛浮躁進玄風的反撥(4)關于此問題,曹勝高《陶淵明與東晉玄學之新變》有詳細闡述,文中談到西晉玄風一反此前之激切空誕,士人群體中普遍流露一種素樸、天真意識,這一趨勢延及東晉,與佛教思想合流后為士人所普遍接受。靜默自守的處世態度“促進了東晉士人檢束自約、拙樸自娛的新風尚”,“東晉抱樸守真思想的形成, 是西晉玄學的新發展,也是佛教思想浸潤的結果。佛教中求真、率真的意識,與玄學中正在生成沖淡、清虛、天真等觀念合拍,使得老莊的守中、養中觀念更加明晰。”見曹勝高《陶淵明與東晉玄學之新變》(《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1期)。[12](P46-51)。回到先秦道家語境,“拙”是一種區別于工巧的內在品格,當時崇拙黜巧之論屢見不鮮,如《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四十五章)[13](P243),《莊子》“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庚桑楚》)[14](P715)、“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達生》)[14](P552)等。在老莊看來,“拙”乃是固守本心、渾樸靜默的表現。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13](P147)、“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莊子·馬蹄》)[14](P290),拙、樸對應著一種清靜寡欲、退守自居的處世姿態。它代表不施外力,安時處順,實為洞察自然之道的“大巧”;而權變、矯飾乃指向世俗意義上的“小巧”,與道家所提倡的“虛靜”背道而馳。這種與工巧相對立的拙樸具體到人的行為上則表現為不善應物處世,缺乏機變。反對機巧詐偽、執著抱樸守真的思想延及魏晉,在“越名教而任自然”風尚的影響下,又成為士人寫作中的慣用表達: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11](P1734)
(傅玄《傅子·通志》)
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11](P1698)
(杜預《奏上黜陟課略》)
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15](P928)
(張斐《表上律法》)
此時期詩歌中亦不乏崇拙黜巧之語,如曹植《當事君行》“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3](634)、張協《雜詩(其七)》“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16](P746)、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17](P234)等。可見,以“拙”對應質樸真誠,“巧”對應變詐偽飾從古以來即為士人共識,他們推崇守拙、養拙的處世哲學,試圖摒棄外部的浮華喧囂,回歸內心的清虛靜默,在精神世界中不斷接近所求之道。要達到這一渾樸自然的理想狀態,就需要戒除功利追求,保持從容淡泊的心境,才不會被塵世的種種“小巧”迷惑。“‘大巧若拙’不僅是反對技術、反對人們改造世界,同時也指向一種天然自守、不為外物所動的精神世界的涵養。”[18](P57)
陶淵明不僅在觀念上繼承了當時抱樸守拙的處世哲學,更值得留意的是,他從躬耕生活與對前賢的同情理解中發掘出一條“以貧嘆拙”的獨特表達路徑,在推崇拙樸人生觀的問題上展現出獨特的思想藝術創新,用切身體驗詮釋出“拙人”的生命底色,使抽象的“守拙”轉化為“拙人”這一豐富而立體的文學形象。
首先,區別于以往士人因時局昏昧而被迫隱遁的無奈選擇,“拙人”乃主動順應本心選擇遠離俗世,這一舉動展現出陶淵明任真自守的人生反思。魏晉之際,士人的佯狂避世之舉固然與性情有關,但更多是黑暗社會與高壓統治所致,其自然任心同時伴隨著揮之不去的苦悶彷徨(5)可參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19年版。書中談道:“在曹氏與司馬氏的權力爭奪中,多數名士被司馬氏殺掉,到景元四年(263)殺嵇康,與政權爭奪糾結著的名教與自然的矛盾便作了一次強烈的大暴露,自然任心受到了最沉重的一次打擊。”(P61)政治高壓之下的出世多帶有幾分不得已而為之的色彩,直至西晉才開始出現贊美隱遁本身、怡悅山水空間的傾向。參[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P121—123)。[19](P61-63)。在陶淵明的表達中,“拙”不僅意味著對現實社會的疏離,它更多指向獨屬于個體的天然質性。如袁行霈先生注“守拙”云:“此‘拙’乃相對于世俗之‘機巧’而言,‘守拙’意謂保持自身純樸之本性(自世俗看來為愚拙),而不同流合污。”[1](P78)這里的“本性”既是一種“愚”,同時又是一種“真”,它與“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1](P122)、“真想初在襟”(《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1](P176)等思想是相通的,強調在變動無常的人生中恪守本真,不被外物牽動和擾亂。“在充滿機巧、聰明的社會中,渴望抱樸守真的人,只能自嘲自己的拙樸。陶淵明把自己不合于世事、不能塵俗浮沉的性情稱之為‘拙’。”[12](P47)其中包含的“真”這一重內涵決定了陶詩之言“拙”與魏晉六朝詩有本質區別(6)牛志強結合書籍傳播史,從對《莊子》思想的吸收與發揮這一角度著重論述了陶淵明對“真”執著追求。文章指出:“陶淵明秉承了《莊子》‘真’之‘本然、真樸’之義,偏重人性的良善與內心的和樂,陶淵明與莊子對‘真’之呼喚都是建立在他們對現實偽善的感受之上的,只是二者面對偽善時所采取的解決路徑不同,莊子之法更徹底,但無法實踐,陶淵明之法比較易行,但容易反復。”(P114)參牛志強《晉代〈莊子〉書籍史與陶淵明的思想實踐》[《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一文。。嵇康“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述志詩(其二)》][16](P489)、謝靈運“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初去郡》)[17](P144)、“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從游京口北固應詔》)[17](P234)等句中的“拙”雖然也屬于自嘲,卻帶有為世路所阻的郁憤不平之氣,這并非真正將自己視作愚拙之人,其本質是痛恨世道昏暗,有志難騁。于淵明而言,“拙”卻是一種真切的自我指稱與切身體認,因為在其觀念中,自己就是一個幾經沉浮而“失其方”的“拙人”。在《感士不遇賦》序中,他描述了大偽之風盛行、君子難以見容的現狀: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1](P423)
在“真風告逝”的時代,如果想要不違背本心,遠離塵世的躬耕生活便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盡管在世俗眼光中,這意味著常人難以忍受的饑寒: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1](P425)
此番剖白既是自明己志,又代表陶淵明對出世行為的理解。他絕不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態,僅僅將歸隱視為世俗生活的補充和調劑,而是從具體的生活出發,對前人絕棄軒冕的心理動機作出深刻體察,“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二句即是其同理心的體現。在此基礎上,“守真”又進一步引申出“適性”的話題。魏晉士人發揮莊子“逍遙”之論,強調“性分”“循性而動”,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及郭象《莊子》注皆對此有詳細闡述。郭象言“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任之自苦,皆得其極”,亦強調得逍遙的關鍵在于“任性”(7)陳引馳對莊學中“循性而動”的思想做了充分論述,參陳引馳《文學傳統與中古道家佛教》(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書中第二章“中古文學中的‘自由’與‘生命’”一節談道:“由循性而得人生之自由,中古文人最杰出之闡釋者與實踐者乃陶潛。詩人深于玄理,‘性’及‘自然’即解說其人生抉擇、生命觀念之要點所在。”(P239)[20](P239)。于陶淵明而言,承認并主動選擇一條合乎天性的人生道路乃是自然常理,這一態度常常通過詩句中的反問語氣得到體現:“平津茍不由,棲遲詎為拙”(《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1](P202)、“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九日閑居》)[1](P70)、“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飲酒(其九)》[1](P251)……隱含在這些詩句中的表達是共通的——如果仕途并非世間唯一出路,那么棄絕此道又豈能被稱為愚拙?在陶淵明看來,仕與隱不存在價值分別,關鍵在于從心所欲、適性而為。因此,“拙人”的出處選擇也就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而是陶淵明成熟完足人格的突出表征。
其次,通過塑造不通世務的“拙人”形象,陶淵明進一步強化了任真自守觀念中的實踐性品格。魏晉時期的“守拙”觀念原本指向當時士人對精神自由的強烈追求,諸如“好樸尚古”(傅玄《辟雍鄉飲酒賦》)[11](P1715)、“藏智以樸,卷舒有時”(管辰《敘管輅》)[11](P1875)等推崇拙樸的表達盡管十分常見,卻多與當時的玄言詩相類,僅停留于對義理的泛泛空談,并未對“拙”的深層內涵作出更多的闡釋和發揮。陶淵明則借助詠貧反思拙人的出處選擇,從而實現其質性自覺與躬耕體驗的深度融合。愚拙之人難以適應遍布機巧的俗世,且又不善生事,無法僅憑勞作換取溫飽生活,個中辛酸實難備陳。陶淵明從未試圖遮蔽饑寒帶來的苦痛,生計憂慮與其質性之拙可謂如影隨形: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
結發念善事,亻黽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
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
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
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
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1](P105-106)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災對農事造成摧殘,致使詩人不得不深陷“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的窘迫境況。一貫有憂生之嗟、感嘆時日苦短[如“感悟愿及時,每恨靡所揮”[1](P168)]的陶淵明,面對這樣的苦楚也不禁“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期待時日飛速流駛。退居田園的逍遙詩意之外還牽系著年成、衣食等深重憂慮,這些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也被詩人納入曠渺的生命思索之中。袁行霈先生評此詩云:“種種貧困饑寒之狀……非親歷者不能道也。”[1](P112)陶淵明的拙人書寫始終建立在深刻現實體認的基礎之上,長年與貧窶相伴所產生的矛盾心情在其筆下自然流露——“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無悔于選擇的從容與橫亙眼前的煩難相依相生,反而增添了其思考的厚重感,因為這一對拙人真實處境的體察和表現恰恰是同時代高談抱樸守拙的士人最缺乏的。陶淵明向來輕視身后浮名,不以所謂“高節”自我標榜,如“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善惡茍不應,何事空立言”[《飲酒(其二)》][1](P235);“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1](P132)。正視貧窶之苦、平衡身心自由與物質生活是其以拙自命、詠貧嘆拙的底色。正如羅宗強先生《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所言:
玄學思潮起來之后,從嵇康阮籍到西晉名士到東晉名士,他們都在尋找玄學人生觀的種種實現方式,但是他們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何在呢?最根本的一點,便是他們沒有能找到化解世俗情結的力量。陶淵明找到了,他找來的是儒家的道德力量和佛家的般若空觀。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可能有他個人的種種因素。但他至少已經證明,玄學人生觀不具備實踐性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為玄學人生觀畫了一個句號。[21](P282)
最后,著眼于文學創作本身,陶淵明采取以貧嘆拙的表達,使“拙人”這一詩歌藝術形象擁有了立體的面貌,并以“拙人”之眼認識世界,傳達了他對出處與適性的深刻理解。借助日常吟詠,陶淵明創造出一個符合自身定位而又超越了古代“貧士”的“拙人”形象,將衣食飽暖等現實憂慮轉化為一種詩性體驗,從而不斷實現精神世界的圓融自足。以往文學作品中雖不乏安于饑寒的貧士與抱樸守真的玄士,卻未曾出現形象豐滿的“拙人”。“拙人”的突出特征是鈍于人事、無法適應社會規則,故只能退居世俗秩序之外的空間。陶淵明曾在《與子儼等書》寫道:
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1](P519)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是淵明人格的真實寫照,是他在人生起伏中形成的清晰而深刻的自我省悟。他理智地認識到這一與外部世界相抵牾的天性“必貽俗患”,但在自嘲自嘆的同時卻依然選擇適性而為,其本質是一種對自我的真正接納。自此,脫胎于陶詩的“拙人”作為一個新的藝術形象走入詩歌史中,“拙人”的特征是執著固守天性、拒斥偽飾卻無悔于自身的出處選擇。隨著時代發展,這一形象在文人群體中產生深遠影響,并在日漸豐富的詩歌表達中得到新的闡釋與發揮,從而進一步凸顯出陶淵明“拙人”書寫的思想貢獻。
三 杜甫、白居易對“拙人”書寫的繼承與變創
在唐代的陶詩接受者中,杜甫和白居易的地位不容忽視(8)有關陶淵明接受史的研究成果頗豐,涉及唐代部分可參李劍鋒《隋唐五代陶淵明接受史概論》(《山東師大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以及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他們同樣在詩歌創作中以“拙人”自居,并同時繼承了陶淵明“以貧嘆拙”的筆法,擴充了“拙人”藝術形象的內涵。著眼杜甫、白居易詩中的相關書寫與創造性轉化,我們將看到士人對順應天性與生存困境這一組固有矛盾所產生的新思考,從而發掘“拙人”在新的詩歌文本中所展現的生命力。
杜甫常常在詩歌中以“拙人”自居,無獨有偶,他在強調自身質性愚拙的同時也往往伴隨著對饑寒生活的刻畫。《投簡咸華兩縣諸子》描述了一位因拙于世務而陷入窘境的詩人:“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22](P262)那“與時異”“臨事拙”的天性使杜甫處處見斥,無奈淪落至衣食未完的境地,這一形容恰好呼應了陶淵明以貧嘆拙的表達。杜甫多次在詩中將自己刻畫為一個愚拙古板、不知變通而疲于應對世事的“拙人”: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22](P668)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22](P944)
(《北征》)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
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22](P1699)
(《發秦州》)
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
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22](P1821)
(《發同谷縣》)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余。
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22](P5075)
(《復愁十二首(其十二)》)
其中《發秦州》《發同谷縣》二首清楚地顯示出這位“拙人”所面臨的窘迫。杜甫自嘲“我衰更懶拙”“平生懶拙意”,強調其拙于“生事”的天性造成了“窮老多慘戚”的現實,與陶淵明“拙生失其方”的感慨可謂異曲同工。可見,盡管二人在出處選擇上異道殊途,卻同樣以“拙人”作為自我形象的寫照,且都將著眼點置于“拙人”不合時宜、常罹饑寒的一面。
然而,杜甫與陶淵明的“拙人”書寫仍然存在著本質性差異。陶淵明盡管亦曾對世間之理做出過質疑[“理也可奈何”[1](P347)],但總體仍將因天性之“拙”而導致的貧寒生活視為一種自覺選擇。身為“拙人”,他選擇適性存真,并將物質匱乏視作理所當然[“必貽俗患”[1](P519)]。在其思維邏輯中,“拙”與“貧”構成一組相伴相生的關系,因此貧窶生活并不意味著無法調和的痛苦,反而是對真純天性與自由心靈的保全。杜甫自謂“拙人”的行為則更像是一種無奈之舉,“竊比稷與契”的心聲顯然更接近其真實的自我期許。他始終懷抱濟世之志,卻因仕途挫敗而常與窮愁潦倒為伴,這是杜甫不得不被動接受的現實。因而此時對自身愚拙本性的強調實屬自我開解,它并不能動搖杜甫“乾坤一腐儒”(《江漢》)[22](P5575)的個人定位。雖然自嘆愚拙,杜甫卻從未放棄心底深藏的濟世之志。他著力描繪窮愁處境,一方面是借以表達對當時士人曲折命運的同情和不平,更重要的則是寄希望于唐室中興、海晏河清,用安定的社會秩序改變失意者的悲慘處境: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
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爐。[22](P185)
(《行次昭陵》)
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22](P1253)
(《洗兵馬》)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22](P670)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22](P2346)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個人的失意囊括于整個唐代社會的變動之中,其所反映的乃是生產的破壞、社會的失序,因此他迫切呼喚能人賢士“整頓乾坤濟時了”。此外,假若杜甫能見用于官場,改變衣食無著的現狀,那么其對“拙人”的認知似乎也將隨之動搖。無論生活之貧還是質性之拙,它們在杜甫筆下都并非處在一種恒定態,而是可以隨社會狀況的改善而發生變化的。但陶淵明卻似乎對“拙人”拮據的生活報以認同態度。于他而言,貧窶只是“拙人”自愿選擇的一種生活,它是以更加不可或缺的精神自由為前提的。陶淵明雖然也懷有“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飲酒(其十)》][1](P235)的愿望,卻并不將之視作一個能夠解決的社會性議題,因此他最終以執守天性的方式與現實達成和解,進而將清貧的隱居生活轉化為詩意田園。換言之,杜甫的“拙人”自稱更多集中于對社會不公的表現與批判,極大地弱化了陶淵明表達中任真自守的一面。
相較陶淵明和杜甫,白居易在自我形象構建上顯示出更強烈的主觀能動性。他屢屢在詩文中勾勒“拙人”形象,并將此藝術形象與其自身獨特的文學風格相聯系。在杜詩中,我們已經看到了“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余”一類以“拙”評價詩歌創作的例子,這仍屬于自嘲自謙之語,尚不具備指稱詩歌創作標準的含義。而到了白居易筆下,“拙”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拓展,“拙人”逐漸超越了不合時宜的愚拙者、不善生事的貧窶者等意涵,成為其獨特人生觀的指稱。
首先,白居易秉持“性分”觀念,主張循性而動,這與陶淵明所論述的“拙”有不謀而合的一面。“工拙性不同,進退跡遂殊”(《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方時為校書郎》)[23](P447)二句即是這一思想傾向的反映。日常詠拙并以“拙人”身份自居是白詩中隨處可見的表達。在白居易看來,自己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顯得那樣愚拙、遲鈍、缺乏天資。他不善為官,“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寄同病者》)[23](P543)、“自慚拙宦叨清貫,還有癡心怕素餐”(《初罷中書舍人》)[23](P1581);不善寫作,“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自吟拙什因有所懷》)[23](P549)、“拙詩在壁無人愛”(《駱口驛舊題詩》)[23](P1102);不善處世,“我受狷介性,立為頑拙身”(《酬張十八訪宿見贈》)[23](P574)、“拙劣才何用”(《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23](P1151)……由此看來,“拙”幾乎已成為他的生命底色。他還專門創作了《詠拙》一詩,表達自己逍遙樂天的人生態度: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
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
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
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
亦曾舉兩足,學人踏紅塵。
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
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云。
從茲知命薄,摧落不逡巡。
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
同此天地間,我豈異于人?
性命茍如此,反則成苦辛。
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
縫布作袍被,種谷充盤飧。
靜讀古人書,閑釣清渭濱。
優哉復游哉,聊以終吾身。[23](P552-553)
“亦曾舉兩足,學人踏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清晰地展現出詩人悔涉紅塵、循性退身的歷程。他放棄對名利的追逐,轉而順應庸常生活,看上去似乎十分接近陶淵明的精神境界,同時還納入早期士人的固窮表達,自述安于“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谷充盤飧”的日常。除了樂享清貧的生活態度,白居易的“拙”還體現在詩歌創作上:
未能拋筆硯,時作一篇詩。
詩成淡無味,多被眾人嗤。
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
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
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23](P549)
(《自吟拙什因有所懷》)
老來詩更拙,吟罷少人聽。[23](P2500)
(《早春即事》)
詩人愚拙的天性、有限的才華使其詩作顯出煩冗平淡的弊病,白居易甚至自覺建構起一條上承陶淵明、韋應物的拙淡詩歌美學路徑,使“拙”固化為其自身的文學個性。他筆下的“拙人”由此成為一個統攝天性之拙、出處之拙與詩文之拙的立體文學形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白居易塑造的“拙人”雖繼承了陶淵明循性而為的一面,卻依然與后者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其中最顯著的一點便是“詠貧”的弱化。晚年長時間分司東都并以刑部尚書致仕的白居易盡管時常強調自己安于清貧,但“縫布作袍被,種谷充盤飧”的描述仍顯得太過夸張,并不符合實際。稱自己拙于仕宦及詩歌寫作則更是與現實情況大相徑庭,畢竟白居易早在數年之前便已詩名遠播。作為典型的士大夫,白居易的出處選擇與實際生活狀況也與陶淵明一類躬耕自食的隱士存在天淵之別。可見,他自謂“拙人”,更多是出于自我建構的需要,即有意識地將拙樸作為獨屬于個體的無可取代的人格與風格。在其價值觀中,“拙人”的意涵已不再是陶、杜詩中那些見斥于世道的愚拙者,而是不受外在聲名束縛、達到身心和暢狀態的完足個體。因此,當白居易以“拙人”自命時,其表達中帶有顯著的自得而非自嗟自嘆意味。遠優于陶、杜的物質條件,也使得白居易不可能真正像陶淵明一樣從容接納極端貧窶的生活,以“拙人”書寫提升任真自守的實踐性品格。可以說,白詩中“拙人”的自我指稱大抵只是一種有意為之的話語策略。
綜上言之,杜甫、白居易著眼自身,從不同視角獨特地詮釋了“拙人”這一藝術形象的內涵。他們在自謂“拙人”時皆融入了表現貧寒生活的成分,前者以“拙人”之視角呈現自己仕途偃蹇、衣食不完的境遇,以此強化兼濟天下的志愿;后者則將“拙”轉化為獲得飽暖生活后隨分自足、淡看功名的人格,并由此人格衍生出平淡拙樸的文學風格。杜甫對“拙”的體認來自仕宦生涯中的無數挫敗,而白居易筆下的“拙”實屬刻意為之的自我形塑。二者的詩歌書寫與陶淵明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回避了陶詩“拙人”書寫中任真自守的實踐性品格,陶淵明在此問題上的獨創意義也因此得到深刻體現。
陶淵明發揮玄學理論中常見的“守拙”觀念,使“拙”具備了抽象的抱樸守真、靜默自處學說之外的新一重內涵,即難以見容于世俗秩序,從而引發關于士人如何獲取心靈自由的思索。在面對極度艱苦的物質條件時,陶淵明沒有簡單地將質疑天道不公、標榜固窮之志作為詩歌主題,而是重點關注如何挖掘自身天性中“真”的本源,以完足自適的人生態度面對遍布機巧的世界,以任真自守的從容與充實自足的精神消解現實的苦痛。他所創造的“拙人”于此意義上超越了以往單薄的“貧士”“高士”形象,在為文學表現注入新活力的同時,也為后世文人開辟了一條探索出處選擇、豐富自身角色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