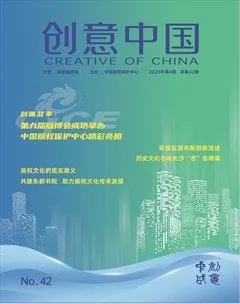俄羅斯文學(xué)的當(dāng)代發(fā)展與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現(xiàn)象研究
薛冉冉 金敏



一、引言
20世紀(jì)初俄羅斯著名哲學(xué)家弗蘭克曾這樣寫道:“在俄羅斯,最深刻最著名的思想與觀念……以文學(xué)的形式表達(dá)出來。我們看到的是滲透著對生活深刻哲學(xué)理解的文學(xué)藝術(shù):除了眾所周知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之外,還有普希金、萊蒙托夫、丘特切夫、果戈理。”可以說,自俄羅斯文化黃金時(shí)代以來,俄羅斯文學(xué)以其深度和廣度占據(jù)著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在蘇聯(lián)時(shí)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更是被授予“人類靈魂工程師”“生活導(dǎo)師”等桂冠。俄羅斯“大聲疾呼派”詩人葉夫圖申科曾高呼“在俄羅斯詩人遠(yuǎn)遠(yuǎn)大于詩人”,換言之,俄羅斯文學(xué)在俄羅斯遠(yuǎn)遠(yuǎn)大于文學(xué)。
二、文學(xué)中心主義的消解
俄羅斯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文學(xué)中心主義:文學(xué)承載的使命感、責(zé)任感使其成為民族文化的精義所在,使其既是哲學(xué)又是心理學(xué),亦是社會(huì)學(xué)。俄羅斯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特別是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家既是思想家、社會(huì)學(xué)家同時(shí)又是哲學(xué)家。莫斯科大學(xué)戈魯勃科夫教授在《為什么需要俄羅斯文學(xué)》一書中多次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價(jià)值和文學(xué)中心主義的積極意義:文學(xué)為我們承載著民族生活的規(guī)范……文學(xué)塑造著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影響著我們對參與歷史進(jìn)程的人物的評價(jià),文學(xué)向我們講述著應(yīng)如何反思自我,在俄羅斯歷史空間中的感受又該是如何。
自俄羅斯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以來,文學(xué)中心主義逐漸隱匿,“文學(xué)僅僅成為了文學(xué)”。俄羅斯自然科學(xué)院院士康達(dá)科夫在其《俄羅斯文化》中概述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的文化特征時(shí)多次提到文學(xué)中心主義被消解的現(xiàn)象:所有的中心和權(quán)威都被消解殆盡,多元化的水平體系代替了垂直的等級(jí)體系,這使得任何文學(xué)作品在社會(huì)文化的對話中都僅僅成為了一種可能,文學(xué)中心主義的消解相應(yīng)地帶來了一種碎片式的社會(huì)生活狀態(tài)。俄羅斯著名學(xué)者、作家、高爾基文學(xué)院校長瓦爾拉莫夫教授在浙江大學(xué)舉辦的俄羅斯文學(xué)啟真講壇“當(dāng)代俄羅斯文學(xué)系列講座”中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身說法:文學(xué)進(jìn)入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純粹的狀態(tài)。文學(xué)就是文學(xué),文學(xué)也僅僅是文學(xué)。
三、大眾消費(fèi)觀念的影響
與文學(xué)在社會(huì)文化中的地位一同發(fā)生改變的是文學(xué)所處的文化場域。當(dāng)文學(xué)成為純粹的文學(xué)時(shí),民眾對文學(xué)的訴求和期待與以往相比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文學(xué)作品的讀者群體也改變了許多。全俄社會(huì)輿論研究中心多年來追蹤俄羅斯民眾的閱讀習(xí)慣、媒介素養(yǎng),其多項(xiàng)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表明,讀者的閱讀傾向和品位越來越個(gè)性化、私人化,讀者群體分化、細(xì)化越來越明顯。傳統(tǒng)的“作家一讀者”鏈條變得脆弱而模糊,沒有一位作家能說清楚自己的讀者是什么樣的……文學(xué)幾乎變成自助式。
與此同時(shí),大眾消費(fèi)觀念的盛行與俄羅斯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吻合,消費(fèi)主義所煽動(dòng)的購買欲望循環(huán)在俄羅斯文化與文學(xué)領(lǐng)域也不斷擴(kuò)散與膨脹。進(jìn)入市場中的文學(xué)圖書首當(dāng)其沖受到消費(fèi)市場節(jié)奏的制約,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出版社幾乎每個(gè)月都推出新的小說作品,大多數(shù)作品在讀者面前僅停留一星期左右,而后便讓位于其他新作,但其他新作也將遭遇如此的命運(yùn)。鮮有小說來得及進(jìn)入到時(shí)代的集體意識(shí)中,也少有作品能夠成為被從容討論的對象,它們更多的是淹沒在遵循買賣邏輯的“軍備競賽”之中。正如戈魯勃科夫教授籠統(tǒng)統(tǒng)計(jì)的那樣,每年大致有三百多部小說面世,其中既有資深作家的作品,也有新人的處女作。不過在這些作品洪流中只有兩三部作品真正能被認(rèn)真閱讀并且獲得讀者回應(yīng)。
作家也同樣被卷入市場“軍備競賽”之中,出現(xiàn)了俄羅斯文論界常說的“第二部小說現(xiàn)象”:當(dāng)某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說暢銷后,出版社立刻會(huì)著手“第二本”的生產(chǎn)。而第二部作品往往是“訂制版”——既不是出于靈感,也不是出于創(chuàng)作構(gòu)思的成熟,多數(shù)僅僅是迎合市場一時(shí)的狂熱需求。有些作家的確會(huì)馬不停蹄地創(chuàng)作下一部小說,而更多的作家則是將以往沒有產(chǎn)生轟動(dòng)或引起注意的作品進(jìn)行再版。也正因如此,讀者買到手里的多是差強(qiáng)人意的“第二部小說”。那么,讀者為什么會(huì)樂此不疲地為“第二部小說”買單呢?一方面是想更多地了解暢銷作家的創(chuàng)作,而另一方面也與消費(fèi)主義所煽動(dòng)的購買欲望相關(guān)。
四、注意力經(jīng)濟(jì)的裹挾
托馬斯-達(dá)文波特分析注意力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作用時(shí)曾指出,信息充足的當(dāng)下稀缺的資源是注意力,特別是在傳媒業(yè)、出版業(yè)、廣播電視業(yè)和網(wǎng)絡(luò)傳媒業(yè),注意力往往能夠決定產(chǎn)品是否成功。⑩注意力的重新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閱讀的深度。俄羅斯大型電子圖書館的創(chuàng)建者及運(yùn)營者莫什科夫在2023年7月份接受訪談時(shí)提到俄羅斯閱讀現(xiàn)狀:俄羅斯從愛閱讀的國家變成了讀一讀的國家。程巍和陳眾議先生在研究中外暢銷書的傳播與接受時(shí)也注意到,在當(dāng)下海量信息的媒介環(huán)境里,讀者集中在閱讀上的注意力逐漸變短,出現(xiàn)了普遍且必然的“淺閱讀”現(xiàn)象。兩位學(xué)者對這一社會(huì)現(xiàn)象做出了解釋:人們每天都要面對知識(shí)爆炸所帶來的海量信息,這種媒介環(huán)境對個(gè)體產(chǎn)生的壓力如同漩渦一般使人焦慮不安,人們在尋找自救方法時(shí)習(xí)得:通過淺閱讀可以獲得將自己置身于媒介環(huán)境之中的安全感,擺脫信息超載所帶來的無法掌控的焦慮。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媒介技術(shù)的突破,小說的呈現(xiàn)方式逐漸多元,紙質(zhì)書、電子書、有聲書、社交平臺(tái)上文學(xué)推介視頻等。讀者的閱讀習(xí)慣也日趨改變,注意力不再專注在小說作品本身,而更容易被聲音、圖像等傳播方式所吸引。在此背景下,俄羅斯小說的影視化加速發(fā)展。作為2016年俄羅斯文壇重要獎(jiǎng)項(xiàng)“大書獎(jiǎng)”的獲得者,作家伊萬諾夫也頗有同感,“一部作品改變世界的現(xiàn)象已不存在,文學(xué)中心主義已經(jīng)終結(jié),現(xiàn)在是社交平臺(tái)中心主義。”俄羅斯文學(xué)期刊《期》雜志主編伊萬諾娃在接受我國學(xué)者鄭永旺的采訪時(shí)開誠布公地說:“俄羅斯文學(xué)中心主義的時(shí)代已經(jīng)結(jié)束,現(xiàn)在是新媒體中心主義的時(shí)代。”
五、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
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jié)構(gòu)分析導(dǎo)論》中提到: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的或書面的有聲語言、是固定的或活動(dòng)的畫面、是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jī)混合……而且,以這些幾乎無限的形式出現(xiàn)的敘事遍存于一切時(shí)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huì)。雖然文學(xué)與影視分屬獨(dú)立的藝術(shù)審美形式,有著各自表達(dá)方式,但兩者在故事建構(gòu)或演繹方面有著同源的敘事邏輯,文字形象的間接性與影視形象的直觀性具有與生俱來的互補(bǔ)性。追蹤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進(jìn)程的學(xué)者盧勃佐夫曾說,文學(xué)與電影的聯(lián)盟牢不可破。
1895年12月,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發(fā)明電影技術(shù),制作并放映了世界上第一批影視作品。半年后,這些影視作品傳入俄羅斯并首次在彼得堡“阿克瓦里烏姆”劇院放映。俄羅斯本國第一部民族電影作品制作于1908年,其后十余年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前夜》,托爾斯泰的《謝爾蓋神父》,契訶夫的《普羅米修斯》,赫爾岑的《偷東西的喜鵲》,高爾基的《母親》等陸續(xù)被搬上熒屏。1929年有聲影片技術(shù)得到突破之后,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的改編更是步入了加速軌道且越來越受到觀眾的關(guān)注。
據(jù)統(tǒng)計(jì),自2000年以來俄羅斯共有110余部影視作品改編自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其中19世紀(jì)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繼續(xù)得到影視化演繹,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等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的作品以及被稱為20世紀(jì)經(jīng)典作家的格羅斯曼、拉斯普京、雷巴科夫、瓦西里耶夫等作家的小說也陸續(xù)被改編成影視作品,這些作品不斷豐富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的名錄。
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每年多于1部的速度被搬上熒屏。據(jù)俄羅斯電影門戶網(wǎng)站film.ru不完全統(tǒng)計(jì),各國改編陀翁作品的影視作品150余部:俄羅斯本國改編數(shù)量多達(dá)65部;英國、德國、美國以及意大利等國的陀翁作品影視化占比大,其中德國是最早將陀翁作品影視化的國家之一,在1909年便拍攝了《罪與罰》。《罪與罰》也是陀翁作品被改編最多的小說,共50余次。在出版界,陀翁小說也一直是俄羅斯圖書市場的暢銷書。俄羅斯出版署每年公布的出版數(shù)據(jù)中有一欄是作家作品的發(fā)行量。自2019年以來,陀翁作品的發(fā)行量穩(wěn)居前三,同時(shí)也是俄羅斯作家中發(fā)行量第一的作家。根據(jù)俄羅斯《生意人報(bào)》今年8月9日的報(bào)道,在2023上半年,陀翁小說的發(fā)行量超過了自2019年以來霸居榜首的“現(xiàn)代驚悚小說大師”斯蒂芬·金作品的發(fā)行量,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俄羅斯發(fā)行量最大的作家。可以說,陀氏小說的發(fā)行量表明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自帶龐大的受眾群體和潛在的影視觀眾,而影視團(tuán)隊(duì)的精心打造則更進(jìn)一步地吸引受眾群體,向我們彰顯了小說作品與影視化改編互補(bǔ)、互哺。
又如俄羅斯文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影視改編的寵兒,三十余部影視作品的藍(lán)本,用研究者多弗格爾的話來說: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最早的改編是德國在1910年制作的黑白默片,而最早的兩部黑白有聲片,1935年的美國版和1948年的英國版,分別由“二十世紀(jì)的蒙娜麗莎”葛麗泰·嘉寶和“戲劇女王”費(fèi)雯·麗飾演女主角安娜。1997年美國導(dǎo)演伯納德-羅斯執(zhí)導(dǎo)了由“法蘭西玫瑰”蘇菲-瑪索主演的《安娜·卡列尼娜》。2012年英國導(dǎo)演喬·賴特選擇凱拉-奈特莉挑大梁飾演安娜一角。2013年意大利版由克里斯丁·杜瓦執(zhí)導(dǎo),維多利亞-普契尼主演。這些代表性的《安娜-卡列尼娜》影片每一部都彰顯著影視媒體所特有的大眾消費(fèi)特征一一吸引受眾注意力,影響受眾感官——充滿強(qiáng)勁的藝術(shù)傳播活力。但這部偉大作品的影視化進(jìn)程并沒有就此止步,據(jù)稱俄美兩國公司正在合作拍攝現(xiàn)代版《安娜·卡列尼娜》,將故事背景搬至現(xiàn)代社會(huì),安娜成了圣彼得堡即將上任新市長的妻子,沃倫斯基是某鋁業(yè)帝國的繼承人。
可以說,經(jīng)典小說之所以經(jīng)典,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小說主題的普世性與超時(shí)代性,永恒的命題總是能跨越時(shí)代之間的溝壑,孕育出新的疑問與答案,而對文學(xué)作品的影視改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學(xué)作品思想內(nèi)涵的藝術(shù)挖掘,用現(xiàn)代的方式去解答來自久遠(yuǎn)的疑惑,詮釋經(jīng)典,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不斷被影視化的進(jìn)程可以被視為一種必然。
六、當(dāng)代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
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在影視改編的數(shù)量上與經(jīng)典作品尚不能相提并論,不過也已初具規(guī)模。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自2000年以來,共有77部小說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電視劇數(shù)量為21)。其中39部大眾小說,如盧基揚(yáng)年科的科幻小說、謝苗諾娃的奇幻小說、頓佐娃和瑪麗寧娜的偵探小說、普羅寧的愛情小說等;38部嚴(yán)肅小說,分別出自烏利茨卡婭、伊萬諾夫、佩列文、普里列平、薩利尼科夫、科茲洛夫等17位當(dāng)代俄羅斯文壇認(rèn)可度高的作家。其中烏利茨卡婭與伊萬諾夫分別以七部和六部作品位居影視化改編的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17位嚴(yán)肅小說作家都曾先后獲得或入圍俄羅斯重要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如“俄語布克獎(jiǎng)”(設(shè)立于1992年)、“全國暢銷書獎(jiǎng)”(設(shè)立于2001年)、“大書獎(jiǎng)”(設(shè)立于2005年)、“鼻子獎(jiǎng)”(設(shè)立于2009年)等等。2000年以來多種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的設(shè)立也可以看作是俄羅斯文壇對注意力經(jīng)濟(jì)規(guī)律的接受與運(yùn)用,對俄羅斯文學(xué)社會(huì)影響力的維持與經(jīng)營。當(dāng)代嚴(yán)肅文學(xué)作品改編的影視化作品幾乎占了半壁江山,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俄羅斯觀眾對當(dāng)代俄羅斯文學(xué)的關(guān)注度高,對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為影視媒介提供的素材質(zhì)量認(rèn)可度高。
在知識(shí)消費(fèi)時(shí)代,俄羅斯文學(xué)經(jīng)典作品自帶“IP”光環(huán),而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多是接受并努力成長為IP的過程中。如小說《彼得羅夫流感》的作者薩利尼科夫在一次訪談中坦言,“創(chuàng)作的過程可以被看作是努力擺脫具象的過程,而影視化則是將作品具象的過程,不過我并不排斥作品的影視化,這能讓我了解到別人對我作品的理解和詮釋。”
當(dāng)代俄羅斯最有聲望的女作家之一烏利茨卡婭以內(nèi)容獨(dú)特,人物鮮活,思想深邃,特別是對人物內(nèi)心犀利剖析深受俄羅斯讀者喜愛。她的作品受到影視界的偏愛,她本人也常常與影視制作團(tuán)隊(duì)合作,將自己的小說改編為劇本。作家伊萬諾夫也非常支持小說影視化:電影改編是小說推廣的重要方式,當(dāng)下的作品必須具有被詮釋、被演繹的潛力,這樣它才能真正地存活于文化之中。面對影視改編,伊萬諾夫也非常坦然:改編總是有得有失,小說改編為影片畢竟是從一種藝術(shù)系統(tǒng)轉(zhuǎn)化為另一種藝術(shù)系統(tǒng)的過程。
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除了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之外,還有一部分被改編為舞臺(tái)劇,在果戈里劇院、彼爾姆劇院等劇院上映,這也可以被稱為一種可視化形態(tài),為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接近、收獲更多的讀者與關(guān)注者提供另一種可能。莫斯科大學(xué)教授諾維科夫非常關(guān)注作家與媒體的關(guān)系,他提到:“在當(dāng)下文化氛圍中,作家不僅以作品與讀者交流,同時(shí)以其生活,以其獨(dú)一無二的個(gè)性與讀者交流。”作家本人對待改編后的影視作品或舞臺(tái)劇的態(tài)度往往會(huì)成為媒體訪談的內(nèi)容,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進(jìn)一步延長了作家和作品的訊息在媒介空間里的存在時(shí)長。
正如前文所說,一部小說面世后會(huì)受到消費(fèi)市場的沖擊,又會(huì)受到注意力經(jīng)濟(jì)的裹挾,能夠真正在文化場域存活下去的是少數(shù),而參與到社會(huì)文化對話之中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當(dāng)代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雖不如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擁有的讀者群體龐大,卻也積累了一定的關(guān)注量,為不同需求層面的潛在觀眾提供了豐富且多樣的優(yōu)質(zhì)影視內(nèi)容。當(dāng)代小說與受眾群體毫無時(shí)空隔閡,聚焦的社會(huì)問題、使用的語言表達(dá)都符合當(dāng)下受眾的審美習(xí)慣,并且大多數(shù)當(dāng)代作家都支持作品得到影視化改編,主動(dòng)為作品尋找改編的可能性,以期作品能夠在影視化改編及傳播中獲得文化生命的延續(xù)。與此同時(shí),當(dāng)代俄羅斯小說影視化過程不斷地豐富著俄羅斯影視的表達(dá)主題,拓展文學(xué)與影視互補(bǔ)的藝術(shù)潛能邊界。
七、結(jié)束語
時(shí)至21世紀(jì),當(dāng)俄羅斯文學(xué)不再處于文化的中心地位,當(dāng)大眾消費(fèi)觀念盛行,注意力稀缺,各種文化傳播媒介彰顯其能力時(shí),文學(xué)作品僅具有藝術(shù)產(chǎn)品的屬性,它雖會(huì)經(jīng)歷市場的“軍備競賽”,讀者的淺閱讀,甚至遭受瞬時(shí)被遺忘的命運(yùn)。然而文學(xué)作品,無論是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還是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其潛在的注意力焦點(diǎn)往往能夠?yàn)樗鼛碛耙暬臋C(jī)遇,使其文化生命在改編及傳播中獲得延續(xù)。與此同時(shí),文學(xué)作品與影視制作的結(jié)合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挖掘兩種藝術(shù)系統(tǒng)的敘事潛力,拓寬它們的表達(dá)邊界。
(作者薛冉冉系浙江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俄語語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金敏系浙江大學(xué)俄語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