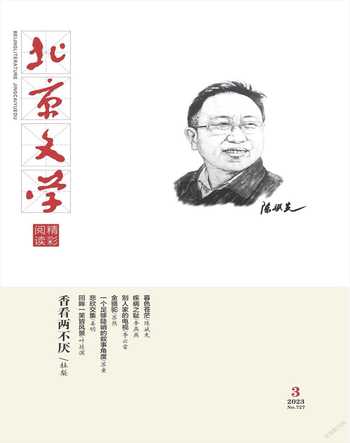金駱駝

那些帶電火花的蛛網越過黃鎮,尋著人的氣息一路蔓延。揮舞的觸手碰到荒漠,像是被四起的黃風刮傷,迅速蜷縮進一旁的小村子里。交織錯節的電線嗞啦作響,給村子帶來向下亮起的燭火,閃爍人影的黑盒,還有日夜不停的轟鳴引擎。多出來的嘈雜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遠處。讓他們心頭長出來一塊石頭,就此壓住金駱駝的消息,十多年沒有人說起。
朝魯不止一次地告訴別人,自己安了幾年的鍋子,就裝上第一天,看得晃了神,就那么一下。好像是說什么油的。也沒啥,就是圖個新鮮。但他從來沒有把心里的真實想法告訴給別人,怕人笑話,讓人說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人再惦記金駱駝的話。
朝魯那天打開電視開關,學著別人的樣子,把一個叫遙控的白盒子對著眼前的小黑盒子按一下,畫面不停跳轉,朝魯撲哧笑出聲:“也就那么回事,和我見過的沒法比。”他打了一個哈欠,打算關電視時,畫面中正好出現一個窈窕女人,站在沙灘上,頂著烈日,往自己身上涂抹,配著熱鬧的聽不懂的音樂,朝魯感覺心里被剜了一下。
朝魯瞇著眼睛,彎著腰湊到屏幕前,想使勁往里看,沒過癮,他又趕快繞到電視后面,黑漆漆的機身擋住視線。朝魯閃回身,廣告結束,朝魯愣在原地,蹲半天,從兜里掏出一根煙,抽幾口,才看見眼前呼出的煙霧有一個大洞。
朝魯揮揮手,一下補平虛空中的缺白。朝魯朝窗戶的方向望去,“和那荒地一樣,就是有點藍。”這是朝魯第一次見到海的所想,之前都是聽說,憑著航沙人的本能,他總覺得除了那遮天蔽日的陰黃外,還有另外的遼闊在等待著他。他雖然不再年輕,失去征服的欲望,但他始終覺得,自己的胸膛里有些東西正在慢慢變大,就是這些東西,讓他擁有比肩征服的自信。
不管大海還是荒漠。那些所謂探險家的存在只是一時,但他們的盛名卻穿越一個又一個的歲月。而那些像朝魯這類生活這些無言廣博身邊的人,他們的臉龐卻一個接一個消逝融入人眼不可及盡的遼遠中。
朝魯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大海,而是遠處白板子上站著的人。在他的認知里,海邊也有像是他這樣的人的。只是女人身旁的精美的草屋讓朝魯頗為感慨,他知道自己的身影永遠不會出現在電視里,讓海邊的人看到,周圍也不會有那么多的熱鬧人群。唯一的歸宿就是漸漸消逝在沙漠的陣陣喘息里。
想到這里,朝魯的眼睛一熱,伸手摸了一下,黏在他眼眶下的沙粒劃了一下臉,順著周圍的皺紋,簌簌落下。他像是突然驚醒一樣,透過窗戶,看著屋外立著的一個泛黃的黑木板,那個陪伴他多年,用來航沙的追夢工具。“你也應該老了,肯定老了。”朝魯往門的方向嘆出一口氣。
自那以后,朝魯多次回想電視里的場景,他想知道,那些海邊草房子里的人是不是也和他一樣,為了一個虛美的傳說把自己和沙漠捆綁多年。海里面會有金魚嗎?還是說會有財寶?究竟是什么驅使他們終其一生,生活在海邊的。他想問問別人,但沙漠風大,每次開口,都會不經意含進一口呼嘯的風沙。
在朝魯小的時候,他總聽祖父那輩的航沙人說起金駱駝的傳說。那些人蹲坐在炕上,端著銀碗,抽著旱煙,雙雙布滿年輪的眼睛發著亮光,語氣堅定地說起遠方沙漠的事:有人說那是祥瑞的象征,見到它,會得到庇佑;也有人說金駱駝是會帶來財富的,凡是它走過的地方,蹄印之下的沙土都埋有黃金;還有人相信,金駱駝本身就是早年商隊遺失的財寶所結化的精靈,只要找到它,就能找到價值連城的古董。
航沙人很多不是黃鎮人。起初,他們都是為了尋找金駱駝,不知何年何月在黃鎮的漫天陰黃中迷路,把根扎進這里,世代做起航沙人。漸漸地,為滿足生計,他們擱置尋找金駱駝的想法,開始幫助牧民尋回無意闖入沙漠的牲畜,也會受牧民之托,用沙船運送一些水和吃喝用品。
每當黃沙呼嘯的時候,朝魯就坐在窗戶邊向外望去。他總能察覺到不遠的陰黃里閃爍的人影,發現他們的足跡,望到他們一點點消逝在沙丘之后。當他學會辨識清楚那些縹緲的人形是誰時,這里的航沙人已經都被吹埋進厚厚實實的沙土之中,這其中也包括他的祖父。
朝魯父親從他祖父的身體下接過那個兩米見長的黃木板,撐起帆,看見上面密密麻麻的窟窿,說這個帆只夠承受一人的死去。朝魯沒有明白父親的意思,他那時只顧金駱駝的蹤跡,在黃沙漫天的日子里,使盡全力,想把自己的目光投得再深一些,他沒有理由地相信——祖父看見金駱駝了。但他年歲已高,拉帆的手在狂風中不小心脫力,被忽起的大風裹挾的沙暴吹上天,又被狠狠地扔到地上。
父親通過祖父設下的成為航沙人三道考驗時,朝魯還不記事。在日后的談及中,祖父滿臉的皺紋總是充滿欣喜地抖動。祖父和他的同輩都認為父親擁有著多年難遇的航沙人潛質,他們把尋找金駱駝的希望全部押到父親的身上。
祖父和他友人離去后,父親一直惦記著搬開身上的重量。在午夜風暴驟起時拉上窗簾,企圖回避那些如炬般閃爍著的目光。他不明白父親對金駱駝興趣缺缺,只滿足于搬運一些無謂的瑣物補貼家用,他明明有著更好的技術,更年輕的體魄,以及更多的時間,來尋找那隱藏在沙漠深處的黃金精靈。
與祖父一輩的最后一位航沙人被風裹進沙崖那天,父親罕見地落淚了。那一代航沙人只留下五塊船帆,其中就包括父親的那一塊,在每個無風的夜晚,朝魯被金駱駝干擾得不能入眠時,總能隔著墻壁聽到父親的嘆息。“唉——嗨。”像是在費力地抓取什么,吃痛,最后不小心放開。
朝魯聽到父親的死訊時并不意外。那段時間一到傍晚,父親把沙帆從船上取下來,坐在門前的木檻上,拉起一個角,透過沙帆的洞窟對著沙漠里的落日望去,恍惚一陣,便掩面嘆息起來,說起今天運貨時,在風沙里遇到的熟人和長輩,甚至有一次,他感覺到妻子的掌紋。那些迷失在沙暴身體里的故人,已經成群結隊,在等待他的到來。
朝魯從學校請了一個月假,用來傳承先輩們的航沙技巧,最后用三天時間,再通過父親的三道考驗。在向縣中學老師說起請假緣由時,老師并沒有聽說過航沙人曾經的輝煌。朝魯手舞足蹈地照著父親的樣子比畫出航沙時的動作:裝風向標,掛帆收帆,用身體的重量和傾斜來控制船頭的角度。老師的驚奇轉瞬即逝,朝魯不知如何作答,也不想對這樣一個外人說出航沙人的秘密。
“不是有車或者摩托嗎?這樣不是拉得更多?”
老師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朝魯只是不想承認。朝魯上初中后,支出一下變大。幾個牧民從黃鎮淘來摩托,依靠晴天的運輸,基本上滿足這片沙漠上居民的日常需求,朝魯父親此時顯得多余起來。他學著周圍牧民的樣子養起羊,拿著鐵鍬產料,把自己的身體完全投進和周圍陰黃格格不入的星點白花之中。
老師來訪朝魯家兩次,身影就徹底隱在沙漠的另一頭,像朝魯這樣莫名其妙退學的孩子在這片陰黃中非常常見。他只能掉轉精力,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渴望而且有能力逃脫陰黃束縛的孩子身上。
朝魯在掌握掛帆系繩的技巧后,沙漠就像蘇醒一樣,朝著黃鎮的方向噴了半個月的鼻息。
視野不好的情況下,航沙人得不到群星和太陽發來的準確訊息,第二項的方向測驗只能作罷。朝魯父親卸下沙帆,讓朝魯舉起三天,觀察呼嘯的風沙最后能夠堵上沙帆幾個窟窿。
第二天的時候,父親接到村里的消息,說是有個大學生計劃橫穿沙漠,在陰黃中已經失聯三天,而那些參與搜救的摩托,被風沙堵住關節和氣管,愣在原地,變成廢鐵。眼下只有航沙人能夠幫忙。而另一個航沙人據說已經搬進黃鎮多年,找人的重擔只能落在父親肩上。
朝魯一夜沒有合眼,他的窟窿只被風沙堵住兩個,他來到屋里的水缸前,背著身,數著墻上的虛影,只有三個,朝魯心里不禁發慌,他又舉起沙帆,對準右眼,模模糊糊的景象讓他產生不好的想法。朝魯依稀記得父親當年經過三天三夜的磨煉,沙帆上只剩下兩個窟窿。他把這一切都歸咎為不好的天氣,他始終堅信自己是駕駛沙船尋到金駱駝的不二人選。多年以后,朝魯知道這和海上用的帆根本不一樣。不管用什么材質來做帆,只要黃風一起,它們立刻就會千瘡百孔。沙帆的航行依靠的是先祖的庇佑,而他認為自己根本就不是做航沙人的料。
朝魯把沙帆交給父親,并沒有向他說明發生的事情。父親匆匆固定好沙帆,乘著風,一頭扎進沙漠的巨口之中。
朝魯再也沒有見到父親,供他懷念的只是一個失蹤的信息。父親也沒有找到那個大學生,等陰黃漸淡的時候,村民們在沙漠中尋見一個渦旋的痕跡,還有一些衣物碎布,沒有一點人的氣息。
等人們默認最后一個航沙人魂歸沙漠,準備離去時,渦旋的中心緩慢浮起一個點。又過幾分鐘,整個沙船從沙漠里浮了上來。人們意識到,最后一艘沙船還要在這片荒野上行駛一段路。
朝魯從夢中驚醒,窗外的人聲順著沙子的路徑鉆進家里。他夢到沙暴把他的家吹垮,所有的門窗吹到天上,壘墻和壘炕的磚塊在沙粒的快速捶打下變成齏粉。他在風暴里揮舞手臂,大喊,想要抓住點什么,失重帶來的絕望籠罩著他,他的身體被風沙一點點擊中,出現裂紋。不知何處飄來的布裹挾住他的全身,他在空中調整方向,著地時,腳趾并沒有傳來沙粒的觸感,他低頭一看,是一個黑色的木板接住了他。
人們拖動著沙船,連同父親的死訊從沙漠深處一同帶給朝魯。朝魯跌跌撞撞沖向沙船,用臉撫過沙船木板的每一寸黑紋,沒有一點溫度,也沒有任何熟悉的氣味。
朝魯想到父親曾講起自己名字的寓意,看向沙漠。人們圍站在他的身邊,像一堆無言的沙塊,他們那些帶有同情的注視,在烈風中轉瞬即逝。等人們走后,朝魯抹干眼淚,看著帆上多出來的一個新洞,拍拍手,爬上桿,卸下船帆,帶回家里。
父親離世不到一個星期,村里就買了兩輛結實的皮卡,以防大風天里出現意外。朝魯記得祖父曾談到過去帶著父親,挨家挨戶上門說起接過衣缽的樣子。眼下,他已然成為最后一名航沙人,這個要有什么紀念?還是要有什么儀式?朝魯想不明白,他只能不停地朝著沙漠的方向看去。
沒有人見證朝魯通過航沙人的三次考驗,更沒有人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要在以前,這是他們村子里的大事,甚至要專門從黃鎮請一些唱歌跳舞的人前來祝場,慶賀新一代沙漠守護人的到來。
朝魯步行幾公里叩開一戶人家的門,見到的只有不解與疑惑。關門聲停歇一會兒,幾公里之外,又響起了敲門聲,像是發問。整個村子幾十戶人家,得不到一個答案。在他們的眼里,自己的存在已是多余,不如回去好好學習,長大以后干點別的事。朝魯不知如何作答,在每一戶人家的門口呆愣愣站一下就離去。朝魯突然想到自家引以為傲的三次考驗,已然成為往日黃風的一部分,而自己朝思暮想的金駱駝,更是成為生怕別人知道的笑話。
想要得到父親的技術完全不可能。人身上最為珍貴的東西是教不了、體會不到的。朝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養羊身上,航沙比起養羊簡單多了。漫天的黃風里,又多出來一陣咀嚼草料的聲響。
自那以后,朝魯的身體在夜里再也沒有傳出生長的聲音。沙漠里日夜不息的沙塵,把他的身形雕刻得精瘦、硬棒,兩個眼睛像是沙漠里迎著光亮的石頭,手指的關節突出,長成紅柳樹瘤的模樣。固定船帆的線繩經年累月地摩擦,把他的掌紋磨平,在上面留下整齊的線段,讓即使不懂手相的人,也能一眼就從朝魯的手上看出,他擁有整個航沙人的命運。
朝魯從父親那里接過的羊,開始還能一年下幾個羔,四五年以后,數量就穩定在四十只。大羊出掉小羊才活,不然下的都是死羔。為此朝魯沒少往村里跑,到處問人,得到答復來來回回就是那么幾句話,含糊不清。他到縣里,花錢找獸醫站的人去接生,最后降下來的還是死羔。
村里開始還派人過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病,還是水草有問題?幾圈下來,沒有看出一點問題。有些老人背后嚼舌根:“航沙人一共四十個人,還不算朝魯。”話傳一圈,到朝魯這兒,已經成為詛咒,有人更是直言不諱,說怎么也得四十一只,朝魯肯定不是航沙人。
朝魯不信邪,把自己的羊分出去五只,寄養在鄰居家的羊圈里,自己每天航沙幾里路,往過送料子,看這樣自己的羊圈里能不能下新羔。不到一個星期,鄰居就讓朝魯把羊帶回去。說他的羊來以后,每晚都能聽見羊圈里面的說話聲,絮絮叨叨個不停,有點吵人。朝魯只能把羊又弄出去,告訴它們該回家了,讓它們自己先往回走。
朝魯接受航沙人餓不死、吃不好的命運。晚上看著窗外的繁星,他不禁好奇起自己的先輩接受命運的過程。在入睡前的朦朧中,一聲脆耳的駝鈴將他喚醒,他湊到窗戶前,看向外面,只有無盡的死寂在蔓延,
正當朝魯以為幻覺,回床入睡時,外面又傳來一陣悠長的鳴叫,響徹天地,朝魯的小屋微微發顫。像是駱駝在叫,朝魯心想。群星的光芒打在地上,沙漠中不知名的結晶以眨眼的頻率閃著微光。月光像雪一樣落在沙上,在風的作用下明滅。朝魯想起縣里上初中時,地理老師提到的鯨魚。那個老師因為支教項目才來這里,是大城市人。她來到黃鎮邊上的沙漠,第一次聽到悠長的駱鳴,想到的是海洋里的鯨魚。在她看來,鯨魚和駱駝都是無邊的廣闊里最大的生靈。年幼的朝魯無法想象出鯨魚的模樣,腦袋里只能把駱駝的形象沾上水,不斷放大。
附近住的人家里沒有養駱駝的。朝魯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他把右手從衣領伸進去,朝著胸口的地方猛地拍打,等膛脯上傳來火辣辣的痛感時,他才穿上鞋,朝門外走去。
沒有風,整個沙漠屏住呼吸,朝魯站了一會兒,就被這安靜壓得喘不過來氣。遠處沙丘的背面,投來一個眼神的溫度。朝魯分辨著這個感覺,沒有一點熟悉的記憶,他朝著那個方向跑去。
遠遠地,朝魯看見一個影子,四條腿,直挺挺地像是放在地上一動不動,在黃色和黑色的交界處等待著他的到來。月色依舊寧靜,空氣中摻雜一些新的氣味,沙土一改往日的冷漠,棉質的觸感隔著鞋從腳底向上攀延,朝魯感覺自己身上的干皮正在被某種濕潤磨平,像是母親的手,舒緩,一下又一下,他的呼吸越來越費力,但身體感覺越來越輕。
“喂!喂——”朝魯聽到有人在喊叫,聲音繞著他的耳郭走一圈就離開了。“喂!”朝魯猛地一驚,這次是一群人的喊叫,等他反應過來,身體已經全部沒進沙里,只剩下一顆腦袋留在沙外。
不是流沙,身子上都是浮沙,還沒落嚴實,腿上施勁就從沙里爬了上來。朝魯想起一種叫夢游的怪事,后悔這幾天自己想錢想瘋了,身體關不住魂。他回頭看看剛剛人聲傳來的方向,看到一群人的影子。朝魯的心跳還沒有緩過來,不敢上前,只留在原地瞪大眼睛。
這時他好像看到一個父親模樣的影子,站在人群最前面。一股冷氣從朝魯背后升起,朝魯用力把腳插進沙里,直挺挺地挺直腰板兒,盡力把氣勢鼓足。
起風了,人群開始消散,化作沙漠中的一部分,父親的影子留下一句話也融進漫天的沙塵里:“還沒到時候,還沒到時候……”
金駱駝是存在的,它比那些羊毛換成的旱煙還要真實。霧氣終會消散,而金駱駝卻在一個又一個沙丘后等著航沙人的到來。
光憑人自己是無法直視金駱駝的,必須要有沙船的存在。沙帆被風晃動,能搖醒受蠱惑的人,沙船和地面的摩擦,能防止人陷進沙里。這是航沙人經過無數次血的教訓得出來的祖訓,但朝魯祖父往上兩代人沒有一個見到過金駱駝,金駱駝的存在就成為傳說,它的出現只存在于航沙人茶余飯后的閑聊和夢鄉中。朝魯祖父沒有告訴自己的兒子,朝魯自然也就無從知曉。朝魯用一只腳踏入沙淵的代價,再度讓這個祖訓顯世,只不過,除了朝魯,已經沒有人再去在意。
朝魯在和友人的一次酒會上談起這事,他的話始終飄不進席中,輕飄飄地浮在屋子上空。“不就是夢游嘛,有啥稀奇?”“再不濟就是讓夜游神抓了單,現在人都往堆里扎,哪像他,荒地上守著個破房子等塌?”“噗……怪不得娶不到媳婦兒。”
沙塵在他的鼻腔里打轉,朝魯的呼吸沉重起來,臉憋得通紅,他抬起拳頭,朝著笑金駱駝最歡的那個人,一揮,不小心擊中溜進屋里的一縷干風。
朝魯沒有勇氣去向自己的友人揮動第二拳,剛剛的一切是他伸懶腰時攥住拳頭的幻想,是對他們否定金駱駝的反擊。他跌跌撞撞從屋里出來,又一步一趔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黃風依舊刮著,從遠處帶來各種各樣的氣味,可朝魯聞不到身前哪怕一點的熟悉氣味。
每當沙塵們以緩慢的姿勢從天上劃過時,朝魯就架著沙船駛進落在地上的陰黃之中。拋下家里因饑餓聲嘶力竭的群羊,轉而朝著金駱駝所在的群黃漫行。金駱駝出現的時間沒有定律,朝魯只能把自己分成兩個,一個頂著烈日,在微微發顫的空氣盡頭,尋找金駱駝的身影;一個身著星光在地上成片的黑魚鱗中,想用腳印踏入另一個腳印。
朝魯在尋證金駱駝的途中,自己又悟得關閉耳朵的技能。沙塵打在耳廓上,落地時發出酥麻的撞擊聲,他深知這個聲音和那些航沙先輩們聽到的一樣。與此同時,耳朵的閉合隔絕的還有遠處的喧鬧人聲。黃鎮濃郁的煙火味飄到村里,村民們嗅到前所未聞的大片鋼筋水泥味。他們以黃鎮作為起點,向著南邊的方向流淌。村子里的人越來越少,只剩下起風時滿村的嘆息。
沙漠上的人,只要聽不到聲音,就絕不會動心。這是村里人歷經十幾代,摸索得出的應對海市蜃樓的方法。作為航沙人,這條規則更是深諳于心,朝魯想不清為啥村子里的人,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敢離開這里,去往南邊一個所知甚少的地方。換句話說,他們連自己腳底下的地方都沒弄清,金駱駝也沒有找到,怎么就離開了?
沙漠的沙塵一寸一寸地向外邁著腳步,像一只癱倒在地的野獸在渴望食物。朝魯每天航沙的距離都會比前一天多平移一點,夜里夢中正甜的時候,朝魯不斷地被握成拳狀的沙粒,擊打窗戶發出的動靜所吵醒。每當這時,朝魯也會伸出手,不停地向窗戶搖晃的部分回拍過去,企圖遮掩沙塵在告訴他是這片地方最后一個人的消息。
黑色的鐵蛇在架子上不斷蜿蜒,它們嗅不到人的氣息,只能把頭伸進這片陰黃的更深處。
朝魯在鐵蛇試探甩動的頭中終日惶恐,擔心這些東西的存在會驚擾于此活動的金駱駝。
鐵蛇們盤踞在沙漠的一隅,蜷縮在一起,化成一個披著綠布的蛋。隨之而來的還有一些施工的人,在他們蠕動的黢黑臉龐中,一個巨大的沙漠主題旅游區要在這里成形。朝魯家的羊在陌生的聲音和景象中絮叨不停,眼里露出的神色和看見沙漠里長出的一棵嫩草沒什么兩樣。
一個陰黃欲墜的午后,幾個穿著西裝的人為了躲避呼嘯的沙暴來到朝魯的屋里,他們叩響房門,還沒等朝魯問清他們的來意,他們就進到屋里,自顧自地站在屋子的中心,像是自我介紹一般,說起項目的規劃。
他們說的話很快就超過漏進屋里的沙粒。見朝魯沒有說話,那幾個人就一邊說著大叔應該沒有見過高樓的樣子,一邊比畫,想方設法向朝魯表達清自己的意思:他們用胳膊在空中擺出房子的模樣,用平移的手掌比作馬路上的汽車,又不停地跺腳,說人多錢就多,生活就變好……
他們說話的時候,朝魯一點也沒有聽進去。他低著頭,在琢磨這些人的到來也許是件好事:不明白現狀的金駱駝可能會在這里迷路,被那些不知名的建筑材料和電線絆住腳,這樣自己遇到的概率多少就會大一些。想了一番,朝魯意識到這是自己在為他們的到來向沙漠辯解。
聽到這幾個西裝人說自己沒有見過世面,朝魯走進廚房,從掃帚上折下一根草回來,照著地上的一層薄沙畫了幾條線說:“這是你們住的地方吧。”西裝人互相指指點點,對著朝魯臥室的小電視機忙使眼色。朝魯抹平地上的線條,用腳又攤過來一些沙子,畫了幾條線,又蹲在地上仔細地描描細節,其中一個西裝人見狀驚呼起來,說,這是他偶然翻閱的文獻中提到的新一代房屋概念,在第四代住宅的基礎上,融合完整的生產辦公等特點,鄰里之間的協作甚至可以達到相對成熟的生產線標準。但這些都是想法,相關草圖設計都不完善。他不明白眼前的這個精瘦男人是怎么弄出來的?
朝魯笑了,說這都是自己親眼見過的,里面人干嗎,自己都一清二楚,而且不止一次,就在前幾天他又見到了。幾句話下來,眾人唏噓,心照不宣地待在原地,看著窗外等沙塵暴的停止。朝魯剛剛畫的圖讓他們以為自己遇到隱世的高人,可細聽其緣由,他們都認為朝魯是在做夢瞎說,草圖什么的都是湊巧。
朝魯沒有說謊,他是真的見過。所有的事物原本就有,人們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把他們的形狀具象化出來。在朝魯航沙尋找金駱駝的時候,海市蜃樓在沙漠與天空的盡頭隨光線不停隱現。沙粒的組合變化,空氣中的濕氣,月光灑射晶石的角度,海市蜃樓在日夜的流轉中始終存在。在這片沙漠中孕育顯現的景象,也無不展現著與外界千絲萬縷的干系,而這一關聯很多時候都超越了時間,讓初見者對自己產生懷疑。有的是雕刻精美的亭臺樓榭,有時候是板板正正的鋼筋水泥,還有時候是不知名的材料融合成的巨狀圓柱體,周圍還有一些不明的飛行物體。
因為常見海市蜃樓的緣故,朝魯對所謂的外界發展提不起來多大的興趣。他的眼界在航沙中一次次被打開,比起村里那些不相信海市蜃樓、只相信自己雙腳丈量出尺寸的人,朝魯的幸運與不幸昭然若揭。在他看來,自己和看到的海市蜃樓沒有區別,水汽做的夢淡出時間,才產生海市蜃樓。而他卻依靠著對金駱駝的日思夜想,維持著和現實的最后一絲聯系。
旅游區建設的聲響壓不住四處飛逸的沙塵,那些建筑材料在這些黃粒的起舞中堅挺不了幾天,大大小小的蟲洞就從內而外地把它們侵蝕干凈。朝魯的破敗小屋屹立著。機器的轟鳴被裹挾著沙塵的大風吹散,同時迷路的還有到這里來的工人們的心智。
旅游工地的工人們被陰黃干擾得無法開工。在白天,他們在暴曬和沙粒的擊打中耗盡體力,夜晚時分躺在床上,他們又被沙漠深處騰起的景象所吸引,在步履蹣跚中一步步走向沙淵,有人就此失蹤。外來的車和人得不到沙漠的認可,他們只能從一個迷失走向另一個迷失。
外來人的雙腳是找不到沙粒和沙粒之中的縫隙的,他們的身影在沙漠中立不安穩。明明開工之前就做過勘探,施了硬化,可蓋起的建筑還是傾斜,彩鋼房也被忽起的狂風卷上天兩次。工人們的怨聲和對失蹤的恐懼不停傳染,不到兩個月,項目的工人們就走了一多半。項目負責人又想從本地人中招些工人前來幫忙,卻發現這里除去朝魯已經空無一人。一股沙漠吹出的微弱氣息,就能把這片地區所有的屋子吹響個遍。
面對旅游項目負責人的上門招聘,朝魯一開始就興趣缺缺,他只管尋人和救人。比起那些實實在在到手的錢,朝魯更向往著金駱駝的財寶。航沙人的世界里,錢和財寶不能畫等號的,而領著所謂的工資去救人更是違背天道。航沙人得到的報酬從來都是隨緣,不能強求。朝魯計劃著如果自己能把航沙傳下去,就要在祖訓里添一條不能領工資的規則,三代下來,肯定又能成為一條祖訓,這是朝魯第一次想到自己應該招個徒弟,往下傳點東西。
沙漠在以另一種方式匍匐擴張著。朝魯在尋找那些工人的過程中,途經的沙土被船底一遍又一遍壓麻,舒緩幾天,它們就又開始向外爬行。房子沾染上來自沙漠的氣味,午夜時分躺在床上,朝魯已經能感覺到沙漠那正在流淌的體溫。朝魯深知只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阻止沙漠的侵蝕,航沙人的先輩們正是在日以繼夜的航沙中,用船底的摩擦和擺弄的風帆來馴服沙漠,但現在人手根本不夠,也不知去何處尋找幫手。眼下,朝魯只能坐等將來某一天沙漠向外的爆發。
如果招幾個徒弟,是不是好一些呢?朝魯躺在床上,腦袋里惦記著停在外面的沙船,為它的去處產生前所未有的擔心。無關金駱駝,也無關馴服沙漠,只和航沙人這一名頭有關。
工地的施工聲稀疏不少,一些沒有活干的工人晃蕩著手里的安全帽,坐在地上沖著沙漠發呆,朝魯有意無意地在他們面前駕駛沙船,但他們的目光總能跳過朝魯,向著更遠的方向迷茫。幾次下來,朝魯已然死心,先不說這些人能不能學會航沙,讓這些人拖家帶口來到這不毛之地,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航沙人的路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走的,也不是每個人都愿意走的。至于金駱駝,在這些人眼里,也許就是一陣風里吹來的笑話。
黃風圍繞工地晃蕩不到五天,里面的建筑材料就化作齏粉,與此消散的還有曾經滿滿當當的人聲和味道。沙漠里除沙漠之外,只留下死寂。朝魯在見到他們第一眼時,心里就知道這一天遲早要來臨,只是沒有想過會有這么快。朝魯感覺一切發生好似沙崩,他只能坐在門檻上回想之前發生的事,思考將來到沙漠挑戰的人的下場。
太陽光嗡嗡作響,沙子在地上窸窸窣窣挪動著身體。不知是不是眼皮沾上沙子,朝魯在思考記憶和將來的過程中,眼皮越來越重。他已經有段時間沒有聽聞到金駱駝的消息,施工隊的離去也許是件好事。
朝魯的鼾聲響到第五下時,被突然出現的年輕小伙兒腳步打斷。朝魯瞇一下眼,認出眼前沒有一點沙粒的高檔運動鞋。
“他們都走完了,你在這里做甚?”
年輕人笑了,說父親因為虧損,著急開發新的項目顧不上管他,他想著正好趁學校放假這段時間,留在這里學航沙。朝魯忍不住咧開嘴,那些沙漠里的狂風罕見地把原本不屬于沙漠的人吹來了。朝魯擺擺手說,一會兒要去鄰居家喝酒,還說這里根本不是他能待住的地方。
朝魯撐起沙帆,乘著風離開。第二天回來時,他看到那個年輕人學著他昨天的樣子,坐在門檻上睡著覺。聽到來人的動靜,年輕人睜開眼,對著朝魯的兩個被酒精泡大的眼睛說:“師傅回來了?”
這聲師傅聽得朝魯心里發顫,他取下沙帆,收好沙船,揉掉臉上的沙粒,對著年輕人說道:“沙船這東西,可不是一般人能弄得了的,后生你行嗎?”
年輕人沒有說話,走到墻根,將沙船放到地上,把旁邊沒有收好的沙帆抖開,學著朝魯的樣子,爬上桿,掛好帆,用麻繩在沙船的兩頭綁好位置。一切完備后,年輕人帶著期待看著朝魯。
“不行,還不夠,再用點勁兒,風沙大,別關鍵時候給吹開了。”見年輕人眼里的光還是閃動著,朝魯本想問問他知不知道金駱駝的事,想來想去開不了口,他已經記不清上次對人說起金駱駝是什么時候的事。朝魯還是先讓他試試駕船。
年輕人沒有相信自己的耳朵,站在原地愣愣地看著朝魯。朝魯揮揮手,?讓他趕快上船。年輕人急急忙忙跑上船,撐起風,正好乘上路過的一陣黃風。朝魯瞇著眼,看見年輕人強扭著身體,顫顫巍巍地在沙上行駛好一會兒,一個轉彎沒有剎住,才從船上甩下來。
朝魯感嘆著他是個好苗子,加以培養肯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航沙人。朝魯回憶起自己的祖父在航沙上已是天賦異稟,而父親更是百年難遇的航沙天才,而自己更是沒有在通過航沙人三道考驗的情況下,安安穩穩航沙幾十年。所有航沙人都做得越來越好,可航沙這行卻越來越衰敗,現在更是只剩下自己一人。
朝魯沒敢細想下去,年輕人的呼喊聲剛好幫助他轉移了思緒。顯然,他也是對自己行駛的距離感到吃驚。
“師傅!您看看我行不行?”
“這哪行呢,我第一次開的時候,直接在沙上溜了半天。”朝魯說這話時,臉上有些發燙,可想到臉上曬出的青石色時,腰板兒不由得又硬氣幾分。
“你這樣我教不了啊,還不如現在早點回你家大房子里歇息著。”
年輕人眼里的驚恐流在地上,弄滑了他的腳,一個趔趄摔在朝魯腳前,這次摔得比航沙那時還要慘,年輕人捂著膝蓋,很是疑惑地看著他。
“教不了,教不了,有這時間,還不如弄點其他的。”說著,朝魯進了屋,關上門。靠著門,朝魯點著根煙。屋外的腳步踱響幾下,就沒有了聲音,朝魯拉開門縫,往外看,看見沙船不知道什么時候回來了,遠處的沙丘上,隱約看到一個金色的身影。
這個后生姓張還是姓李?朝魯琢磨半天,又記得聽施工隊的人說他爸姓王。這后生好像年輕時候的自己,一臉精干相,只不過比自己那會兒白凈多了。算了,算了,圖啥。沙漠的呼吸吹來一代代的年輕人,又用風沙在他們臉上雕刻出年輪,究竟誰是誰,什么是什么已經不重要了。朝魯抬起頭,翕動幾下眼皮。剛剛往外看時,眼睛不小心落進沙漠的灰。墻的另一邊響起羊群的饑餓叫聲,他癱靠在門上,用手遮住了一只眼睛。
作者簡介

蘇熱,蒙古族,現居呼和浩特。文藝學碩士在讀,有小說、評論見于各刊。
責任編輯?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