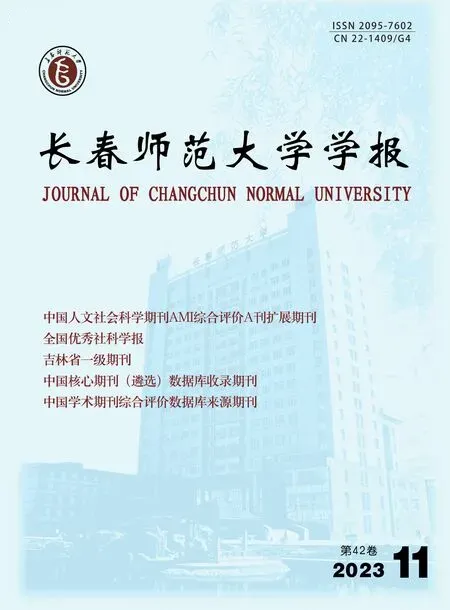先秦政治傳播觀念探究
——基于“樂”的維度
雷大川,趙湘瑾
(1.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 2.韓國漢陽大學 音樂學院,韓國 首爾 04763)
先秦之際,“樂”不僅是一種藝術形態, 也是一種涵蓋政治、宗教等諸多意蘊于一體的文化符號, 包含極為深邃而豐厚的精神意境。美國學者曾將中國上古之“樂”的功能歸納為:宗教功能、教育功能、統治功能及哲學意義,其實在傳統中國社會,尤其是先秦時期,樂舞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功能,即政治傳播功能。在古代中國社會,“樂”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傳播方式。
一、“樂”通于神明:先秦政治傳播觀念的神啟意蘊
政治的宗教化、王權的神權化是上古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神的旨意是政治正當性的終極來源。為了維系王權統治,歷代王朝統治者都將君臨天下的政治權威歸結為神靈的旨意。在上古社會的整體文化心態中,樂舞“通于神明,參于天地”[1]。“樂”是神明的聲音,是神諭的傳達[2]。上古先王通過祭祀樂舞這一象征儀式傳達王權神授的政治信念,從而樹立王權統治的終極權威,即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3]。
宗教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沒有宗教神靈意識的萌芽,就沒有人類精神境域的開啟。如果說人類社會是一種理性秩序的存在,那么宗教以神圣方式使社會得以秩序化。正是通過宗教活動的展開,社會運轉所必需的理性秩序與內在凝聚力才得以建立。宗教的精神權威形成了神權體制,這是早期國家政治體制形成的前提與條件。
政治正當性問題是政治領域中的根本問題,政治權力只有實現自身的合理化、正當化,才能確立政治統治的根基。宗教是文明與國家形成的契機[4]。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中,“宗教一直是歷史上流轉最廣、最為有效的合理化工具”,也是人類文明秩序合法化最適用的工具和手段。宗教可以將社會中難以穩定的實在結構與一種終極性的存在聯結在一起,從而使社會政治結構獲得一種神圣性的資源和根基。它讓人們忘記這個秩序是人創造的,而是神建造的秩序[5]。在古代中國社會,歷代先王自稱“天子”,將自身的王權統治歸結為“奉天承運”的政治授權,其根本目的就是將王權神權化,將王權政治宗教化。誠如張榮明先生所言,商周社會就其政治形態而言是“宗教政治”,宗教構成了政治的前提和本質,政治于是宗教化[6]。 當時的國家政治“完全是借宗教之力得以推行的,當時君主的宗教活動,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大事,重大的國家大事全包容在宗教活動中。”[7]
大約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中國已形成王權與神權、世俗權力與精神權威相統一,亦即“政教合一”的政治傳統。在而后的發展歷程中,這一政治傳統在不同時代雖然表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但從總的趨勢來看,中國“政教合一”政治傳統的發展方向是王權越來越利用神權,神權越來越服從于王權,這一政治特征在殷商、宗周之際漸趨明顯。
政治的宗教化、王權的神權化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使得神靈的意旨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終極來源。祭祀作為一種溝通神人的宗教儀式,在古代中國社會逐漸被視為首要的國家大事,所謂“祀之與戎,乃國之大事”[8]。“祀”之所以成為首要的“國之大事”,全部奧秘就在于通過祭祀這一象征性活動“隆興上下之神”,把王權神授這種無形的政治宗教意念轉換成感同身受的精神體驗,從而建構起“天帝合一”“祭政合一”的現實情景,如此便為世俗的王權注入了終極的政治權威。
在傳統中國社會,祭祀活動涵蓋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基本內容。祭祀活動與宗教典制既是古人類的文化核心,也是古人類政治生活的綱維。祭祀儀式既是一種宗教文化現象,也是一種政治現象。人類社會最初的組織手段之一是原始宗教及其祭祀活動,故最初的國家即所謂“祭儀國家”。[9]考古研究發現,早在仰韶文化期間,就出現了“與祭祀有關的標志圖案和符號,以此顯示某些權力,并提供唯一一種宗教祭祀在政治或其他場合發揮作用的線索”[10]。可見早在新石器時代,祭祀即與政治權力有極為緊密的內在關聯。時至殷商時代,祭祀與政治權力之間極為緊密的內在關聯才有確鑿的文字資料可考。
李學勤先生說:“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有祭祀也就必有樂舞”[11]。劉師培在《舞法起源于祀法考》中斷言:三代以前之樂舞,無一不源于祀法。在上古先民的文化心態中,祭祀樂舞是神人相通的精神載體,即所謂“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12]。樂舞作為上古先民最為本真的生命情態,具有“形而上”的精神境域,寄寓著靈魂超越、“神人以和”的精神意蘊與宗教功能。在蒼茫邈遠的上古時代,堅韌的生命意志與神往的天國追求,使上古先民在沉醉于樂舞之時,“跨過了現實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的鴻溝,走向了魔鬼、精靈和上帝的世界”[13]。對上古先民來說,“樂”不再是一種審美藝術,而是“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12]。
音樂的宗教超驗體驗是一個普世性精神境域,在中國有極為悠遠的文化淵源。從一定意義而言,中國傳統的樂文化就是一種宗教文化。早在中國上古之初,“樂”就承載著“神人以和”的宗教意蘊。《尚書·堯典》云: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由此可見,早在三皇五帝之際,上古先民就相信“八音克諧”即可“神人以和”。在傳統中國文化中,音樂不是一種審美的藝術形態,而是一種“人神相通”的天道韻律。對上古先民來說,“樂通人神”不僅是一種觀念,更是一種通達神靈世界的現實路徑,他們虔誠地相信通過“樂”就可以實現人神相通的目的。
“有祭祀也就必有樂舞”是一個普世性宗教文化現象。顧希佳在《祭壇古歌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寫道:
祭祀儀式中要唱歌,這也幾乎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它是從祭祀儀式中的禱詞、咒語發展而來的。可以設想:人類要跟神靈溝通,讓神靈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就必須在儀式上把自己的這層意思表達出來。表達的方式,不外乎是手勢、語言。手勢和身體姿勢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舞蹈和繪畫;語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歌唱,這是很自然的。[14]
原始歌、樂、舞的上述兩大特點,在古代中國的祭禮儀式中有更為顯著的彰顯。《周易正義》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在上古先民的神化思維中,“樂”是人神通達的天道韻律,故祭神必用樂舞。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見諸多種典籍。如《詩經·小雅·甫田》云:“我田既藏,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社。”農夫慶賀秋收,敲響琴瑟鼓樂。迎祭田祖,祈求郊后始耕之時有甘雨降臨,保佑禾稼豐收,故用琴瑟和鼓樂祭祀。
在祭祀儀式中,樂舞有極為重大的神奇意義:對神而言,有召喚、感應神靈的功用;對人而言,它可以表達人對神的虔敬篤誠之情與至誠之心,讓人在神秘的宗教氛圍中實現“神人通達”“神人以和”的天國追求。雖然時至宗周時代,祭祀儀式中的宗教意蘊有所減弱,但“樂”與禮相互融合為“禮樂”仍為祭祀儀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動,對國家上層建筑起到奠基、發展和鞏固作用。祭祀禮儀是國家上層建筑的具體體現,在祭神樂舞中,神在其中感之、應之,人在其中化之、教之,國便成之、固之,如此即形成了傳統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形態。
在上古中國社會,王權以祭祀為依托,以“樂通人神”為指向,形成了王權、宗教與藝術緊密相聯的政治文化形態。政治的藝術化、宗教化是上古中國政治的特有品格。著名學者張光直在《中國青銅器時代》 一書中指出,在上古時期,不但“政治、宗教、藝術是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作為通天工具之一的藝術,實在是通天階級的一個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權力之獲得與鞏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與戰車、戈戟、刑法等統治工具相比的。
在“樂和神人”“樂達天界”的宗教情結中,上古先王在祭神儀式中“先奏是樂,以致其神”,歌詠頌詞以達天庭。《詩經》“頌”及“雅”中的某些篇章,即是上古王侯舉行祭神儀式時專用的“樂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瑕文王,既佑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觀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15]
周天子通過歌詠頌詞營造出一種天人唱和、神諭下達的神秘語境,向天下萬民傳達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意義,從而為西周王朝尋找到政治統治的正當性。
上古社會是一個神治的社會,天國中的神是一切事物存在的終極依據。歷代先王若君臨天下必須取得天神的旨諭,否則即不具有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自遠古以來,通天的巫術、神靈的祭祀已成為統治者的專利,只有占據通天祭神的特權,才有資格君臨天下,并建構政治統治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樂”作為“人神通達”的精神境域,是“王權神受”旨意的傳達,在上古中國社會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政治傳播功能。
二、“樂”以象政:先秦政治傳播觀念的時代特征
在人類的文化思想史中,“象征”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有的人類學家甚至認為象征的意義之重大幾乎可以與生命的出現相比。有了象征,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可以通過少許象征表達傳遞。對上古中國先民而言,“樂”是一種政治象征符號。通過“樂”這一象征符號,君主的政治權威得以傳達,君臣的政治等級意義得以展現。“樂”的政治象征意義是上古中國政治秩序的精神依托,象征意義的瓦解常常即是政治秩序的崩潰,即所謂“禮崩樂壞”而天下失序。
回溯古今中外的政治發展史便可發現,幾乎所有政治系統的運轉都離不開某些象征符號的應用。哈羅德·D·拉斯韋爾在《政治學》一書中明確指出,對政治象征符號的操縱是各類權力精英駕馭環境、實現其政治目標的主要途徑之一。從一定意義而言,創設一種政治象征,就意味著設定了一種權力關系,任何政治象征的變更也必然標志著權力關系的改變。政治象征在政治領域中的意義極為重大。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政治只是一連串抽象的符號,這一意味深長的話語雖顯得有些絕對,卻向人們表明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政治象征在紛繁復雜的政治領域之中有極為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人類的傳播活動是一個以信息為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政治信息是由象征符號與思想意義構成的,人類區別于動物信息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人類能夠使用象征符號來傳達象征意義”,因此人類的政治傳播活動“可以作為象征性社會互動活動來把握”[16]。象征是一種“表象”與“意義”的結合,“意義”與“表象”是緊密關聯的整體。在現實社會中,沒有無“表象”的象征,也不存在無“意義”的象征。“象征”以物化的形態來呈現,但就其根本而言,“象征”乃是一種意義的表達,“象征”的物化形態只是概念與意義的有形載體。人類政治傳播在現象上表現為“象征”符號的交流,實質上則是“意義”的交流與表達。
象征作為一種符號、一種暗示、一種隱喻,其本身有兩層意涵:一是意義,二是意義的表達。在政治傳播活動中,政治象征行為就是通過使用特定的象征符號傳達特定的政治意義。無論是具象象征形態(如物體、語言文字及行動)還是抽象象征形態(如思想、觀念及關系),就其功能而言,無不是一種政治意義的表達。鼎本為一種具象的金屬器物,但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語境中,“鼎”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金屬器物,而是王權意識的一種有形化表達。政治象征形態多種多樣,國家、階級、黨綱、標語口號以及紀念節日、紀念性建筑物、旗幟、勛章、儀式以及游行等都屬于政治傳播形態。
中國文化以“象”為本,“象喻”意識是中國文化的意識根源。在巫卜文化的浸染下,歷經先秦學者的思想闡釋與精神超越,“象喻”意識彌漫于政治、倫理以及審美等諸多領域。“樂象”觀念即是“象喻”思維在禮樂文化中衍生的重要政治范疇,具有極為深遠的政治意義。在“象喻”文化背景下,先秦儒家常常將政治與音樂等同視之,尤其是“孔子把政治完全藝術化了。”[17]“樂”在古代中國社會已不再是一種審美藝術形態,而是一種極具政治象征意義的政治文化符號。
“樂”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絕非一種單純的審美藝術形態,而是一種內涵政教意蘊的精神載體與象征符號。古代先哲對“樂”的闡釋,就其根本而言,更多的是以“樂”為示例來隱喻特定的政治理念,如“夫樂,天子之職也”;“王者功成作樂”。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樂”象征著至高無上的王權,表達著“君臨天下”的政治理念。
在上古中國政治文化中,制禮作樂是王者的特權。上古先王開國創業、平定天下后,往往要通過制禮作樂“以章其功”,宣揚其一統天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
在古代中國社會,“樂”是帝王權力的象征,只有建基立業、開國安邦的帝王才有資格制禮作樂。《呂氏春秋·古樂》曰:
王者功成作樂,沿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五異世,不相襲禮。
相傳夏朝的開國之君大禹“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治水有成,創立了開國基業,于是命皋陶作樂“以昭其功”。據先秦典籍記載,夏朝時代的樂舞《大夏》,其內在意蘊就是頌揚大禹治水的歷史功績。《呂氏春秋·古樂》云:
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謬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
在上古時代,“樂”不但是擬人化的政治地位、政治身份的象征,還是各個部族政權的象征。在遠古社會,部族政權林立,各個部族政權為強化族群認同,都要制定各自的“圖騰之樂”以標示自身的主體性。這些“圖騰之樂”如同現代社會中的國歌、國旗,既是各個部族政權的精神象征,也是上古帝王的身份象征。《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云: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
興舞作樂是天子的專有職責,唯有君王才有資格作樂,這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政治觀念。這一重要觀念經由古代典籍不斷記述宣揚,逐漸衍化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心理意識。
公私不分、家國一體、君父合一是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的基本形態。這種特定的社會形態使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呈現為一種倫理政治型文化。在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把政治和倫理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于從一定意義而言,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就是一種倫理化的政治,政治的倫理化與倫理的政治化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大本質特征。長久以來,中國學術始終將道德倫理與社會政治作為話語主題之核心,尤其是在儒家的禮樂文化傳統中,“樂”是政治倫理的象征,是政治等級意識的宣示。
《樂記》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鄭注:“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所謂“樂通倫理”即是指“樂”與社會等級關系相互類通,因此它可以在協調、規范社會關系方面發揮重大作用。《樂記》還指出:
圣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禮記·文王世子》亦說:
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在上古中國社會,天子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相見等禮儀昭示著尊卑長幼之序。從《禮記》中的《樂記》《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等篇可以看出,“樂”與社會政治制度密切相關,是社會倫理等級的象征,宣示著倫理等級觀念,不同的樂舞規格與不同的政治地位相匹配。這樣便顯示出禮樂儀式的莊嚴肅穆,顯示出禮別貴賤的社會意義。
從本質意義而言,政治象征作為一種政治意義的存在,通過心理情境的設定,創設一定的政治態度與政治愿景。每一個政治象征的興起,都是在反映某一時代的希望與需要。為獲取或維持政治權力,政治精英總是通過政治象征藝術的運用來激發人們的政治情感,任何精英都將共同命運的象征作為旗號來感召大眾以建構自身的政治正當性。[18]在上古中國社會,上古先王通過樂的象征意義,彰顯自身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固化尊卑有序的政治等級意識,從而建構政治心理權威。
三、“樂”以致化:先秦政治傳播觀念的內在精髓
政治傳播就其根本而言不僅僅在于政治觀念的傳達,尤為重要的是如何觸動人、感化人,從而把政治觀念內化為一種政治認同情感。“倘若信息內容不能感染人、觸動人,使人心悅誠服,那么就算它來自可信度極高的信源最后也終歸無效”[19]。上古先民雖然對這一政治傳播定律缺乏學理意義上的總結,但對如何使人心歸化有較為深刻的體認。早在先秦時期,荀子即有深切感悟:“夫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1]。感情真摯的藝術能夠深入人心、感化人心,使政治價值觀念深入人心,從而把政治價值觀念內化為一種政治認同的情感,達到“心悅誠服”的效果。
從一定意義而言,人是一種感性的存在。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情感是心理活動的組織者,人的情感傾向決定自身的價值偏好與行為取向。在政治社會中,情感的作用與意義尤為重大。情感是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的“黏合劑”,缺乏共同的情感傾向,政治社會將分崩離析,政治權力的建構也無從談起。如何透過政治觀念的傳播來培育政治認同的情感傾向,始終是一個永恒的重大政治問題。雖然先秦儒家學者對“政治認同”這一術語缺乏概念上的認知與理論上的自覺意識,但對政治認同的情感轉化有較為深入的闡釋。
在政治領域中,采用何種方式實施政治傳播,或者說如何通過政治傳播有效地實現政治認同,是政治傳播領域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政治價值觀念的宣揚只是政治傳播的表面層次,感化人并使政治理念內化為一種認同的情感才是政治傳播的根本目的。就其根本而言,政治傳播的過程即是政治認同情感的生發過程。人的情感有其自身的生發規律,情感的培養和沉淀不能全然靠說理,情感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種內心體驗。美的東西總是帶有感情,而且它常常把不可言狀的情感以具體生動的形象、鮮明獨特的形式表現出來,讓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使人在想象中體驗到審美情感。
在政治傳播中,政治的說教與灌輸不但難以生發政治情感,有時反而會激起抵觸逆反的心理情緒。如果把政治理念以藝術的方式內化為人們的審美情感,則會使人心悅誠服,從而達到最佳的政治傳播效果。因此,在政治傳播中,審美藝術具有極為重要的特別意義。
從心理學角度解釋,審美活動之所以能有效地達到政治傳播目的,是因為審美藝術向受眾群體傳達的信息是通過“立體通道”傳遞的,即把信息通過“說理”“形象”“情感”三條通道傳達給受眾群體,使其形成立體的、生氣勃勃的、完美的映像。這種映像內蘊理性的骨架、情感的血肉,使受眾群體從心理上樂于親近它,因而產生良好的信息接受狀態和加工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所要傳播的信息便有了切實的說服力、感染力。在政治傳播中,如果能把生澀的政治理念內化為審美意境,賦予靜止的名詞概念以審美的意象,就會打動人的靈魂、激蕩人的情感,使受眾群體生發情感的共鳴,使政治傳播達到內隱化的高妙境界。
審美藝術不僅具有寓教于樂的特點,而且具有潛移默化的內隱性特征。它可以回避正襟危坐、耳提面命的生硬與造作,把傳播內容以鮮活動人、生動可感的形式表現出來,讓受眾群體沉浸于審美的意境之中,在獲得美的享受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受到熏陶、感染。這種審美的享受既是情感的愉悅,又是理性的感悟。此時,欣賞者并不自覺,但傳播內容蘊含的思想理念在潛移默化中沁人心扉,內化為人們深層的心理情感。
中國古代先民對“審美傳播”這一現代術語雖然不具備理論意義上的闡釋,但對通過“樂”這一審美形式宣揚特定的政治價值觀念、培植政治效忠情感有極為深切的感悟。《樂記》作為儒家的經典文本,其基本要義之一即是強調將宗法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念內化于“樂”的審美意境之中,其“目的是通過審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在‘樂’的潛移默化中由審美境界升華到道德境界”[20]。
“化”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具有極為深遠的思想意蘊,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非常重視“化”在政治領域中的重大意蘊。《正韻》中說:“化,告誥諭使人回心歸化。”可見,“化”是側重于內心世界的變化、精神領域的開化。中國古代先哲大都注重“化”的深遠意蘊。《老子》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與老子思想不同的是,儒家以積極入世的情懷矢志不移地踐行以“文”化民“化成天下”的治世思想,如《周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樂”是“文”的重要意涵之一,從現代傳播學角度而言,“以文化成天下”可以解讀為通過“樂”這一審美的方式傳播思想觀念,使民心歸化,從而有效地治理天下。
“經世以文,化成天下”可以說是儒道文化的內在精髓。儒家以“樂教”施政天下,其中的一個根本政治目的即是在潛移默化中收攏民心、“化成天下”。從人的本性而言,生硬的政治說教極易引起人們的反感抵觸情緒,難以實現政治認同的目的。最為適當的教化是“寓教于不教之中”,通過審美的意境傳達理性的價值理念,在不知不覺之中使受眾群體感悟到教化的內容,在潛移默化之中達成政治認同的目的,從而實現“化成天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化成天下”的思想主旨內蘊著先秦政治傳播觀念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