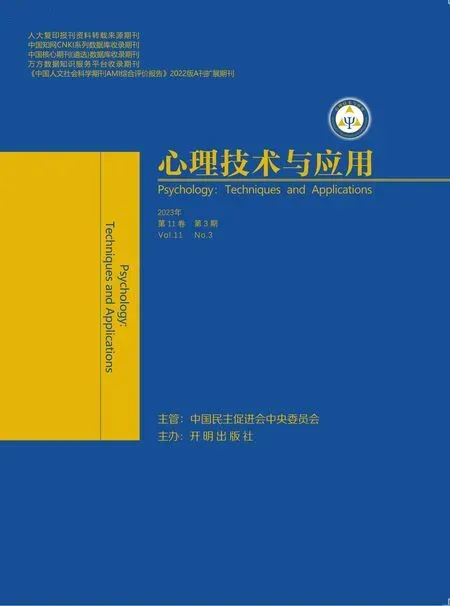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與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關系:鏈式中介效應分析
賈曉珊 孟歡蕾 侯艷天 朱海東,3
(1 石河子大學師范學院,石河子 832003)(2 陜西省富平中學,渭南 711701)(3 石河子大學心理應用研究中心,石河子 832003)
1 問題提出
隨著網絡技術的進步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網絡游戲產業發展繁榮,網絡游戲也逐漸成為眾多網民尤其是青少年群體所喜愛甚至沉迷其中的一種娛樂方式。據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聯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1),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已達1.83億,除上網學習和聽音樂之外,玩游戲成為未成年網民最經常從事的網絡活動,參與比例高達62.5%,足以說明網絡游戲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然而網絡游戲類型豐富多樣、內容良莠不齊,青少年心智發展尚不健全,明辨是非和抵御外界誘惑能力較弱,如若受到網絡游戲中不良信息的誘導,很可能對其身心健康不利。以往研究多圍繞暴力視頻游戲對個體攻擊性或親社會性的影響機制(Anderson et al.,2010;You et al.,2015)。近年來,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研究者也開始關注內容積極友好的視頻游戲對個體的正向影響,研究重點也逐漸轉向親社會視頻游戲對個體心理與行為發展的積極意義。
親社會視頻游戲是指游戲主題帶有明顯親社會性質(Chambers &Ascione,1987),包含少量或不含暴力內容,玩家和游戲角色以非暴力方式進行相互幫助和支持的游戲類型,可能對玩家短期和長期的親社會行為起促進作用(Gentile et al.,2009;Vieira,2014)。親社會行為則涵蓋了在社交過程中個體所表現出的一切有利于社會關系和諧的行為及趨向,不僅反映出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水平,同時也是其心理健康狀況和社會適應能力的重要體現(寇彧,唐玲玲,2004)。為更好解釋親社會視頻游戲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者提出了一般學習模型。該模型認為,個體對當下行為的決策是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激活了認知、情緒等內部狀態而發揮效用。如若這一過程得到強化和重復,將會影響個體長期的行為傾向(Buckley &Anderson,2006)。也就是說,通過接觸親社會視頻游戲可影響個體內部狀態繼而促進其親社會行為增加。此前有研究證明,無論是短時接觸親社會視頻游戲抑或是自我評估的日常視頻游戲接觸情況均能顯著預測個體當前及后續親社會行為的發展(劉衍玲等,2019;Greitemeyer &Osswald,2010)。但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是如何經由個體因素對其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的,目前仍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共情作為一種理解他人情緒情感變化并據此做出適當反饋的個人能力(潘彥谷等,2013;Jolliffe &Farrington,2006),被視為個體做出親社會行為的重要促動因素 (van der Graaff et al.,2018)。研究發現,共情在兒童和青少年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Bartlett &Anderson,2013;Shoshani et al.,2021),即使將這一中介機制置于長程的縱向研究背景之下依然適用(Prot et al.,2014)。鑒于目前國內關于共情在親社會視頻游戲與親社會行為之間作用機制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探討,且多以大學生群體為主(邱淑慧,2019),能否直接推論到青少年群體尚還存疑。因此,本研究將以初、高中生為研究對象,驗證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是否通過共情的中介影響其親社會行為。
此外,視頻游戲所具備的另一關鍵特征是其包含的道德屬性。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媒介,視頻游戲匯集融合了多元的道德價值理念,使玩家被動接受預設的游戲模式,因而能潛移默化地傳播其所要向受眾傳達的道德觀念(馬歇爾·麥克盧漢,2009)。道德認同是個體在社會文化環境中建立的以道德品質為核心的自我概念,反映了個體對社會道德價值內化與認同的程度(Aquino &Reed,2002)。青少年處于心智不斷發展、道德價值觀念培育塑造的關鍵階段,需要通過接觸各類道德實踐活動,汲取其中的道德知識,逐步建立符合社會規范的道德觀念(陳月華,程冰櫻,2016)。因此,作為青少年日常接觸的一種娛樂活動,視頻游戲也就成為了青少年學習道德知識,提升道德意識的途徑之一。然而,如今的視頻游戲中充斥著大量不道德因素,長期沉溺其中將荼毒青少年身心健康,甚至引發青少年道德失范行為(吳月華,2020),已有研究表明暴力視頻游戲會使玩家道德情感扭曲,降低其道德內疚感,進而誘發攻擊行為(Greitemeyer &Mclatchie,2011)。道德認同作為個體實施道德行為的重要激勵因素,已被證實能增強青少年親社會傾向(Carlo &Padilla-Walker,2020)。基于此,親社會視頻游戲中傳遞的互助、合作等正性道德價值觀能否激發青少年道德認同從而鼓勵其做出更多親社會行為?需進一步驗證。
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是分別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親社會行為的過程中起中介作用還是以連續的方式中介二者關系?對這一問題仍需深入探討。有國外學者指出,共情作為一種道德情感,在個體道德發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共情所觸發的情感痛苦會激活個體相應道德認知,進而促使其做出道德行為來改善他人不利處境(Eisenberg &Morris,2001)。國內學者劉聰慧等(2009)則提出共情的動態模型,該模型解釋了個體的共情源于情緒、認知和行為系統的動態交互作用,當個體對他人處境產生共情時會結合自身道德準則判斷共情是否符合社會倫理規范。若符合,可能進一步激發道德行為,若不符則結束這一過程。相關研究也已證明,青少年對他人處境的感同身受有利于深化自我道德概念,最終形成道德認同,并且反映在具體的道德行為中(Sharifi et al.,2016;Stilwell &Thomas,2001)。但同時,也有研究者認為,共情是將已形成的道德認同轉化為親社會認知和行為的重要動力(Hoffman,2001),高道德認同個體能以自身內隱或外顯的道德標準判斷求助者的處境,進而對其產生共情,以此激發親社會行為(Kaur,2020)。有實證研究發現道德認同能經由共情的中介影響個體捐贈行為(Lee et al.,2014)。因此,我們推斷共情和道德認同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中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模型1)。同時,考慮到道德認同對共情也可能存在正向預測作用,本研究提出另一鏈式中介模型進行驗證,即道德認同和共情在親社會視頻游戲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模型2)。

圖1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共情、道德認同和親社會行為關系的假設模型(實線代表“假設模型1”,虛線代表“假設模型2”)
如前所述,本研究基于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的一般學習模型,擬探討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共情與道德認同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具體分析過程不僅能進一步闡明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影響的內在機制,同時該研究結果還能為今后借助網絡游戲平臺對青少年進行道德意識滲透,發揮網絡游戲的正性功能,提升青少年道德素養提供可行的實踐路徑。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選取西北某省市當地兩所普通中學,一所初中,一所高中,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匿名施測。利用學生自習課時間現場發放問卷,每位學生在填答之前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共發放問卷840份,剔除空白、未填寫人口學數據、漏填題數占總題數1/3以上和規律性作答等無效問卷后,最終回收問卷777份(有效率為92.5%)。被試平均年齡為14.96±1.74歲,初中422人,高中355人;男生392人,女生38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游戲接觸經驗問卷
采用Anderson和 Dill(2000)聯合編制的游戲接觸經驗問卷,經翻譯修訂后適用于本土研究(Teng et al.,2018)。該問卷要求被試根據以往接觸電子游戲的經歷列出三款視頻游戲,并分別對游戲的使用頻率和內容(暴力/親社會)進行五點計分。而后根據“親社會視頻游戲(暴力視頻游戲)接觸程度=∑[游戲內容(暴力/親社會)×游戲使用頻率]/3”,得分越高說明個體接觸相應游戲內容越多。由于本研究僅關注個體對親社會視頻游戲內容的接觸,故將相關暴力內容進行控制。本研究中該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2。
2.2.2 青少年親社會傾向量表
采用寇彧等(2007)根據Carlo編制的親社會傾向量表進行修訂后的中文版。該量表包含六種親社會類型,分別是“公開的、匿名的、利他的、依從的、情緒的、緊急的”,共26題。采用五點計分(1代表“非常不像我”,5代表“非常像我”),得分越高說明個體在不同情境中的親社會行為傾向越高,并可廣泛應用于青少年群體。本研究中該量表各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6、0.79、0.77、0.80、0.79、0.84,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3。
2.2.3 人際反應指數量表
采用Davis(1980)編制,后經張鳳鳳等(2010)修訂,在國內廣泛使用的人際反應指數量表。該量表包括四個維度(觀點采擇、想象力、同情關心、個人痛苦)共22題。采用五點計分(1代表“非常不恰當”,5代表“非常恰當”),得分越高說明個體越能理解他人處境,即共情能力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各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3、0.70、0.68、0.79,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7。
2.2.4 青少年道德自我認同問卷
采用萬增奎和楊韶剛根據Aquino和Reed編制的道德自我認同問卷修訂后的中文版(萬增奎,楊韶剛,2008)。該問卷包括兩個維度(內隱性和外顯性)共16題。采用五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說明青少年道德認同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各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0和0.81,總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1。
2.3 數據分析
使用SPSS 25.0整理錄入數據并進行一般性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而后采用AMOS 27.0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假設模型。
3 研究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所得數據均為研究對象自我報告,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響,故使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所有題目進行檢驗,結果共提取出15個主成分,并且第一個主成分解釋的變異為18.8%,小于規定標準40%,說明本研究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響。
3.2 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共情、道德認同和親社會行為兩兩之間均顯著相關,因性別、年齡和暴力視頻游戲接觸與主要變量相關顯著,故在后續分析中進行控制。

表1 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3.3 中介作用檢驗
本研究擬使用AMOS建立兩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共情和道德認同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中介作用,即檢驗假設模型1和假設模型2,并采用Bootstrap法,設定重復抽樣5000次檢驗中介效應。
首先,在控制性別、年齡和暴力視頻游戲接觸的基礎上對假設模型1數據擬合,表2結果表明數據和假設模型1擬合良好(χ2/df=3.53,CFI=0.95,TLI=0.93,SRMR=0.05,RMSEA=0.06)。為保持模型美觀和簡潔,不呈現控制變量路徑,簡化后的中介模型見圖2。模型1顯示,直接路徑中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顯著預測親社會行為(β=0.15,p<0.001);中介路徑中,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顯著預測共情(β=0.25,p<0.001)和道德認同(β=0.09,p<0.05),共情顯著預測道德認同(β=0.36,p<0.001)和親社會行為(β=0.32,p<0.001),道德認同顯著預測親社會行為(β=0.27,p<0.001),因此假設模型1成立。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通過共情影響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量為0.08,95%置信區間為[0.048,0.119],表明共情的中介效應顯著;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通過道德認同影響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量為0.03,95%置信區間為[0.001,0.055],表明道德認同的中介效應顯著;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通過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鏈式中介影響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量為0.02,95%置信區間為[0.012,0.039],表明該鏈式中介效應顯著。

表2 假設模型1和假設模型2中介模型擬合指標

圖2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共情、道德認同和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模型
其次,對假設模型2進行數據擬合,具體操作方法同上。表2結果表明數據和假設模型2擬合良好(χ2/df=3.69,CFI=0.95,TLI=0.93,SRMR=0.05,RMSEA=0.06)。中介模型見圖3,結果顯示,除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指向共情(β=0.19,p<0.001)和道德認同(β=0.18,p<0.05),道德認同指向共情的路徑系數(β=0.34,p<0.001)與假設模型1不一致外,其余路徑系數均與假設模型1一致,假設模型2也成立。中介效應檢驗表明,假設模型1和假設模型2的總中介效應量和鏈式中介效應量相等,模型1共情的中介效應量大于模型2共情的中介效應量,而模型2道德認同的中介效應量大于模型1道德認同的中介效應量(見表3、表4)。

表3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共情、道德認同和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分析

圖3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道德認同、共情和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模型

表4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道德認同、共情和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4.1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與親社會行為正相關顯著,且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直接效應顯著,即對親社會視頻游戲的頻繁接觸可直接增強個體親社會行為傾向,該結果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劉衍玲等,2019;Harrington &O’connell,2016)。一般學習模型中的長時效應模型認為,對親社會視頻游戲的長期接觸會使個體行為產生長時效應。這可能是由于個體長時間在親社會性質的游戲體驗中習得了親社會知識和經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親社會腳本,從而具有更高的親社會傾向(Gentile et al.,2009;Greitemeyer et al.,2012)。親社會視頻游戲不僅滿足了青少年利用網絡游戲進行娛樂放松的需求,同時也拓寬了他們學習親社會知識的途徑,為親社會行為踐行奠定了基礎。
4.2 共情和道德認同的單獨中介作用
本研究進一步揭示了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如何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即探討了共情和道德認同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親社會行為的中介作用。研究首先證實了共情在二者關系間的中介作用,這與國外學者在兒童和青少年群體中的研究結果一致(Bartlett &Anderson,2013;Shoshani et al.,2021)。此前有學者發現共情作為兒童青少年親社會媒體使用和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量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即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亞其他地區均得到了一致的結果,并且還證明了這一中介過程存在長期的積極效應(Prot et al.,2014)。親社會視頻游戲屬于親社會媒體之一,長期接觸之下提升了青少年對他人的共情能力,從而對親社會行為的發生起到了促進作用。
其次,道德認同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過程中也起中介作用,即青少年對親社會視頻游戲中所傳達的道德觀念進行自我內化與認同,同樣也培養了其道德水平,影響了其道德行為的發展。目前雖尚無研究直接表明道德認同在二者關系之間起中介作用,但根據Aquino和Reed(2002)的觀點,道德認同是在一定的環境氛圍中形成,這關系到個體能否將感知到的道德觀念融入自我道德圖式中。研究發現,初中生感知到的學校道德氛圍經由道德認同這一中介路徑影響其親社會行為(杜秀蓮,高靜,2019)。而蘊含著豐富道德資源的網絡游戲,依靠其傳播力強、規則意識明顯和網絡空間社區化的特點,玩家長期接觸必然會受到其中道德氛圍的影響進而塑造自我道德價值觀(任建東,2008)。并且有學者表示可利用網絡游戲的正性價值對青少年進行道德素養培育以促進其道德行為的發生和發展(吳月華,2020)。
4.3 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鏈式中介作用
與假設一致,本研究發現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可經由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這一結果也得到了共情動態模型的支持(劉聰慧等,2009)。一項有關消費者慈善行為的研究證明,共情和道德認同的相互作用能影響消費者慈善行為,較高的共情水平提升了消費者的道德認同,進而促進了慈善行為的發生(Yang &Yen,2018)。相關研究也指出,共情與道德認同呈正相關(Detert et al.,2008),且共情可正向預測青少年道德認同(扈芷晴等,2022),感知理解他人處境也能促使青少年逐漸深化自我認識,并最終形成道德身份認同(Sharifi et al.,2016)。因此,基于當前青少年接觸視頻游戲的背景,向其提供更多親社會內容的視頻游戲能提升青少年的共情能力,深化其道德認同,從而增強其親社會行為傾向。
此外,本研究還證實了親社會視頻游戲通過道德認同和共情這一中介順序對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表明道德認同也能正向預測共情,這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郭英等,2022;Kaur,2020)。青少年在親社會視頻游戲中習得了對其中蘊含的道德元素的認同,這可能會使其在助人背景下激發對求助者的共情,從而向受助者伸出援手。假設模型1和模型2均成立,兩個中介模型的鏈式中介效應量相等,說明共情和道德認同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影響,即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既可經由“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鏈式中介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也可通過“道德認同和共情”的鏈式中介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需要強調的是,本研究僅是一項橫斷研究,而且目前多數研究更關注共情對個體道德認同的影響(扈芷晴等,2022;Sharifi et al.,2016),雖然本研究從數據結果上證明了道德認同對共情也存在正向影響,但難以從發展角度區分共情和道德認同的先后順序,因此將來需要采用長程的縱向研究更好地厘清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關系。
綜上,一方面青少年對親社會視頻游戲的長期接觸能提升其共情能力,深化其道德認同,從而增強其親社會行為傾向;另一方面青少年對親社會視頻游戲的接觸能塑造其道德認同感,引發個體對求助者的共情,從而提高其親社會行為發生的可能性。由此可見,網絡游戲在青少年道德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親社會性的網絡游戲環境為培養青少年道德情感及其認知和行為的發展提供了平臺。
4.4 研究啟示和教育建議
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作用機制中,青少年既可直接通過長期接觸親社會性的視頻游戲內容學習和強化自身親社會傾向,也可經由共情和道德認同的中介作用間接發展親社會行為。因此,基于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青少年道德情感、認知及行為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如何進一步增強這一結果效應需要重點關注。
對家長和教師而言,大可不必過于擔憂和限制青少年接觸網絡游戲,合理引導其適當接觸具有親社會性質的視頻游戲既可以相對減少其對負面游戲內容的接觸,同時還能促進其親社會行為的學習和發展。對網絡游戲開發與運營商而言,應當嚴格遵守行業規范,在開發與宣傳上不能為了商業利益而有損青少年健康成長,可在游戲情境設置、游戲規則設定以及玩家互動關系之中建構與滲透道德理念,使青少年能將在親社會網絡游戲中學習到的道德知識更好地遷移應用到現實的人際生活之中。此外,還應由政府制定法律政策監督和非政府組織的道德監督以及全社會的積極參與,為青少年營造親和友好的網絡游戲環境,提升青少年道德素養,促進其親社會行為的發展。
4.5 研究局限
本研究雖進一步揭示了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內部機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只驗證了一般學習模型中的長時效應,探討了長期接觸親社會視頻游戲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但未檢驗短時接觸親社會視頻游戲是否能得到同樣的結果,今后可設計游戲任務以驗證其是否成立。其次,采用橫斷研究設計,難以確定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尤其是共情和道德認同的中介作用順序,未來有必要采用縱向追蹤設計以明確二者的先后發展關系。最后,由于采用問卷調查,被試很可能受到社會贊許效應的影響,導致對有些內容作答不真實,今后可采用實驗任務調查被試的內隱態度和行為,以獲得更加真實和準確的結果。
5 結論
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共情、道德認同可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過程中起單獨中介作用。同時,共情和道德認同的關系是雙向的,分別在親社會視頻游戲接觸影響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過程中起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