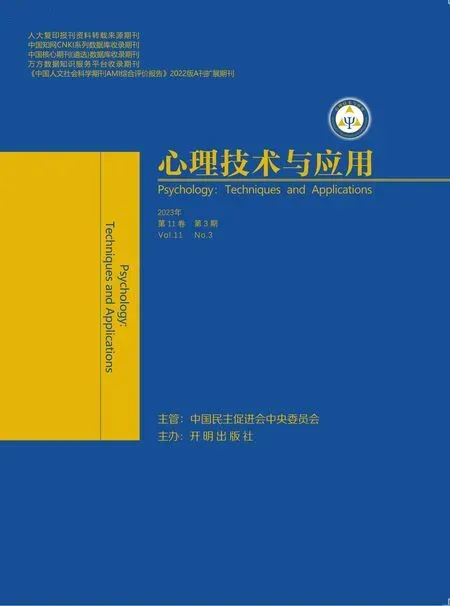調節模式對懷舊的影響: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鏈式中介作用
王鑫慧 王懷勇
(上海師范大學心理學系,上海 200234)
1 引言
撫今追昔,情不自禁。當代社會大學生群體承受了許多壓力,懷舊現象比比皆是。這一現象對促進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有重要意義(黃光梅,常保瑞,2019;Leboe &Ansons,2006)。懷舊是一種“對過去飽含渴望的”的情感(Pearsall &Hanks,1998;Routledge et al.,2008),是一種積極高于消極的混合的復雜情緒(Batcho,2013)。以往研究主要探討了懷舊的功能(Hepper et al.,2021;Sedikides et al.,2021;Van Tilburg et al.,2019)和影響懷舊產生的主客觀刺激(李斌等,2015;薛婧,黃希庭,2011;Stephan et al.,2014)。懷舊是一種與自我相關的救贖性情感,人們會利用其來應對威脅和調節情緒(Cavanagh et al.,2015;Van Tilburg et al.,2018)。然而,懷舊的產生或偏好存在個體差異(Sedikides et al.,2008)。目前,懷舊的個體差異研究已成為懷舊領域學者們關注的熱點(Baldwin &Raney,2021;Seehusen et al.,2013)。例如,許多研究者將懷舊與人格變量結合起來,發現依戀回避程度低、神經質和具有退縮動機等特質的個體更容易懷舊(Barrett et al.,2010;Seehusen et al.,2013;Tullett et al.,2015;Wildschut et al.,2010)。懷舊是以現在為標準評估過去時產生的當下缺失感所引起的一種思念過去的情感體驗(Johnson-Laird &Oatley,1989),它伴隨負性情緒而生,作為情緒修復機制而發揮作用(Wildschut et al.,2006)。評估過去和負性情緒是引起懷舊的重要因素,自我調節領域的研究發現,調節模式與負性情緒、評估過去密切相關(Higgins et al.,2003;Hong et al.,2004;Kruglanski et al.,2013)。自我調節是個體選擇目標及策略并采取行動以實現目標的過程,主要分為評估和運動兩種模式(Kruglanski et al.,2000)。這兩種模式在認知和情感上皆存在差異(Hong et al.,2004;Kruglanski et al.,2000;Pierro et al.,2018)。那么,評估模式和運動模式在懷舊上是否存在差異?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作為與調節模式和懷舊有密切聯系的因素,評估與情緒在兩者之間發揮什么作用呢?評估模式者會因未能做出最佳選擇而產生反事實思維,進而對過去進行評估和假設(Higgins et al.,2003;Pierro et al.,2008),假設過去如何做結果可能會更好,而這一心理模擬過程會引起個體羞恥等負性情緒(Markman et al.,1993;Roese &Kai,2017)。相比運動模式,評估模式更多與負性情緒相關(Kruglanski et al.,2016),而后悔是定位于過去的負性情緒之一。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后悔是反事實思維所引起的負性情緒結果(Coricelli &Rustichini,2010;Pierro et al.,2008;Sevdalis &Kokkinaki,2006)。懷舊是個體應對心理不適和修復個體情緒狀態的工具(Cavanagh et al.,2015)。因此本研究選取基于現在對過去進行評估和假設的反事實思維,以及定向過去的情緒——后悔兩個變量作為本研究的中介變量。不同于以往研究從懷舊功能角度探討人格特質對懷舊的影響(Barrett et al.,2010;Zhou et al.,2008),本研究從懷舊產生的認知-情緒雙路徑的角度來揭示調節模式如何通過反事實思維和后悔進一步影響懷舊的內在機制,以及反事實思維和后悔在其中的鏈式中介作用,這也成為本研究要回答的問題之二。
2 假設提出
運動和評估模式是個體選擇目標及策略并采取行動以實現目標的常用的兩種方式(汪玲等,2011;Kruglanski et al.,2000)。運動模式關注狀態的轉變,秉持“只管去做”的原則,不在乎當下狀態(王懷勇,陳翠萍,2021;Higgins et al.,2003),而評估模式秉持“做正確的事”的原則,對備選方案進行全方位、批判性的評估和比較(Kruglanski et al.,2013;Mugon et al.,2018)。現有研究表明,運動和評估模式存在諸多差異。首先,時間視角上,根據運動-時間性界面理論,運動模式者定位未來,淡化過去,他們不愿意從事過去的活動或懷舊(Kruglanski et al.,2016;Orehek et al.,2014)。評估模式與過去時間定向呈正相關,他們更關注過去的遺憾或者已經發生的事情(Amato et al.,2014)。懷舊是對過去事件的情感記憶,相對更符合評估者的動機取向。其次,在情緒感受方面,運動模式更多與樂觀等積極情緒相聯系(Kruglanski et al.,2016),而評估模式更容易受到負性情緒等消極因素的影響(Choy &Cheung,2018;Hong et al.,2004)。懷舊伴隨負性情緒出現,能起到恢復個體情緒狀態的作用(Newman &Sachs,2020;Sedikides et al.,2008)。此外,Pierro等(2013)發現,評估模式與懷舊呈正相關,運動模式與懷舊呈負相關。綜上,提出假設1:調節模式負向影響個體的懷舊,評估比運動模式者更容易產生懷舊。
根據調節模式理論,運動模式者注重實際行動,很少關注決策結果(Kruglanski et al.,2000);而評估模式者會仔細評估所有備選方案以求最佳決策結果(Mugon et al.,2018;Pierro et al.,2008),更關注細節(Pierro et al.,2011)。研究發現,相比運動模式者,面對負性事件時評估模式者會因為過度評估而產生反事實思維(岳玲云等,2011;Kruglanski et al.,2000)。Kahneman和Tversky(1982)指出,反事實思維是在心理上對已經發生過的事進行否定,進而建構一種可能性假設的思維活動(楊紅升,黃希庭,2000),其反映了對過去的關注。相關神經電生理證據顯示,評估模式者產生的反事實思維更強(岳玲云等,2011)。先前的研究將懷舊與反事實思維作了間接的聯系(Gilovich et al.,1998)。反事實思維通常發生在與自我相關的消極事件之后(Summerville &Roese,2008),會引發個體內疚、羞恥等負面情緒(Markman et al.,1993;Roese &Epstude,2017),懷舊伴隨這些心理不適出現,起到應對不適的作用(Sedikides &Wildschut,2019)。綜上,提出假設2:反事實思維在調節模式與懷舊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
研究發現負性情緒是懷舊產生的原因之一(Sedikides &Wildschut,2017;Wildschut et al.,2006),而后悔就是負性情緒的一種(徐田田,王懷勇,2021)。如前所述,運動者對自身評價更積極(Vazeou-Nieuwenhuis et al.,2017),與樂觀等正性情緒呈正相關,而評估者則容易產生低自尊、悲觀等負性情緒(Choy &Cheung,2018)。Hong等(2004)推測運動和評估模式在主觀幸福感上所產生的差異是因評估者過度評估而引發后悔所致。Pierro等(2008)研究發現評估模式者比運動模式者更容易體驗到后悔。懷舊可以調節個體的負性情緒(Newman &Sachs,2020;Wildschut et al.,2006)。后悔作為一種負性情緒,我們推測它的出現會引起懷舊。此外,Gilovich等(1998)在指導被試回憶后悔事件并評估自身感受時,被試會產生懷舊。據此,提出假設3:后悔在調節模式與懷舊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心理學研究中,后悔是在反事實思維的框架下展開的(杜柏玲,萬明鋼,2009)。反事實思維與情緒密切相關(劉琴等,2017),后悔正是基于反事實思維而產生的一種負性情緒(Coricelli &Rustichini,2010)。運動模式個體傾向于追求下一個目標,而非糾纏過去,因此其后悔程度更低(Kruglanski et al.,2010)。研究發現,更多的反事實思維會引起更多的后悔 (Pierro et al.,2008),這是因為負面結果的發生意味著個體沒能作出正確的評估,因而評估模式個體更可能產生反事實思維,進而產生更多后悔,而后悔這一負性情緒增多,懷舊就容易伴隨而來(Newman &Sachs,2020),運動模式者恰好相反。綜上,本研究推測調節模式可能影響反事實思維,而反事實思維會引發個體后悔,最終導致懷舊產生。因此,本研究通過構建一個鏈式中介模型進一步揭示調節模式影響懷舊的機制。為此提出假設4:反事實思維與后悔分別在調節模式和懷舊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且作用方式可能是順序的,表現為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鏈式中介作用(見圖1)。

圖1 鏈式中介模型
3 方法
3.1 被試
選取450名在校大學生參加本研究,刪除不認真作答問卷后,共收回有效問卷398份,有效回收率88.44%。其中男生168人,女生230人,平均年齡為21.85±4.93歲。被試填寫問卷后獲得報酬。
3.2 研究工具
(1) 調節模式量表。采用Kruglanski等(2000)編制的調節模式量表,包括運動和評估兩個分量表,各包含12個題目,如“我是一個說干就干的人”“我會花大量的時間羅列我的優點和缺點”等,采用Likert 6點計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以運動模式得分均值減評估模式得分均值為調節模式指標,該指標反映了運動和評估兩種模式之間的相對優勢,指標值越高表示運動模式越占優勢(Orehek et al.,2012)。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為0.75,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崔楠等,2016;王懷勇,陳翠萍,2021)。
(2)反事實思維量表。采用Rye等(2008)編制的負性事件反事實思維量表,該量表共16個題目,分為無參照下行、他人參照上行、自我參照上行、無參照上行四個維度。采用Likert 5點計分,主要測量個體的反事實思維水平,比如“我想到事情的結果可能會更糟糕”等,得分越高,反事實思維數量越多。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為0.80,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f=2.39,SRMR=0.05,CFI=0.87,TLI=0.84,RMSEA=0.06。
(3)后悔主觀評價。為衡量被試后悔的程度,使用Baron(2000)采用的主觀評價法,在回憶最近感到挫敗的事件后,需要對此事件的后悔程度進行評分,題目為“你對此挫折事件的后悔程度評分”,采用四點計分形式,1~4分別代表“完全不后悔”“有一點后悔”“后悔”“非常后悔”這四個度量值,數值越大,代表后悔的程度越高。
(4)懷舊量表。采用Routledge等(2008)編制的南安普頓懷舊量表。被試被告知懷舊的定義,即在情感上對過去的渴望,要求其回答懷舊對他們的重要性和懷舊的頻率,如“懷舊對你來說,價值有多大?”“你是否經常感到懷舊?”,使用Likert 7點計分。最初問卷有五個題目,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之后改為七個題目,得分越高懷舊越強。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為0.76,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薛婧等,2011;薛婧,張睿,2013;Zhou et al.,2008)。
3.3 數據處理與分析
采用SPSS 26.0和Mplus 7.0 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
4 結果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未經旋轉時,共13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公因子解釋百分比為15.56%(小于40%),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調節模式、反事實思維、后悔與懷舊的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及相關分析顯示(見表1):調節模式與反事實思維、后悔、懷舊呈顯著負相關;反事實思維與后悔和懷舊呈顯著正相關,后悔與懷舊也呈顯著正相關,說明適宜進行后續的中介效應分析。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結果
4.3 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中介作用
將調節模式作為自變量,懷舊作為因變量進行層次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調節模式能解釋懷舊6.3%的變異(β=-0.22,p<0.001),但當反事實思維和后悔進入回歸方程后,調節模式對懷舊的影響不再顯著。

表2 反事實思維和后悔在調節模式和懷舊之間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
使用Mplus 7.0對反事實思維、后悔、調節模式與懷舊的鏈式中介模型進行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比Bootstrap(重復抽樣5000次,置信區間為95%)檢驗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單獨中介以及二者鏈式中介的95%置信區間不包括0。具體地說,鏈式中介模型結果如圖2所示,模型擬合良好(χ2/df=1.56,CFI=0.99,TLI=0.97,RMSEA=0.04,SRMR=0.03)。從圖2可看出:調節模式負向預測反事實思維(β=-0.29,p<0.001)和后悔(β=-0.22,p<0.001),反事實思維(β=0.25,p<0.001)和后悔(β=0.28,p<0.001)正向預測懷舊;反事實思維正向預測后悔(β=0.37,p<0.001)。

圖2 鏈式中介模型
進一步中介檢驗表明:總中介效應為-2.13,占總效應(-2.86)81.34%,如表3所示,調節模式到懷舊的直接效應為-0.71,但調節模式到懷舊的直接效應并不顯著(p>0.05)。調節模式→反事實思維→懷舊,即間接效應1(-0.95,占總效應33.39%);調節模式→后悔→懷舊,即間接效應2(-0.79,占總效應27.80%);調節模式→反事實思維→后悔→懷舊,即間接效應3(-0.39,占總效應13.81%)。間接效應遠大于直接效應,說明反事實思維、后悔及反事實思維→后悔在調節模式與懷舊中分別發揮單獨和鏈式中介作用。

表3 調節模式作用于懷舊的中介效應值與效果量
5 討論
5.1 調節模式對懷舊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調節模式負向預測懷舊,驗證了假設1。本研究從“個體差異”的視角出發探討了調節模式對懷舊的影響,豐富了調節模式領域的研究,支持了不同調節模式存在差異的結果(Higgins et al.,2003;Pierro et al.,2011;Woltin &Yzerbyt,2020),也拓展了懷舊領域個體差異的研究。根據調節模式理論(Kruglanski et al.,2000),運動模式者很快會轉移到對下個目標的追求中,不糾纏于過去(Higgins et al.,2003;Kruglanski et al.,2010);評估模式會因追求最佳選擇而拘泥于比較和評估,糾結過去并產生懷舊(Pierro et al.,2013)。另一個潛在解釋是評估模式與負性情緒密切相關(Choy &Cheung,2018;Higgins et al.,2003),懷舊會被個體用來修復情緒狀態 (Cavanagh et al.,2015;Routledge,2015)。當然也有研究發現消極和積極情緒都會引起懷舊 (王國軒等,2018;Wildschut et al.,2006),但運動-時間性界面理論-評估模式更關注過去(Amato et al.,2014),運動模式更關注現在和未來(Kruglanski et al.,2016),這一觀點也為調節模式和懷舊的因果關系提供了一定支持。
5.2 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從懷舊產生的心理過程角度探索了調節模式與懷舊的中間機制,研究內容上有一定的創新。研究發現反事實思維在調節模式和懷舊之間發揮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2,且該路徑的效果量在總間接效應中占比最大。為了“最佳”選擇,評估模式者產生更多反事實思維(Kruglanski et al.,2013;Pierro et al.,2008),從而強化悲觀、后悔等負性情緒,進而使用懷舊來修復情緒狀態(Sedikides &Wildschut,2017)。不同于以往研究強調反事實思維的類型(逄曉鳴等,2012;Roese et al.,1999),數量也是衡量反事實思維的一種方式(Alquist et al.,2015;Kasimatis &Wells,2014),本研究立足于反事實思維的數量,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研究還發現,后悔在調節模式與懷舊中也發揮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3。其中調節模式對后悔的負向預測與Pierro等(2008)的研究結果一致,評估模式者有做“最正確”決策的動機,更難做到自我寬恕(Pierro et al.,2018,2020),因而更容易后悔,陷入對過去的擔憂,這種定位過去的負性情緒會帶動個體產生懷舊(王國軒等,2018;Sedikides et al.,2008)。
另外,反事實思維與后悔的鏈式中介作用成立,本研究的核心理論假設——假設4也得到了驗證,為調節模式如何影響懷舊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解釋。評估者比運動者更容易產生反事實思維和后悔(劉妍潔,陳旭,2012;Beck &Crilly,2009;Pierro et al.,2008)。Zeelenberg等(2002)認為當個體認知到如果先前采取其他行為,行為的結果會更好時,后悔這一負性情緒就產生了(Sevdalis &Kokkinaki,2006;Turman,2005)。當評估模式者產生定位于過去的思維和負性情緒時,懷舊也會伴隨個體的負性情緒而生,以修復個體情緒(Sedikides et al.,2008)。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調節模式理論和運動-時間性界面理論 (Kruglanski et al.,2000,2016),本研究將調節模式、反事實思維和后悔三者對懷舊的影響進行了串聯,從心理過程角度揭示運動模式和評估模式在懷舊上產生的差異及其心理過程機制,這些發現不僅表明了調節模式和懷舊之間的關系,解釋了這種聯系背后的兩種模式在認知和情感上的差異,還驗證和發展了調節模式理論與運動-時間性界面理論,為后續相關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本研究通過將調節模式引入懷舊進行探討,實現了對前人發現的擴充,回應了以往研究者關于探索調節模式和懷舊之間內部機制的呼吁(Pierro et al.,2013)。
5.3 研究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有重要的貢獻:(1)發現懷舊會因不同的調節模式而異,據此可以引導不同模式的大學生采用懷舊的方法緩解心理壓力,順利度過大學生活。(2)驗證了反事實思維和后悔的鏈式中介作用,有助于人們理解運動和評估模式者的內在差異以及懷舊產生的心理過程,進而更有針對性地引導兩種模式的大學生合理利用懷舊來調整認知和情緒,更好前進。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只采用橫斷研究探討調節模式對懷舊的影響。今后可采用縱向研究等更具有檢驗力的方法進一步探索。其次,尚未探索評估模式者是否會從懷舊中獲益。以往研究表明悲觀和有強烈反芻傾向的人懷舊會引發更低的自尊 (Garrido,2018;Gebauer et al.,2008)。未來研究可以做進一步探討。最后,個體行為是其特質與所處情境共同作用的結果(Magnusson &Stattin,1998),未來研究可從環境特征變量上出發來探討調節模式對懷舊產生影響的邊界條件。
6 結論
(1)反事實思維在調節模式與懷舊之間起中介作用;(2)后悔在調節模式和懷舊之間起中介作用;(3)反事實思維和后悔在調節模式與懷舊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