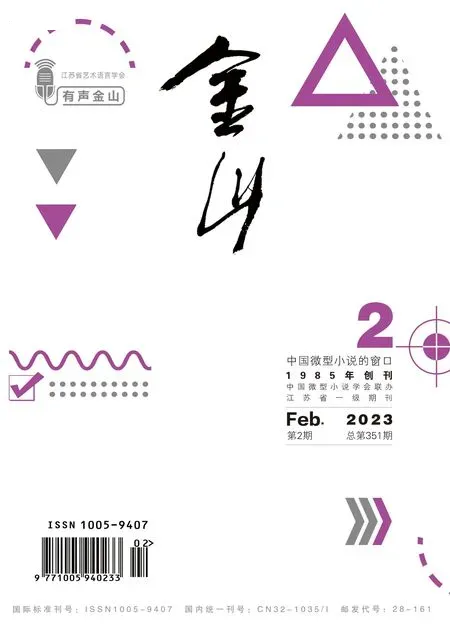東坡村的牛馬驢騾
河北/律新民

誦讀:江蘇非魚
獨 角
壩上東坡村的蘭朵哭聲淘淘,淚水漣漣。她丈夫王彪被獨角頂死了。
獨角是頭牛。它掙脫犁杖追撞郭守亮時,王彪沖上去握住了它的那只角,獨角一甩頭,牛角撞在王彪肚子上。
哨音尖嘯而急促,嘟嘟——嘟嘟——開會啦。
生產隊長馬啟狠吸一口煙:“獨角頂死了王彪,保不準哪天再頂別人,將它殺了分肉,還是賣了分錢,大家說咋辦?”
郭守亮從臉頰上移開顫抖的雙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公理,必須殺獨角祭王彪!”
壩上沒有不下雪的冬天,一尺來深的積雪,別的牛連空水車都趕不出去,身大力不虧的獨角卻能往返十二里去拉水。沒有獨角拉回水,村里人只能融化積雪越冬,淡黃色的雪水,喝上一口,串著野蒿子的辛辣味兒。
“獨角……牛沒罪,它頭上那角有罪。它一頭撞不死王彪,是它頭上的角頂死的。”蘭朵的話語轟然放大了滿屋的哭泣聲。
馬啟宣布:“按蘭朵的意見,鋸掉有罪的那只角,明天給王彪送葬時,焚牛角祭亡靈。”
人到中年的王彪和蘭朵,家中土炕從來沒涼過,蘭朵被蚊子蹬一腳,王彪也得心疼好幾天。不知是籽種不行,還是地畝不行,就是不生娃。這無兒無女的,出殯送葬誰扛幡?村里的小字輩呼啦啦搶著扛,郭守亮握緊幡桿不撒手。
送葬隊伍緩緩蠕動著。郭守亮手持魂幡仰天呼號:“大路朝天走半邊……王彪大哥回來呀!回來呀!”
王彪的墳前燃起莜麥秸,熊熊火焰暖了春天的風。蘭朵跪在墳頭,雙手將牛角緩緩地推入烈火中。焚燒牛角的腥辣味兒從火中撲出來,又隨著升騰的縷縷白煙,云上了湛藍湛藍的天。
誰都聽得見,哞……哞……哞……村里傳來了牛吼聲。
火燒云
東坡村的那掛膠輪馬車,兩匹稍子馬油光水滑黑緞面,駕轅的紅騮馬,一朵飄動的火燒云。
車把式高連奎屬鼠,綽號“老耗子”,年近五十歲,天生笑臉卻愛罵人,嘴邊常掛著“狗娘養的王八蛋”。你指責他罵人,他就說:“我是趕大車的,不罵人。”言外之意,被罵的都是牲畜。
一件突發的事兒,讓老耗子愛罵人的習氣一扳閘,剎車了。
馬車滿載著幾百張綿羊皮駛入一路下坡的盤山道,坡路將盡的時候,馬車的剎車閘線崩斷,溜坡了。老耗子向前沖去,要拽住稍子馬圈停馬車,他一把沒抓住馬籠頭,自己卻摔倒在車道上,駕轅的火燒云掠過瞬間,叼住他的棉襖一甩頭,將他甩出車道外。
老耗子瘸著腿追過山彎時,馬車竟然奇跡般地停住。他撲通跪在地上,給火燒云連磕三個頭。
“你說出花來,這車我也不趕了!”老耗子硬是將馬鞭交給了生產隊長馬啟。
幾年后,火燒云老了,撤下來干輕活。老耗子告訴妻子,火燒云將來老死,就埋進咱家墳地。
沒想到老耗子又罵人了。
“狗娘養的王八蛋,把火燒云按驢肉價兒賣了,你還算人嗎?今天我不趕大車也罵牲畜。”
老耗子在隊長家門口跺著腳罵,隊長貓兒似的沒敢出屋。
暖 驢
大年初一,插隊知青安達懷揣一壺熱酒,去畜棚給大黑拜年,大黑是頭驢。
臘月,安達騎上大黑,冒嚴寒踏積雪,去平安堡郵局取父親匯來的五元錢,再給隊長捎買二斤白酒。
回程剛走幾里路,鋪天蓋地刮起白毛風。安達從大黑背上跳下地,放長韁繩讓大黑牽著走,此刻,他只能相信老驢識途。
驟降的氣溫,冷透了。安達扭開軍用背壺蓋,咕咚咕咚幾口酒,一股熱流躥上身。
大黑突然停住,轉身用頭拱蹭安達的懷。噢,忘記給它戴棉頭套了。
壩上的嚴寒天氣里,騎驢騎馬外出,都要用棉頭套護住它們的腦門兒,否則,它們會被凍傷顱腦而躺倒。
安達解開白茬皮襖,將大黑的頭摟進懷,暖著它。
大黑又牽著安達搏擊風雪繼續前行。焐暖了大黑卻消耗了安達的熱量,他咕咚咕咚又喝幾口酒。
天哪,大黑又停住了。
安達敞開皮襖摟進大黑的頭,大黑又像哺乳的孩子找到了娘。
飲酒——焐驢——前行,飲酒——焐驢——前行……不知循環了多少次,大黑牽著安達回到知青點兒。
畜棚里,安達從懷里掏出酒,咕咚咕咚飲下去,解開皮襖敞開懷,大黑扎進他懷里。
大黑鼻翼呼出的熱氣暖暖的。安達傾聽著大黑的喘息聲,還有其它牲畜吃食草料的咀嚼聲。
花 舌
花舌是東坡村的黑騾子,駒子時,飼養員老溫頭兒發現它舌頭青白斑駁,花舌。
老溫頭兒說,花舌牲畜愛記仇,招惹了這種牲畜,保不準哪天一頓蹶子,踢慘你。
騾子長到八個月就該調教,花舌兩歲多了,籠頭沒戴過。它無拘無束,搶馬的草,搶牛的料,掠食青青的莜麥苗。它像撒歡兒的風,在村中飄來蕩去,人們老遠就躲它。
隊長馬啟終于揚言要馴服花舌。他指揮幾個小伙子,拖起大繩纏住花舌的腿。馬啟悶足勁兒,咣的就是一膀子,將花舌撞倒在地。解開大繩,驅使花舌重新站起來,又用大繩纏繞它的腿……花舌在馬啟面前瑟瑟發抖。
馬啟給花舌備上鞍子,勒緊肚帶,調好雙蹬,騎上它穩穩地繞村子轉了三圈兒。
突然,花舌一蹶子將隊長尥下地,掙脫嚼子,一溜煙顛了。
花舌重獲自由,橫蹦豎躥,還時常立于村頭土丘昂首嘶鳴,它喚不出東方日出,卻也有幾分君臨天下的愜意。
那天早晨,花舌陷進了一處廢薯窖,脖子卡在窖檁上憋斷了氣兒,人們爭相圍觀。
花舌的舌頭從嘴角耷拉出老長,淡粉色的舌頭,根本沒有青白斑駁的花紋,馬啟瞪了老溫頭兒一眼。